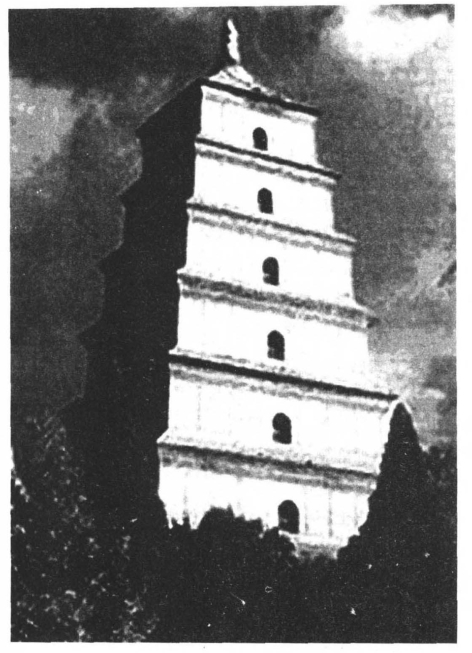-
1.1诗卷长留天地间——编辑手记
-
1.2引子
-
1.3目录
-
1.4第一章 浪迹丰草长林
-
1.4.11.“诗法乃家学所传”
-
1.4.22.盛唐艺术的熏陶
-
1.4.33.“开元全盛日”
-
1.4.44.漫游吴越
-
1.4.55.”一览众山小”
-
1.4.66.“放荡齐赵间”
-
1.4.77.陆浑庄:风林纤月,看剑引杯
-
1.4.88.“方期拾瑶草”
-
1.4.99.“亦有梁宋游”
-
1.4.1010.李、杜的知己之交
-
1.5第二章 旅食京华的悲辛
-
1.5.11.“旅食京华春”
-
1.5.22.献诗:“到处潜悲辛”
-
1.5.33.从军之念:“何由却出横门道?”
-
1.5.44.献赋:“词感帝王尊”
-
1.5.55.牢骚:“儒术于我何有哉?”
-
1.6第三章 游离盛唐诗坛之外
-
1.6.11.盛唐诗风
-
1.6.22.《饮中八仙歌》:浪漫群体中的清醒者
-
1.6.33.“仙侣同舟”的游兴
-
1.6.44.慈恩寺塔:览景与阅世的高度
-
1.6.55.《丽人行》:辛辣的嘲讽
-
1.6.66.《兵车行》:沉痛的哀叹
-
1.6.77.《咏怀五百字》:长安十年的总结
-
1.7第四章 赋到沧桑句便工
-
1.7.11.“渔阳鼙鼓动地来”
-
1.7.22.逃难:“北走经艰险”
-
1.7.33.被拘长安:“感时花溅泪”
-
1.7.44.“日夜更望官军至”
-
1.8第五章 乾坤含疮痍 忧虞何时毕
-
1.8.11.投奔凤翔:“辛苦贼中来”
-
1.8.22.羌村:“归客千里至”
-
1.8.33.《北征》:杜诗中的第一大篇
-
1.8.44.曲江水畔的酒徒
-
1.8.55.“三 吏”
-
1.8.66.“三别”
-
1.9第六章 关陇客泪 蜀道悲歌
-
1.9.11.秦州:“客泪堕清茄”
-
1.9.22.寂寞边城,故人入梦
-
1.9.33.往同谷:“我生苦飘荡”
-
1.9.44.艰难的蜀道
-
1.10第七章 成都草堂 暮年客愁
-
1.10.11.草堂:“野老墙低还是家”
-
1.10.22.“自笑狂夫老更狂”
-
1.10.33.“久客惜人情”
-
1.10.44.晚年心境:“不堪人事日萧条”
-
1.10.55.漂泊梓阆
-
1.10.66.重归草堂:“殊方又喜故人来”
-
1.10.77.去蜀:“残生随白鸥”
-
1.11第八章 夔府孤城:人生和历史的反省
-
1.11.11.沿江而下:“天地一沙鸥”
-
1.11.22.夔州:“且就土微平”
-
1.11.33,怀古:“怅望千秋一洒泪”
-
1.11.44.回忆:《壮游》与《八哀诗》
-
1.11.55.秋兴:“每依北斗望京华”
-
1.11.66.愁思:“泣血迸空回白头”
-
1.11.77.诗即生命
-
1.11.88.出 峡
-
1.12尾 声
-
1.13附录一
-
1.14附录二
-
1.15后 记
1
杜甫传: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