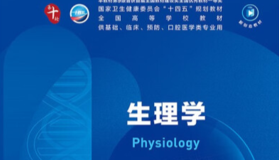禁不住的真理之光
——血液循环的发现及启示
1628年,在英国Frankfurst这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位不出名的印刷者印刷了伦敦内科科学院院士威廉·哈维(William Harvay)一本仅有72页的小册子:《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因而开始了医学史上崭新的一页。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哈维用无可辩驳的实验依据,严密的逻辑推理,一举推翻了统治医学界一千多年之久的盖仑的“血液潮水学说”。真理之光,射进了笼罩着宗教迷信阴影的死气沉沉的医学圣地。孕育了一千多年的血液循环理论和新的实验医学这对孪生子,从此获得了新生。
公元二世纪,盖仑(Gallen),这个欧洲古代医学家、实验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为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贡献。他扩展了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概念、认为研究和治疗疾病应当以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为基础;他在肌肉和脑神经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熟悉脑的大体结构,认出了七对脑神经;他做了多种重要的生理实验,纠正了动脉内含有空气的谬论;他弄清了结扎动脉和静脉对脉搏的影响,明确了脉搏频度和呼吸的关系。一句话,盖仑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正是这些杰出的医学成就,使他在古罗马名声显赫,不可一世。
然而,作为一个学者,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与否,常常决定着他的科学研究的生命。不幸的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盖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里渗进了目的论的污泥浊水。这种神秘的目的论,给他的学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认为身体的构造和一切生理过程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体内各种过程均为非物质力量的作用。他所创立的血液潮水学说的基础是心室中隔有小孔,这些小孔的存在是为了他所设想的目的的。他是这样理解血液运行的:消化产物经胃肠而注入门静脉,肝脏里的血经静脉运行全身,掌管营养等低级机能,而通过心室中隔小孔进入左心室的血与经过气管肺静脉而到左心室的精气结合,成为第二生命精气,由动脉运行全身为生命的根源,其中一部分到脑成为第三精气(灵气),掌管运动感觉等高级机能。血行的中心,静脉系在肝,动脉系在心。血流的现象为潮水般一涨一落。精气是生命的要素,身体只不过是灵魂的工具。可悲的是,盖仑忘却了他原来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当耶稣被其信徒奉为救世主,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时,盖仑学说中的神秘目的论及不可思议的非物质力量,却成了基督教的婢女与奴仆。盖仑被提到医圣的宝座上,成了不食烟火的先知先觉。他对自然科学和医学有用的贡献被中世纪的烦琐派和僧侣们置之高阁,而他的唯心主义的医学偏见却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与教条。正如巴浦洛夫指出的一样:关于动物和人类机体活动的概念,呈现出高度蒙昧无知和现在难以想象的混乱,可是这些概念却为科学经典遗著的不可侵犯的权威性所神圣化了。这就表明,科学一旦成为迷信,成为宗教的工具时,它就不再是人类思想解放的武器,而变成了桎梏人类思维的枷锁。盖仑以后的一千多年间,很多医学家屈服于迷信与宗教裁判所的高压,成了“医圣”的狂热信徒。他们引经据典,死背教条,宁愿相信上一世纪人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不敢逾越雷池半步,医学的发展停滞了。
但是,真理总归是真理。尽管教会的权力像炎阳一样酷热,可以令德意志皇帝蓬头跋足,苦求忏悔;尽管宗教裁判所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切敢于冒犯教义信条的人视为异教徒并处以死刑,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是无所畏惧的。人们在医疗实践中,逐渐地发现盖仑血液潮水学说与实际大有差异。终于,一个勇敢的叛逆者站出来说话了,他就是比利时的解剖学家维萨里(1614—1564)。维萨里仔细地解剖研究了人体的结构,他发现盖仑所剖验和论述的并不是人体而是动物的猴子和猪。只有纠正盖仑的错误,尊重客观事实,才能造福于人类。维萨里感到责任重大,他不能再沉默了。1643年,维萨里的《人体构造》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时问世了。声声惊雷,打破了科学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维萨里在这部巨著中详细正确地描述了人体的构造,纠正了盖仑的许多错误见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心室中隔不存在小孔,血液绝不可能由此而通过,从而动摇了盖仑“血液潮水学说”的根基。他指出人体左右肋骨都是十二根,无情地嘲笑了神学家们关于上帝抽出亚当的一根肋骨而创造了夏娃,因而男人左右肋并不相等的奇谈怪论。这样,维萨里亵渎了上帝,冒犯了教会,等待着他的是诽谤和迫害。他终于被迫停止了科学研究,在绝望中烧掉了自己的大部作品,最后流落异乡,因饥饿和疾病死于希腊南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维萨里的叛逆并不是孤掌独鸣的。与他同时代的西班牙学者“异教徒”塞尔维斯更加勇敢地站出来捍卫真理。他从实践中确定: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不是经过心脏中隔的小孔,而是经过肺脏作“漫长而奇妙的纤回”,他描述了血液如何在肺中沸腾起来并改变颜色。这就基本上提出了肺循环学说。然而,“在塞尔维斯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并且还活活地烤了他两个钟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塞尔维斯把生命连同他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一起献给了人类的医学事业,并在焚烧他的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对真理捍卫者的迫害,并不能停止人们对真理的继续探索。维萨里的许多继承者,一步步地找到了维萨里关于血液循环模糊推测的证实与依据。他的学生科洛姆波追踪了血液在肺中运行的整个途径,哈维的老师法希利齐乌斯记述了静脉瓣,以此证明血液是从静脉流向心脏而不是经静脉自心脏流出。可是,这些前驱者并没有对整个血液循环作出说明,更未曾给血液循环以科学的解释。
先驱者们未尽的事业落在了一个未来的巨人身上。1678年4月1日,这位巨人——威廉·哈维出生在英国福克斯东的一个小康家庭。他进过剑桥大学。1699年他又有幸地来到了意大利水上城市威尼斯,就学于为逃避天主教迫害而从教王领域西班牙逃出来的科学家们创办的巴丢阿大学——当时西欧先进的医学中心。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的医学训练,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和注重实验方法的思想熏陶。他的老师就是发现静脉瓣的法希利齐乌斯,他的密友之一是英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培根。而后者关于实验在研究自然科学上的作用的观点给哈维的工作带来很大的益处。哈维在老师的影响下,潜心研究起血管的构造及血液循环的问题了。他用严密而又巧妙的推理,首先发现盖仑的血液潮水学说最易被人忽视的弱点:假如心脏两心室容积为二英两,心脏每分钟跳72次,一小时为72×60 = 4320次,那么一小时左右心室排出量各达8640英两,约三倍于人体的平均重量。他大胆地设问:如果血液不是在体内作循环地运行,那么每小时三倍于人体重量的血液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显然,盖仑的血运学说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血液究竟是不是在体内作循环的运行呢?哈维懂得,唯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严格的科学实验。他深思熟虑地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方法,先后进行了包括爬行类、甲壳动物和昆虫等几十种动物的实验。哈维的假设,被雄辩的事实证明了。
1616年,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哈维抛出了第一颗炮弹,确认血液循行系继续不停地并永远向一个方向移动。他的学说是严谨的,他在已有的基础上又持续了十三年的研究。1628年,他出版了划时代的文献——《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哈维研究的结论可归结为:①血液是循行着的;②动脉与静脉相移行是在四肢及身体的远隔部位有着直接的吻合或经由肌肉的间隙,亦或是两路并进,③动脉是从心脏输出血液的血管,静脉是运回血液到心脏的血管,二者都是血液的导管;④心脏的运动和鼓动是血液循环的唯一原因。
当然,按照现代的观点,哈维的血循学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没有显微镜,哈维只能把动—静脉的沟通说成是多孔性的组织,他也未能发现血管的收缩性,而把血管看成是运输的导管。同样的,他也忽视了呼吸、肌肉、肠运动、血管的搏动及心内压变化对循环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无论我们怎样估价哈维对生理学和临床医学的贡献,都是不过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定为一门科学”。只有在生理学的基础上,十八世纪的病理解剖学才得以建立,以后才有近代实验临床医学的开始。
闪烁着人类智慧光芒的哈维血循学说的问世,并没有给这位巨人带来玫瑰花和桂冠。哈维所触犯的是宗教化了的科学,所面临的是炙手可热的中世纪最野蛮与残酷的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尽管哈维具有游说争取相识者的惊人本领,尽管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著作在一个不出名的地方出版,并把它奉献给查理国王,尽管哈维有着跻身于贵族之列的身份,他也免不了遭受辱骂和嘲笑。反动分子做出了大学决议:“禁止血液体内循环学说。”
哈维并不是无所顾忌的,他清楚地了解他的前辈和同辈们的悲惨命运。但是,由于出自对真理的热爱,他不畏艰险!他在他的名著的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论关于血液的分量和来源是很新奇而为一般世人所未听见的,因此我不但恐怕少数人的嫉妒而有伤于我,而且恐怕所有的世人和我作对,因为习惯思想差不多是人类的第二天性,任何理论一旦种下之后,便生着了很深的根蒂。对古人的尊敬,差不多人人都是为此。不过,现在我的主意是下定了,一切都付托于爱真理的热忱和思想开通者的同情。”他又说:“事实进入我们的感官并不问我们的意见如何,自然现象并不屈从于古人。”事实正是如此,血液就在体内不停地循环着,任何宗教的压力、迷信、偏见,任何大学决议都无法禁止得住!
哈维的血液循行学说终于被人们接受和发展了。当我们目睹今天日新月异的医学现状,再回头看看哈维的血液运行学说创立的坎坷历程,难道我们不会觉得,科学沦为迷信的可悲,盲目崇拜圣人的可笑,勇于献身真理的可敬。真理之光是任何力量也禁不住的。 (王庭槐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