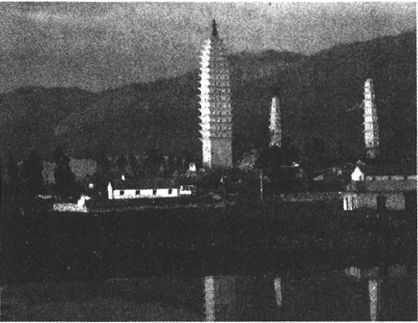-
1.1目录
-
1.2出版说明
-
1.3开头语
-
1.3.1——略说隋朝
-
1.4第一章 隋朝的政治和经济
-
1.4.1一、隋文帝励精图治(上)
-
1.4.1.1——隋初的政治
-
1.4.2二、隋文帝励精图治(下)
-
1.4.2.1——隋初的经济
-
1.4.3三、大运河与赵州桥
-
1.4.4四“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
1.4.4.1——暴君隋炀帝
-
1.4.5五、王薄和窦建德起义
-
1.4.6六、瓦岗军威震中原
-
1.4.7七、杜伏威、李子通扫荡江淮
-
1.5第二章 唐朝的盛世
-
1.5.1一、晋阳起兵和定鼎关中
-
1.5.1.1——唐朝的建立
-
1.5.2二、镇压义军统一天下
-
1.5.3三、玄武门之变
-
1.5.4四、纳谏与任贤
-
1.5.4.1——“贞观之治”第一
-
1.5.5五、“国家大事唯赏与罚”
-
1.5.5.1——“贞观之治”第二
-
1.5.6六、反击突厥和统一西域
-
1.5.6.1——“贞观之治”第三
-
1.5.7七、均田制度
-
1.5.8八、府兵制度
-
1.5.9九、“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
1.5.9.1——科举制度
-
1.5.10十、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
1.5.10.1——唐代汉藏友好关系
-
1.5.11十一、“西天取经”
-
1.5.11.1——卓越的翻译家和宗教家玄奘
-
1.5.12十二、武则天的统治(上)
-
1.5.13十三、武则天的统治(下)
-
1.5.14十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
1.5.14.1——“开元之治”(上)
-
1.5.15十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
1.5.15.1——“开元之治”(下)
-
1.5.16十六、繁荣富丽的长安城
-
1.5.17十七、曲辕犁和含嘉仓
-
1.5.17.1——农业的发展
-
1.5.18十八、“齐纨鲁缟车班班”
-
1.5.18.1——手工业的发展
-
1.5.19十九、商业和交通
-
1.5.20二十、渤海与黑水府
-
1.5.21二十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
1.5.21.1——唐朝中外文化的交流
-
1.5.22二十二、鉴真和阿倍仲麻吕
-
1.5.22.1——唐日友谊的使者
-
1.6第三章 唐朝的衰落
-
1.6.1一、安史之乱的原因
-
1.6.2二、安史之乱的经过
-
1.6.3三、安史之乱的影响
-
1.6.4四、袁晁、方清起义
-
1.6.5五、反击吐蕃、回纥战争的胜利
-
1.6.6六、藩镇割据局势的形成和“奉天之难”
-
1.6.7七、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两税法
-
1.6.8八、永贞革新
-
1.6.9九、国家专卖制度和社会矛盾
-
1.6.10十、“元和中兴”(上)
-
1.6.10.1——政治改革
-
1.6.11十一、“元和中兴”(下)
-
1.6.11.1——蔡州大捷和全国重新统一
-
1.6.12十二、牛李党争
-
1.6.13十三、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
-
1.6.14十四、李德裕和武宗朝局
-
1.6.15十五、“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
1.6.15.1——张议潮光复河西走廊
-
1.6.16十六、裘甫起义
-
1.6.17十七、庞勋起义
-
1.6.18十八、黄巢起义(上)
-
1.6.19十九、黄巢起义(下)
-
1.7第四章 隋唐的文化
-
1.7.1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
1.7.2二、火药的发明
-
1.7.3三、张遂和唐朝天文历算学的发展
-
1.7.4四、医学的发展和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
-
1.7.5五、史学的发展及其重大成就
-
1.7.6六、佛教道教的发展和西方宗教传入
-
1.7.7七、唐诗的发展
-
1.7.8八、杰出的诗人李白
-
1.7.9九、一代诗史
-
1.7.9.1——伟大的诗人杜甫
-
1.7.10十、人民的诗人白居易
-
1.7.11十一、韩愈、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运动
-
1.7.12十二、传奇小说
-
1.7.13十三、变文和词
-
1.7.14十四、艺术园地绚丽多彩
-
1.8附录一 隋朝帝系表
-
1.9附录二 唐朝帝系表
-
1.10附录三 隋唐大事年表
-
1.11中国历史大讲堂
1
中国历史大讲堂:隋唐史话
 、吉温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执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败政局的重要因素。
、吉温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执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败政局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