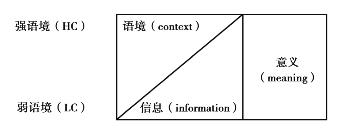-
1.1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
-
1.2《跨文化交际》编委会
-
1.3总 序
-
1.4前 言
-
1.5目录
-
1.6第一章 概 论
-
1.6.1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的界定
-
1.6.1.1一、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
-
1.6.1.2二、跨文化交际与人际关系
-
1.6.1.3三、跨文化交际的表现形态
-
1.6.2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学相关术语
-
1.6.2.1一、异质文化
-
1.6.2.2二、他者文化认同
-
1.6.2.3三、文化信息编码
-
1.6.2.4四、符号解码
-
1.6.3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及相关学科
-
1.6.3.1一、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
-
1.6.3.2二、跨文化交际与人类学
-
1.6.3.3三、跨文化交际与心理学
-
1.6.3.4四、跨文化交际与传播学
-
1.6.3.5五、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
1.6.4【原典阅读】
-
1.6.4.1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
-
1.7第二章 文化与交际
-
1.7.1第一节 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
1.7.1.1一、文化的概念
-
1.7.1.2二、文化的特征
-
1.7.1.3三、文化的层次
-
1.7.2第二节 交际的概念
-
1.7.2.1一、基本概念
-
1.7.2.2二、交际的特点
-
1.7.2.3三、交际的方式
-
1.7.2.4四、文化与交际
-
1.7.3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
-
1.7.3.1一、跨文化交际的表现形式
-
1.7.3.2二、跨文化交际的四个阶段
-
1.7.4【原典阅读】
-
1.7.4.1语境和意义
-
1.8第三章 语言与文化
-
1.8.1第一节 语言的功能和本体
-
1.8.1.1一、语言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
-
1.8.1.2二、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
1.8.1.3三、语言的表现形式:口语和书面语
-
1.8.2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1.8.2.1一、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
1.8.2.2二、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
-
1.8.3【原典阅读】
-
1.8.3.1文化与语言
-
1.9第四章 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交际
-
1.9.1第一节 语言要素与跨文化交际
-
1.9.1.1一、词汇与跨文化交际
-
1.9.1.2二、语法与跨文化交际
-
1.9.2第二节 语篇与跨文化交际
-
1.9.2.1一、语篇与思维模式
-
1.9.2.2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篇差异
-
1.9.3第三节 语用与跨文化交际
-
1.9.3.1一、跨文化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文化差异
-
1.9.3.2二、会话合作原则
-
1.9.3.3三、礼貌原则
-
1.9.3.4四、言语行为与跨文化交际
-
1.9.4【原典阅读】
-
1.9.4.11.The Matrix of Face: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
-
1.9.4.22.A Tentative Comparison of First Naming Between C...
-
1.10第五章 非语言交际
-
1.10.1第一节 非语言交际概述
-
1.10.1.1一、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
1.10.1.2二、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和发展
-
1.10.1.3三、非语言交际的特点
-
1.10.1.4四、非语言交际的功能
-
1.10.2第二节 非语言交际的分类
-
1.10.2.1一、体态语
-
1.10.2.2二、副语言
-
1.10.2.3三、客体语
-
1.10.2.4四、环境语
-
1.10.3第三节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
1.10.3.1一、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的特征
-
1.10.3.2二、如何避免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冲突
-
1.10.4【原典阅读】
-
1.10.4.1The Silent Language
-
1.11第六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
-
1.11.1第一节 地球村
-
1.11.1.1一、全球化概念的界定
-
1.11.1.2二、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
1.11.1.3三、全球化条件下不同组织层面的具体表现
-
1.11.2第二节 全球化进程与跨文化交际
-
1.11.2.1一、推动跨文化交际的全球化因素
-
1.11.2.2二、”地球村”区域意识的建立
-
1.11.2.3三、全球化媒介的作用与表现
-
1.11.3【原典阅读】
-
1.11.3.11.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Village
-
1.11.3.22.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
1.11.3.33.The Culture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
1.12第七章 跨文化交际的挑战
-
1.12.1第一节 文化认知与跨文化交际
-
1.12.1.1一、文化认知中的刻板印象
-
1.12.1.2二、偏见与歧视
-
1.12.2第二节 跨文化适应
-
1.12.2.1一、跨文化适应的内涵
-
1.12.2.2二、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式
-
1.12.2.3三、文化休克
-
1.12.3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中的认同
-
1.12.3.1一、文化认同
-
1.12.3.2二、社会认同
-
1.12.4【原典阅读】
-
1.12.4.11.Culture Shock: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
-
1.12.4.22.Immigration,Acculturation,and Adaptation
-
1.13第八章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
1.13.1第一节 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
1.13.1.1一、交际能力
-
1.13.1.2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
1.13.2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要素
-
1.13.2.1一、跨文化敏觉力
-
1.13.2.2二、跨文化认知能力
-
1.13.2.3三、跨文化行为能力
-
1.13.3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途径
-
1.13.3.1一、培养跨文化敏觉力
-
1.13.3.2二、培养跨文化认知能力
-
1.13.3.3三、培养跨文化行为能力
-
1.13.4第四节 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前景
-
1.13.4.1一、“跨文化”相关学科的增加推动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建设
-
1.13.4.2二、多国跨文化交际合作研究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发展
-
1.13.4.3三、全球新现象、新事物扩大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围
-
1.13.5【原典阅读】
-
1.13.5.11.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 Synthes...
-
1.13.5.22.Becoming More Intercultural
1
跨文化交际
1.7.4.1
语境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