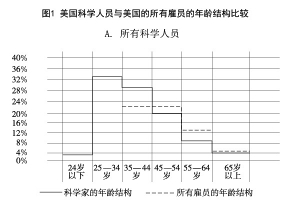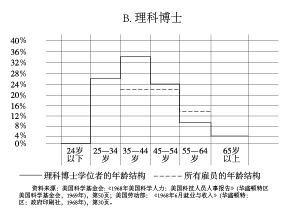-
1.1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中一个发展着的研究纲领的预示(代中译本前言)
-
1.1.1一、 简论观念的预示
-
1.1.2二、 科学的精神特质
-
1.1.3三、 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个自我例证的主题
-
1.1.4四、 优势积累与劣势积累
-
1.1.5五、 优先权冲突与正在浮现的关于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
-
1.1.6六、 科学中的多重发现:战略研究的一个基础
-
1.1.7七、 科学论文变化着的特性: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的差距
-
1.1.8八、 科学中的问题选择问题
-
1.1.9九、 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的恰当事例:“清教与科学”假说
-
1.1.10十、 附录:“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个三词组的产生和传播
-
1.2作者序
-
1.3编者导言
-
1.4第一部分 知识社会学
-
1.4.1编者导读
-
1.4.2第一章 知识社会学的范式
-
1.4.2.1一、 社会环境
-
1.4.2.2二、 知识社会学的范式
-
1.4.2.3三、 存在基础
-
1.4.2.4四、 知识的类型
-
1.4.2.5五、 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
-
1.4.2.6六、 受存在制约的知识的功能
-
1.4.2.7七、 进一步的问题和新近的研究
-
1.4.3第二章 兹纳尼茨基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
1.4.3.1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类型
-
1.4.4第三章 关于社会学研究方式的社会冲突
-
1.4.4.1一、 社会学发展的诸阶段
-
1.4.4.2二、 社会学研究方式冲突中的某些一致性
-
1.4.4.3三、 社会学论战的类型
-
1.4.4.4四、 结论
-
1.4.5第四章 政策研究的方法维度和道德维度
-
1.4.5.1一、 研究的基本原理
-
1.4.5.2二、 探索范围
-
1.4.5.3三、 探索取向
-
1.4.5.4四、 文化环境
-
1.4.5.5五、 组织环境
-
1.4.5.6六、 总体情况环境
-
1.4.5.7七、 界定实际问题和应用问题
-
1.4.5.8八、 界定问题时的价值框架
-
1.4.5.9九、 研究的经济体制
-
1.4.5.10十、 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类型
-
1.4.5.11十一、 研究与政策之间的科学差距
-
1.4.5.12十二、 研究与政策的个人间差距和组织差距
-
1.4.5.13十三、 理论与应用社会科学
-
1.4.5.14十四、 方法论与应用社会科学
-
1.4.6第五章 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
-
1.4.6.1一、 社会变迁与社会思想
-
1.4.6.2二、 局内人信条
-
1.4.6.3三、局内人信条的社会基础
-
1.4.6.4四、 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社会结构
-
1.4.6.5五、 作为“局外人”的局内人
-
1.4.6.6六、 局外人的信条和视角
-
1.4.6.7七、 交换、权衡与综合
-
1.5第二部分 科学知识社会学
-
1.5.1编者导读
-
1.5.2第六章 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观点
-
1.5.2.1一、 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中心主张
-
1.5.2.2二、 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的知识观
-
1.5.2.3三、 文化决定论与子系统的相对自主性
-
1.5.2.4四、 经验研究:科学社会学的定量指标
-
1.5.2.5五、 相对主义与科学真理的标准
-
1.5.2.6六、 科学知识的选择性积累
-
1.5.2.7七、 对话主题
-
1.5.3第七章 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
1.5.4第八章 科学与技术兴趣中心的转变
-
1.5.4.1一、 研究方法
-
1.5.4.2二、 科学产出率
-
1.5.4.3三、 科学兴趣指标
-
1.5.4.4四、 学科之间的兴趣转移
-
1.5.4.5五、 提出一个问题
-
1.5.5第九章 科学与军事的相互作用
-
1.5.6第十章 对科学社会学的忽视
-
1.6第三部分 科学的规范结构
-
1.6.1编者导读
-
1.6.2第十一章 清教对科学的激励
-
1.6.2.1一、 为了“赞颂自然界的伟大创造者”
-
1.6.2.2二、 “使人类过上舒适的生活”
-
1.6.2.3三、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
1.6.2.4四、 向科学转移
-
1.6.2.5五、 世俗化过程
-
1.6.2.6六、 宗教和科学的整合
-
1.6.2.7七、 科学和清教中隐含的假设的共同性
-
1.6.3第十二章 科学与社会秩序
-
1.6.3.1一、 对科学怀有敌意的根源
-
1.6.3.2二、 社会对科学自主性的压力
-
1.6.3.3三、 纯科学规范的功能
-
1.6.3.4四、 令公众感到神秘的高深莫测的科学
-
1.6.3.5五、 对有条理的怀疑态度的公开敌视
-
1.6.3.6六、 结论
-
1.6.4第十三章 科学的规范结构
-
1.6.4.1一、 科学与社会
-
1.6.4.2二、 科学的精神特质
-
1.6.4.3三、 普遍主义
-
1.6.4.4四、 “公有性”
-
1.6.4.5五、 无私利性
-
1.6.4.6六、 有组织的怀疑
-
1.7第四部分 科学的奖励系统
-
1.7.1编者导读
-
1.7.2第十四章 科学发现的优先权
-
1.7.2.1一、 作为社会冲突的优先权之争
-
1.7.2.2二、 科学的制度规范
-
1.7.2.3三、 科学的奖励系统
-
1.7.2.4四、 对优先权的矛盾心理
-
1.7.2.5五、 对文化上强调独创性的各类反应
-
1.7.2.6六、 强调优先权的功能和反功能
-
1.7.2.7七、 结论
-
1.7.3第十五章 科学家的行为模式
-
1.7.4第十六章 科学中的单一发现和多重发现
-
1.7.4.1一、 培根的科学发现的问题群
-
1.7.4.2二、 自我例证的多重发现假说
-
1.7.4.3三、 关于多重发现的假说
-
1.7.4.4四、 多重发现的模式
-
1.7.4.5五、 关于科学天才的社会学理论
-
1.7.5第十七章 作为战略研究基础的多重发现
-
1.7.5.1作为战略研究基础的多重发现
-
1.7.6第十八章 科学家的矛盾心理
-
1.7.6.1狂喜综合征
-
1.7.6.2潜隐记忆(“无意识的剽窃”)
-
1.8第五部分 科学中的评价过程
-
1.8.1编者导读
-
1.8.2第十九章 “承认”与“优异”富有启示性的双重含义
-
1.8.2.1一、 工具性承认的含义
-
1.8.2.2二、 荣誉性承认的含义
-
1.8.2.3三、 优异的品质含义
-
1.8.2.4四、 优异的成就含义
-
1.8.2.5五、 承认与优异之多重关联的结构和功能
-
1.8.2.6六、 奖励系统的功能和反功能
-
1.8.3第二十章 科学界的马太效应
-
1.8.3.1一、 奖励系统与“坐第41席位者”
-
1.8.3.2二、 奖励系统中的马太效应
-
1.8.3.3三、 交流系统中的马太效应
-
1.8.3.4四、 马太效应与重复功能
-
1.8.3.5五、 马太效应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
1.8.3.6六、 马太效应与科学资源的分配
-
1.8.3.7七、 小结
-
1.8.4第二十一章 科学界评价的制度化模式
-
1.8.4.1一、 评议人体制的制度化
-
1.8.4.2二、 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评价模式
-
1.8.4.3三、 编辑和评议人的评价行为
-
1.8.4.4四、 《物理学评论》的档案抽样分析
-
1.8.4.5五、 投稿者的地位差异
-
1.8.4.6六、 分派评议的模式
-
1.8.4.7七、 采用率的地位差异
-
1.8.4.8八、 相对地位与采用率的差异
-
1.8.4.9九、 评议人体制的功能
-
1.8.5第二十二章 科学人员的年龄、老龄化与年龄结构
-
1.8.5.1一、 科学增长与科学界的年龄结构
-
1.8.5.2二、 年龄分层与科学知识的体系化
-
1.8.5.3三、 科学角色
-
1.8.5.4四、 科学界的老人统治
-
1.8.5.5五、 科学人员的年龄、社会分层与合作
-
1.8.5.6六、 年龄分层和科学兴趣的中心
-
1.8.5.7七、 结束语
-
1.9参考文献
-
1.10译后记
1
科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