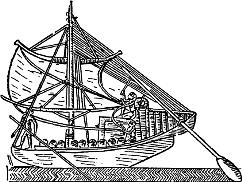第八章 古帝国时期的埃及王国与其邻人
现在,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最古老的国家于公元前3千纪在东地中海世界所处的人类环境来研究其发展。我们将简略概括埃及人与其他东方人之间发生的行动与反动。这些行动与反动最初只根据埃及人的文献确定,后来当其他文献被发现时,便根据迦勒底、赫梯、亚述、克里特-爱琴和巴勒斯坦的纪念物来揭示。我们将尽力描绘各种人类群体在形成自我进而形成国家中所进行的坚韧努力,以及那些得天独厚的民族创造帝国的野心,这种创造帝国的野心将把东方世界组织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这种努力和野心经常因无能为力或组织的弱势以及野蛮民族的入侵而遭受挫折,这些野蛮民族在当时仍未开化,他们在寻找更好的土地,渴望享受这种东方文明,而这种东方文明就像野蛮主义黑暗中的灯塔,把所有游牧民族都吸引过来了。事实上,古代东方每个伟大的民族——埃及人、迦勒底人、亚述人、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都曾致力于完成这种任务。所有这些建立帝国的企图都因连续不断的移民潮和定期攻击而不断起伏且都已失败,直到希腊和罗马时期,这种建立帝国的企图才得以实现,希腊和罗马文化支配整个地中海世界达几个世纪之久。
第一节 前人所传埃及的孤立
为了论述埃及与其临近民族的关系,我们最好先考察古代和近现代历史学家经常表述的一种观点。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埃及拥有独特的风俗、宗教、艺术和文字,原因是埃及在这个尼罗河河谷内发展起来,似乎处于孤舟之中,借助沙漠、海洋和瀑布与其他人类隔绝开来。我们完全可以承认这种藩篱通过保护埃及免于入侵而促进了埃及的发展。从各个方面进入埃及之路既有限又狭窄,不适于各民族和军队的迁入。如果入侵者被迫穿越广阔的沙漠进入埃及,那么他们将面对累日缺水或缺乏给养的危险;如果他们从地中海而来,那么一旦海战失败,他们将面对与其根据地失去联系的危险;这也是海上民族和亚述人多次遇到的命运,更不必说近现代入侵者了。不管怎样,埃及的孤立只是表面现象;当历史观察的范围扩大时,我们发现埃及的“奇特”实际上只是一种“古老”。我们将在下一卷叙述埃及人各种令人惊奇的风俗在其他原始社会中也能发现,只是一种很古老的社会状态的遗俗,只不过在所有古代有史民族当中,唯独埃及保存了这种遗俗而已。我们不能把埃及文明作为一种不正常而且例外的类型;普通人类发展的规则(laws)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埃及与其邻人之间有很古老而持久的联系。
我们首先考察地理条件。每一条可航行的河流都是“活动的道路”。当时,尼罗河处于两大台地中间,尼罗河的沙子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吮吸着水分,使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活变得不稳定,但尼罗河提供了一条有丰富粮食供给的水道。尼罗河的一端侵入了非洲内陆的中心地带,另一端则通往地中海,而地中海是通往各岛屿、小亚和广袤无垠的内陆的海路。而且,埃及几乎以另一个更适于航行的海——红海为界;后者比沙漠更适于把埃及与也门和阿比西尼亚联合起来,而非分裂开来,也门和阿比西尼亚的文明很早就发展了。最后,苏伊士地峡(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此地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形成了三角洲与叙利亚之间的一座桥梁。埃及的地理条件是这样的,以至于尽管埃及是一个四周环沙的绿洲,但她形成了从古代世界各个文明中心到黑非洲中心地区旅行的唯一一个便利走廊;同时,埃及还把北非沿海地区和阿拉伯以及小亚连接起来。
因此,埃及历史时期的种族是多种异质成分杂合而成的产物;这个国家的人口始终是混合种族,我们已经在前面辨别出了这些不同种的人们:苏丹人、利比亚人、闪族人和地中海人。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大自然强加于埃及人的经济条件,那么这些经济条件证明了埃及人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不得不从邻人借用生活必需品。尼罗河河谷向最初的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植物,但可食用之植物种类的贫乏令自然学家惊奇不已。借助农业获得更多的食物之前,这个植物界只提供了几种野生植物;至于蔬菜食物,最初的居民只有一些水果(主要是棕榈)、纸莎草和荷花(他们吃纸莎草和荷花的根茎)以及一些草本植物。坎德勒和施威恩福特告诉我们,三种谷物(大麦、粟和小麦)野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波斯西部和地中海盆地,而这三种植物最终使埃及成为世界的粮仓。[1]结论是原始埃及人可能在他们狭窄的花园里栽培和改良一些土生植物;但利用谷物的大规模农业则是从外国输入的。[2]
另一方面,埃及本土也富产动物,但这些动物对于人类来说要么危险,要么无用途;鳄鱼、河马、蛇、蝎子、豹子、狮子、狐狸、豺狼、大象、长颈鹿以及诸如隼鹰和兀鹰这样的猎鸟,既妨碍文明人类的劳作,也不适于家养。四足动物中只有两种适于饲养,一种是驴,是努比亚高原土产的驴,是埃及人最好的载重兽;另一种是长角牛,从很早时代就在努比亚存在了。[3]埃及人正在驯养羚羊,而且我们早就在埃及人的田园中发现了鸽、鸭、鹅。但是,根据大多数动物学家的观点,山羊与猪,甚至羚羊,都作为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进行贸易或物物交换的商品而来自亚洲,更不用说像鹿这样稀有的动物了。尼罗河提供了大量的鱼,虽种类繁多,但很少可食用,甚至后来经常成为禁忌对象;尼罗河盛产芦苇的两岸藏有鹌鹑、田凫、燕子和大量的鸟,尤其有大量蹼足动物;但与沙漠中的狩猎相比,狩猎和捕捉栖息于尼罗河丛林中的野兽更危险,这些精彩的狩猎活动后来被描绘在埃及坟墓的墙壁上。
埃及地下的矿产资源也很缺乏。埃及沿尼罗河河谷的确有丰富的沉泥、黏土、优质或粗糙的石灰石和密度大的砂石,其他地方也有各种岩石——玄武岩、花岗岩和蛇纹石等,但埃及既没有青铜、铁、金、银,也没有锡。埃及人从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河流与山脉中的沙子或金属矿中焠取金子,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盛产金子。[4]埃及人也在西奈半岛发现了金子,但产量不多,[5]且多数是碳酸化合物,不易熔化;他们不得不向塞浦路斯寻求青铜,向安纳托利亚寻求铁(埃及人在任何时代都很少使用铁),向其他不知名的中间地带寻求锡和银。
埃及也缺乏森林,甚至在努比亚,森林也很少。后来,乌木从尼罗河上游输入,但普通木材不得不从小亚(尤其黎巴嫩)输入[6],因为黎巴嫩盛产树木。“圣树”(Sacred Trees)、无花果树和鳄梨都是也门的土产树木,没药和香树也都是也门的土产树木。埃及土产木材或典型木材是柿树、怪柳和荆毬,都是坚硬而不易加工的木材,因此,房屋、器具和航海之舟都不能用这些木材制作。
现在我们也知道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埃及人已熟悉畜牧、农业、航海和金属的使用(如果不是金属的提取的话),到提斯王朝时期,埃及人已经提高了石头和青铜器的加工、农业和工业生产以及建筑的水平。就埃及缺乏植物、动物、矿物和森林等自然资源而言,埃及农业、畜牧业和工业的这种突出发展证明了埃及曾从小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和阿比西尼亚等生产国进口动植物和矿物。
著名的自然学家和人种学家乔治·施威恩福特的研究支持了这种假设。他已经就地研究阿拉伯和埃及的动植物以及民族达几十年了。施威恩福特在其所称的“古代文明三角洲”——巴比伦、也门和埃及——观察到了三种谷物(大麦、粟和小麦)的种植以及三种动物(牛、山羊和绵羊)的饲养。这些动植物都野生于西亚,而且自那以后,都逐渐移植到了东方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些动植物分布的年代顺序和接下来文明的年代顺序首先是巴比伦,然后是也门,最后是埃及。[7]我们不能讨论施威恩福特提出的观点的价值。就我们现有的知识状态而论,人类对动植物的饲养和栽培由首先发现于埃及的动植物和工具的遗物证明了,这完全是事实。在巴比伦之前1000年,在也门之前几千年,埃及已经有了农人、牧人和手工艺人从事工作。
埃及的邻人怎样从商业上渗入尼罗河河谷的?我们这里又一次遇到了亚洲人或阿拉伯人入侵埃及的理论和一个军事装备精良的民族军事征服埃及的理论,作为征服者的这些民族把自己较高级的文化赋予战败的埃及人。我们已在前面说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这种说法。公元前3500年之前,在埃及之外,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完全有效地组织起来追求征服政策的社会。相反的情况似乎更可能发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埃及人占据了巴勒斯坦,然后从那里带回了埃及缺乏的动植物。但证据缺乏或不充分。无论如何,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的征服观点呢?北非,尤其是埃及,依靠土壤和种族与接近的亚洲和南地中海地区有联系。从整体上来讲,埃及的动植物都属于西亚和非洲,[8]而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埃及的居民就依靠船只(图14)和商队与阿拉伯、巴勒斯坦以及地中海有了商业关系。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关系足以解释新石器时代和提斯王朝时期的埃及人怎么能从未开化且具有埃及所缺乏的某些自然财富的人们那里输入谷物和动物,而这些谷物和动物输入埃及之后便在尼罗河河谷繁荣起来。正如种族的杂交和语言的互借那样,当时也有经济因素的交换。这样,小麦、蔬菜、桑麻、小牛、大牛适应埃及水土的时期似乎证明了埃及、也门、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之间存在持续不断的交往。这或许是埃及最不孤立的时期,因为埃及还不能自给自足;当时埃及与其邻人的商业关系对于埃及人的繁荣发展是必要的,纵使其邻人的文化不如埃及发达。

图14 北方埃及人驱逐海上入侵者(前王朝时期)[9]
而且,不久之后,形势便反过来了。埃及土地上的杂草被铲除,农民居住在埃及,依靠驯养动物致富,在沙漠各处都占优势,沙漠借助灌溉渠道分布水流。这种土壤得到了很好的开发,所得收获无与伦比;外来产物在埃及土地上得到改良,并变成了当地物种,它们最终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了其故乡的同类产物,又或者依靠尼罗河环境的优势,这些产物发生了变化,并很快获得了一种物质,之后不再变化而为尼罗河所特有,即所谓“埃及物种的固有特性”。[10]借用希罗多德的话,整体上来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并获得了邻人的赠礼。埃及肥沃的土地或许不得不等待外来谷物。但由于政治组织的关系,埃及很快便被改造,从半附属国的地位变成了农业生产和艺术生产的一流中心和出口国。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埃及花纹燧石刀和燧石手镯以及硬石花瓶无可比拟的美丽中察觉到了埃及这种工业优势,而这种工业优势从公元前3千纪就在古代世界被再次肯定了,并保持了几乎4000年之久,直到大约公元前5世纪希腊工业的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埃及对外政策的这一切,都受到农业和工业创造中的优势以及这种经济优势的支配。埃及所有农民和工匠都很富有,并寻找把其产品输往国外的道路;反之,埃及也依赖于邻邦的几种主要产品。
埃及对其邻人的影响或许可以追溯到人类生活最早的时代。如果我们接受塞尔基(Sergi)似乎已被证实的理论,那么南欧和西欧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与最早的埃及人都属于地中海种族。非洲和欧洲借助直布罗陀海峡、西西里岛和多岛而架起的“桥梁”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仍可从河上通行。曾徘徊于第四纪欧洲大草原和森林里的非洲庞大哺乳动物一定从这些桥梁上走过。人类和他们的产品可能也走同样的道路。欧洲新石器时代制造的工具和武器在材料和技术上都与埃及人的工具和武器非常相似,这绝非偶然;瑞士和萨伏依栽种埃及人首先选种的大麦、粟和小麦这三种典型的植物,作为他们的食物,这也绝非偶然。[11]大约公元前4500年,埃及人开始制作青铜和时尚全铜工具,而其他人类仍使用石器;然后,尼罗河技术上的优势必然为他们创造一种不可抵抗的优势。正是在这时,埃及的“邻人”出现在埃及的第一批纪念物上;而且也正是在这时,我们才能够开始研究古代人们的相互关系。
我们这里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此时,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图画纪念物上他们对自己的描绘来描述埃及人和他们的邻人了,而不仅仅在头盖骨的测量和语言学的帮助下确定人类种族。
第二节 埃及人和他们的邻人:人种和种型
历史时期埃及的纪念物所描绘的民族可概括为四类——埃及人、利比亚人、闪族人和尼格罗人。前两个民族属于哈姆种族;他们被认为与闪族非常相似,但又与非洲尼格罗人十分不同。
尼罗河流域中的“黑土地”(Black-earth)深处有人居住,他们就是埃及人。雕像和木乃伊表明埃及人面部为卵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鼻短直而微削,唇厚而多肉。他们通常身材高大,肩部宽阔,颈直而结实,腹或臀部皆不萎垂。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臂与腿的肌肉都不很发达。他们的皮肤本来是白色的,但由于阳光的照射而变成了红褐色。他们的头发黑而不卷曲,通常很短,用帽子或假发保护之。他们的胡子通常很稀少,更通常的情况下是被剃光。通常,他们的服装是男人围一条腰布,女人穿一件挂肩紧身长袍。
从地中海到阿斯旺的尼罗河左岸,在苏丹一段的尼罗河两岸以及西部绿洲居住着利比亚人。[12]在沙漠台地上,他们是游牧民族,而在绿洲和努比亚,他们又是定居民族。利比亚人大多皮肤呈白色,眼睛为蓝色,头发秀美,这些特点表明他们是哈姆种族与来自地中海的民族混合而成。利比亚人高而强壮,比埃及人的肌肉更发达;头发编成辫子,垂于肩际。有时,他们的前额有一小发髻。他们的嘴唇之上有微微上翘的胡须,胡须上端略尖。他们的衣服是一种腰布,有时是羊皮袍,颜色鲜艳而有花纹。男女都文身,戴着镯子和项圈;有一个皮囊保护着男子的生殖器。[13]除了利比亚人,我们在马麻利卡发现了特黑努人,而在塞尔提斯境内生活着马舒沙人(即希腊人中的马克星人)。

图15 埃及的种型(古王国时期)
在尼罗河南部,从第一瀑布到第二瀑布是努比亚;努比亚的名称在埃及人那里是库什。努比亚人身材雄伟,头发或曲或直,包含几个部落,例如华华特人、伊尔特人和伊曼人,[14]似乎与利比亚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努比亚人与尼格罗人明显不同,因为尼格罗人的鼻子扁平,唇厚、发卷曲,而且努比亚人与所有黑皮肤民族都明显不同;而黑皮肤民族后来才出现在埃及人殖民的尼罗河流域的部分地区。[15]
在南部的尼罗河右岸,埃及人遇到了马梭义人,马梭义人似乎是近现代的比沙里斯人。直到索马里海岸的红海海滨居住着蓬特地方的居民。他们的容貌和体型都与埃及人相同,只是须短而且须尖向上扭曲。艺术家凭借自己的想象以同样的胡须装饰埃及神的胡须。
尼罗河中游东岸阿拉伯沙漠的山脉和大草原是因条人(他们的名字曾被读作阿努)的领土。他们对应于特罗哥罗迪特人,斯特拉波[16]认为这些人居住在这些地区。他们是闪族贝都因人,靠掠夺和经商为生。苏伊士地峡沿路和西奈半岛上居住着赫琉沙人——“沙上居民”——阿努人、曼条人和森条人,他们都是真正的亚洲人,既是游牧民族,也是定居民族。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论述这些民族的特征。
提斯王朝和孟菲斯王朝的埃及与其非洲邻人不同,处于多数游牧而不开化的民族中间,是一个掌握着政治、军事、工业和农业组织的国家。因此,两者相比,埃及自然会在整个历史上保持优越地位。
努比亚人很不容易地生活于瀑布地区,因为这里地势狭小而荒芜,只是肥沃的埃及与尼罗河上游丰美地区之间的一个水道,所有野生动物皮、象牙、珍贵香料和鸵鸟毛都来自尼罗河上游这一丰美地区。努比亚人是这种小规模商业的中间人,而且在尼罗河上给商船导航或在沙漠中给商队做向导。他们经常来到下游的埃及和三角洲,他们在这里受雇为农业劳动力,但他们主要被雇用为雇佣兵、卫兵和警察;这些重要职位之所以适合他们担任,是因为他们的性情勇武顽横。埃及人很快便不得不防卫自己,以防止较为富有的尼罗河下游过分引诱尼罗河上游不幸的人们。后来,埃及的危险来自苏丹的尼格罗人:这些尼格罗人富有动物和矿物,并掌握冶金术的秘密,随时由努比亚进入艾利藩厅,渐行渐远,最终引导尚武好战的游牧民族掠夺埃及人的城镇。
尼罗河两岸的利比亚人和东岸的特罗哥罗迪特人护送商队,把蓬特和也门的金、银、兽皮以及香料或利比亚绿洲的产品以及昔兰尼加的牛羊运往埃及。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畜牧者和猎人(他们饥饿的牛以绿洲和沙漠边缘的草为食)来说,埃及是一个可以祈求援助的地方,换言之,埃及是一个他们可以采购粮食的市场。他们用自己凝结的牛乳、乳酪和肉换取小麦,并搜寻人工制品,以确保来自阿拉伯或苏丹和利比亚的商队运回商品。
对于尼罗河肥沃的土壤背景而言,这些利比亚人和特罗哥罗迪特人都呈饥饿的掠夺者的容貌,总是寻找机会掠夺爱好和平而又勤劳耕种的埃及农夫。他们从来就不是埃及人真正危险的来源,因为他们还没有迅捷的马匹以供运输货物之用;驴是他们唯一的驮兽,但速度很慢且不能负重远行;虽然有骆驼,[17]但很少使用,[18]骆驼在伊斯兰时代是沙漠部落稳定而强有力的工具。面对这些游牧民族时,埃及曾时刻提防、雇用警卫,实行巡查,而巡查的责任则交给了埃及雇用的利比亚人。几个部落例如马舒沙人的部落曾作为雇佣兵为埃及服务。埃及也以同样的方式雇用马梭义人为雇佣兵。法老发现以工资的方式报酬这些野性难驯的流寇,使埃及免受侵略,是一种很好的计策。只是到了底比斯帝国的末期,利比亚人才结成了一种联盟,并在移民潮的促动下,开始严重地威胁埃及,这时临时性的计策很难把利比亚人驱逐出去了。[19]除了这些例外时期,游牧民族只是结成小队来攻击埃及。为了防止这种攻击,埃及不得不始终保持一种戒备森严的防卫,但野蛮人也可以被雇用为雇佣兵或商人,从而使之接受一种调停,因为只有这些职务才可以充分展示其天才。
就亚洲人而言,埃及的地势又大不相同。在苏伊士地峡和沙漠地区——在埃及边境上建立起了一个长达75英里的沙漠障碍——之外,亚洲在地中海沿岸开放其农业台地、森林及港口,以促进海上贸易。内陆产品都运到这里,这是埃及所知可以出口的一个大世界。到公元前4千纪,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兰国家都在这里发展起来。法老埃及已不必再向此类文明程度各异的民族借植物以栽培,借动物以饲养(不管怎样,马匹直到公元前16世纪才从亚洲来到埃及),但埃及仍输入主要产品——青铜、金、铁、珍稀石头、建筑木材和羊毛物品等等。埃及方面也向亚洲输出制造品,如器具、武器和珠宝,因为三角洲工厂具有艺术上和技术上的优势,所以亚洲人殷切需要这些制造品。商队乘驴穿过叙利亚和沙漠进行这种贸易,也有些商队走海路进行这种贸易。有人认为船只主要是亚洲的,或者如果船只是埃及的,那么水手也是外国人,这种观点或许是错误的。我们虽然不敢断言埃及的海运在地中海上扩展了多远,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埃及与爱琴海和巴勒斯坦沿海的商业交往已经建立起来;在阿拜多斯新石器时代的坟墓中,褐色或红色泥制花瓶以雕刻线构成的几何图形装饰,以白色泥浆为壳,或覆盖以刺孔的装饰品,这些花瓶是爱琴海的土产品。[20]因此,在历史时代伊始,三角洲与塞浦路斯(青铜产地)和北部叙利亚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就已存在了。所有这些小岛和海上民族都被埃及人称为豪涅布人,即埃及背后的民族。[21]
小亚不仅与埃及进行长期不间断的商业交往;而且小亚注定要在与埃及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在东方的整个历史上,亚洲对于埃及所占的地位与日耳曼人对于罗马帝国所占的地位相像,是起源不同的各民族的大熔炉,反映了从目前的俄罗斯到中国西藏的大草原更北方地区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移民的震动与冲击。自此以后,定期的侵略潮流源源不断地出现,而这些潮流的最后巨浪达到了巴勒斯坦,有时甚至到达了埃及边境。法老帝国在亚洲方面频繁受到威胁,并易于受到亚洲各民族所有迁移和冲突的震动。
读者从我们上面的全面考察中可以得知,埃及不仅不孤立,不仅不与周围世界断绝往来,还时刻受到嫉妒之目光的注视。一方面,埃及具有一种吸引力,作为一个富有的国家,埃及可以为游牧民族和饥饿的民族的服务与体力劳动提供和平、安全以及食物保障;另一方面,埃及的沙漠边境只能暂时阻止迁徙中的民族。毫无疑问,埃及早就有能够使其零落散乱的邻人尊敬一个集权、法治而又能继续从事内部发展及繁荣工作的国家的威严与实力。埃及能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利用其邻人提供的人力和原材料资源。但针对游牧民族的掠夺和移民的迁移,埃及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准备一种计划,首先为了防御,然后是为了征服。一世纪一世纪过去之后,我们发现埃及逐渐采取防守边疆的计划,例如在艾利藩厅屯驻少量警备兵以防止努比亚人和尼格罗人进入埃及。不久,埃及人扩大其防守范围,设置边防区,并在蛇形碉堡后面驻兵防守。最后,埃及采取攻势;在亚洲方面,埃及所受的威胁最严重,埃及组织经济保护国,当这些经济保护国不足以保护埃及以使之免受攻击和延期入侵之时,埃及便决定从军事上占据动乱的地方。这包含一种外交政策,实验一种集权国家之后,再实验一种世界帝国,这种实验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有时引人嫉妒,有时引人反抗。我们现在必须逐一描述这种军事扩张的历史,这种道德萌芽的历史和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埃及、迦勒底和其他民族也都在这种历史中起重要作用。
第三节 提斯埃及的对外关系
根据文献判断,从提斯王朝开始直到第三王朝结束(大约公元前3315年至公元前2850年),埃及与其邻人的关系有时和平,有时战争,完全依赖于尼罗河边境的部落对埃及边境尊重还是设法侵略埃及的耕地而定。这些冲突的责任似乎不应该由埃及负责。埃及国王既需要聚精会神地谋求“南北两地的统一”,又要设法耕种整个尼罗河河谷,从而他们只能以严厉的讨伐和方法适当的攻击来应对外来侵略和惩罚游牧民族的入侵,但不占领邻邦,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在那尔迈统治时期,马麻利卡海岸的利比亚人(即特黑努人)曾与三角洲的埃及人联盟,对抗南方的埃及人,与三角洲的埃及人一样,被希拉康坡里斯的国王打败。他们不得不缴纳贡赋,我们在美尼斯的象牙舟上发现他们在国王面前列队;从他们下垂的发辫、头上的顶结和尖须,我们可以辨认出他们。[22]
我们发现,在很早时利比亚部落一方面与绿洲居民通商,一方面也与尼罗河河谷的居民进行通商。除了牛羊和各种牛奶及乳酪食品之外,埃及人还常常向利比亚人购买一种价值昂贵的“利比亚香料”,[23]因为我们发现国王、神和死后成神者的祭品单上列有这些香料。
努比亚人也出现在美尼斯调色板上的战败者中间。[24]第二王朝的卡塞克亨姆曾提到他带回埃及的俘虏中有努比亚人,[25]但没有任何纪念物向我们证实前三个王朝的国王们在努比亚执行了有效的征服。
相反,在东部边境,最初的提斯国王们确实渡越边界,不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是受到一种确定的征服计划的启发,为了占领西奈半岛的铜矿。我们很容易理解,当埃及的所有邻人(苏美尔人除外)仍使用石器和石制武器之时,一种矿物能使拥有此种矿物之人制造铜工具和铜武器,那么这种矿物对于一个初生的文明是多么重要啊。马哥哈拉干谷的岩石墙中藏有丰富的矿物,而这种矿物或多或少具有生产力——绿松石含有3%至4%的氧化铜,后者是铜中的一种含水矽酸盐,含金属非常多,而花岗岩则含有铜元素的碳酸盐和含水矽酸盐。其实,这些矿物的重要性或许被夸大了;反之,今天我们说这些矿物一点都不重要,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26]柏德罗承认矿物在人类演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7]游牧民族曾在这些山中散有零碎矿物的土地上点火,人类才第一次在地中海地方见到铜受热之后与其他物质分离开来并掺杂于死灰之中。西奈半岛是世界上首先发明冶金术的地方。
在萨拉比特-埃尔-凯德姆的马哥哈拉干谷,我们仍能看见岩石中开凿的坑道,并能随时拾起矿工所使用的石镐和木槌,砍砸墙体的铜凿子,以及就地熔化金属的坩埚,而金属渣滓仍堆积成山。[28]这些遗物的历史价值因如下事实而大为增加,即它们依靠雕刻在岩石上的浅浮雕来确定时间。第一个众所周知的遗迹是美尼斯继承人之一的隼鹰王斯麦克赫特的美术品;他被描绘在国王外衣上,头戴白冠或红冠,一只手握着贝都因人的头发,另一只手举起权标头锤杀之。[29]斯麦克赫特之后,直到第十八王朝矿山开尽之时,大多数法老仍派遣远征军出征西奈半岛,在珍贵的金属墙上铭刻铭文。
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西奈矿石的开采已是埃及国家的一种正式事业,埃及始终垄断这种事业。铭文列举了管理产业的官员、技工、保卫工事安全或运输安全的战士或水手。只有国家才能从事这种性质的大事业,私人不可能成功地从事这样的工业。提斯君主国通过组织矿物的开采证明了自身的能力,矿物的开采是为了转变其臣民的物质生活和工业以及政治关系。因此,埃及国家为了自身和社会而保护这些金属矿山,而这些金属矿山使埃及极大地扩张军事力量和工业活动成为可能。
这样,自世界历史伊始,法老便追求侵略权力,而这种权力以暴力为基础。西奈最初的居民赫琉沙人及其邻人阿穆人在得知埃及人从西奈开采红色金属,用以制作武器、工具、花瓶和装饰品之时,他们的贪婪之心便油然而生。斯麦克赫特的一个继承者隼鹰登(乌塞菲斯)把自己描绘为“东方民族的破灭者”。[30]此后,法老的记录和浅浮雕经常叙述法老的军队战胜悲惨的游牧部落的功绩,而这些游牧部落喜欢控制矿工以勒索赎金或者获取一部分金属。后来,埃及人不得不防卫亚洲人掠夺矿工,并扩展其军事范围。因此,军事征服是由经济上的贪婪导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独裁政治掌握了它需要的西奈矿山区,并于5300年前便开始了长期的侵略和所谓的经济战争,而侵略和经济战争是文明的伴随者。

图16 西奈的斯麦克赫特
法老们又在西奈北部控制了由苏伊士地峡和西奈进入亚洲的通道。在这一地区,埃及人遇到了定居的阿穆人、赫琉沙游牧人(他们居住在沙地里)和特罗哥罗迪特人(因条人)以及其他闪族部落,如曼条人和森条人。
这些贫苦民族埋伏在道路两旁,劫掠往来于亚洲与埃及之间的商队,而这些商队从亚洲运来用于建筑阿拜多斯国王坟墓的地面和屋顶的巨大松柏、埃及缺乏的矿物和某些农产品,并从埃及把木材、石头、骨头和象牙制作成的手工制品运往亚洲,这些手工制品体现了埃及人无与伦比的技艺。为了确保这些商路的安全,提斯王朝的法老不止一次派遣临时远征军,暂时降服部落。
埃及人横越“环豪涅布的大水域”而与爱琴海岛屿通商,埃及人称这个大水域为地中海。埃及人从克里特带回铭刻着几何装饰图案的克里特—爱琴花瓶,这些花瓶的装饰图案或黑地白雕,或于红地上刻有白色螺旋形图样及花草图样,或为褐色地上刻有刺孔的三角形。[31]仍有疑问,这些商品或诸如玛瑙之类的其他商品是否直接来自欧洲;这些商品或许是由利凡特港口转运而来的,而这些港口早在腓尼基人之前就积极地参与贸易活动。尤其拜布罗斯(凯奔)一定早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了,因为埃及语中的航海工具的古老名字是凯奔,即“拜布罗斯之舟”。[32]
第四节 孟菲斯埃及的防卫计划
第四王朝伊始(大约公元前2850年),法老君主国便成功地将其人民组成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当时埃及人民能够进行农业轮作、驯化和豢养动物并知道金属提取和冶炼的秘密。因此,在国内产生如此有效的效果和深思熟虑的政策,被尽可能深入地应用于埃及与其邻人的关系。第三、四、五、六王朝或孟菲斯王朝[33]的国王们确定并追求一种非常远大的政策。他们不再满足于应对游牧民族的侵略;他们详细拟订了一套防卫计划,而这套防卫计划很快便转变成一套侵略计划,鉴于历史规律,这种计划对付游牧民族时并不能十分有效地驱逐其攻击,而且战争必将引入敌人兴起之地区的心脏地带。
法老们在利比亚方面组织了一个“边防区”,称为“西方的大门”(aimenti)。在斯尼弗鲁统治时期(大约公元前2840年),这一地区的管理事务交给了高级官吏梅腾。[34]当第四王朝的国王们[35]仍以铁腕统治其王国时,这一方面的边疆防务十分牢固。在第五王朝时代(公元前2680—前2540年),利比亚人利用王权旁落的机会侵略埃及国境,这次侵略的重要性由驱逐这次侵略所需的各种努力所证明。在萨胡拉的葬祭庙中,一个浅浮雕庆祝埃及人的胜利(大约公元前2670年),描绘了大批俘虏——123400头牛、223400头驴和山羊,绵羊之数与此相当(当然,这些数字不能完全确信)。利比亚首领的头上有一发髻垂于前额,全身纹刻,腰间系着五颜六色的羊毛布,颈部围着多彩项圈,他们都被作为俘虏而带来,伸手祈求法老的宽恕。[36]这次入侵的荡平非常彻底,效果历时持久,因为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利比亚人都很安静,而且从第六王朝直到中王国(第十三王朝)结束,利比亚人一直向法老提供雇佣兵。因此,一种军事协定结束了埃及西部边境的战争,并使“西方的大门”受到尊敬。
同样谨慎的政策也实施于南部边境。在尼格罗人的压力下,努比亚人侵入埃及,第三王朝末期(约公元前2890年)左塞王(Zoser)决定在第一瀑布上游设立一个边防区,后来被称为“十二里格之地”(Twelve League Land),从艾利藩厅到希拉西卡米诺斯。[37]不久之后,斯尼弗鲁[38]便从这里出发侵略努比亚,然后他带回来7000个俘虏和20000头牛。在第四王朝统治时期的一段和平期之后,第五王朝的末代王乌那斯不得不再次进行军事远征,他建立了“南方的大门”(a-shema),即南方的边防区。[39]它的卫城是艾利藩厅,那里有一道7.5英里长的砖墙(第十二王朝建立)(今日仍存在),横跨尼罗河河谷和从沙漠进入埃及的道路。
不管怎样,这些措施并没有成功地阻止努比亚人从苏丹源源不断地涌入埃及,与埃及人杂居并融合在一起,进而分布到尼罗河河谷。这些黑人和尼格罗人四处游荡,或者劫掠,或者作为农业劳动者、警察或战士而进行工作。第六王朝的国王们试图限制这些游牧民族的兴起,并把这种丰富的而又危险的人力转移到正常的用途:他们承认尼格罗人和努比亚人为“被镇抚者”[40],并从这些人当中雇用士兵以填充军队,雇用工人为王田耕作。埃及国王不仅从华华特人、伊尔特人和马梭义人当中招募士兵,而且这些部落的首领或许以纳贡的形式向埃及国王供给淘金匠、木材、花岗岩、树胶、树脂和其他货物。为了使这些部落处于服从状态,占领他们的土地最终成为必要之事。珀辟一世远征至尼罗河上游。努比亚的美国大学最近的考古挖掘证明尼罗河上游曾被殖民,直到凯尔马(第三瀑布)、纳帕塔和麦罗埃地区。
法老在这个上埃及上游安置的最有用的代理人是艾利藩厅的王子。[41]这些法老在阿斯旺山中开凿的坟墓为我们保留了他们曾征伐努比亚国土的记事文。麦然拉和珀辟二世(大约公元前2490年)曾先后几次派荷尔胡弗前往第二瀑布附近的伊曼地方。荷尔胡弗第二次出发时率领着一支驴商队,驴身上驮着埃及小工业生产的廉价货物——项圈、手镯、香料和武器。他受到了游牧民族的热情欢迎,他向游牧民族宣传国王的权力,用礼物获取他们的爱戴,调和互相残杀或与利比亚人战争的各部落。规劝他们崇拜“所有君主之神,”[42]这相当于归顺条约。7个月之后,他带领着300头驴回到埃及,驴身上驮着乌木、香根、树胶、象牙、鸵鸟毛、兽皮和金子。[43]有一次,荷尔胡弗带回来当加部落的一个侏儒。这些侏儒在宫廷里非常受宠爱;他们被雇佣来在神祇崇拜或丧葬崇拜中执行某些仪式——跳舞,舞蹈是这些侏儒的部落特有的,并且有一种宗教意义和魔法效果。因此,当珀辟二世听说荷尔胡弗带着侏儒返回时,便给荷尔胡弗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透露出珀辟二世急切地想见到这个侏儒。“当加人与你在舟中之时,你须小心,应派有经验之人照顾,以防其坠入水中;当他在夜间休息之时,你须派有经验之人与其同卧,这些有经验之人应加倍关注他。因为陛下更愿意见到这个侏儒,而非你从蓬特之地运回的所有珠宝。”
尽管法老进行了这些征伐,但法老的支配之地仍未巩固下来。艾利藩厅的另一个贵族珀辟尼赫特,曾先后两次奉珀辟二世之命,“率领精选的最勇敢士兵”讨伐伊尔特人和华华特人。他带回了大批人畜。为了报复麦克胡,他率军对华华特人进行了一次讨伐,但他被杀死,尸体留在了敌人手中,直到他儿子塞布尼再次率军征讨华华特人,寻得其尸体,带回埃及焚化。[44]在那之后,很少有文献提及孟菲斯法老干涉努比亚的举动。但我们了解麦奈恩拉和珀辟斯的事迹,这允许我们相信孟菲斯法老的继承者们继承了他们这些中非殖民者一贯的策略——防卫和侵略政策,旨在对付强悍好战的部落,这些游牧部落总是休息几年之后便再次卷土重来,并且在穿越了广阔的苏丹之后,便无法控制了。
在亚洲方面,最初的那些法老也采取同样的监视政策。正如他们在第四王朝伊始便在西边和南边创建边防区,他们也在东边挖壕宿营以保护下埃及的第十四诺姆或“东方之点”。通过扎鲁到达巴勒斯坦海岸的北路由荷鲁斯之路的要塞控制。穿过图米拉特干谷的南线由设防的要塞控制;伊姆霍特普之门和荷鲁斯涅布玛阿特之地[45]这样的名称,允许我们认为这个基础营帐或这个东方边防区是由左塞王(伊姆霍特普是左塞王于大约公元前2895年雇佣的建筑师)和斯尼弗鲁王(涅布马阿特是斯尼弗鲁王于大约公元前2840年雇佣的建筑师)组织的。他们的监视远及西奈,西奈就在这个吸引人的区域之内。埃及人在这里为东方之神塞甫图和哈托尔建筑了神庙,我们在这里看到国王斯尼弗鲁参加崇拜,处于“众神”中间。[46]这证明西奈曾是埃及人占领的领地。在这里和努比亚(荷尔胡弗把埃及神祇引入到这里),埃及神祇与当地神祇并列,法老本人也在西奈被崇拜为神。在异地创立这种政治崇拜就等于创建一种保护国。
但是,如此巩固的边境仍不能阻止亚洲或闪族游牧部落的攻击。这样的证据可以在左塞王以及其继承者塞奈克特和斯尼弗鲁留在西奈的胜利画面中发现。在斯尼弗鲁统治时期,巴勒摩石碑曾简单地提到“满载着香柏的四十艘船到达了(埃及)”。[47]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香柏只能来自黎巴嫩周围地区;这些香柏是在拜布罗斯装上船的。这个事件说明埃及与西奈之外的地区之间有正规的商业关系,这种商业由国家控制。这些货船上的货物代表了埃及人索取的一种贡赋吗?这种学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尚待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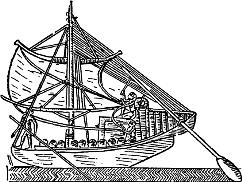
图17 埃及的船只(古王国时期)
在第四王朝权力鼎盛、国家繁荣之时,东部边境处于太平状态,但在第五王朝,东部边境的战事又起,而第五王朝时期,埃及人与闪族人之间更亲密的关系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第五王朝伊始,法老们便为太阳建筑神庙以使他们的名字永恒;这些是很新型的圣所,中间有一个方尖碑,[48]而太阳神拉以前在埃及万神殿中本来地位不高而且其教义也来自亚洲,现在则升为主神了。赫利奥坡里斯祭司集团成功地将这种崇拜强加给王室家族。之前,法老被认为是古老的国家隼鹰神荷鲁斯在地球上的化身,这之后,法老宣传自己为“拉之子”[49],在加冕时,除了荷鲁斯之外,他还采用一个由拉神的赞美称号构成的“太阳”名。奉献给太阳的神庙证实了国王对这个新保护神的忠诚,这个保护神自此以后便控制了埃及宗教。这种演进的重要性和意义不容易把握,但这种演进标志着闪族影响的回归吗?拉的优势是沙马什的胜利吗?方尖碑是一种宇宙吗?太阳神崇拜的教义应归于一个闪族神学家学派吗?[50]我们仍缺乏充分的文献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无法阐释这些问题便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无论这些教义是否直接从亚洲借用而来,无论一种哲学是否已经在赫利奥坡里斯萌芽(这种哲学的萌芽是因埃及与亚洲的联系激发的),但第五王朝时期闪族人影响埃及的学说因如下事实加强了而非削弱了,即第五王朝时期埃及人与亚洲人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
埃及战士的坟墓为我们保留了埃及征伐尼底亚城的历史情景。尼底亚城似乎位于叙利亚,因为其居民体现出的所有特征——身体魁梧、辫发细长、长袍恰恰结束于小腿部位——在日后仍是闪族的特征。这座城市是一座卵形堡垒,侧面有塔,而这种布局是如此像亚洲城镇的类型,以至于埃及人用这种符合作为表示亚洲被征服之国家的城市的限定符。城内居民恐慌而自怜,而埃及战士则把梯子搭在墙上,并用破城锤攻击城墙。然后,幸免于难的妇女儿童都沦为俘虏。[51]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指明这个模糊的绘画是第五王朝哪个确切的时间完成的。但萨胡拉所建的太阳神庙中的浮雕可以弥补这种不足,浮雕告诉我们,萨胡拉在叙利亚进行了征伐(约公元前2670年)。我们看到了军队乘船出发和获胜返回的场面:埃及人站在装有水手、船桨和沉重装备的大船上,赞扬萨胡拉,而亚洲俘虏(可通过体型和服装清楚地判别出来)伸出他们的手向国王祈求宽恕。[52]其他浮雕把国王描绘为一个半鹰半狮的怪兽,把亚洲人踩在脚下,在我们面前描绘出来的是亚洲的战利品,其中包括黎巴嫩的熊。[53]所有这些画面尽管不完整,但能解释为埃及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干涉(约公元前2 670年)。[54]
如果当时埃及人确实在小亚作战,为了在那里建立统治,那么我们没有必要承认商业关系因此更为密切,思想的交换随货物的交换而发生,而商人和运输工具都可作为宗教教义传播的工具吗?因此,闪族哲学家们的哲学推测和有时严厉的道德曾影响到了奥西里斯教义,这也是有可能的,而奥西里斯崇拜与拉神崇拜在埃及几乎同时发展起来。[55]如果这些假设能被证实,那么这些假设将使埃及人在叙利亚的这些最早的殖民地更有意义。
总而言之,在第三至第五王朝的君主制统治时期,埃及的法老们并未追求我们今日所说的侵略性对外政策;他们只巩固自己在尼罗河流域的地位,占据努比亚和西奈的要塞,组织边防区,但除了采取和保护西奈的金属矿物而外,始终没有从事侵略战争。法老们成功地迫使邻近游牧民族尊重尼罗河谷。法老们能够规驯更有智慧或更宜于管理的利比亚人和特罗哥罗迪特人,并将其引入文明,而利比亚人和特罗哥罗迪特人之后将为埃及提供劳力和雇佣兵。这种外交政策纯粹以创立一个统一而强固的王国,并确保能防御文化落后而渴望染指埃及的邻人的入侵野心为根据。
然而,在与外国人接触时,法老王朝很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义务、责任和优势;埃及民族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野蛮人当中一个有组织的民族。这些情操揭示了一种初生的爱国主义。(第六王朝)金字塔文当中一篇颂诗精彩地表述了这些情操。有韵律的诗节是奉献给世界的创造者图姆和法老-荷 鲁斯的。这些诗节颂扬了埃及的美丽与肥沃,用神秘的名字“荷鲁斯之眼”称呼埃及——即“法老 荷鲁斯”的创造物,并夸耀埃及的安全。
歌颂你,图姆……歌颂你,荷鲁斯的创造物,他[56]曾以其包蔽之臂庇护你。
他不允许你服从西方人,
他不允许你服从东方人,
他不允许你服从南方人,
他不允许你服从北方人,
他不允许你服从地球中央之人,
但你必须服从荷鲁斯。
正是他装饰了你,
正是他建造了你,
正是他创造了你,
所以无论他去往何处,你都应做他嘱咐之事。
你应该把你所拥有的多禽的沼泽水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将要拥有的多禽的沼泽水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所拥有的木材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将要拥有的木材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所拥有的祭品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将要拥有的祭品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所拥有的所有物品献给他,
你应该把你将要拥有的所有物品献给他;
而且你应该把你所拥有的物品卖到他所心悦的地方。
(埃及的)大门因为像神伊安穆泰夫一样的你而牢不可破;
而且埃及的大门不为西方人而开,
埃及的大门不为东方人而开,
埃及的大门不为南方人而开,
埃及的大门不为北方人而开,
埃及的大门不为地球中央之人而开,
但埃及的大门为荷鲁斯而开。
正是他创造了埃及的大门,
正是他提升了埃及的大门,
正是他守护埃及之门,以抵御塞特[57]对你所造成的一切侵害。
因为他以他的名字Foundation创造了你,
因为他以他的名字Town打倒塞特。[58]
无论这首颂诗如何使人安心,我们都仿佛听到了来自亚洲塞特地方的一种恐吓的回声。文明国家存在这里,宗教关系继商业交往之后发展起来。正是巴勒斯坦的政治形势迫使第六王朝的法老们在商船之后派遣战船、商人之后派遣军队,而这种政治形势的原因在文献中并不清晰。我们现在应研究此地的传说和纪念物,我们或许能从中发现埃及干涉巴勒斯坦的诸多原因。
【注释】
[1]在埃及和巴比伦,啤酒和小麦淀粉具有相似的名称,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p.200—229;参见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5,vol.1,27。
[2]布列斯特德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包围尼罗河河谷的多石灰石台地与同样形成的巴勒斯坦高原一样,曾是野生小麦的萌芽之地。James H.Breasted,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reprinted from the Scientific Monthly)(Oct.,1919),p.316。
[3]Bos Primigenius的头颅断片曾发现于尼罗河河谷法尤姆冰河时代的沉淀物中。James H.Breasted,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reprinted from the Scientific Monthly)(Oct.,1919),p.448。
[4]Schweinfurth,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es de l’Egypte,Cairo,vol.IV,268.
[5]J.de Morgan,Prehistoric Man,London,1924,p.114,或许夸大了西奈青铜矿的贫乏度。
[6]在革命时期,商业生活受到干扰,埃及痛苦的原因之一是不能从黎巴嫩输入木材;参见Gardiner,Admonitions,p.32。
[7]关于施威恩福特思想的有趣概括将在E.Hahn的论文“Babylonien,Jemen,Aegypten”,in Prüssische Jahrbücher,CLXXXVII,i,pp.49ff中找到,论文发表于伟大的科学家的80岁生日之时。
[8]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5,vol.1,p.33.
[9]参加G.Benedite,Le Couteau de Gebel-el-Araq。
[10]关于这种联系,可参见施威恩福特在Baedeker的Egypt一书中所写的一个章节“论人口的起源与目前的状态”。
[11]James H.Breasted,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reprinted from the Scientific Monthly),(Nov.,1919),p.426;J.de Morgan,Prehistoric Man,London,1924,p.169.
[12]直到第十二王朝,Libu这个名称才出现;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167。
[13]J.de Morgan,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s de l’Egypte,Paris,1896—1897,2vols,pp.165—167.
[14]参见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p.180ff。
[15]Junker,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VII,p.121.
[16]St r abo,XVII,786.
[17]Schweinfurth,Zeitschr.f.Ethnol,1912,p.633已注意到阿斯旺地区第六王朝的一个浮雕描绘了一个骆驼和骆驼夫。
[18]参见Lefèbure,Le Chameau en Egypt。
[19]参见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and in the Ancient East,pp.336ff。
[20]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228;参见J.de Morgan,Prehistoric Man,London,1924,pp.126—127。
[21]埃及人面南确定其方位。
[22]Quibel l,Hierakonpolis,Pls.XV,XXVI,XXIV;Petrie,RoyalTombs,1stDynasty,vol.I,4.
[23]Maspero,“La table d’of frandes,”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Annales du Musee Guimet),Paris (1897),p.22.
[24]Petrie,Royal Tombs,II,3,30a;J.de Morgan,Recherchessur les origins de l’Egypte,Paris,1897,vol.II,167;Garstang,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LII,61.
[25]Quibell,Hierakonpolis,pp.36—41、48.
[26]J.de Morgan,Prehistoric Man,London,1924,p.114.
[27]Compte-rendu de l’Acad.des.Sciences(Aug.,1896).
[28]Petrie,Sinai;参见James H.Breasted,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reprinted from the Scientific Monthly) (Dec.,1919),pp.564—570。
[29]R.Weill,Recuei des inscriptionsegyptiennes de Sinaï,p.97;Petrie,Sinai,p.45—47.
[30]Spiegel burg,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XXV,p.38.
[31]这些是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Knossos)发掘出来的,属于中新石器时代的水平;参见R.Dussaud,Les civilizations prehelleniques dans le basin de la Mediterranee,2nd ed.,Paris,1914,pp.36f;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228。
[32]Sethe,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lv,7.
[33]关于孟菲斯王朝的国内历史,参见The Nile and Egyptian Cilizition。
[34]Sethe,Urk.,i,2;参见Bragsch,Dict.Geographique,p.1288。
[35]大金字塔的建筑者奇奥普斯(Kheops)、肯夫瑞(Khephren)、迈西里努斯(Myceriuo)等等。
[36]Borchardt,Grabdenkmal des Königs Sahure,i i,p.13.
[37]Sethe,Dodekaschoenos,and 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LI,p.58.
[38]Palermo Stone,Schafer’s edition,p.30.
[39]根据我在C.R.Acad.des Inscrips.(1918),p.105中提到的第六王朝铭文,这些铭文可以追溯到古王国。
[40]Decree of Pepi I at Dashur;参见Moret,“Chartres d’mmaite,”Part III,Journal Asiatique(1917)。
[41]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265.
[42]荷尔胡弗的铭文,Urk.,i,126。这个短语也可翻译为“为了国王而崇拜所有神”。
[43]关于荷尔胡弗的文献,参见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Chicago,1906,vol.I,pp.352ff.;Sethe,Urk,i,120ff。
[44]Urk.,i,135f f.;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Chicago,1906,5vols.,pp.365ff.
[45]Inscription of Uni,i,21;Sethe,Urk.,i,pp.102—103;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Chicago,1906,vol.I,p.312.
[46]Lepsius,Denkmäler,ii,137;Weill,Recueil du Sinaï,pp.137ff.
[47]Schaefer,l.c.,p.30.
[48]Alexandre Moret,Mystèresègyptiens,3rd ed.,Paris,1922,pp.302f f.
[49]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250.
[50]关于确定的回答,参见W.M.Müller,Egyptian Mythology。
[51]Petrie,Deshasheh,Pl.4;参见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àla philology etàl’archeologiee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Paris,vol.XXXII,p.46。
[52]Borchardt,Sahura,II,Pl.15.
[53]Borchardt,Sahura,II,pp.16—21,pp.3—8.
[54]最近,蒙德特(Montet)先生在拜布罗斯发现了花瓶碎片,这些碎片上带着第五王朝几位法老的卡图什(1922年在卢浮宫展出)。
[55]Breasted,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p.26中的观点就是这样。
[56]他由神荷鲁斯和法老构成,法老是荷鲁斯在地球上的形象。
[57]塞特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敌人,也是亚洲人的神,后来被称为苏特胡(巴力神)。
[58]Pyramid of Pepi II,edited by Sethe,Spr.,587.最后一行town与指称塞特神服从埃及的某字之间有一个几乎无法翻译的双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