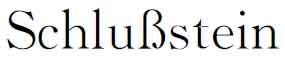-
1.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
1.2谨以本书纪念莱纳·维尔(Reiner Wiehl)教授
-
1.3绪论 康德肇始的“转向美学”与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
-
1.3.1一、课 题
-
1.3.2二、德国唯理念主义:术语和所指
-
1.3.3三、康德与近代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
-
1.4第一部分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中的“工具”作用
-
1.4.1第一章 “非体系的”谢林的体系功绩
-
1.4.1.1第一节 谢林思想在体系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
1.4.1.2第二节 艺术进入哲学体系的必然性
-
1.4.1.3第三节 “艺术—哲学”与体系哲学之难题
-
1.4.2第二章 康德的先验思考:艺术作为问题进入哲学体系
-
1.4.2.1第一节 艺术进入批判体系的问题总体关联
-
1.4.2.2第二节 艺术哲学与先验批判
-
1.4.2.3第三节 一种艺术哲学的任务
-
1.4.2.4第四节 艺术对先验的哲学体系的意义
-
1.4.2.5第五节 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划界与互补
-
1.4.2.6小 结
-
1.4.3第三章 早期谢林的体系建设:理智直观与悲剧的艺术直观论证
-
1.4.3.1第一节 早期文献的连续体系建立尝试
-
1.4.3.2第二节 绝对者与理智直观
-
1.4.3.3第三节 理智直观的悖论
-
1.4.3.4第四节 借助美感直观阐发理智直观
-
1.4.3.5第五节 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悖论的解决
-
1.4.4第四章 自然哲学的进路
-
1.4.4.1第一节 谢林自然哲学的发生学线索
-
1.4.4.2第二节 自然哲学的先验诉求
-
1.4.4.3第三节 自然总体关联中的自我
-
1.4.4.4第四节 自然整体作为创造性的系统
-
1.4.5第五章 艺术在哲学之内:System中的“工具”命题及其功能
-
1.4.5.1第一节 先验哲学的反思特征
-
1.4.5.2第二节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关键地位
-
1.4.5.3第三节 工具命题的体系位置和内容
-
1.4.5.4第四节 Organon、Organ与<img class="row1" src="images/P1...
-
1.4.5.5第五节 艺术的体系工具功能审查
-
1.4.6结语 原理的启示和见证
-
1.5第二部分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1802—1805)中的存在论神...
-
1.5.1导论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的存在论维度
-
1.5.2第六章 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艺术哲学
-
1.5.2.1第一节 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
-
1.5.2.2第二节 同一性哲学的基本观念
-
1.5.2.3第三节 艺术哲学作为绝对美学
-
1.5.2.4第四节 自然哲学的洞见与艺术哲学的构想
-
1.5.2.5第五节 神话作为艺术的形而上根基
-
1.5.3第七章 先验推演:艺术在宇宙中的存在论地位
-
1.5.3.1第一节 神和宇宙的理念
-
1.5.3.2第二节 艺术作为“观念的万有”最高级次
-
1.5.3.3第三节 艺术与绝对美
-
1.5.3.4第四节 表述论——哲学和艺术
-
1.5.4第八章 哲学神话学的理性建构及主要结论
-
1.5.4.1第一节 无限者的诗性生存
-
1.5.4.2第二节 “诸神说”与“诸理念说”
-
1.5.4.3第三节 诸神形象的总体性
-
1.5.4.4第四节 诸神的形象法则:绝对美和永福
-
1.5.5第九章 神话之存在论结构
-
1.5.5.1第一节 神话一般的概念
-
1.5.5.2第二节 神话的普遍性和无限性
-
1.5.5.3第三节 神性构型及其“反射”,构成力与想象
-
1.5.5.4第四节 神话作为真正的象征
-
1.5.5.5第五节 神话作为一切艺术的“质料”
-
1.5.6第十章 希腊神话作为实在论的神话
-
1.5.6.1第一节 将宇宙直观为自然
-
1.5.6.2第二节 自然的诸神与真实的象征
-
1.5.6.3第三节 神话与神秘
-
1.5.6.4第四节 史诗作为类族与个体的统一
-
1.5.6.5第五节 悲剧是所有艺术的自在及本质的最高显现
-
1.5.7第十一章 基督教作为观念的神话
-
1.5.7.1第一节 基督教作为普遍历史
-
1.5.7.2第二节 最后的神与无限的宇宙
-
1.5.7.3第三节 基督教神话质料的整体性
-
1.5.7.4第四节 历史的诸神与主体性的象征
-
1.5.7.5第五节 诸个体的世界、天命与自由
-
1.5.8第十二章 新神话作为绝对的综合
-
1.5.8.1第一节 “新神话”的产生问题
-
1.5.8.2第二节 历史与无时间性和解
-
1.5.8.3第三节 新神话与新艺术
-
1.5.8.4第四节 天才与艺术作品
-
1.5.8.5第五节 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
-
1.5.9结 语
-
1.5.10缩略语及引用说明
-
1.5.10.1一、德文版谢林原著引用说明
-
1.5.10.2二、引用德文原著缩略语说明
-
1.5.11参考文献
-
1.5.11.1一、德文部分
-
1.5.11.2二、谢林著作汉译及研究文献
-
1.5.12后 记
1
艺术与神话: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