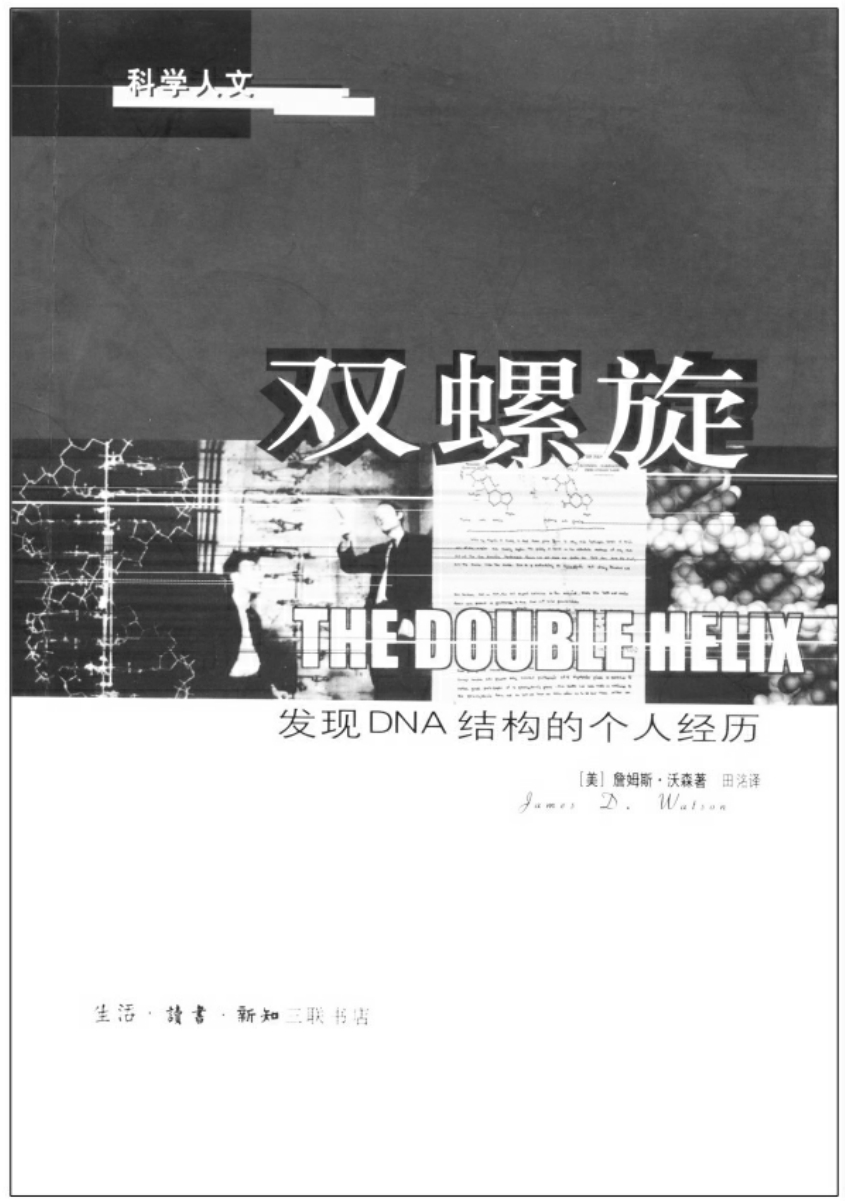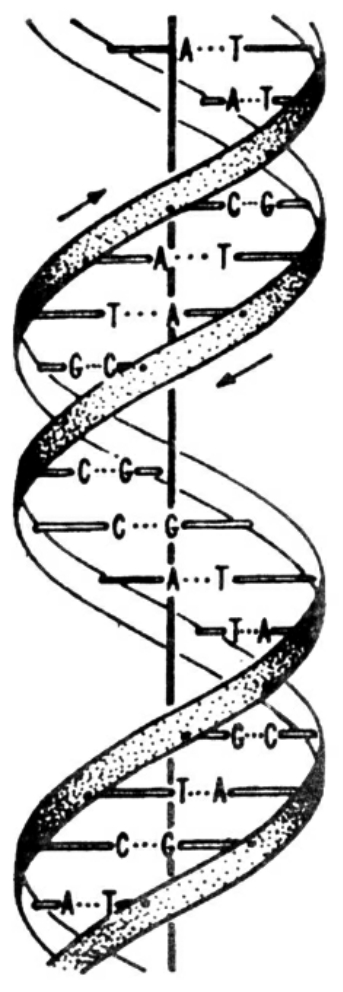-
1.1前 言
-
1.21 星云世界的水手哈勃一天传奇般的生活
-
1.32 推销银河系的人——博克
-
1.43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
-
1.54 科学史上的悲剧人物哈伯
-
1.65 约里奥-居里夫妇
-
1.76 20世纪科学怪杰鲍林
-
1.87 为世界而生的霍奇金
-
1.98 穆利斯和科恩伯格的一场官司
-
1.109 摩尔根被误认为是清洁工
-
1.1110 缪勒的坎坷路
-
1.1211 情有独钟的女杰芭芭拉
-
1.1312 自然的见证人卡逊
-
1.1413 自律甚严的卢里亚
-
1.1514 对歌剧无限热爱的梅达沃
-
1.1615 酶的情人科恩伯格
-
1.1716 DNA研究的奠基者富兰克林
-
1.1817 阿西莫夫的悼文:《永别了,朋友》
-
1.1918 避孕药的是非——杰拉西
-
1.2019 克里克的选择
-
1.2120 备受争议的沃森
-
1.2221 巴尔的摩的两次校长风波
-
1.2322 德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芙尔哈德
-
1.2423 萨谬尔逊:我如何工作
-
1.2524 “叛逆者”弗里德曼
-
1.2625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勒
-
1.2726 穿过沼泽地的豪尔绍尼
-
1.2827 逃脱病魔控制的天才纳什
-
1.2928 活泼严肃可爱的希尔伯特
-
1.30主要参考文献
-
1.31后 记
1
啊,科学家也这样?——科学大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