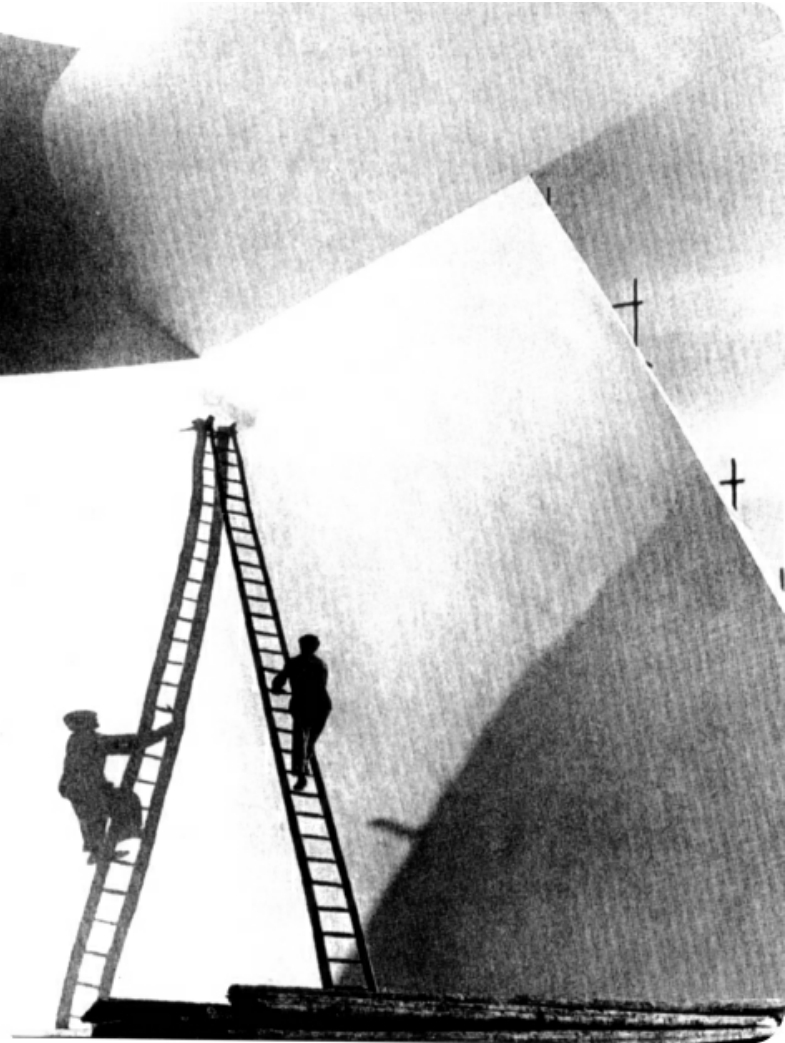-
1.1前 言
-
1.21 特立独行的女数学家诺特
-
1.32 神秘兮兮的拉马努金
-
1.43 库朗的“双城记”
-
1.54 数学神童维纳
-
1.65 博弈论的奠基者冯·诺依曼
-
1.76 哥德尔的逻辑人生
-
1.87 天性乐观的乌拉姆
-
1.98 爱多士:给我一个四位数!
-
1.109 永不言弃的哈尔莫斯
-
1.1110 特立独行的斯梅尔
-
1.1211 悲剧性的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
-
1.1312 弗里什,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教授
-
1.1413 “野猪”普拉切克
-
1.1514 “图书馆长老”塞格雷
-
1.1615 九死一生、大难不死的朗道
-
1.1716 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翰·巴丁
-
1.1817 爱德华·特勒:一个没有人能够读懂的人
-
1.1918 热衷欣赏神秘事物的约翰·惠勒
-
1.2019 最喜欢恶作剧的费曼
-
1.2120 对诺贝尔奖不敬的莱德曼
-
1.2221 争强好胜的盖尔曼
-
1.2322 格拉肖:“我的帽子总算保住了!”
-
1.2423 钱德拉塞卡的科学之路
-
1.2524 年轻气盛的海森伯
-
1.2625 伽莫夫——世界最幽默的科学家
-
1.27主要参考文献
-
1.28后 记
1
啊,科学家会这样?——科学家的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