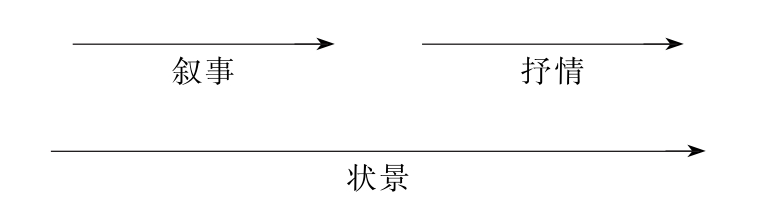二、时间向度
时间向度上的虚实相生结构说起来比较复杂,因为这必须牵扯到叙事与抒情写意的关系。一幅山水画可以不叙事,因为它只有一幅画面,它可以只状景,它的意境可以通过景物和笔墨营造。一首诗也可以不叙事,因为在诗里,人物形象可以隐藏起来,它的意境可以通过写景、抒情营造。但一部电影却绕不开叙事这道门槛。电影可以不抒情,不写意,却不能不叙事。因为,电影由于其“照相”的本性,其客观记录的本性,其时间与空间的复合性,其工业产品的属性,其对票房的依赖性,必须叙事,必须讲故事。《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电影是为叙事、为讲故事而生的,以活动的画面叙事成为电影最本质的特征。在电影里,叙事是皮,而抒情、写意则是毛,抒情、写意之毛必须依附在叙事这张皮上。即使是公认的诗电影,也绝脱离不开叙事,比如前苏联叶夫图申科的《幼儿园》,所有的诗情画意都依附在一个小男孩在战争中成长的故事上。再比如费穆的《小城之春》,“发乎情,止乎礼”、“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意境依靠的是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两个恋爱三角的故事。
那么,叙事与抒情写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又怎样参与意境创造呢?让我们还是先从诗谈起。
人们在谈论诗的意境时,往往有一种偏见,似乎意境只与“情、景”相关,而与叙事无关。但实际上,从大量优秀的古典诗词来看,即便是一些纯粹的抒情诗,也少不了叙事,如前面钱复所言:“盖每一诗皆赋也。”前面我们所举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如果缺了前面“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叙事,则后面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抒情就无所依附了,也就无法表达对友人的无尽怀念,那意境也就决非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样子。王国维在论及意境时常常将状景、抒情、叙事三者并列,如:“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5)王氏所言恐非武断,我们举一首唐伯虎的诗来说明这个道理。相传一年春天,唐伯虎从家中偷跑出去踏青。走到半山腰,累得又饿又渴。突见不远处一个亭子里,一群墨客骚人正在吟诗。旁边细腰把盏,娥眉研墨,红袖添香,好不热闹。唐伯虎急忙凑上去,墨客骚人的诗实在不敢恭维,细腰、娥眉、红袖们的芳颜也委实无法称道,但酒杯里的香气却十分令人垂涎。于是他便上去要酒喝。酒岂能随便喝?得作诗。唐伯虎接过笔,在纸上先写了俩字“七绝”,看看众人,挥笔写下两行:“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写不下去了,墨客骚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连那些芳颜们也无不掩唇、捧腹。在七绝这样的格律诗里,音可以谐,但字决不能重。写出重字,就是没学问,就是不会作诗。这两行里,几乎全是重字。这能不令人笑话吗?唐伯虎起先假做汗颜,惹得墨客骚人们一个个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待他们被捉弄得差不多了,唐伯虎才蘸蘸墨汁,大笔一挥,又写出下面两行:“举头红日白云低,五湖四海皆一望。”这一下,墨客骚人们不笑了,他们呆呆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不禁唏嘘长叹。
如果单从后两句看,写景、言情固然壮丽博大,但比之唐诗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的胸襟;比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星河落九天”这样的境界,还是相差甚远。但为什么“举头红日白云低,五湖四海皆一望”会让那些墨客骚人乃至我们都唏嘘长叹呢?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前面的“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那两句的铺垫。这两句是什么?正是叙事。正是因为“一上上到高山上”,才会有“五湖四海皆一望”的视野和境界。唐伯虎通过“一上一上又一上”把我们的视点带到高山上,使我们猛然之间把眼界向五湖四海拓开。
意境创造虽然不能说离不开叙事,但叙事确实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其实,即使山水画也未必没有叙事,千仞大山之下,一老翁蹒跚而上那是什么?河边林下,两三老翁对弈茅屋之中,那是什么?
叙事在抒情诗里扮演了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事是人物的活动,既包括当时当地的活动,又包括此前的、引起人物之所以做出这种活动和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情的事件,它往往是导致诗人之所以产生创作冲动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原因。因此,它又规定着诗的特殊情境,决定着诗人感情的走向和其笔下景色的意蕴,成为我们理解寓于景色之中的情绪的向导。再看欧阳修的《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如果没有“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这两句叙事,那“庭院深深深几许”……那“雨横风狂三月暮”便失去了一个“以我观物”的特殊的观察点,景物便无法“皆着我之色彩”,而后面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也就表达不出一个深闺怨妇的哀叹。
再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杨玉环被处死马嵬坡后,唐明皇回到京城: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
这无疑是《长恨歌》里最精彩、最感人的段落,它通过对未央宫里景物的描写,表现了唐明皇对杨玉环的无尽怀念。但如果没有前面的叙事,如果没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如果没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它还会那么动人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叙事不仅为诗的特殊情境提供了一个视点,它的更重要的作用是其连接景与情的结构性功能。它成为写景与抒情的基础,它或为写景创造条件和动机,或为抒情提供思想依据。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前面第一章谈到诗的意境构成时并没有谈及叙事,而只是谈到景与情。是的,景与情是构成意境的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是显性的。在一首诗中,构成意境的常常还有第三大要素,就是叙事,只不过这一要素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这正如一座大厦,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它地面以上的建筑,但如果没有地底下的地基,这大厦能支撑起来吗?你在地面上看不到它,但正是它决定了一座大厦的高低。叙事是抒情、写意的基础,它正如一座大厦的地基。
在诗里,叙事与写景、抒情的构成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叙事与写景(抒情)两分。
这又可分为两种次类型:
(1)先写景(抒情),后叙事。
杜甫《登高》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由于年老多病,连酒都不能喝了,艰难潦倒之中独自登台远望,于是风急天高、无边落木均有了悲情色彩。)
范仲淹《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碧云黄叶、斜阳芳草的秋色由于诗人的羁旅怀乡之苦而蒙上了浓郁的悲情,深夜难眠、借酒消愁的叙事,使我们明白了景中所含之情。)
(2)先叙事,后写景(抒情)。
李白《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第一句、第二句叙事中包含写景,而写景中亦隐含抒情,但首先是叙事。叙事为后面的写景、抒情规定了特殊的情境。有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之快,才使后两句透露出还乡的喜悦与快慰。)
李清照《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阕叙事:去年秋天的时候,心爱的人独自乘船走了,从此便日夜盼望鸿雁传书;下阕展开写景、抒情,以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景色,引出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无奈。)
还有一首王国维的《浣溪沙》也可以作为佐证:
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金焦在眼苦难攀。
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人天相对作愁颜。
第二种类型:叙事与写景抒情融为一体。
苏东坡《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这里,我们要好好研究这种叙事技巧。写景是为了造境,叙事有时候也是为了造境。它可以通过叙事来造境。原因是人物活动必然在特定的场景内进行,利用人物的活动就可以带出此活动的场景。于是,叙事便兼有了写景的功能。而且,由于人物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场景也必然随着人物活动而发生变化,这就叫做“移步换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既是对人物活动的叙述,又是对场景的描写,而且是运动中的描写。这岂不是电影中的跟移镜头吗?再者,既有了活动中的人物又有了运动中的场景,那么,情感这个蕴藏在人物内心的元素不也就有了有所附丽的外在形象了吗?事有了,景有了,情有了,意境不也就有了吗?于是,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中看到了诗人内心那种达观泰然的境界。
苏东坡是运用这种技巧的高手,他的两首《江城子》都是这种技巧的典范。“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之豪迈、激昂,“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之清冷、凄苦境界都依这样一种技巧。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叙事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在这里叙事不是抽象化的叙述,而是形象化的叙事,此叙事有人物,有活动,有故事,有场景,更有形象化、视觉化的“画面”。此等叙事是融叙述、写景、抒情为一体的叙事。这种叙事方能构成抒情写意的基础,方能造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古典诗词中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我们费了那么多笔墨,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要说明,在诗词中叙事是创造意境的结构性元素,它能够与写景、抒情构成灵活的虚实相生的结构,为意境的创造提供特定的视点、情境和内在的依据。
我们发现这种“叙事—抒情”的虚实相生的结构正是在电影里营造意境的最主要的方式。也就是说在电影里,情与意是依靠景与事这两个东西抒发出来的,意境也就在这“景—事—情”的虚实结构中萌生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空镜头营造意境。在空镜头中没有人物活动,当然也就无所谓叙事,但在电影中空镜头的意境依然逃脱不了时间因素的作用。如果没有前因后果的叙事,如果没有蒙太奇的连接,一个空镜头能表达什么意境?比如《我的父亲母亲》中在后期常常出现的那个教室,如果没有一开始的那一番建造,如果没有后来的先生被抓,如果没有招娣在山上的那一阵穷追猛赶,那个教室也许仅仅是一个景致、一个教书的场所而已。它变不成先生的形象,变不成招娣对先生的那一番刻骨铭心的爱,更变不成对那个时代的强烈的批判。要知道那个教室是专门为先生盖的,那是他的身份、他的魅力的体现,那里面有招娣的一片真情,那块红所代表的是招娣的心。
《城南旧事》的结尾,这是我看到的影片中最令人激动的结尾之一:父亲的墓地、逐渐远去的宋妈的身影、漫山遍野的荒草红叶,伴随着悠扬哀伤的音乐,将小英子的别情离绪一泻千里地倾泻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前面那三个故事,如果没有她的三个朋友——一个疯子、一个小偷、一个老保姆的不幸遭遇,你能体会到那种意境吗?只有在这些故事发生之后,你才能从那满山的红叶中感受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意境。
意境讲究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电影里,如果没有叙事之“言”,那无尽之“情”便无从生发,无从体现。事与发生此事之景,实乃情、意之基础也。
在诗与画里,我们既可以以实带虚,也可以以虚带实,但在电影里却必须并且也只能以实带虚。事与景作为可见的实体性元素构成召唤性结构的前端,而情与意作为不可见的虚体性元素则构成其后端。一个镜头、一个段落首先要完成叙事任务,然后才能过渡到抒情、写意。叙事为抒情写意提供基础和动机,抒情写意使叙事升华和产生概括意义。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电影里叙事与抒情的虚实相生也可分为两种类型——叙事与抒情两分和叙事与抒情一体。第一种类型由蒙太奇体现,第二种类型由长镜头体现。
先看第一种类型。
我们先举《香魂女》中的一个例子。在那个荒诞的新婚之夜,当客人们都散去之后,香二嫂来到儿子的新房。她只看到那一片狼藉的床上傻睡的儿子,而儿媳环环却不见踪影。待她仔细翻查一遍被褥后,她发现那床上并没有她所期待的“婚事”的痕迹。于是,她走到临湖的后门,她看到在一片凄凉的夜风与月色中,环环正在湖边擦洗肩头。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在夜风中轻轻摇曳的、如泣如诉的荷花(图5-3)。这组镜头,按我们中国古典美学的说法就是“比”,以环环比荷花,美丽的环环犹如那凄苦的荷花,在夜风中、在冷峻的月色中无声无息地哀叹。一个美丽如花但一贫如洗的姑娘就是这样度过了她的新婚之夜。

图5-3A

图5-3B
(见彩插5-3A/B)
前面的叙事和后面的状景并没有直接表达感情,但两个镜头一经并列,我们便明显地感受到了其中的意味。这意味是导演通过镜头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正如两行诗句一经并列所产生的意味一样。事是实的,环环在夜色中擦洗身体;景也是实的,荷花在夜风中摇曳。但那虚,那悲情与哀怨却从这两个镜头的关系中萌生出来,这岂不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再如《天云山传奇》,当冯晴岚在贫困中死去之后,画面上一连出现了七个空镜头:烟雾缭绕之中冯晴岚面带微笑的照片,墙壁上悬挂的破衣烂衫,灶台上的菜刀和几块没切完的咸菜,破碎的光影斑驳的窗帘,寒风凛冽中摇摇欲坠的茅屋,屋前小河上孤零零的独木桥,屋后小径旁缓缓旋转的老水车……(如图5-4)。我们谁也不可否认,这些景物,这些冯晴岚生前所使用、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都已化为对她死亡的哀悼,对她生命的惋惜。正如《长恨歌》里杨玉环死后,唐明皇回到宫里的那段描写一样:“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这不是典型的化实为虚,化虚为实,化情思为景物,化景物为情思吗?而这“化”是由蒙太奇这个“美学的变压器”实现的。

图5-4A

图5-4B

图5-4C

图5-4D

图5-4E

图5-4F

图5-4G

图5-4H

图5-4I
两组镜头的对列与两行诗句的对列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们都会在对列关系中相生、萌发出新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电影与诗是相通的,镜头和蒙太奇的关系也就是一种虚实相生的关系。爱森斯坦对这种关系做过最权威的论述:“在《蒙太奇1938》一文中,我们在对蒙太奇做最终的明确表述时写道:……由展开中的主题在诸因素中选取的片段A,和也是从那里选取的片段B,一经对列起来,就会产生出一个能最鲜明地体现主题内容的形象……也就是说,图像A和图像B应该从展开中的主题内部各种可能的特征中这样来选取,使得它们的——恰恰是它们的,而不是别的因素的——对列能在观众的感知和感情中唤起最完整的主题本身的形象……”(6)“正确的和至今仍是正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蒙太奇片段的对列不是二者之和,而更像是二者之积。说它是二者之积,而不是二者之和,是因为对列的结果在质上永远有别于每一单独部分。”(7)
蒙太奇为什么会与诗相通?这个道理爱森斯坦早就说过:“电影的原理并不是从天上掉落人间的,而是在人类文化的深层中发展出来的。”(8)爱森斯坦曾深刻地研究过俄罗斯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视觉结构、声音结构或声画结合的结构中,无论在塑造形象、构成情境或‘魔法般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场人物的形象方面,无论是普希金的作品或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都同样存在着同一个蒙太奇的方法。……每一个领域不管沿着看起来多么互不相关的途径前进,它们始终不能不在方法的最终一致和统一中走到一起。”(9)有意思的是,我国清代美学家刘熙载也有相似的说法:“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每上句与下句转关接缝,皆机窍所在也。”(10)
再来看第二种类型,叙事与抒情一体。
所谓叙事与抒情一体是指叙事与抒情同处于一个镜头之中,镜头在完成叙事任务以后不是马上结束,而是继续延伸。画面较之前面没有增加新的实际内容,景物实体及其空间范围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景的性质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叙事的时候,景是作为事件的背景而存在的,此刻它是客观的,状景与叙事在时间和空间都融为一体。但叙事任务完成后,景的性质则由客观变为主观,由事件的背景变为作者的情感媒介,画面上的人及其动作不再单纯地叙述具体的事件而是变成景物的一种组成部分,变成一种情感元素共同参与抒情任务。此刻状景与抒情融为一体,景物化为情思,情思化为景物,叙事与抒情由此而虚实相生。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结构图说明这个问题。
叙事—抒情之虚实相生结构图:两个层面——叙事—抒情;状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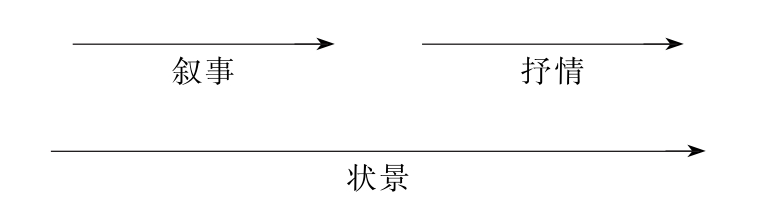
可以看出两个层面的时间值是一致的,同时推进。但第一层面中叙事与抒情是历时性的,先叙事后抒情;而第二层面与第一层面是同时性的,状景始终与叙事—抒情同时推进。
在《可可西里》的最后,弹尽粮绝的日泰终于追上了那群盗猎的匪徒,此时日泰已经单枪匹马而匪徒却成群结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日泰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向匪徒挥起拳头,匪徒的枪响了,日泰倒在雪地上。匪徒们扔下日泰和那个惊魂未定的记者向雪山尽头走去。这个镜头在完成了上述动作之后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一动不动地停留了一分多钟。远处雪山横亘,天苍野茫;近处狂风裹着飞雪怒吼于天地之间。景物由事件发生的背景转化为作者的情感媒介,转化为主观的情思,诉说着悲愤慷慨之情。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绝对没有镜头切换,有的时候,这种叙事—抒情的任务也许需要几个镜头组成一个段落共同来完成。这些不同的镜头也许会有景别的变化,也许会有角度的变化,但景域范围和事件没有发生变化,镜头切换只起连接作用而镜头间并没有新的质产生,也就是说只有时值的延长和情感的延伸。比如《可可西里》日泰被打死那个场面,它实际上是四个镜头。上述那个镜头是大远景,叙事完成后延长了1分12秒。第二个镜头是大全景,48秒。第三个镜头是全景,25秒。第四个镜头是日泰的头部特写, 21秒。这后续的三个镜头并没有新的事件发生,它们只是第一个镜头时值的延长和情绪的延伸。
再如《我的父亲母亲》最后那个抬棺的场面,它开始于1小时9分08秒,先是画外音交代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抬棺的人,然后,村长把生子给他请人抬棺的钱还给生子。到这里叙事已经完成,但抬棺的场面继续往下延伸了长达2分20多秒,从白天一直到夜晚。开始时那一片茫茫大雪、那漫长而弯曲的道路只是“抬棺”这个事件的空间背景,它是叙事任务中交代时间与天气情况的一个环节。但叙事任务完成后,那茫茫大雪随即上升为感情的媒介,与那漫长的默默行进的抬棺队伍一起,化为对父亲的怀念、崇敬之情,那曲曲弯弯的漫长的道路也随即化为呼唤真情、象征道德的回归之路(图5-5)。

图5-5
那么,从叙事到抒情以何为契机?抒情又是如何从叙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观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是怎样感受到叙事的结束与抒情的开始呢?我们怎样从那并没有变化的镜头中感受到景物性质的变化,感受到此时此刻那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的景物已经转化为主观的情思了呢?这之间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起到像蒙太奇那样的“美学变压器”的作用呢?
我们发现这个“美学变压器”确实是存在的,音乐、音响就是最常用的“美学变压器”之一,其他的还有诸如风、雨、雪、雾等虚体性的景物要素。这些虚体性的要素与作为实体的景物要素又构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的结构,在光学镜头、画面构图、光线与影调等镜头语言的帮助下,使叙事转化为抒情,使景物转化为情思(当然在蒙太奇充当“美学变压器”的时候,这些镜头语言要素的作用仍然存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蒙太奇,而在这种长镜头结构里,声音与镜头语言要素则成为主要角色)。比如《城南旧事》的结尾,比如《天云山传奇》中那个“山路弯弯,风雪漫漫”的雪中拉车的场面,离开了音乐音响,离开了风雪,其言外之情、象外之意岂可想象?再如上述《可可西里》的那个场面,当匪徒们杀死日泰离去以后,随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狂风裹挟着漫天飞雪呼啸而至,刹那间整个银幕变成一片怒吼的海洋,风凄厉而肃杀,雪狂舞而冲天。远处横亘的雪山、莽莽的雪原,随之变成悲愤慷慨之情洋溢于天地之间。《我的父亲母亲》抬棺的场面,当村长把钱还给生子,告诉他来抬棺的人谁都不要钱之后,伤感而深情的音乐轻轻奏起,接着,脚步声、风声一同响起。音乐与音响将那一片茫茫大雪,将那漫长的、曲曲弯弯的道路和默默地抬棺的队伍顷刻之间转化成对那位父亲、那位坎坷与穷困一生的先生的怀念、崇敬,转化为对正义与道德、对人间真情的呼唤。我在我校导演专业刚入学的一个班(2006级)就抬棺这个场面做过实验,在村长把钱还给生子,亦即对话包括画外旁白都结束后,关掉声音,放了一遍,然后打开声音把同一片段又放了一遍。请学生们回答声音对画面的作用。28位学生中有23位(占82.14%)都认为声音对画面的抒情产生了重要作用。现摘抄几位学生的话:
学生1(冯硕):“(无声时)让人觉得很平常,在情感上没有任何起伏,让人觉得波澜不惊,有些杂乱,而不是以往的那种美(按,即彩色部分)。在加入了踩雪的音效和背景音乐后,加强了画面的冲击力和动感,众人抬棺在音乐的帮衬下也更有感染力。”
学生2(朱艺):“(无声时)整个片段感觉沉闷,哀伤悲凉的气氛无法烘托,整段抬棺过程显得漫长而无味,观众很难感受到其中包含的感情色彩。(有声时)不但整个场面得到很好烘托,更使画面不再显得单一而古板,非常恰当地加强了画面的抒情强度。与其说声音为影片增色不少,不如说声音为这一片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生3(田思梵):“(无声时)影片所要表现的抬棺出殡的情节不能够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多是中景和远景镜头,感觉不到送葬人的悲伤情感。无声的片段让人觉得略显单薄,起不到推动情感发展,使观众受感动的效果。(有声时)先突出的呼啸的风声和断续的脚步声,烘托出视觉效果的萧索意味。接着传出了贯穿整部影片的主旋律,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渐渐清晰起来的笛子独奏与往事的那种悠扬的弦乐合奏呈现对比,对比出了悲伤的情绪,也仿佛在送葬的同时回忆了那段彩色的美好的爱情往事,使观众在两种情绪的交织中深受感动。”
学生4(沈千之):“(无声时)因为对内容的了解只能凭借画面的叙事,所以我更关注画面,画面有很多叠化部分让我觉得很长很累。抬棺的队伍很长,但在无声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气势。(有声时)声音部分非常抒情的音乐,让我了解了导演的意图是抒情。队伍行进得很慢,但比较浩荡、沉重,配上音乐后觉得气势被推出来了。”
学生5(高源):“在无声的片段中,我只能通过看和想来接受画面中的信息。我看到的是漫天的大雪、斜乱的大风,还有大风中抬棺的人群和车辆。我在努力地观察人们脸上的表情,但大部分的远景只能给我一个群体的画面。从画面中我只能体会到他们在不停地向前走,更换抬棺的人,他们的心情是悲伤的,而在这样的天气来抬棺,也是表明他们对死者的尊敬。在有声片段中,我听到了风雪的呼呼声,内心感受十分寒冷。人们走路踩雪的声音也让我觉得道路异常难走。虽然人们没有语言,镜头又十分少,但浅浅的、轻缓的笛声让我感到伤感,再配合大雪中人群前进的画面,让我仿佛也成为人群中的一员,自己也参加在葬礼之中,是我,也表现出了对死者的哀悼。”
从学生们的话和那个82.14%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认定,声音确实能够起到“美学变压器”的作用。音响与音乐使得镜头从叙事转化为抒情,引发了观众对画外之意的联想;声画结合以致虚实相生,形成了电影意境的召唤性结构。清郑绩说:“生变之诀,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八字尽之矣!”(11)景物要素之虚实,物质要素与镜头语言之虚实、画面与声音之虚实、镜头与蒙太奇之虚实、叙事与抒情之虚实,电影意境就是在这种虚虚实实的相生、召唤结构中萌生、引发、创造出来的。
【注释】
(1)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3)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4)同上书,第163页。
(5)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载《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89页。
(6)〔前苏联〕谢尔盖·爱森斯坦:《垂直蒙太奇》,载《蒙太奇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7)同上书,第279页。
(8)同上书,第123页。
(9)同上书,第324页。
(10)刘熙载:《艺概·诗概》,转引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页。
(11)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载潘运告编:《清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