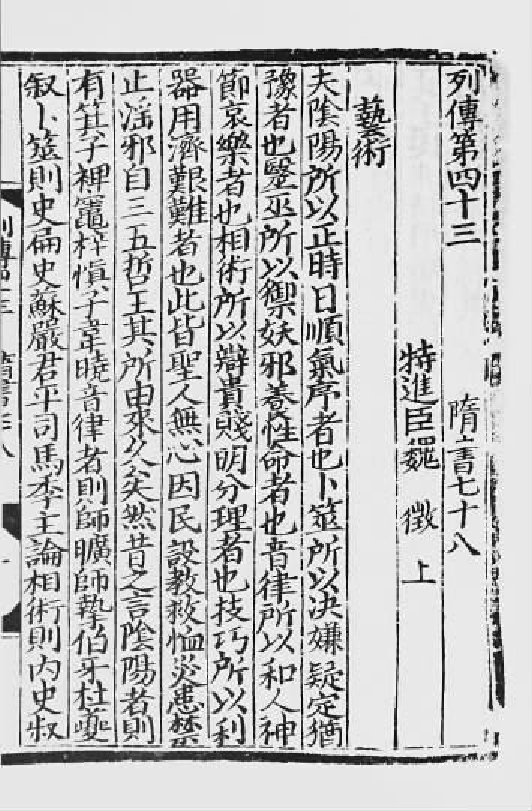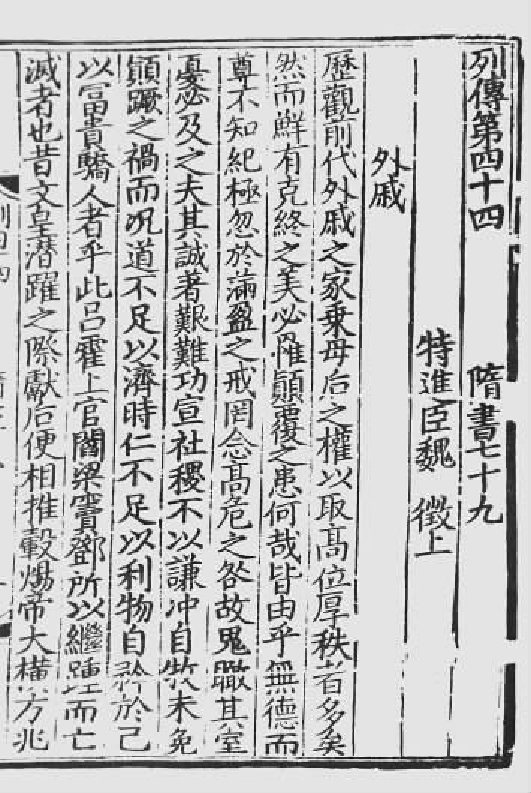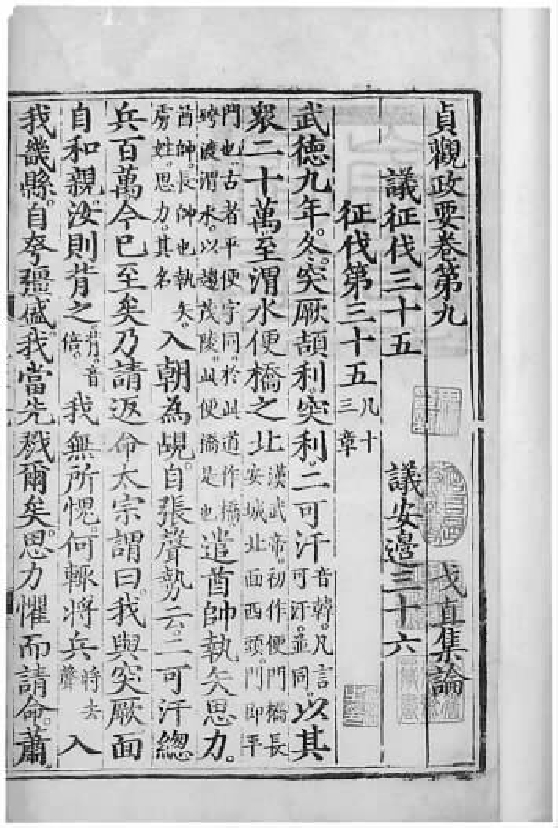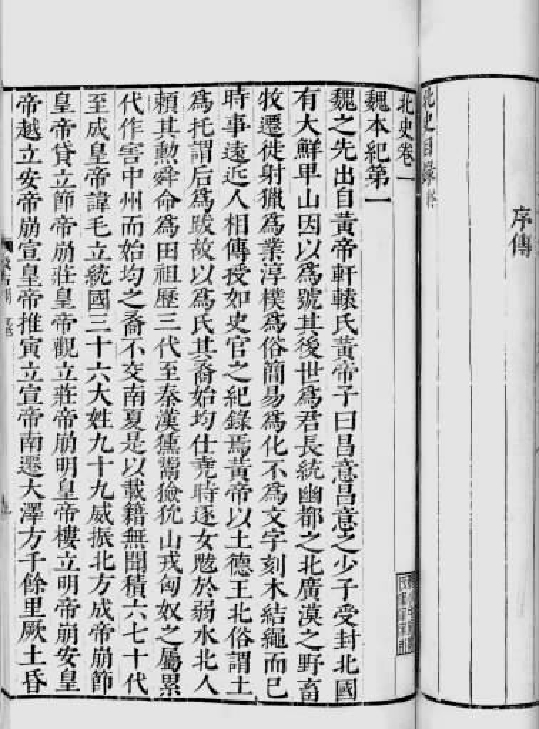-
1.1引 言
-
1.2目录
-
1.3第一章 十三岁为总管
-
1.3.1第一节 有感于北周之亡
-
1.3.2第二节 三人辅佐
-
1.3.3第三节 父皇严教
-
1.4第二章 北御突厥
-
1.4.1第一节 离间之计
-
1.4.2第二节 和亲之策
-
1.4.3第三节 武功不懈
-
1.5第三章 平定南陈
-
1.5.1第一节 博采平陈之策
-
1.5.2第二节 出任行军元帅
-
1.5.3第三节 驻扎六合挥兵
-
1.5.4第四节 活捉陈后主
-
1.5.5第五节 押解降帝到京城
-
1.5.6第六节 论功行赏
-
1.6第四章 立为皇太子
-
1.6.1第一节 杨勇失宠
-
1.6.2第二节 夺宗之计
-
1.6.3第三节 禁锢杨勇
-
1.6.4第四节 兴大狱
-
1.6.5第五节 立为皇太子
-
1.7第五章 即皇帝位
-
1.7.1第一节 禁锢杨秀
-
1.7.2第二节 镇压同党
-
1.7.3第三节 隋文帝之死
-
1.7.4第四节 即皇帝位
-
1.8第六章 平息杨谅之叛
-
1.8.1第一节 杨谅叛变
-
1.8.2第二节 十九州响应
-
1.8.3第三节 派杨素率骑征讨
-
1.8.4第四节 嘉奖平叛功臣
-
1.9第七章 营建东都
-
1.9.1第一节 东都之营建
-
1.9.2第二节 并非在汉魏故城上的修建
-
1.9.3第三节 营造东都之目的
-
1.10第八章 开凿南北大运河
-
1.10.1第一节 分段开凿运河
-
1.10.2第二节 开凿运河的动机和条件
-
1.10.3第三节 运河开凿的特点
-
1.10.4第四节 “隋民不胜其害,唐民不胜其利”
-
1.11第九章 复开学校
-
1.11.1第一节 复开学校之原因
-
1.11.2第二节 复开学校之内容和特点
-
1.11.3第三节 复开学校之意义和影响
-
1.12第十章 创置科举制
-
1.12.1第一节 科举制度之背景
-
1.12.2第二节 科举制度之特点
-
1.12.3第三节 科举制度之影响
-
1.13第十一章 颁发《大业律》
-
1.13.1第一节 制定《大业律》之缘由
-
1.13.2第二节 《大业律》之主要内容
-
1.13.3第三节 《大业律》之主要特点
-
1.13.4第四节 《大业律》之影响
-
1.14第十二章 改良风俗
-
1.14.1第一节 兴 学
-
1.14.2第二节 尊 孔
-
1.14.3第三节 行 孝
-
1.14.4第四节 制 礼
-
1.15第十三章 重设郡县制
-
1.15.1第一节 废三级制
-
1.15.2第二节 重设郡县制
-
1.15.3第三节 重设郡县之原由及意义
-
1.16第十四章 改革官制
-
1.16.1第一节 中央政府之设置
-
1.16.2第二节 改革官制之要点
-
1.16.3第三节 改革官制之目的
-
1.17第十五章 扩大推行均田制
-
1.17.1第一节 扩大推行均田制之原因
-
1.17.2第二节 扩大推行均田制之内容
-
1.17.3第三节 扩大推行均田制之意义
-
1.18第十六章 强化府兵制
-
1.18.1第一节 强化府兵制之背景
-
1.18.2第二节 强化府兵制之措施
-
1.18.3第三节 强化府兵制之意义
-
1.19第十七章 经通西域
-
1.19.1第一节 经通西域之起因
-
1.19.2第二节 经通西域之方法
-
1.19.3第三节 经通西域之意义
-
1.20第十八章 性格及其爱好
-
1.20.1第一节 性 格
-
1.20.2第二节 好读书
-
1.20.3第三节 爱作文辞
-
1.21第十九章 巡幸天下
-
1.21.1第一节 首游江都
-
1.21.2第二节 首次北巡
-
1.21.3第三节 再次北巡
-
1.21.4第四节 西巡河右
-
1.21.5第五节 再游江都
-
1.21.6第六节 第三次北巡
-
1.21.7第七节 第四次北巡
-
1.21.8第八节 第三次游江都
-
1.22第二十章 远征高丽
-
1.22.1第一节 一征高丽
-
1.22.2第二节 二征高丽
-
1.22.3第三节 三征高丽
-
1.22.4第四节 远征高丽之目的及其影响
-
1.23第二十一章 镇压杨玄感之乱
-
1.23.1第一节 杨玄感举兵
-
1.23.2第二节 “从者十万”
-
1.23.3第三节 急调重兵反击
-
1.23.4第四节 诛杀杨玄感党羽
-
1.23.5第五节 杨玄感举兵性质及其影响
-
1.24第二十二章 江都之变
-
1.24.1第一节 “莫敢以贼闻奏”
-
1.24.2第二节 宇文氏兄弟谋变
-
1.24.3第三节 隋炀帝之死
-
1.24.4第四节 政变军西行
-
1.24.5第五节 政变者之败亡
-
1.25第二十三章 义军蜂起
-
1.25.1第一节 一呼百应
-
1.25.2第二节 瓦岗军威震中原
-
1.25.3第三节 河北义军重击隋兵
-
1.25.4第四节 江淮义军逼近江都
-
1.25.5第五节 无奈义军蜂起
-
1.26第二十四章 李渊父子举兵
-
1.26.1第一节 李渊的“自晦”之计
-
1.26.2第二节 晋阳起兵
-
1.26.3第三节 “尊隋”旗下的进军
-
1.26.4第四节 直驱长安
-
1.26.5第五节 唐王朝之建立
-
1.27附录 隋炀帝大事年表
-
1.28后 记
-
1.29重版补记
1
隋炀帝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