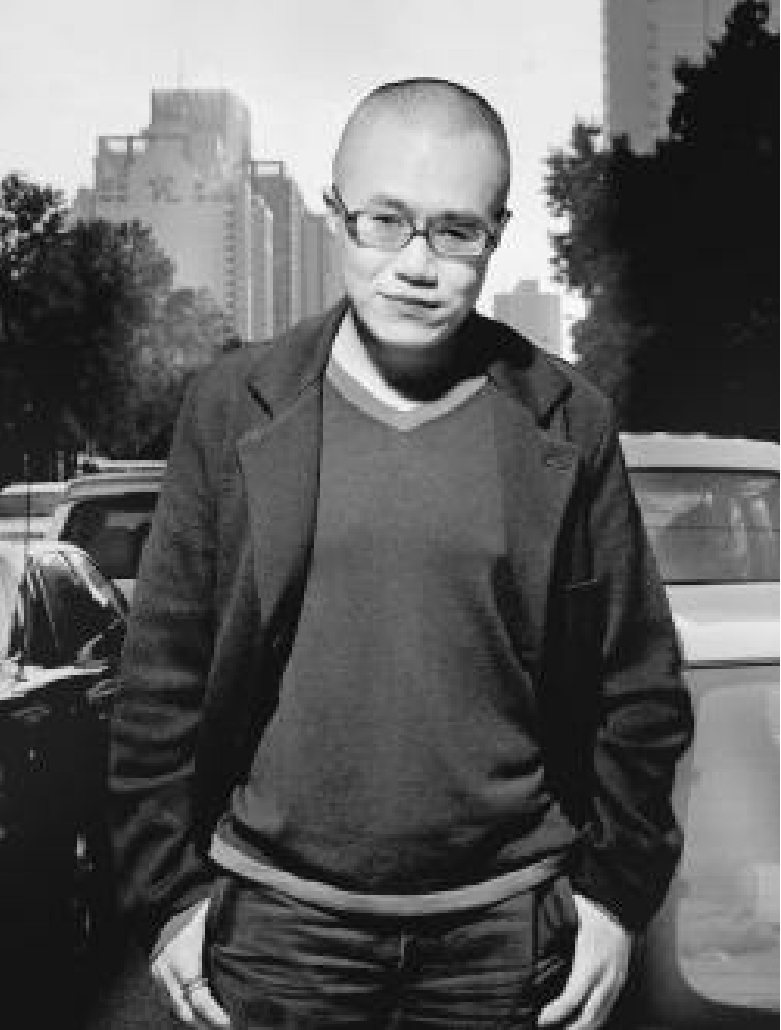梁文道:关掉屏幕,凤凰就像收音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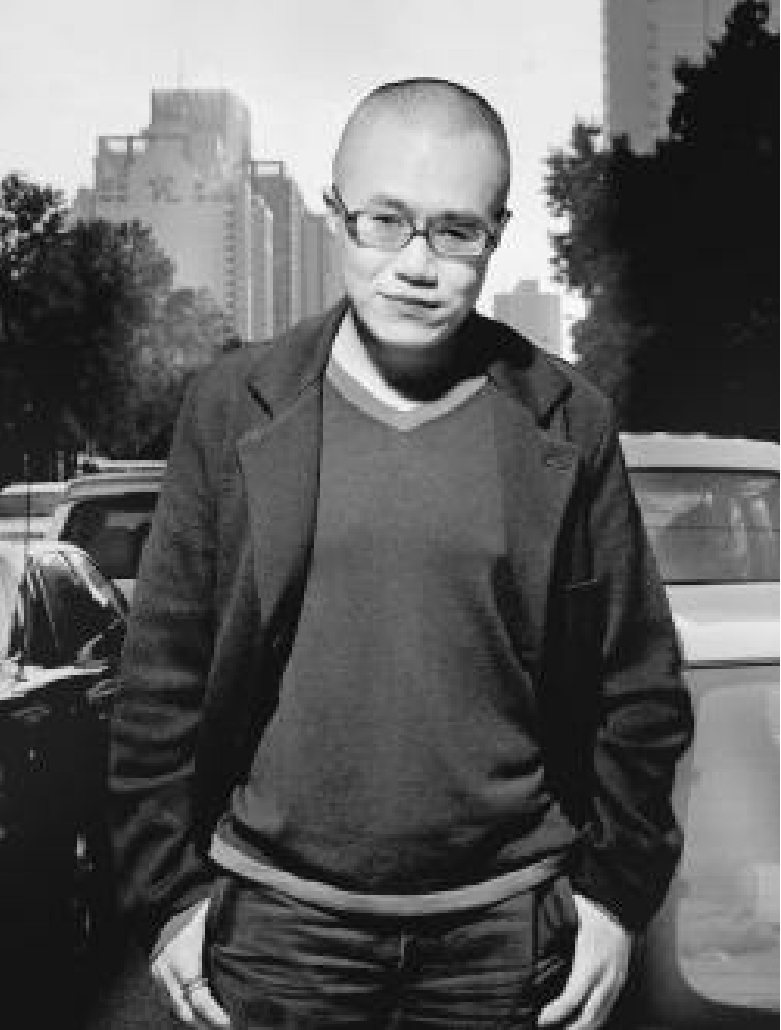
梁文道
现任凤凰卫视评论员、《开卷8分钟》主持人。
20世纪90年代末因客串性质做起《锵锵三人行》,不久之后以评论员身份入驻凤凰卫视,与窦文涛、许子东一起被誉为“锵锵铁三角”。除此之外,他也主持《大话世界杯》、《两极之旅》、《走进非洲》、《文道非常道》、《开卷8分钟》等凤凰节目。
1970年出生于香港,成长在台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尝试过实验剧场的编、导、演;担任过文艺团体及非政府组织的董事、主席或顾问;参与过各类社会维权、反战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撰写过艺评、影评、时政评论并将一直写下去的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纸杂志专栏作家。
昊灵:王昊灵
文道:梁文道
做媒体是为了产生影响,凤凰是最合适的平台
昊灵:文道老师,您入驻凤凰已有十多年了,其间两进一出凤凰,是什么吸引您来凤凰,或者再次回到凤凰?
文道:我一开始做凤凰那是个意外!那时候只是因为我去帮忙做《锵锵三人行》,被找去做嘉宾,然后做着做着就一直做下来,后来还帮他们做别的节目,后来他们问我,要不要干脆进来工作?然后我就干脆进来工作。那时候没有任何的考量,有节目就做,我就当做(它是)一个挣钱的工作而已,那是十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只做了六七个月吧,就走了。因为我又去了商业电台当台长,去做电台管理工作,是香港的一家电台。这个做了一年多、两年,然后才再离开那个职位,再到凤凰来。
那后来我第二次回来呢,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已经不想再做那么多香港媒体,我想在内地多做些事情。现在在内地,你要在媒体工作,又是希望这个媒体开放一点、容忍度比较高的话,最方便的就是凤凰。
我做媒体工作基本上也是为了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去介入一下今天媒介的公共讨论,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凤凰应该是一个内地电视媒体里最适合的一个。
昊灵:如果您想要在内地做些事情,又希望产生影响力的话,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影响力远远大于凤凰的央视呢?
文道:第一,央视不认识我,我也不会去央视;第二,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因为第一,一开始我在香港,我不会搬到北京去住;第二,央视不是你说去就去的嘛;第三,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内地做媒体,有很多东西不能说、不能做。
昊灵:现在央视已经做了很大的改版动作,那么您觉得改版之后的央视如何呢?
文道:我觉得还是这样。
昊灵:如果就“央视改版”这件事情来讲呢?
文道:我看了一下,现在形式上它很活泼了,可是本质上分别不是太大,就是内容比重上,它有些差异了,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宣传的特点。
昊灵:这个很难摆脱或者改变吧?
文道:央视的问题,或者说所有官方媒体的问题:第一,它有很多的限制让你不能说话,这是大家常常看到凤凰和央视的分别之一;但是在我看来,我更看重的是第二个分别,就是不止是你说话空间的大小,而且还有你有没有不说某些话的权利。平常大家关注的是,你有没有说什么的自由,但是你有没有不说什么的自由,这个在我看来更重要。
凤凰很重人情味,对我很宽松
昊灵:您曾在香港电台工作过,也为不少报纸写过或是仍在写专栏,在您看来,凤凰与其他媒体的区别是什么呢?
文道:因为我真正在这种受雇的媒体机构不多,我在很多媒体工作,但是我是写东西,那我写东西的状态,跟那个媒体没多大关系,像《南方周末》、《明报》这些,我基本上不跟人往来,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其实在凤凰也是一样,我是处于一个非常独立的状态,我回来做节目,做完我就走,写东西我就写,写完我就交,我也不认识那些人,不跟那些人打交道。可是,凤凰到底我是受雇的,而且那么固定的是要回来上班,所以难免会认识许多同事。
昊灵:这么说来,您当初是怎么愿意受雇于凤凰的?
文道:所以我虽然受雇于凤凰,我也争取到了最大的自由。比如说,我到处跑,她也不管我。
昊灵:还是说,凤凰就是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氛围,大家都享有这个自由?
文道:我不肯定,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但起码对待我的态度上,我觉得凤凰对我很宽松。
我还要说回一点,就是我刚刚说我工作过的香港媒体机构是很business(商业)的、公事公办的,凤凰相对而言是个家庭式的,或者是比较中国式的管理方法。
不是家庭式的,应该是中国式的,就是注重人际关系、注重人情味,比较多的管理上不是太(严苛)……我知道很多的内地媒体已经相对制度化,但是它又没有香港的那么制度严密,就是很多的行政规则,香港是很严的、很清晰的;但凤凰不是。比方说,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况,1月1日要出个新节目,但是到12月20日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个节目是什么。
昊灵:但是1月1日还是照样出了?
文道:对,还是出了!我们最高纪录据说是一个晚上弄出了一个新节目!凤凰常常处于这样的状态,从我这种香港人的态度看来,是太随便了一点,这其实就显示出来她的领导意志很强。
一个台长说,我决定要怎么样,现在要叭叭叭马上就去,这是很仁智的一种状态,我觉得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可是另一方面,可以讲回对我的自由管理,因为我跟同事不是太熟悉,我只有部分(凤凰人熟悉),评论员我会比较熟,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但是我是从来很优待的:我在外面写东西,他们不管的;我做别的电视台,他们也不管。以我所知,这跟央视的分别很大,因为我知道央视主持人在外边任何东西都非常受限制。
昊灵:似乎是的,据说央视主持人不能拍广告,除非这个广告是公益性质的。
文道:不只广告,他连到外面座谈会做主持也不行的,但是我们完全不管这些事情。
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宽松的部分当然还是跟政治有关的部分。
昊灵:原来您指的是这样的“政治自由”,我本以为您说的是节目上的言论自由。
文道:那个是一点,我觉得是几个层面的。
昊灵:那么对于节目的言论,您是怎么拿捏的?
文道:我不拿捏。节目上的言论可以说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但我们要知道很多人可能节目里面很乖,但是外面可能要干很多什么事。在别的内地的媒体,如果你要搞这些事,你也就会被“冰住”或怎么样。比如说你不能去签《08宪章》这些事情,我都做了,他们也没管我。我觉得这个宽松对我的体验与别人不一样的就在于,不仅言论上没有限制我,更重要的是我个人别的行为上面,她不限制。
昊灵:有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在凤凰,男人直接当畜牲使。您觉得您在凤凰的工作如何,累吗?
文道:我觉得是很累的。在凤凰工作,因为我们的人少,人非常少。当然,这个人少也跟我们某种制度相关,比如说我们节目,你会知道我们大部分节目,除了我们纪录片的节目之外,很多节目是靠主持人带动的,像《一虎一席谈》啊、《锵锵三人行》啊,完全是谈话节目,而这些节目呢,我们走的制度是主持人制,跟央视完全不同。央视是制片人为中心,然后编导,主持人是最后一个亮相出来负责说话的一把喉咙一个声音,但是在凤凰不是这样子的。
所谓主持人制,比如说像我刚刚做的《开卷》(《开卷8分钟》),那完全是我来决定讲什么书,我来决定用什么风格讲,我来决定讲多少东西,什么内容,对不对?我们大部分节目是这样。那不是说我们监制或编导就完全没有权利,不是的,但是我们主持人的主导权更大,特别是在评论节目上面,就更清楚。我们全都是评论员控制,主导它要讲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特殊制度。
只有像我们这样子,什么三更半夜找不到主持人,“你回来帮我们主持个节目”,那些东西是在你主持人脑子里面的,你就容易很快地凑合一个节目出来。
凤凰的特别,在于领导意志式的管理模式
昊灵:不少凤凰人都说自己非常信任刘长乐先生,您觉得他是如何赢得大家信任的,并且能够融合那么多人才的?
文道:我不知道,有吗?看信任是指什么意思。
我不是对他忠心耿耿、为他卖命地工作,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工作。我不见得对凤凰会有多大的忠诚或热情。你给我一个平台,让我能做我的事情,我对这个很满意。
我当然很感激刘长乐的这种宽容,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但是我在这里工作,不是因为他个人,事实上我跟他个人也没什么往来。我在凤凰呆了十年,包括做嘉宾到现在,我跟他吃饭,不是单独,是一大伙那种,恐怕不超过四五次。
昊灵:那您以一个员工,或者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刘长乐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领导?
文道:这有一个变化过程,以前曾经有一段时期,他是一个比较注重个人的(领导风格)。
昊灵:您是指他让每个人张扬其自己的个性?
文道:对!那会儿他和大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就是凤凰草创时期,十年前,我刚来的时候到七八年前,那时候凤凰规模很小。规模小的时候,中间没有那么多管理人员,上下关系很紧密。很紧密的时候,他会时常亲自对许多节目发出他的指示、他的看法。
昊灵:那刘长乐先生对您有没有什么指示?
文道:没有。因为我当时做《锵锵三人行》或是做别的一些串场节目,他不见得有什么指示,但是他会聊,但具体聊些什么我忘了。他会有很多意见,然后呢,他会常常就一些管理问题,行政问题写一些指示出来,然后会张贴出来。那写这些东西就很中国嘛,中国领导人很喜欢写一些这样的……
昊灵: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些指示是他亲笔书写的,还是打印出来的?
文道:字打出来的,但他会签名。就那种:大家要注意怎么样,精神上要怎么样……这些东西,那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了,写东西的情况少了,直接跟前线对话的情况也少了,因为整个公司庞大了,中间管理队伍增强了。
昊灵:所以老师您所指的变化具体是由密切亲近到现在的相对疏离?
文道:应该说一开始管理是很直接的,比较建立在似乎想要做朋友的那种感觉,他跟某些主持人,在我看来像是很朋友的交往方法。到后来就是有距离了,我的感觉是,整个公司在制度化,因为早年比较没有制度化,比较像一个大家出来打江山的一个团队的感觉。现在整个公司变得很大,当然行政管理要制度要严明了,它就比较不再依赖一种个人的魅力、个人跟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来维持。
昊灵:那凤凰的这种制度化与一般其他公司的制度化有什么区别吗?
文道:没什么区别,还不太完整吧。在我看来,她在香港是很特别的一个媒体机构。因为一般香港的媒体机构会制度化得完整一些,整个流程、程序是很清晰的,那凤凰是有这些流程、有程序的,但是问题是她仍然保留了一种领导意志式的、个人指挥的这种管理模式。
把屏幕关掉,你可以把凤凰的节目当收音机来听
昊灵:文道老师可以算是亲历或见证凤凰整个崛起的过程,您觉得凤凰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文道:我想是利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给予她的空隙,然后在这个空隙底下把握好,这个空隙当然就是在中国的媒体普遍不可能像凤凰这么宽松自由的时候,给了她这么一个口,这个口使得她能够掌握好这个机会,提供了这个口最适合提供的节目。
比如说,凤凰不会去做湖南卫视式的娱乐节目,那正是因为……(娱乐不是凤凰擅长的),所谓的不擅长,其实是一个选择,不一定是不擅长,一开始是一个选择,不需要走娱乐路线的,因为你掌握了这样一个难得的空间和机会,你跑去做娱乐就浪费了。
昊灵:但是凤凰一开台时的中文台主打“城市青年台”的定位,难道不是偏娱乐的吗?
文道:也不是,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的娱乐,她要有娱乐元素,但她仍然注重资讯、谈话这样的一种感觉,只不过越到后来这个路线就越鲜明,整个娱乐的因素就被压缩。
昊灵:相对的,现在凤凰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
文道: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依赖这个外在的条件了。假如有一天,这个外在条件被收缩得很紧……比方说现在可能能感觉到,因为凤凰现在的影响力比以前大了,认知度比以前高了,就被当局注意得越来越多了,那么你就很容易受到限制,你如果受到限制的话,就不会跟别的电视台、内地电视台有太大的分别了。
又或者反过来讲,非常理想化的,假如有一天,全中国的媒体都放开了,那么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分别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你怎么样?假设大家都受限制,假设大家都开放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赢下去呢?怎么样走出你自己的特色,能够生存下去?
从我做节目人来看,要有一个很强的节目制作能力,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凤凰正在琢磨转型的东西。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凤凰是一个主持人制度,凤凰大多数节目都是谈话节目,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你把我们屏幕关掉,你可以把我们凤凰的节目当收音机来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么依赖一个主持人的声音,或者是这种说话的节目来带动的话,它就会有危机,那么你必须要转向成更有节目制作能力的那种公司。
我觉得现在的凤凰也已经在转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比如《凤凰大视野》啊等专题节目,或者像《冷暖人生》、《中国江河水》,我觉得这种节目是比较扎实的,是比较容易长远。
我不是说我们这些主持人、评论员不重要,而是说你不能过分倚重这些前台的人,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
昊灵:所以,您觉得凤凰以后的长远发展重点是要将节目做得更电视化?
文道:更电视化,然后更掌握到一个在现有的自由空间下,尽量把它利用到底……那么去建立一个品牌。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品牌形象了,否则将来如果媒体越来越开放的话,你的竞争优势、相对优势就会减少。
有时候我觉得凤凰的节目太过注重品牌营销多于节目制作的能力,这也是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最明显是我们新闻节目。现在好转了一些,我记得有一阵子,我觉得我们的新闻节目是出问题的!
昊灵:是哪一阵子呢?
文道:我不太记得了。我举一个例子,凤凰很喜欢标榜自己“9.11直播”,或者是“俄罗斯车臣人质危机”我们怎么深入现场、到第一线。在我看来,我们标榜一种英雄式的新闻观,就是我们的记者比谁都勇敢,像闾丘(闾丘露薇),她在巴格达不愿撤出来。我当然认为这是很英勇的行为,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只把这些当成是你唯一的招牌!
第一,这种情况、“9.11”这种情况不会每年都发生的。
第二,这不是个日常新闻的状态,日常新闻的把握恐怕比这种时候更重要。就不能说“有大事我存在”,我们常标榜这一点。然后你标榜这一点的同时连带一个问题,“有大事你存在”,会不会有一天,大家放得越来越开,比如说央视改革,最明显的一点,如果今天发生“9.11”,央视绝对不会晚一天再播,因为整个尺度变了嘛,它绝对跟得上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第三,一个新闻团队的能力,其实我们的综合能力不一定比得上别人。当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看到,你不一定比得上人家,比如说“汶川地震”就很明显,凤凰的优势就不见了,凤凰的优势只是在于海外,而这个优势将来会被赶过;凤凰第二个优势,是懂得做品牌效应,懂得宣传自我,懂得说我们记者多厉害,有时候“有大事我存在”这个说法说着说着就会变成注重“我存在”多过于那件“大事”,这是我常常批评的,其实很多新闻媒体都容易犯这种错误。风灾水灾,总是要让自己的记者站在雨里面,几乎是要被吹走,或者被吹得飞起来一样,用这个来显示你们电视台冒险患难的精神。
昊灵:这样做是不是想要达到一种电视的效果?
文道:不是,它要展示我们多厉害,那是一个英雄主义!你到底关心的是那个风灾对当地居民的危害多大,还是想让别人看到你在表演你有多勇敢跟你所谓的专业精神呢?我觉得这个界限要掌握得很清楚。而凤凰有一阵子,我觉得在这上面是有些迷失的,大家太过于鼓吹那种我叫做是“英雄式新闻观”的做法。
采访时间:200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梁文道办公室
【采访小札】
我面对的是一个太过丰富的人,丰富到我几乎要焦虑地将我们独处聊天的近半小时全部用作思考,都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来“挖掘”这相隔仅一张桌子、一点架子都没有的香港公共知识分子。
幸好当时的菜鸟学生对“梁文道的丰富”认识不深,也幸好当时有个重要的任务、明确的主题,于是化解了本该形成的局促不安,没有让手足无措的尴尬场景成为现实。
在评论员办公室外的吧台前,我碰到了前来泡咖啡的道长,无知者无畏地请他给我些许时间谈谈他眼中的凤凰,他欣然跟我约定两天后的午后,并应我要求二话不说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了我随身携带的本子上。
那天,刚录完节目的梁文道如约而至,由于晚上要赶着跟“老窦”[1]吃晚饭,抱歉地说“时间不多”,我当然不能妨碍孝顺儿子与老爸的约会,没有寒暄没有铺垫,访谈即刻切入正题。

作者与梁文道
我们的交流不断地被打断,期间四人先后“冲进”他的办公室,他也迅速接了三通电话,几乎都以“依家唔得闲”[2]、“约佐老窦”[3]来推脱婉拒,更有迪拜“粉丝”远道而来,只为与偶像见个面、拍个照,梁文道的繁忙生活可见一斑。
即便不胜其扰,却也客气有礼的道长更能立刻转换角色,接着先前的话题继续侃侃而谈,顺畅到不留一丝被打断过的痕迹,这着实是个令人佩服的“技能”。
油画界的作家陈丹青也是个言辞犀利的评论家,他曾定义这个同样光头、同样架着眼镜的同行是个“学贯中西、集两岸三地视野一体的文化人”。在台湾与香港教育的交错浸润下,梁文道的思想颇为辩证、严谨,“比较”是个在其谈吐间频繁出现的词汇;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道长用堪比最后一次卷烟[4]的认真态度思考,回答得随意却到位,那种信手拈来的一针见血绝对是时时处于思考状态的自然流露。
当年,刚加盟《锵锵三人行》的梁文道被节目“土著”窦文涛嫌弃“长得那个样子,怎么能上电视?”而现在,梁文道已在电视上游刃有余,不少人更习惯梁文道的《开卷》,梁文道的《锵锵》,他也乐于自谦“只是个电视人”。
访谈完毕的我恢复“粉丝”本性,要求合影,道长大气应允,又一次站到相机镜头前摆出招牌的内敛笑容。事后我才知道,看重自由的他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有一点点造作、硬要把姿态定格”的拍照。
【注释】
[1]粤语,意为“老爸”。
[2]粤语,意为“现在没空”。
[3]粤语,意为“约了老爸”。
[4]由马家辉所著的《伤城:梁文道,和我的香烟》一文是“最后一次卷烟”的出处,有兴趣的可自行“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