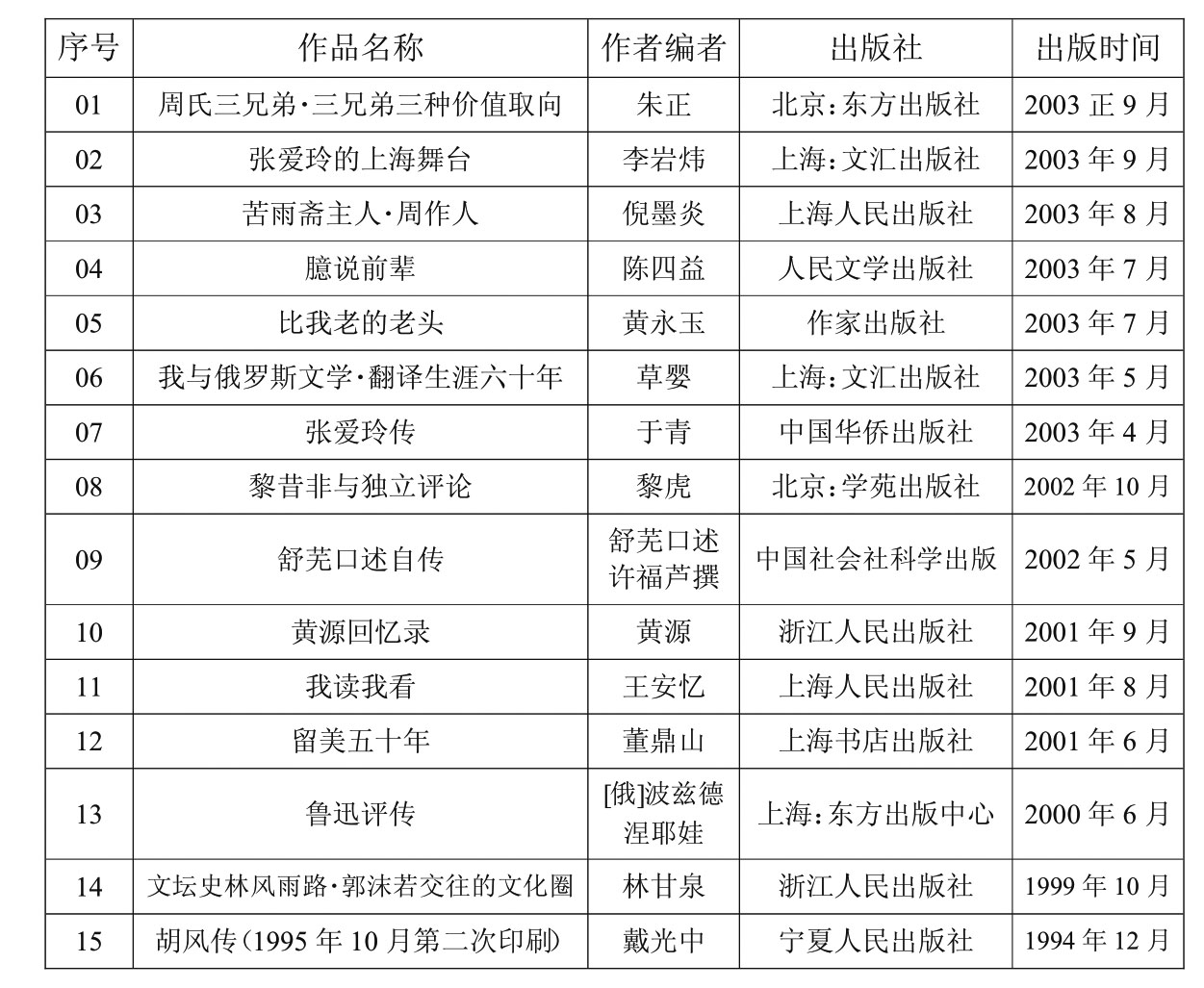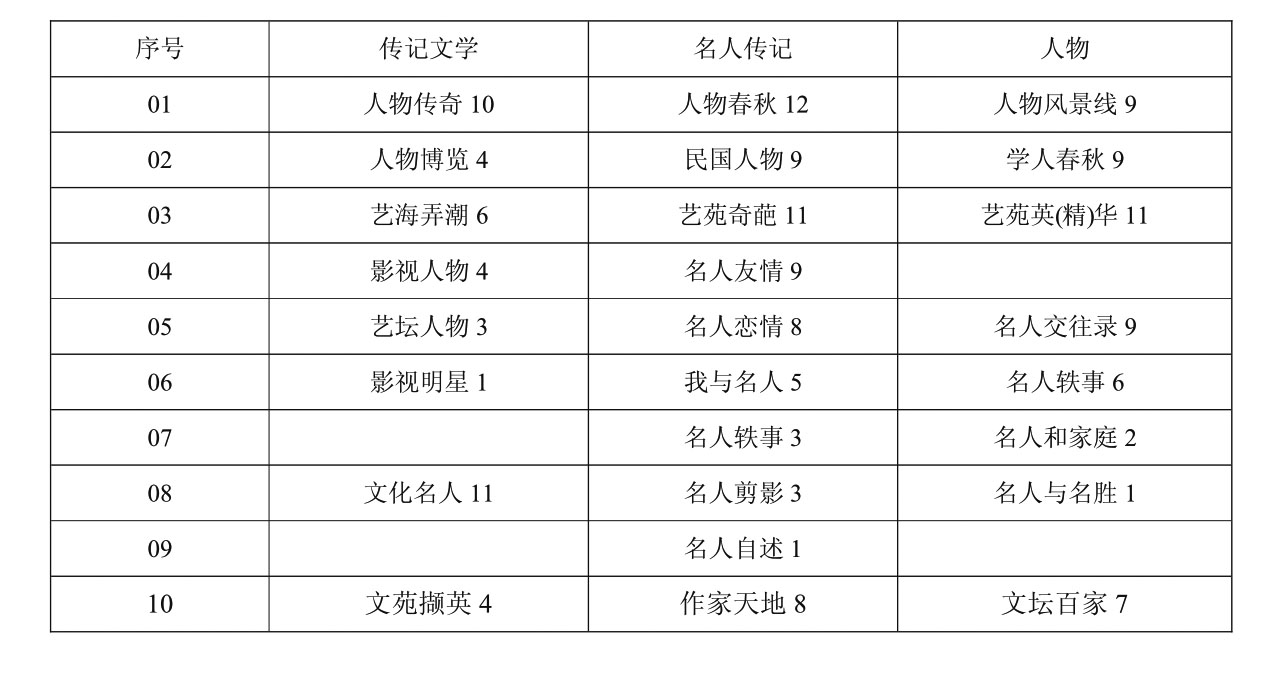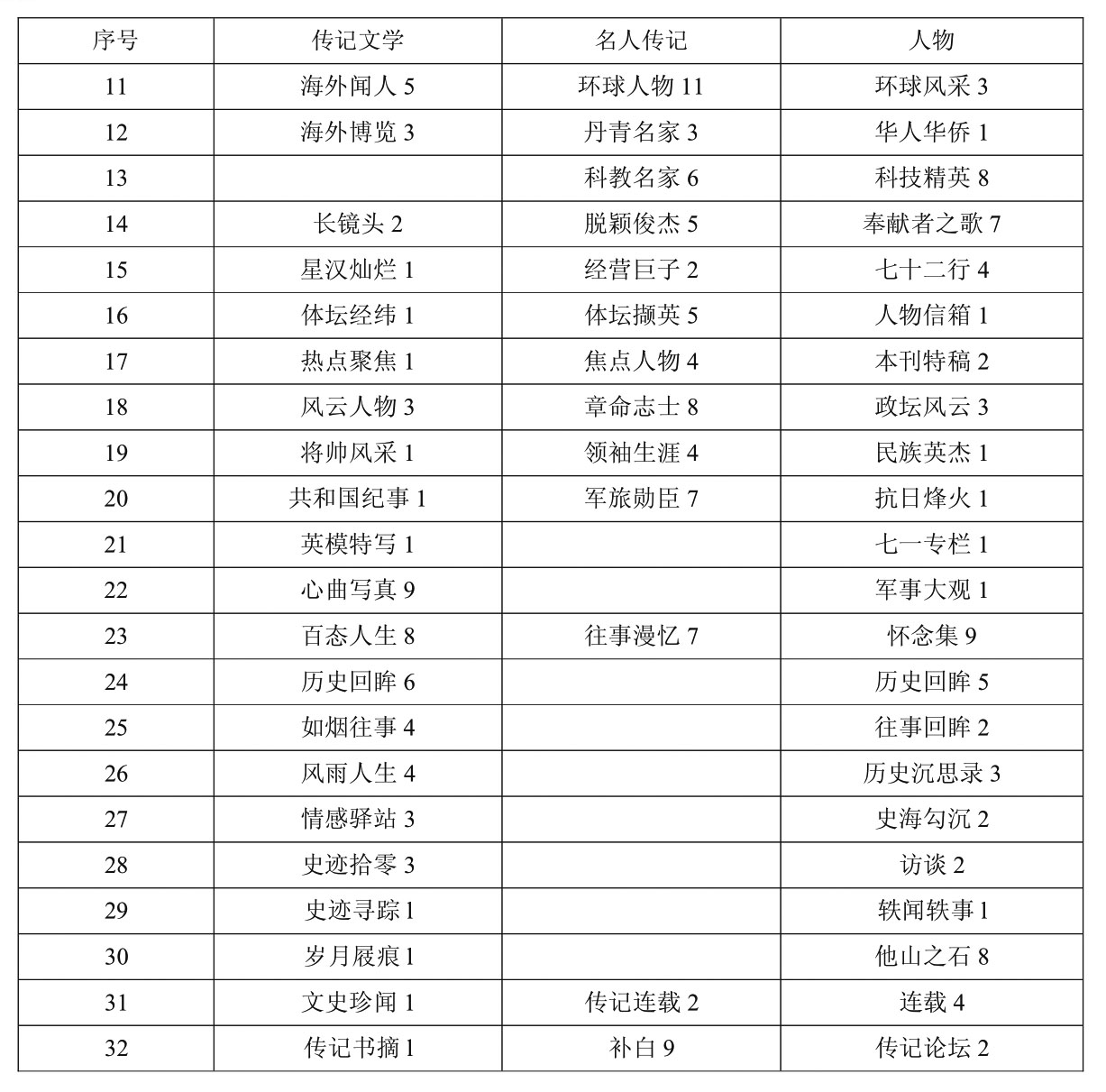-
1.1序
-
1.2第一章 思潮与文体
-
1.2.1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范畴及其流变
-
1.2.2论散文的神质
-
1.2.3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和批评要求
-
1.2.4诗人性情和文学的意义(A稿)——兼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
1.2.5诗人性情和文学的主体性关照——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讨论
-
1.2.6走过现场:当代诗歌的文化批判
-
1.2.7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和自由写作
-
1.2.8不老的诗情:台湾文学的三维透视——20世纪台湾文学的一种历史考察
-
1.3第二章 鲁迅研究
-
1.3.1近代中国与鲁迅的文化选择
-
1.3.2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历史文化寻绎
-
1.3.3《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其叙事结构
-
1.4第三章 郭沫若研究
-
1.4.1诗人郭沫若政治情怀和社会理想的人性阐释
-
1.4.2倡导之功 创造之力——五四白话新诗的发生和奠基
-
1.4.3一个田园牧歌的小品文时代——散论郭沫若20年代文艺性散文
-
1.4.4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探微
-
1.4.5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
1.4.6心底温情写郭老 笔墨轻盈语谨慎——漫评《20世纪文学泰斗——郭沫若》一书
-
1.5第四章 “京派”文学
-
1.5.1“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
-
1.5.2“京派”作家的审美精神
-
1.5.3从废名到《大年》:文学的审美与批评
-
1.5.4论汪曾祺小说艺术的和谐美
-
1.6第五章 当代作家与文本细读
-
1.6.1展现生命诗意和大地浪漫的文学——张炜小说创作述评
-
1.6.2张炜《古船》社会影响的再批评解读
-
1.6.3从生活的细微处发掘文学意义的人——赵德发的短篇小说和他2003年的新作评述
-
1.6.4语言的艺术写意与绘画——贾平凹散文《邻院的少妇》赏析
-
1.6.5叙述的策略、简洁和内在力量——浅议余华小说特色
-
1.6.6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
1.6.7《玉米》的人称及其叙述态度、叙事情感
-
1.6.8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
-
1.6.9当代文学的最新阅读与批评——杨少衡“官场小说”的叙事批评
-
1.7第六章 西部文学与地域特色
-
1.7.1陕军东征与世纪末文学哗变
-
1.7.22006年宁夏文学阅读札记三篇(另附旧稿一篇)
-
1.7.2.1乡土文学的朴实文本:《村庄的语言》
-
1.7.2.2小说追求的叙事意义:《一人一个天堂》
-
1.7.2.3新锐作家的独特故事:《去尕楞的路上》
-
1.7.2.4附:老作家马知遥先生速写
-
1.7.3精致而独特的小说叙事——石舒清《果院》的批评阅读
-
1.7.4悲郁乡土的叙事与解构——从《村庄的语言》再谈宁夏乡土文学
-
1.7.5贴近文本的心灵探险——陈继明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讨论纪实
-
1.7.6文学,源自心灵的诗意与美好——与郭文斌对谈《点灯时分》
-
1.7.7坚守自我与乡土,追求心灵的写作——《黄河文学》首届签约作者专辑总评
-
1.7.8后 记
1
雕虫问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