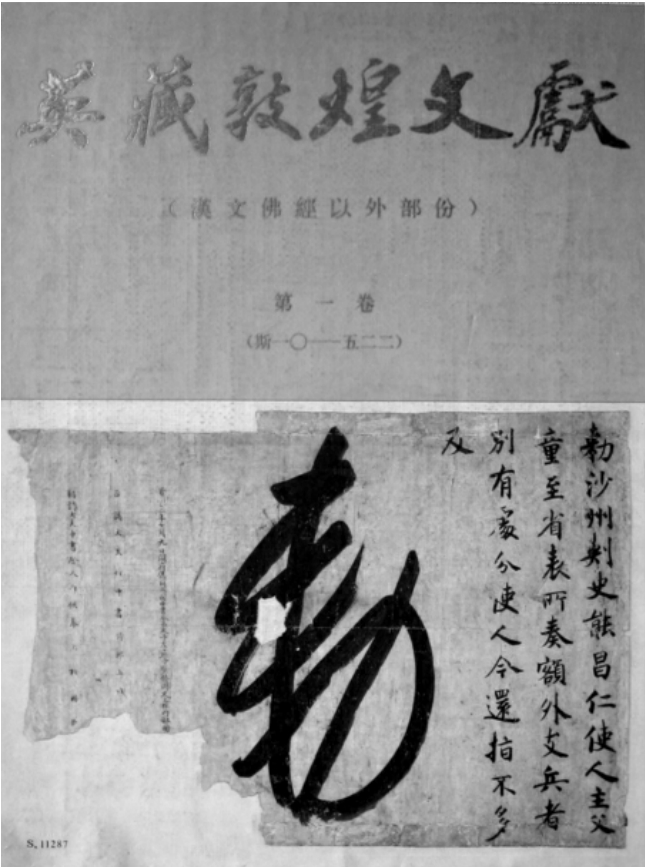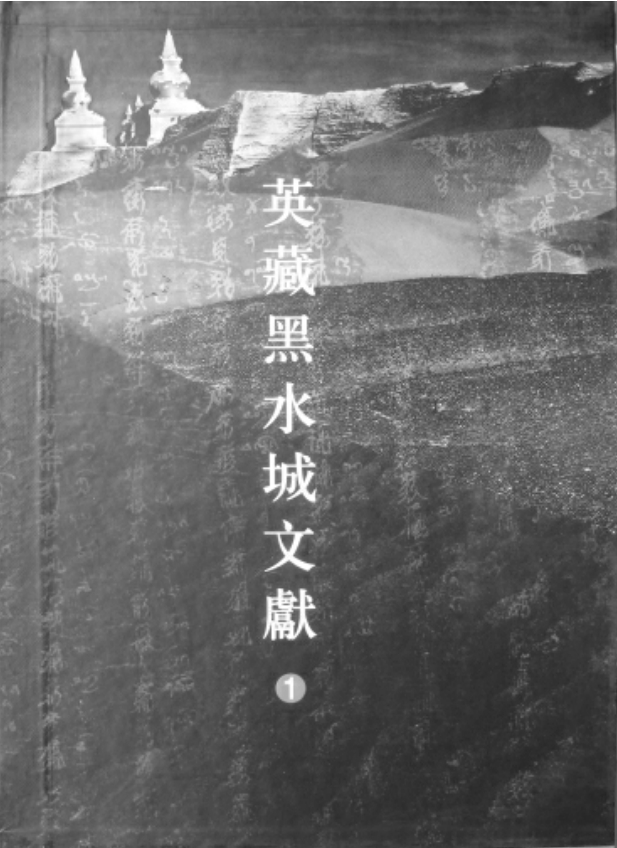三、斯坦因的收获与英藏敦煌文书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实惠与极高的声誉。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发现者金质勋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则给他一笔巨额的现金以祝贺他的成就;在布达佩斯,他被奉为立了大功的好儿子。当他重访“故里”时,布达佩斯沸腾起来,“午餐、宴会,还有晚餐应接不暇”。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并且成为“亚平宁俱乐部”的成员。1909年8月10日,他给艾伦写信说:“听说,与我同获此殊荣的有12个人,其中包括约瑟夫·胡克尔爵士(皇家植物园创始人)、南森(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人道主义者)、杨哈思本、柯曾等,全都是些令我望尘莫及的名字。”(43)另外,还使他高兴的是,那个为他帮了大忙,对盗劫敦煌文物立了殊勋的蒋师爷——蒋孝琬,也由于斯坦因的积极推荐,得到了他本人所渴望得到的奖励,当上了喀什英国领事馆的汉文秘书。

斯坦因(摄于1929年)
当然,对斯坦因来说,最高兴的是终于加入了英国国籍,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最使他高兴和出乎意料的是得到了官方的承认:1910年6月斯坦因被授予“印度帝国骑士”称号。咨勋局专门给他发了通知,并说明了在皇家觐见厅接受陛下封爵时的礼仪、穿戴等问题。斯坦因绝对没有想到,在中国敦煌所窃得的宝藏,会把他带进皇家觐见厅参加崇高、庄严的受封仪式。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得到了欧洲学术界的极力赞扬。中亚细亚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教授曾经把把斯坦因称作是“他的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铀元素的发现者伦纳德·伍利爵士把斯坦因在中国西北的探险,说成是“一个考古学家对古老世界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胆和最冒险的突击”。(44)并说斯坦因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45)

身着出席授勋仪式的斯坦因
然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对斯坦因的劫夺,却有正确的看法,并表示极大的愤慨。早在1935年,英国埃里克·泰克曼爵士就在其《土耳其斯坦旅行记》一书中说:“运输队把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我国新疆地区)的寺院、石窟、坟墓和废墟中的无价之宝,一批一批地运往外国的博物馆,从而使中国永远地失去了这些珍宝。对此,中国人无不怨声载道,而外国人也无法加以否认。”(46)英国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对于斯坦因的劫夺,“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无异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行为”。并说要了解中国人民对敦煌遗书被盗的情感,其“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使一个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内,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47)
众所周知,敦煌遗书发现不久,甘肃学政叶昌炽就建议当局全部运到兰州保管。后因运费无力筹措,才于1904年命令敦煌县府先行检封,并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从法理上说,从那时开始,这批文物已是中国政府的财产,王道士是无权出卖的。斯坦因若不知底细,误买了,乃是买了赃物,事发之后,仍应交出。何况斯坦因不仅明了王道士无权卖,实际上根本是他和蒋孝琬‘说服’王道士演出这幕‘监守自盗’的”。(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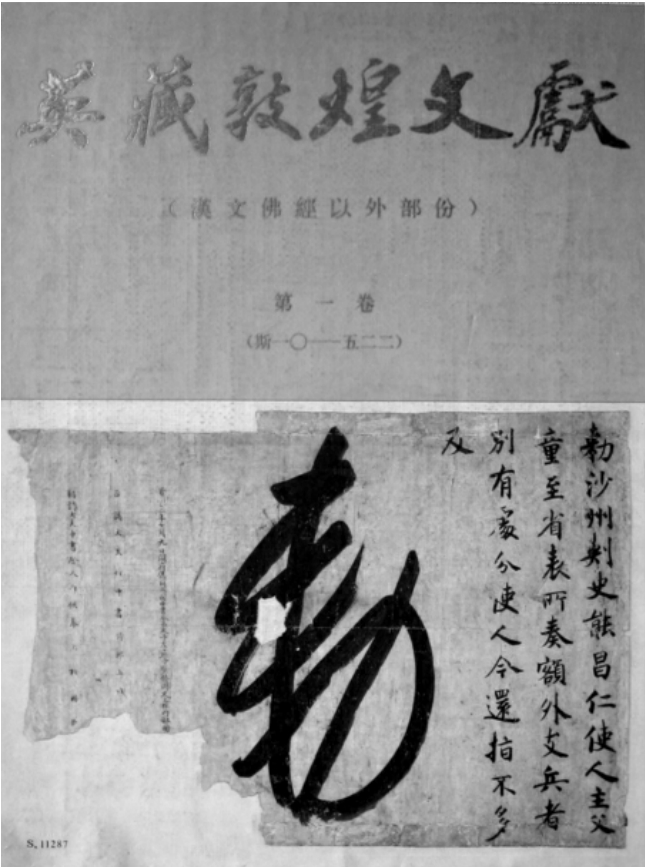
《英藏敦煌文献》封面
当然,斯坦因是付了一些钱,但并非是他自称的那样“公平”,因为他只付了200两银子。斯坦因明白,这是低得近乎荒谬的价钱。在把东西运抵安西后,他就得意地给朋友写信说,这批文物只花了130英镑,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和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49)
斯坦因在中国所窃去的全部收藏品,按照资助他的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之间在其出发前所签署的分配方案,写本部分,凡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和回鹘文书写者,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用于阗文、龟兹文、藏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书写者归前者,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后者。其他发现品如钱币、绘画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但斯坦因回国后却改变了分配办法:为了研究方便,文书部分归大英博物馆收藏,印度方面只取若干样品;图画部分归印度博物馆所有,大英博物馆只取若干作样品。据有的学者检视两地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窃文物,“发觉大英博物馆所谓的留取若干,实际上是尽取菁华;印度博物馆的留取若干,则无论质量,都无足轻重”。(50)1973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英国博物馆分立,保存在原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中的斯坦因所获文献,移入了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楼保存。
关于英国所藏敦煌遗书,长时间不知其详细情况和数量。因为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刚开始编号时,仅仅按照语言和出土地点大体上作了一些归类,就被编为Or·8210~8212三个总号之中。Or·8210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后来就缩写为S。1954年,英国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将所藏敦煌卷子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这套胶卷共收录了6980个卷子,即S·1~6980号,它不仅未包括古藏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的卷子,就是汉文卷子也是不完全的。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就是我国学者刘铭恕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新收到的缩微胶卷编制的。当时还有2000多件没有编目。1957年翟理斯编成了《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该目录共收录了8102个敦煌汉文卷子,但并没有完全反映英国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的收藏情况。近年来,英国图书馆修复部又陆续从敦煌绢画、写经、经帙等已编号文物或文献上揭出许多残片,在总编号后顺序增加,目前已编到13677号。(51)S·1~13677号敦煌写本,不论长短,一纸一号。从总体上看,S·6980号以前的写本比较完整,有不少长达10米以上者,缩微胶卷和台湾黄永武先生编的《敦煌宝藏》已将它们全部收录。而S·6981号以后的写本,主要揭自经帙或绢画,残片较多,大多数为一两尺长,还有许多只有巴掌大小,因此在一个号下,各残片又细分为A、B、C等。如S·6998A,S·6998B等。
1991年,英国图书馆邀请北京大学荣新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锠赴伦敦进行S·6981~13677号的编目工作,由荣新江负责非佛教文献,方广锠负责佛教文献。其中荣新江所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一书,已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4年7月出版。由于荣新江先生学识渊博,尤精于敦煌文献,故该书是目前敦煌文献目录方面比较适用、权威的一部工具书。该目录除标题外,还包括对写本外观、内容、专有名词、题记、朱笔、印鉴、杂写、年代及与其他写本关联情况的提要,凡能找到的有关该号写本研究的文献和图版,亦作了著录说明。
为了使英藏敦煌文献早日公布,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共同编辑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英藏敦煌文献》共15卷,收录了S·1~13677号中所有的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由于图版是根据原卷拍照的底片制成,较为清晰。该书自1990年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了14卷,最后一卷是目录索引等,正在出版之中。
Or·8211/1~3326号主要是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所获文献,但也有一部分是第二次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等。这一组文献,除了Or·8211/1~3326号这种博物馆编号外,还有斯坦因根据文书来源而标的原始编号,如T·编号指在敦煌长城烽燧所获汉简,N·表示尼雅出土佉卢文文书,M·T表示麻扎塔格出土文献,L·A或L·B指楼兰遗址所获文献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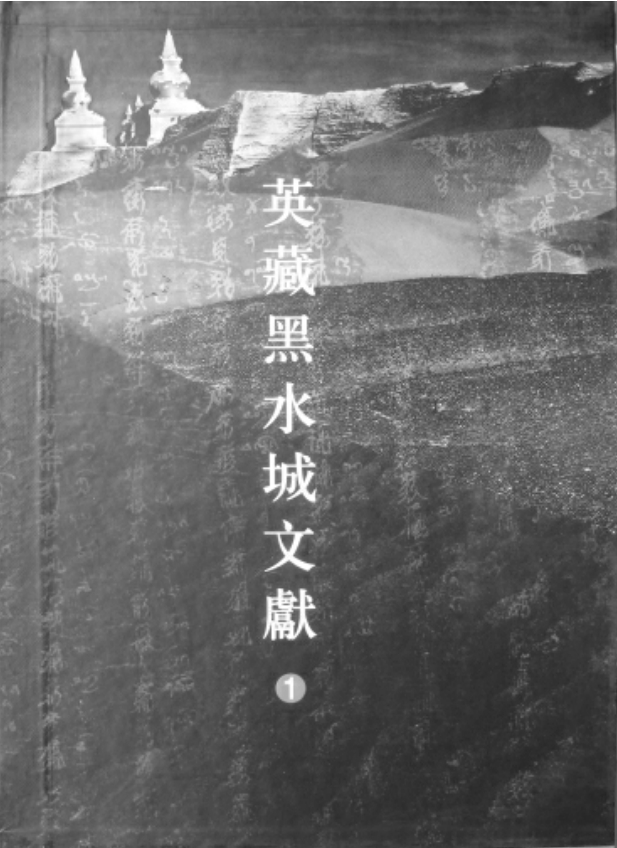
《英藏黑水城文献》封面
Or·8212/1~195是民族语言或民族语言文字混在一起的文书,其中有梵文、佉卢文、藏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突厥文、回鹘文和汉文,出土地点则有敦煌藏经洞、敦煌长城烽燧、吐鲁番、和阗等地。Or·8212/196~199为予留空号,迄今未用。Or·8212/200~855是木简或纸本汉文文书。Or·8212/856以下,是汉文或其他语言文字残片。
如前所述,根据斯坦因考察前提供经费的多少而签订的协议,其中一部分文献文物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有。该馆原是英国占领印度后,由东印度公司设立的,1947年印度独立后,便归英联邦对外关系部所属,后来又划归英国图书馆参考部管理。1991年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合并为东方与印度事务收集品部。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梵文、于阗文、藏文、吐火罗文等语言文书,大多收藏在这里,其中包括敦煌藏经洞文书,如斯坦因所获敦煌藏文文书的大部分就收藏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斯坦因所劫夺的敦煌文物,主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早在1921年,斯坦因就选取了其中的精美绢画48幅,编成《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在伦敦出版。后来,韦陀对英国博物馆所藏美术品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选取了其中的精品,编成三卷《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于1982年至1984年由英国博物馆和日本讲谈社用英、日两种文本在东京联合出版。
敦煌文物与文献一样,都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绢画上的题记、纸画旁边或背面的文字,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们应当将他们与藏经洞遗书一样对待,给予应有的重视。
【注释】
(1)加兰·坎在《东方仲斯》第141页,伦敦亚洲出版社1964年版,转引自(英)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2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2)转引自《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第61页。
(3)转引自《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第62页。
(4)转引自《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第63页。
(5)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84~85页。
(6)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89页。
(7)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18页。
(8)参阅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第37页~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9)参阅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第30页~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0)参阅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第56页~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11)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阗废墟记》第306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12)《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7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联合出版。
(13)转引自(英)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11页。
(14)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18页~219页。
(15)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16)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64页。
(17)《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2页。
(18)《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2页。
(19)《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3页。
(20)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68页。
(21)《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4页。
(22)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70页。
(23)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72页。
(24)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25)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72页。
(2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7页。
(27)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77页。
(28)《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8页。
(29)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79页。
(30)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31)《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87页。
(32)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88页。
(33)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91页~292页。
(34)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95页~296页。
(35)见《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97页。
(36)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298页。
(37)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300页。
(38)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305页。
(39)《外交部卷(1909年6月,81号~87号)》,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326页。
(40)斯坦因著、王竹书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号。
(41)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366页。
(42)《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9页。
(43)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333页。
(44)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6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5)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6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6)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作者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7)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7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8)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载台湾《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
(49)1906年4月14日斯坦因致艾伦函,参阅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50)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载台湾《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
(51)关于英藏敦煌文献文物的编目、收藏情况,详见荣新江先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一章“英国收藏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