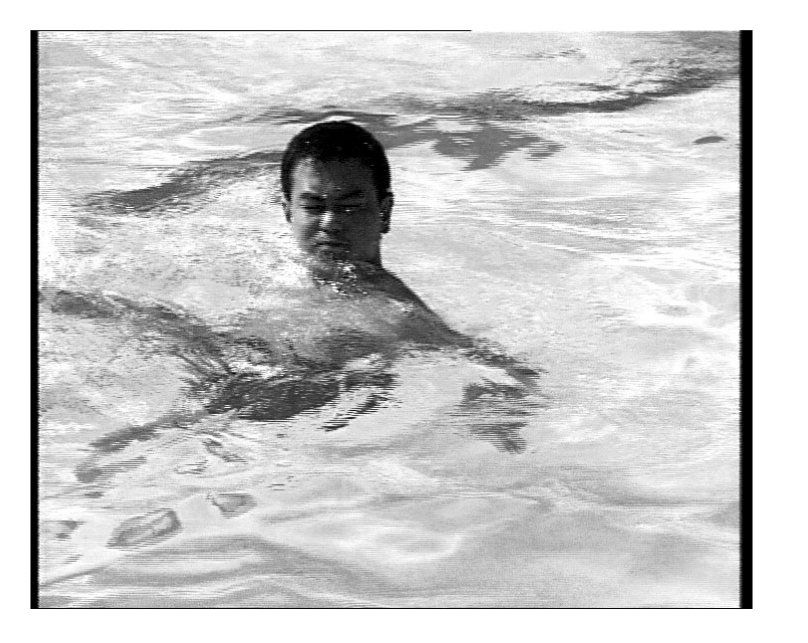《梦游》:弥散着荒诞的世像——纪录片编导黄文海访谈(1)
片名:《梦游》(Dream walking)
片长:86分钟
类型:人文类纪录片
编导/摄影/剪辑:黄文海(使用摄像机型:SONY PD100AP)
拍摄时间:2004年夏天
出品时间:2005年
参赛纪录:《梦游》入围2006年1月“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的国际竞赛单元;2006年3月获“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大奖”(Grand Prix Cinema du Reel——刘洁补述)
《喧哗的尘土》入围2004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奖”竞赛单元;2005年获法国“马赛国际电影节”国际纪录片竞赛单元“乔治·波格尔”奖等。
梗概:2004年夏天,行为艺术家李娃克从北京来到南阳,帮助画家王永平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在拍片期间,这些艺术家们常在一起谈论着艺术、宗教、人生……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形成了极大的落差。“魔头贝贝”在网络上被评为“天才诗人”,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却是个“看门人”……丁德福如今很少作画,在家庭、学校、情人的世俗纠葛中沉浮着,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李娃克随时利用空闲做着自己的行为艺术,有时他给小女孩的脚化妆,然后将身上穿的寿衣剪下一块来包裹着那只化了妆的脚,有时他在聚会时赤身裸体地倒立着,反复地表达着他的生存感受——“无聊”……剧组没钱,管理散乱,拍摄时断时续,王永平深深地陷入了焦虑之中……强烈的幻灭感,使他们滋生出了一种“人类的良知”,在看似荒诞的行为里,凸显着的却是一种本质的真诚、一种活着的努力。虽然他们把自己放逐到了人们的记忆之外。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梦正长。

图21 纪录片编导黄文海
【访谈背景】
我是缘着纪录片《喧哗的尘土》找到黄文海的。吸引我关注的,倒还不仅仅是这部片子连续在国际、国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而是从《喧哗的尘土》中透射出创作者的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实质。待到我们见面时,黄文海已经完成了他的新作——纪录片《梦游》,我们的交谈便自然从《梦游》出发了。
在黑白视像中,《梦游》从始至终都有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诗人“魔头贝贝”说:写诗就是畜生做梦。“弦月挂在星空里。/霜打的荷叶,像舌头伸出水面。/假戏成真,一晃十年。”……他们近乎癫狂地活着,喝酒、打牌、和小姐嘻戏;他们谈论艺术、宗教、人生……一种难以名状、却深入骨髓的落寞与无聊弥散出了屏幕的画框……混沌而粗痞,荒诞中透着真诚。第一次看完《梦游》,除了感觉怪异、混乱、污浊之外,好像没有太多印象,可是却有了一种从此“放不下”的感觉。而总会去想:是他们“病”了,还是我们“病”了!是现实把这些艺术家挤压到了主流艺术的边缘(或者说是主流艺术的底层),使他们的精神状态显得那么无着、那么虚无、那么可笑?还是我们随着物欲的膨胀,放弃了我们本来就该拥有的精神现实?!
这种思辨的力量,是《喧哗的尘土》的余绪,它超越了《梦游》本身的表达,甚至超越了与黄文海同时代生人通常所拥有的生活态度、知识结构和审美取向。
上世纪70年代初,黄文海出生在湖南。大学期间,他学习过绘画艺术,毕业后从事过图片摄影工作。1995年,黄文海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学习。一年后,进修结业,黄文海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打工,出任过记者和编导等职,其间他也开始拍摄纪录片。四年后,黄文海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成了一个独立的制作人。他说“纪录片就像体验生命的镜子,我在纪录片中寻找自己。所以我一直庆幸2000年时我能从中央台跳出来,走向纪录片。因为,在电视台只有体制和模式,而没有自己。”
从《大河沿》、《北京郊区》、《军训营纪事》到《喧哗的尘土》,黄文海不断地寻找着自我。无疑,《梦游》正是他体验生命的又一个过程。
受访者:黄文海 纪录片编导 独立制作人
访问者:刘 洁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传播学院 博士生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2)
时 间:2006年1月11日
地 点:北京通州天赐良园

图22 黄文海与刘洁访谈照
关注,其实是彼此的相遇
刘 为了更简单地感受《梦游》,少受点影响,我事先没有看你给我的简介和导演阐述,而是约了两个朋友一起来看片子。说实话,刚看到第一个镜头,我们三人都感觉有些懵……
黄 呵呵。
刘 一个杯盘狼藉的场景中,三个赤裸的男人,两人闲坐喝酒,一人弹着吉他曲《爱的罗曼史》……他们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但看着、看着我就回想起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对这几个游离于当代“艺术圈”之外的“非艺术家”(自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并不陌生。我有不少朋友,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受“’85新潮”的影响,大搞装置、架上、行为、观念摄影等现代艺术的活跃人物。
但我不熟悉的是当年这些充满着激情和思索的人,这些曾经凭着各自的作品在90年代获得不小的荣誉的人,“活”到了今天的生存状态。
黄 《梦游》就是纪录这种状态的。
刘 从片子里,感觉得出你跟李娃克他们有很好的交融,沟通得特别好,你们以前就认识吗?
黄 对。我跟李娃克是在2001年偶然认识的。当时,我作为制片人,正在拍一个16毫米的电影《北京郊区》,讲述的就是艺术家的故事。那时,娃克作为导演,也在拍他的一个片子,叫作《缝》。
刘 但认识和关注,是两回事。你怎么会有兴趣去关注这样一群人?
黄 我不太想用“关注”这个词来说我的片子。比如,以前在拍《喧哗的尘土》时,别人会说我在关注社会底层的人,在关注农村、关注小城镇的人,到了《梦游》就说我在关注艺术家。其实,不是我在拍它(指片子),而是它在拍我,是我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遇见了它,彼此相识一段时间后,又各自开始着自己的旅程。你可能觉得我很唯心,但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这句话能更清楚地表达出我的真实想法。
刘 说得很好,这种相遇正好是一种内心的应和。
黄 我感觉,每做完一部片子,实际上就等于把过去的生活打了个结,这时你才能看得很清楚,才能对这段经历认识得比较清楚。有朋友问我,拍纪录片又不能为我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还能够拍下去吗?我想,可以。我觉得,拍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修行有很多“法门”,可能拍纪录片就是我修行悟道的一个最好的“法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应该拍下去。
这种感悟的获得,最早是在拍《军训营纪事》的时候。当时我吓了一跳,我拍的这些孩子们的生活、老师和学生的那种关系,简直就是我初中生活的搬演!我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会形成像我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自觉地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了。其实,拍片子有两个过程,一个就是在拍摄中能够很直觉地去拍,另外就是在剪辑台上对这些素材能够进行反思、揉捏和组织。在剪辑台上,你的意识、你的反思的自觉性可能会更强。
刘 悟道之后,自然明白:无论拍片、写作、赋诗、作画等等,从来表达的都是“自我”。后来,你又怎么介入到李娃克他们的拍片活动里的?
黄 李娃克挺有名气的,他做过“寿衣的行为”,影响比较大。他年纪比我大,是50年代末出生的。我是80年代后期才开始学艺术的,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2004年的5月份,“现象工作室”朱日坤他们搞了一个纪录片展,李娃克和我同时被邀请,我们再次相遇了。娃克说他正准备去南阳,一个画家朋友王永平要拍部片子,他去当摄像。我当即就感到这里面肯定很有意思,那时我正好有时间,也有点儿钱,就决定7月份跟着他去拍个片子,我们一拍即合。后来,这个片子拍得很快,一个多月吧,就拍完了。
刘 在《喧哗的尘土》里,一群小镇上的普通人在这“拜金”、“拜物”的时代里,面对着物质的匮乏、责任的沦丧、伦理的淡漠,而“无路可走”,他们打麻将、通过收看“天线宝宝”来买地下六合彩、推卸着未婚先孕的责任……你纪录了中国一些普通人“活着”的一种状态;而在《梦游》里,你好像更加逼近一种“心灵”的状态、一种精神的状态?
黄 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执着特别像《喧哗的尘土》中买六合彩的那种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教育,其实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在一元化价值标准之下,你以为你在追求艺术啊,追求什么的,其实你是功利的,但是你当时不自知。现在,艺术家的成功似乎是在金钱上的成功,如果不是这样,别人会认为你是疯子或者是傻子。拍完了《喧哗的尘土》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跟他们一样,也经历着一个很大的幻灭,我那时其实也挺彷徨的。虽然我对《喧哗的尘土》里的人们很同情、很怜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在我看来,人应该有一种自我拯救的力量,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2000年,在我29岁的时候,我“遇见”了高行健的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那本书直接促使我从中央台出来。当时我看了那本书以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觉得自己还“有戏”。因为我那时已经很颓废了,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灰色的中年男人的感觉。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后,我成了一个独立的制作人,在纪录片中我寻找自己。从《喧哗的尘土》到《梦游》,仿佛一面镜子观照着自己,让我不断地思考,也就让我很自然地由纪录一种“活着”的状态到纪录一种心灵的状态,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
拍摄,本来就是在拍自己
刘 面对《梦游》里的这群艺术家,我虽然没有初次遇见的那种大惊小怪,但还是感觉要恰当地形容、述说他们,还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粗痞但不萎靡,癫狂而不麻木,放逐自己却绝不放弃自我……他们人情练达却又不失赤子之心,诡异但又不失温情。让我感动的是李娃克离开前,配合他做行为艺术的小姑娘问他能不能不走,他给小姑娘买了书包和鞋子……
黄 娃克认她做了干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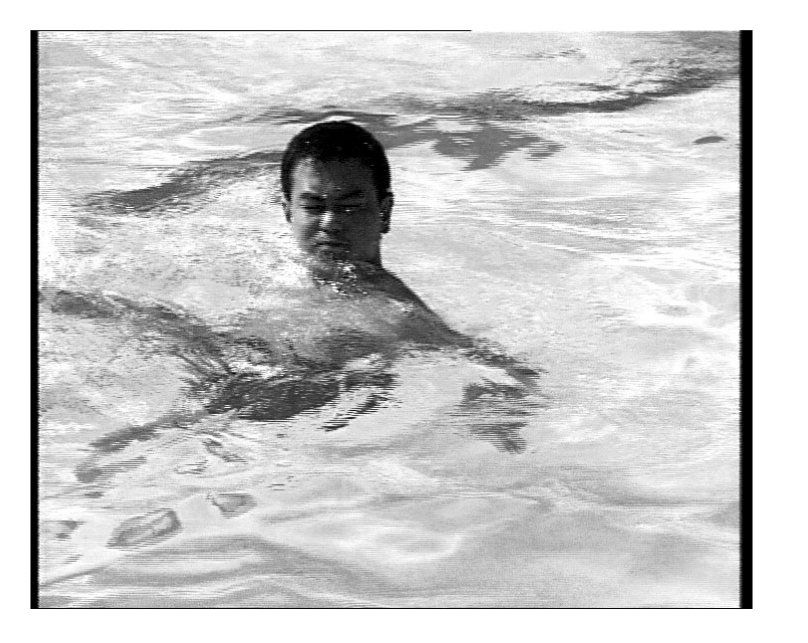
图23 纪录片《梦游》(2006,中国,黄文海)
刘 这群人每天行进着却没有方向,就像丁德福喝醉后站在马路中间说:“向南,红灯区,没钱;向那边,工商银行,抢钱,没胆;向北,文体中心,锻炼,太瘦,没劲;只有回去喝酒……”我感觉李娃克他们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做着一次生命的行为艺术,而你是用片子来推衍你对现实、对生命的认知和思考?
黄 其实,这个片子更多地呈现出了集权国家里,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我们从小就认为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李娃克、老丁他们是比我们长十多岁的知识分子,’89以后他们面临着一个转折。在权力和金钱并重的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变成了“天线宝宝”似的实用价值观。因为“天线宝宝”好像能够给你带来钱!艺术家面临着尴尬的现状:如果不带来金钱的话,艺术是没用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常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这就像一个要去改变世界的人,当他伸出拳头的时候,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或者是软绵绵的,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空,消耗掉了!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自我作践的东西,就表现在:如果你说我没戏,那我就说“我他妈的就不是人”。你作践我,我更加百般的自我唾弃。从某种程度来讲,娃克、老丁这些人他们也开始怀疑艺术了。在西方,有“艺术乃拯救之道”的说法。《一个人的圣经》对我的意义,在于让我觉悟到:生活在铁板一块的环境中,仍有可能成为“人”,生而为人是一种挑战。
刘 我们似乎丧失了一种最初的直接。
黄 我老回想起我十几岁时,初次看到凡高的书信选、凡高的画和莫蒂里阿尼的传记时,我是多么地激动!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世界!还有一道窗户!你还可以过着另一种生活!
刘 那种感觉,很纯粹。
黄 但在我剪那段时——娃克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拍打着他的睾丸,老丁赤裸裸地猥亵着他原来的画作……我感到特别地绝望!我当时泪流满面。他们在“’85新潮”时期是出色的艺术家,到了年近50岁的时候,居然做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行为,也是比较无聊的行为!他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却全部消耗掉了。两具幽灵在意欲中挣扎的影像,仿佛是叔本华哲学话语的戏剧呈现。叔本华说:这个世界有个意欲在横行霸道!意欲的焦点是生殖器。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摆脱这个意欲!这个意欲,具体地说就是功利、钱。如今,我们往往会失去当年我们“遭遇”艺术时的那种很纯真的感觉。
刘 是一种最初始的状态。
黄 对,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难道艺术它不给你带来功利的东西,就毫无意义了吗?有一次我去巴黎的时候,莫蒂里阿尼的画已经在那展出八个多月了,展期一年。当时,在画廊外面下着大雪,巴黎人连绵一公里地站在那儿,等候观看画展,我们也加入到人行里了。莫蒂里阿尼的画,像金子般的颜色,特别纯粹。真的是让我特别地感动,特别地激动!我思索了很久。
刘 尽管《梦游》有这样的意义,传达着你的一种认知,具有一种警示作用,但是你担不担心自己又会落到另一种境地——“DV人总喜欢把镜头对准‘脏乱差’”的一种认识定势里——就像有人评价说:90年代初,纪录片人总喜欢“老少边穷”一样,认为他们忽视了生活的主流,而有了“拿着自家的裹脚布给老外看”的嫌疑?
黄 我的家庭背景和《喧哗的尘土》里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我应该还比较顺,如果我还在电视台工作的话,也不可能拍出那样的片子,只有当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活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跟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压力和存在于你身上的是一样的。我离开中央电视台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同样会感觉到:如果我没有办暂住证的话,我一样也会害怕警察的。再就像《梦游》里的那些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多多少少都在我的身上也发生过,我和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捷克的哈维尔提出“道德上的病人”,他表达得可能更准确些。我觉得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只是你患得重与不重、漠视它或不漠视它而已。我一直都反感那些人说我们常关注“脏乱差”和“老少边穷”的现象,他们或许住在搭建的盆景般的花园里,已经养成了漠不关心和视而不见的生活状态了。
刘 或者说是一种俯视的心理。
黄 他们根本没有生存体验!
刘 是,的确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黄 拍纪录片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多人,动不动都说自己拍了一百多盘、两百多盘的素材,其实面对这么多素材,你可能会迷失的。你说你既能拍农民,又能拍工人,怎么可能呢?其实,你就是在拍自己!就像小川绅介一样,他说他不敢拍农民,后来硬是到农村生活了很多年,他才敢拍农村。
刘 对,小川绅介后来拍了《牧野村千年物语》。
黄 认识别人就是认识自己,拍别人仍然是在内心里找自己。
表达,应该回到最初感觉
刘 李娃克、“魔头贝贝”、王永平、丁德福他们其实就是借艺术来满足梦想的人,他们常常“泡”在酒里,把艺术和生活搅在了一起,分不清戏里戏外,这使他们一方面面临着生活的尴尬和窘迫,另一方面又无比愉悦地享受着一种做梦般的快乐——虚妄而荒诞。生活,是他们的,表达是你的。你一开始就找到表达的路径了吗?
黄 对于《喧哗的尘土》里的人,我是同情而不是喜欢,但《梦游》里的那些人,“魔头贝贝”、娃克、老丁等,我是很喜欢的,到现在为止,我和他们仍有联系。对于他们的艺术观点、看法,我也是认可的。应该说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话语。在我们一块出游,走访一些搞艺术的朋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艺术倾向是如此的接近,这时“魔头贝贝”对我完全敞开了。我觉得只有当对方向你完全敞开的时候,你随后才能拍到很好的素材。
刘 这时,拍摄也顺畅了?
黄 很顺。带子是DVCOM格式的,40分钟一盘,我一下拍了110多盘。可是,片子在8月份拍完后,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因为我不知该怎么去剪,该怎么去表达?《喧哗的尘土》是四条线索,它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每件事情都有个结束点;而《梦游》,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结束点,更多的是日常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王永平的片子也没拍完,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无从把握。
刘 为什么呢?
黄 这一百多盘带子,虽然拍得很顺,但在拍的时候就感到是最不可预知的。拍《喧哗的尘土》的时候,普通人的生活大都有一个惯性,我都会比较自信地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嘛,直觉就知道我的机位应该在哪儿,拍得不是特别麻烦、特别困难;但是在拍《梦游》的时候,我永远是处在那种惊奇状态中的,我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艺术是混杂在一起的,你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当然,在看素材的时候,娃克说很多时候他们是在作“行为”,但他也很意外:“我怎么一直在喝酒,怎么喝了一辈子啊!”
刘 真是很茫然吧。后来是怎么拎出那个表达的“线头”的?
黄 《喧哗的尘土》,在2004年11月份入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我感觉我的作品进了一个最好的纪录片电影节了。于是,我存着一个很大的幻想——或许能接到国外的单,能给国外的电视台打打工。出国前,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策划,包括它的发行和以后的一些计划等。准备资料、办签证,费尽了千辛万苦,总觉得这是个机会呀。在电影节上,我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发行单元区,而不去看片子,很不放松,很把它当了一回事。可是后来,感觉它跟我想象得相差太远了。整个活动,就像是一次朋友的聚会。连那个被我们奉为大师的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也就那样背了个布包,一身休闲就来了,朴素得让人觉得他就是来会老朋友的。
刘 呵呵,后来你的心态变平和了?
黄 那次把我的一些幻想给“破”了以后,我轻松多了,于是就明白:那里其实就是一个放松、透气的地方。我在想:你拍片子的意义何在?我的阿姆斯特丹之行不就应该跟那次和“魔头贝贝”、娃克他们一起出游的那种状态一样嘛!
刘 表达,也应该是一种轻松的、透气的方式。
黄 是,表达有你最初的一种需要。创作完成后,就把作品拿出来给别人看,如果有对你的作品感兴趣的,那我们就用共同的话题来谈论、来交流。这可能就是创作、拍片子的最初意义吧,别的其实都挺虚的。
刘 从一种最朴素的感觉,你找到了表达的起点?
黄 是啊,我回到了最初的感觉。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以后,我突然感到,可以剪《梦游》这个片子了。我剪的第一段就是“魔头贝贝”他们的出游。一路上,很有意思,我们换了无数辆车,公共汽车、中巴、摩的,然后是火车,联系了不少“诗友”,别人也不搭理我们,但我们还是特别的快乐,一路谈论着艺术的话题。后来,碰见一个诗人,那个诗人见到我们的头一句就是:“横断山上有蚂蚁和云雀/有几个外省女人从一辆红色中巴车钻了出来/对着远处的红枞大叫起来/就像被谁×了一样……”然后,魔头贝贝说:好啊,很直接!没有虚的地方,娃克也说好。很幽默的场面。
那段片子一剪完,我就觉得《梦游》这个片子可以前后承递了。我在家里剪了一个多月,基本结构就搭建起来了,慢慢地修改着,2005年七八月份就定了稿。它的后期时间可比《喧哗的尘土》要长呀。
意象,融合着整体的情绪
刘 你的片子,好像特别注意找亮点、找意象?
黄 我剪片子,往往是先有个意象之后,就能迅速地剪下去了。
刘 这一点,咱俩很像。我写东西时,也这样。
黄 拍完《喧哗的尘土》,我是在“非典”结束的第二天回到北京的。有一天,我心里冒出一个意象——一只手揉捏着一块肉,与它相对应的是一组画面——按摩室里,那个16岁的女孩给40多岁的中年男人老谢按摩,我突然发现我这个片子“有戏”了,它可以作为结尾放在最后,然后再往前找,就成了。
刘 《梦游》也是这样吧。
黄 是。《梦游》在剪之前,我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意象,就是一个人站在大海边,对着大海张着嘴,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直直地盯着这虚空。海是湛蓝、湛蓝的,突然海面上有一种雾一样的东西升腾起来,慢慢地向那人袭来,那是硫酸的浓雾,那人被慢慢腐蚀着,却又离不开岸边,因为他的脚被铸在了那里,他被一层层腐蚀着,就像瑞士超现实主义雕塑大师贾克梅蒂的雕塑一样,那人变成了一个非常易碎的雕塑站在那个地方。这个意象,在拍摄之前和后来,就一直搁在我心里,最后触动我的是阿姆斯特丹之行,它对应着“魔头贝贝”出游,形成了整部影片的结构契机。《梦游》这个片子,更多的是不讲究故事的连贯性,而是讲究一个一个片段的组接和氛围的营造的。
刘 是啊,从《喧哗的尘土》到《梦游》,你的片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初看时,感觉混乱、摸不着头绪,谁是谁弄不清楚。但,随后看着、看着,人物就慢慢“浮现”出来,你所要表达的东西也才渐渐地清晰起来。你好像有意模糊了人物和人物关系,模糊了人物的生活环境和活动地点,也模糊了片子的线索,比如对出场的人物不作字幕或者画外音的交代,对人物活动的地方、场景也基本不作交代,只是让观众通过画面和对话来感受。这样做是为了排斥一种新闻的“明确性”吗?
黄 是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大多数的纪录片,新闻性都过强了,因为我以前干过,我知道。所以,在我的片子里,我不强调某一时、某一地、某一人物,我更多的是强调意象和主题的不同变奏。有人说我在拍某某某,我觉得不对,我更多的是拍我自己吧,是拍那一阶段的我自己。所以,在《喧哗的尘土》里,我把人名和地名都虚化了,《梦游》更是这样。
刘 这是现代派作品通常的表达方式:虚化掉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虚化掉人名、地名,人变成了一种表达的符号。
黄 对,我不想像新闻报道似的,去表达某人、某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在《喧哗的尘土》里,我想表达一种整体的心理状态,一种很浮躁、很喧哗的状态,一种幻灭感。而《梦游》,我更想表达的是一种很虚无的状态。
刘 你的片子有很明显的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式的“直接电影”的风格,而且在《喧哗的尘土》和《梦游》里,都有一致的表现,怀斯曼也很反对新闻的明确性。实际上,你片子里的这些人,在当下是这样的,没准在清朝也是这样的。
黄 是的!上次放片子的时候,有个老外也觉得,这些人可能在明朝的时候也是这样。
刘 其实,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人性共通的东西。当初,你还接触过什么创作方法?什么样的创作风格影响过你?
黄 我以前在电视台的工作,都是个学习的过程,虽然学到的方法都比较惯常,但我的基本功打牢了。我上过周传基老师的剪辑课,这对我的自学很有帮助。我还比较注重搜集各种影像资料。对我最有启发的就是,2001年9月,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中国独立电影展”。影展前后放了上百部片子,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地下电影和独立制片人的纪录片作品,记得最后一场是在汽车露天电影院放映了贾章柯的《站台》。吴文光的《江湖》、杨丽娜的《老头》……我一直都很佩服他们,当时我有一种没搭上班车的感觉。但对他们的拍摄方法和题材,我都感觉很亲切,我想我应该也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吧。
刘 你是怎么接触并了解到“直接电影”这种风格的?
黄 “直接电影”的片子,以前就看过。怀斯曼的片子我搜集了七部,其实看得也不是太明白,因为是原版的,美国土语,听不太清楚,但我从中知道了他的拍摄方法。
我觉得,我的表达还受到了一种综合的影响。比如,费德里柯·费里尼的《罗马风情画》,我第一眼看到就吓了一跳,片段式表达,我觉得真是梦寐以求,而且不感觉陌生。昆德拉的小说,也不是那种线性的,有好多的故事、好多个人物,也有好多种变奏。我现在看《庄子》,觉得《庄子》那片段式的表达,也像纪录片。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对影像的论述,那感觉简直像是禅宗语言!前面说一句,后面说一句,似乎都不相干,最后一想,觉得太棒了,它整体构成了一种意象!其实,现代艺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并不是我们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在于你是否能“看见”。
刘 虽然,在《梦游》里,你不讲“故事”,但你把节奏剪了出来了。你觉得节奏感比线索的清晰更重要吗?
黄 对!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电影更接近音乐,应该是一个有节奏的视觉流程。
我认为,在片子里表达一种氛围、一种节奏是比较重要的,而故事的戏剧性要很强。曾经有一位制片人问我:你的片子里死人没有?我说没啊!他说那没有戏性啊!对他们来说,死了人就具有了最大的戏剧性。我突然觉得特别可怕!这种预设故事性的拍法,特别恶心!有很多人说他的片子拍了很多年,他在等,等什么呢?可能就在等别人死?!一想到这,我心里就一揪。
刘 真是功利、麻木!
黄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不愿意去预设一些故事性的事情。如果,你拍片时预设了故事的结局,那就会让你产生长久的“道德焦虑”感,一种拷问就会直抵良心:是不是拍摄促使了事情朝着那个不好的结局发展了?!
刘 当然,故事性不仅仅指这些了。
黄 片子的节奏,这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也是内心节奏的映照。我是比较反对那种不严谨的做法的,我很注意片子的节奏和紧凑,要尽量不让观众“跳”出来。所以,《梦游》里没有访谈、也没有看镜头的画面,我在剪辑的时候尽量把这些都剔除了。我觉得应该有点神圣的东西吧。
刘 那么,《梦游》里的那种片断似的、节奏感很强的剪辑方式,也是采用了“怀斯曼式”的从“孤岛”到“群岛”的剪辑方式吗?
黄 对,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剪的。这里面有个“语言”问题,一场一场的“戏”,先把它一块一块剪出来,再按照一种脉络,进行节奏似的串联,或者是拼帖式的串联。这节奏,当然是你内心的一种节奏。
刘 这种方式是不是能更好地表达你自己?
黄 至少是在《梦游》这个片子里吧,以后怎么弄我也不清楚,得就素材、题材而言了。

图24 纪录片《梦游》(2006,中国,黄文海)
风格,非如此不可的表达
刘 李娃克、王永平他们在影片中“搬演”着自己的生活,你纪录着戏里戏外的他们,在《梦游》里“搬演”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融合的。这让我想起了陈可辛的《如果·爱》,在片中“搬演”似乎很自然地就滑向了“生活”,“生活”也很自然地延伸到了“搬演”里,这使得片子形成了一种虚构的表象。《梦游》,也有这样的品质特点。你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自觉地这么去做的吗?
黄 我明确意识到了,是有意去做的。娃克他们“搬演”着他们过去的生活,那个剧组也很奇怪,来人就演,没来人就等着,他们还做着他们的行为艺术,他们的生活和艺术本来就是融合在一块的。在我的片子里,没有去强调这是在拍电影,那是在拍他们的生活,而是都统筹在一种“梦游”的状态下。这种状态就是我要的,对我来说娃克他们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打乱了一些界限,是我很明确地结构出来的,这更像是在剧场的感觉。
刘 我很欣赏影评人王梆评价的这段话,我念一下:“作为纪录片,《梦游》的成功之处在于,导演在没有添加任何布景、台词、情节及一切演绎的情况下,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虚构感’……她再一次重复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在司空见惯、正常的、符合标准和逻辑的生活里面,到底存在着多大层面的‘虚构’?而人又是如何通过一点一点的虚构,获得‘真实’?”
黄 她说得真好。对我来说,一个作者风格的形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史的熟悉,另一个是要有个人的生存体验。一定要有个人的生活体验!风格是什么?就是:非如此不可的表达方式!虽然,有人接受,也有人不接受;有人理解,也有人不理解。但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你的作品要表达出你的真诚度,就要对你自己不说谎!我觉得,作品更多的是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
刘 正是缘于这样的表达风格,你的片子就可能会抽象到了一种隐喻的层面,因此它对收视习惯就提出了挑战,对收视的要求就特别高,它得目不转晴地去看,稍一跑神,就会错过了很多信息。因为,在《梦游》里,是没有画外解说、没有交代性字幕的,一切涵义都靠结构来呈现,都靠画面来表现,都靠人物表达来体现。我是看了几遍之后,才把李娃克和丁德福分清楚,才看清楚“魔头贝贝”进出的那道门上写着“警卫一班”的字样。这就和通常收视电视片、肥皂剧的习惯非常不同,得非常专注、非常认真地去看、去捕捉。你会不会只注重了自己的表达效果,而忽略了收视的效果,因为观众大多是“隔山看牛”啊?
黄 收视效果,我觉得这词挺虚的。打工的时候,老板说了算,有模式,我就按样片模式来做。干我自己的事情时,那就是我说了算,我必须给自己一个空间,或者说给自己一个透气的方式。
刘 面对观众,你不能光“自言自语”。收视效果,的确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它迫使我们不能漫无边际地去“自由”发挥,但限制是一种力量!
黄 所有表达的努力,都要就素材而言,你不能想当然!许多人拍片子,报一个选题后,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必须这样去做。其实,创作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我强调在现实前提之下的努力,拍片子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创作,就是在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把自己的眼光弄得纯粹一点,多读些书,真实地生活着,你就能观察到很多东西,也能表达出很多东西。
刘 如果,你很有效地表达了自己,让观众在收看的时候能有一种很契合、很顺畅的收视感觉,这是不是更好呢?
黄 就收视效果而言,我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我的片子不长,很多是按电影长度来剪的,我的东西都是很简洁的,《梦游》是从100多个小时里选择出80多分钟的,这就是想让观众能像你一样专注地去看。做作品,我还是比较负责的、认真的,这样的态度就不可能太散漫,因为它是时间的艺术。所以,片子本来就应该特别专注地去看。
从这么多次片子拿出去放映的经历来看,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观众的,当看到别人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能够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比如吴木坤、苏七七和王梆写的东西,看后让我找到了自信。
刘 表达、解读,都很重要。
黄 有好多纪录片人,特别是独立制片人,多数是题材决定片子。通常,他们碰见一个好题材就能够拍出好片子,碰不到好题材就拍不出来了,落差很大。《梦游》之后,对我来说,题材已经不成问题了,抽象的东西我也能够表达了。现在,我要拍一些有关佛教的题材,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可以试一试了。
刘 2004年,在北京国际纪录片展映会上,法国纪录片《是与有》的编导菲利贝尔说了一个观点,我们觉得特别好,他说:纪录片人要拍那些超越了题材的东西。比如表面上他在拍医院,但他实际上根本不是仅仅在拍医院,而是已经超越了医院这个题材,就像张以庆,表面上在拍“幼儿园”,其实他把这当成了一种审视社会的方式。菲利贝尔说:一个纪录片人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导游,要带领着你的观众去游历。
黄 菲利贝尔说得太好了!《梦游》,实际上就是我开始向内心的漫游。
刘 为什么要选择用黑白的画质来表达?
黄 刚开始也不是黑白的。有一天,我在剪辑房,试着把魔头贝贝游泳的那一段调成了黑白画质的。那一刻,我吓了一跳!魔头贝贝就像在冥河里游泳一样,“梦游”的意境很强烈。OK!于是我把片子都调成了黑白画质的。一种感觉,其实就在一堆素材里蠢蠢欲动着。这个片子,我是在家里剪的。每天早上8点起来,“啪”地把窗帘拉上,很幽暗,也跟梦游似的,每天晚上我就到大街上跶,挺奇怪的,那一个月的状态跟片子里呈现的状态太一致了。所以,黑白画质可能强化了这种感觉。
刘 《梦游》这个片名,我觉得很好。它除了有一种混淆了现实与梦幻的混沌感以外,还有一种盲目的温暖和放逐了目的的快乐。因为,他们依然有着一种理想,是什么?说不清楚,但他们无目的地快乐着。他们跟着“魔头贝贝”满世界乱跑,遇到同是写诗的知音,就一起坐在马路边上喝酒,遇到不搭理他们的,也没关系,依然故我。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就像在梦游。原来的片名好像不叫《梦游》?
黄 叫《静静地锯》,是“魔头贝贝”的一句诗:“魔头贝贝是我全部的人/他在我里面/静静地锯……”这是一种分裂,就像我跟你讲的在海边的那个意象。后来,随着我对人物的慢慢理解,我比较积极、宽容地去看待这一切了。
刘 说说你的理解。
黄 娃克决绝地抛弃了一切(甚至家庭),仍在于他要让自己的存在留下“印迹”,他全部的行为以此为根据。老丁这位被生活虚无化了的人,也仍然保有一份道德的底线,他没有加入到学校的“阶级斗争”中去,那个狼群的世界!贝贝今年又写了一首已有三千行的长诗,他仍然在找机会去出游。永平开始拍有关自己的电影,这也就意味着“寻找自我”的开始。在总体虚无的环境里,这些人仍保有着他们个人的姿态,一种自我的努力和证明,这就是自我拯救,也是对这个“自我作贱”文化的不屑。在这个功利的世界里,娃克说:在猪群里,哪有成功和失败!我的下一部影片也许起名为《长河》。
刘 《静静地锯》倒是和《喧哗的尘土》在风格上有呼应,但感觉太隐讳了,文学色彩也浓了些。《梦游》,给人一种氛围的感觉,一种中性的感觉,不是直接去判断、隐喻,它更包容。
黄 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就改成《梦游》了。
【链接】黄文海对怀斯曼影片的反思(片段)
从怀斯曼开始,现代艺术的作品种类中多了一门叫“直接电影”的东西。与别的现代艺术品相比,它一点也不逊色。从而使它自身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的概念,融入进艺术电影的范畴之中。
我现在理解了,他为何给自己的影片拍摄,设定一个不长的时间。因为,他的影片是不需要戏剧性的,他仅仅去呈现生活中的碎片,他是一个荒诞世界的见证者,而且他深知事实的丰富性,暧昧永远高于作者的主观臆断。如一个月或三个月,不像我们有些人动不动就称自己的影片是长达多少年拍成的。
为何要如此长的时间呢?有一次我和一个人有一场对话:“你的影片中有死人没有?”/“没有。”/“那不能让人震撼啊!”其实,他所说的“死人”,乃是影片中的戏剧性高潮。我还知道,有些制作人手中拍了一些人的素材,但迟迟没有将作品完成,乃是他们在等待着主角的死亡。“他死了后,这影片就能让人震惊,就值钱了!”这样的拍摄者心中,藏着怎样的一颗邪恶的心啊!在这里,我们不从道德上去评论拍摄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从作品所要承载和表达的哲理,如何与拍摄手段和最终呈现的形式有关。
在这一点上怀斯曼与其同时代的荒诞派戏剧家们是共通的。如尤奈斯库曾表示,他的戏只是提供见证,不进行说教。那么,剧中的思想又靠什么来体现呢?他们认为,应该依靠舞台形象本身,这其中包括人物的具体动作、舞台布景与道具等因素。贝克特称这种技法为“直喻”,尤奈斯库则称之为“延伸的戏剧语言”,意思就是,让舞台、道具说话,把作品思想变成像。因此,有人说尤奈斯库的剧本不是供阅读的,而是供观赏的,因为在观看过程中,动作、道具、场景可以给人以最感性、也最直接的印象,而阅读剧本,则无从体会“直喻性”的场景与道具的意义。
怀斯曼的影片没有戏剧性,故事情节弱,人物没有强烈冲突的性格。他如“苍蝇”一般盯着那里的人,仿佛仅仅是在“见证”。“见证”一词,在现代作家中屡屡提及,如米沃什、哈维尔、克里玛等人,正如有一句诗叫“活下来,并且要记住”。那些人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如同置身于某一剧场,怀斯曼的“机构”其实就是一个个特定的剧场或实验试管,身处其中的人物,他们的动作、言语、以及背景都是“直喻”——一种直接的表述。通过整部影片营造着一种氛围——弥漫着让观众感同身受。
怀斯曼“直接电影”的产生,乃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哲学背景上,如存在主义哲学。怀斯曼60年代在巴黎生活,其时正是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蓬勃发展之时,他回美国后的笫一部影片《提提卡荒唐剧》,仿佛是荒诞派戏剧的搬演。理解怀斯曼,根本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首先应将其视为一位现代艺术家。在对他的采访中,他屡次提及他爱读小说,他每年拍摄一部影片,他要同他心仪的伟大小说家们一样,营造一个独属于他个人的世界,如同福克纳的小说,永远发生在那个他自己臆造的、小小的如同邮票一般大小的世界里。
【访谈结语】
在我整理着本次访谈期间,黄文海发来短信,告知《梦游》已入围“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的“国际竞赛单元”,这也是本届电影节唯一入选“国际竞赛单元”的中国大陆的纪录片。我感受着字里行间传递过来的喜悦。
零星的爆竹声,一次、一次地炫示着:新年就要到了。生活,在又一个轮回里展开着人们的期望。尽管,有思考也罢,无思考也罢,生活都竟自流淌着,然而当我们将生活与创造、将生命与思辨相融合的时候,生命就有了新的品质。这生命的品质,也就如同它来时一样,自然得和滋养它的生活根根相系地长成了一体。
这正如黄文海,在生活之流中依顺着自身理智的力量,表达着他的独特认知和“立场”,于是他的生命便也有了别样的品质。
【注释】
(1)本访谈发表于《南方电视学刊》2006年第1期。
(2)此为作者当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