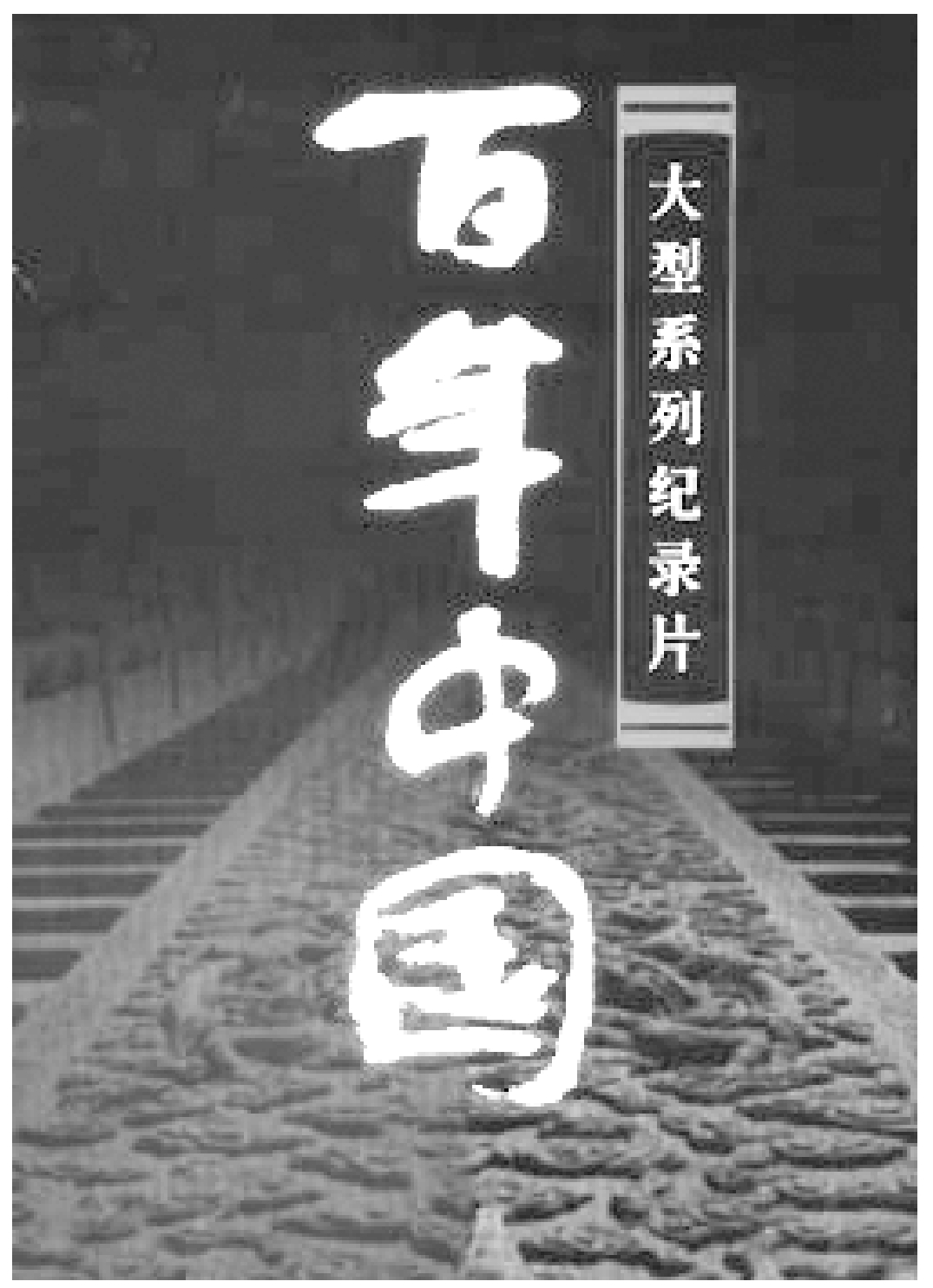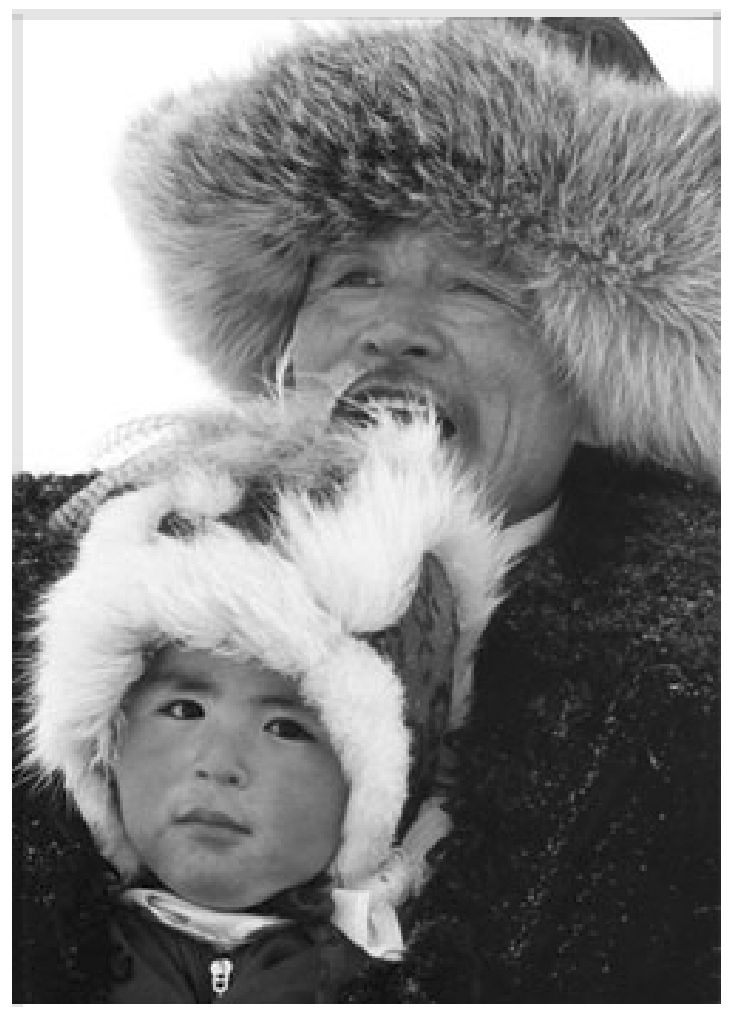-
1.1序一
-
1.2序二 影视艺术理论 迈向美学层级——读《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
-
1.3绪章 一个半岛似的虚构概念
-
1.3.1第一节 纪录片的“虚构转向”
-
1.3.2第二节 纪录片的虚构之影像表意
-
1.3.3第三节 研究的路径与现状
-
1.4◎上篇 本位的视阈
-
1.4.1第一章 影像表意的研究背景
-
1.4.1.1第一节 在语言学转向中影像成为意义
-
1.4.1.2第二节 影像功能的不同认知
-
1.4.1.3第三节 影像成为一种意义:研究的价值与特征
-
1.4.2第二章 纪录片的虚构:影像表意的内涵
-
1.4.2.1第一节 在影像的呈现中表达意义
-
1.4.2.2第二节 在观者的体认中获得意义
-
1.4.2.3第三节 影像表意的不同媒介特质
-
1.4.3第三章 纪录片的虚构:表意生成的形态与特性
-
1.4.3.1第一节 纪录片的三种基本类型
-
1.4.3.2第二节 虚构的表意:在纪实的断点处生成
-
1.4.3.3第三节 纪录片虚构表意的功能特性
-
1.5◎中篇 历时的视阈
-
1.5.1第四章 纪录片的虚构:影像的初萌语境
-
1.5.1.1第一节 影像媒介与自然物
-
1.5.1.2第二节 影像复现与表意功能的实验与应用
-
1.5.1.3第三节 非虚构与虚构的滥觞
-
1.5.2第五章 纪录片的虚构:观念的生成语境
-
1.5.2.1第一节 弗拉哈迪时代:虚构与纪实浑然共生
-
1.5.2.2第二节 真实电影时代:虚构与纪实自觉分离
-
1.5.2.3第三节 新纪录片时代:虚构与纪实复归融合
-
1.5.3第六章 纪录片的虚构:中国的衍生语境
-
1.5.3.1第一节 纪录与虚构的依存
-
1.5.3.2第二节 纪录与虚构的误解
-
1.5.3.3第三节 虚构表意策略的应用
-
1.6◎下篇 共时的视阈
-
1.6.1第七章 纪录片的虚构:与其他虚构表意形态的异同
-
1.6.1.1第一节 纪录片化的“故事片”与故事片化的“纪录片”
-
1.6.1.2第二节 在“真人秀”节目中的虚构表意
-
1.6.1.3第三节 在栏目化节目中的虚构表意
-
1.6.2第八章 造型风格的表现(上):情景的再现
-
1.6.2.1第一节 纪存生命的形态
-
1.6.2.2第二节 延展时空的再现
-
1.6.2.3第三节 构建叙事的框架
-
1.6.3第九章 造型风格的表现(下):思辨的重构和心绪的呈现
-
1.6.3.1第一节 思辨的重构
-
1.6.3.2第二节 心绪的呈现
-
1.7◎个案研究 中国新派纪录片人系列访谈
-
1.7.1《幼儿园》:一种审视的方式——纪录片编导张以庆访谈
-
1.7.2《老宅2003》:让自己的语言生长——纪录片编导李汝建访谈
-
1.7.3《房东蒋先生》:在个性的舒展中呈现——纪录片自由创作者梁子访谈
-
1.7.4《雾谷》:只为推开一扇窗——纪录片编导周岳军访谈
-
1.7.5《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剧情框架中的生命纪录——纪录片编导胡庶访谈
-
1.7.6《梦游》:弥散着荒诞的世像——纪录片编导黄文海访谈
-
1.7.7《毕摩纪》:直抵心灵的情绪穿越——纪录片编导杨蕊访谈
-
1.7.8参考文献
-
1.7.9后 记
1
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