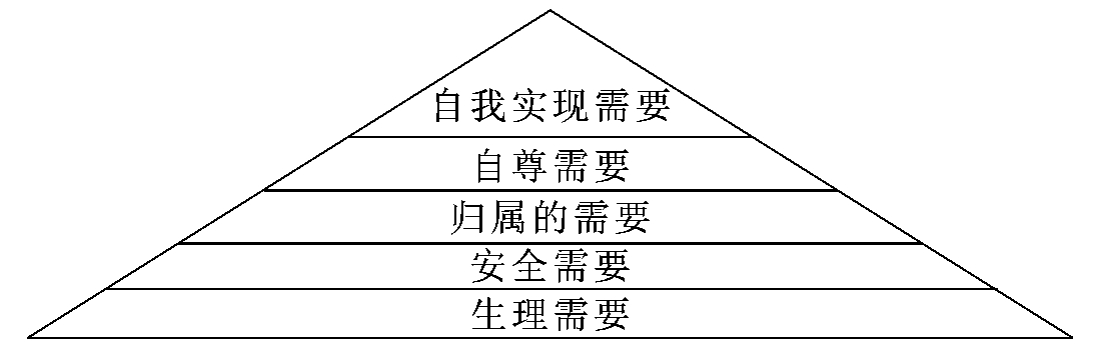-
1.1绪 论
-
1.1.1一、什么是文学概论
-
1.1.2二、为什么要学习以及怎样学习文学概论
-
1.2目录
-
1.3第一章 文学本体论
-
1.3.1第一节 文学是人学
-
1.3.1.1一、文学是对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
1.3.1.2二、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作家心灵化的能动反映
-
1.3.1.3三、文学作为人学的一般本质和文学的源流关系
-
1.3.2第二节 文学是审美人学
-
1.3.2.1一、文学与哲学人文科学:两种人学的比较
-
1.3.2.2二、文学的情感性
-
1.3.2.3三、文学的形象性
-
1.3.2.4四、文学的情感性和形象性的关系
-
1.3.3第三节 文学是语符化的审美人学
-
1.3.3.1一、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比较
-
1.3.3.2二、文学用语言表情、造形的宽泛性和深刻性
-
1.3.3.3三、小结:关于什么是文学的综述
-
1.3.4第四节 文学作品
-
1.3.4.1一、文学作品及其结构层次
-
1.3.4.2二、文学作品的有机构成和基本属性
-
1.3.4.3三、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诸要素
-
1.3.4.4四、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
-
1.3.5第五节 文学作品的体裁
-
1.3.5.1一、文学作品的体裁及其划分
-
1.3.5.2二、诗
-
1.3.5.3三、小说
-
1.3.5.4四、剧本
-
1.4第二章 文学价值论
-
1.4.1第一节 文学的审美价值
-
1.4.1.1一、价值与文学的价值
-
1.4.1.2二、文学审美价值的基本取向
-
1.4.1.3三、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动态的生成和实现
-
1.4.2第二节 文学的审美作用
-
1.4.2.1一、文学审美作用的动力源泉与内部构成
-
1.4.2.2二、文学审美作用的总体特点
-
1.4.2.3三、文学审美作用的心理学分析
-
1.5第三章 文学创作论
-
1.5.1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主客体
-
1.5.1.1一、作为文学创作客体的社会生活
-
1.5.1.2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我
-
1.5.2第二节 文学创作过程
-
1.5.2.1一、文学创作过程作为以灵感为过渡的,从构思到传达的过程
-
1.5.2.2二、文学创作过程作为情感和形象的典型化过程
-
1.5.3第三节 文学的创作方法
-
1.5.3.1一、创作方法的含义和种类
-
1.5.3.2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
-
1.5.4第四节 文学创作风格
-
1.5.4.1一、文学风格的基本含义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
1.5.4.2二、文学的个人风格和文学的时代风格与民族风格
-
1.5.4.3三、文学风格的多样统一
-
1.6第四章 文学接受论
-
1.6.1第一节 文学接受及其主客体
-
1.6.1.1一、文学接受的概念
-
1.6.1.2二、文学接受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
-
1.6.2第二节 文学欣赏
-
1.6.2.1一、文学欣赏的性质和意义
-
1.6.2.2二、文学欣赏的创造性解读
-
1.6.2.3三、共鸣:文学欣赏进入高潮的标志
-
1.6.3第三节 文学批评
-
1.6.3.1一、文学批评的性质、任务和文学批评家的素养
-
1.6.3.2二、文学批评的标准
-
1.6.3.3三、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类型
-
1.7第五章 文学发展论
-
1.7.1第一节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
-
1.7.1.1一、文艺的起源与原始人的社会生活
-
1.7.1.2二、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发展
-
1.7.1.3三、两种发展过程的局部不平衡性
-
1.7.2第二节 文学创作与接受的矛盾运动
-
1.7.2.1一、文学发展中的他律和自律
-
1.7.2.2二、文学创作作为生产与文学接受作为消费之间的供求关系
-
1.7.2.3三、他律-中介-自律: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大概描述
-
1.7.3第三节 文学创作中创新与继承的矛盾运动
-
1.7.3.1一、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的创新
-
1.7.3.2二、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的继承
-
1.7.3.3三、文学创作中创新与继承的矛盾运动和“推陈出新”方针
-
1.8全新修订版后记
1
文学概论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