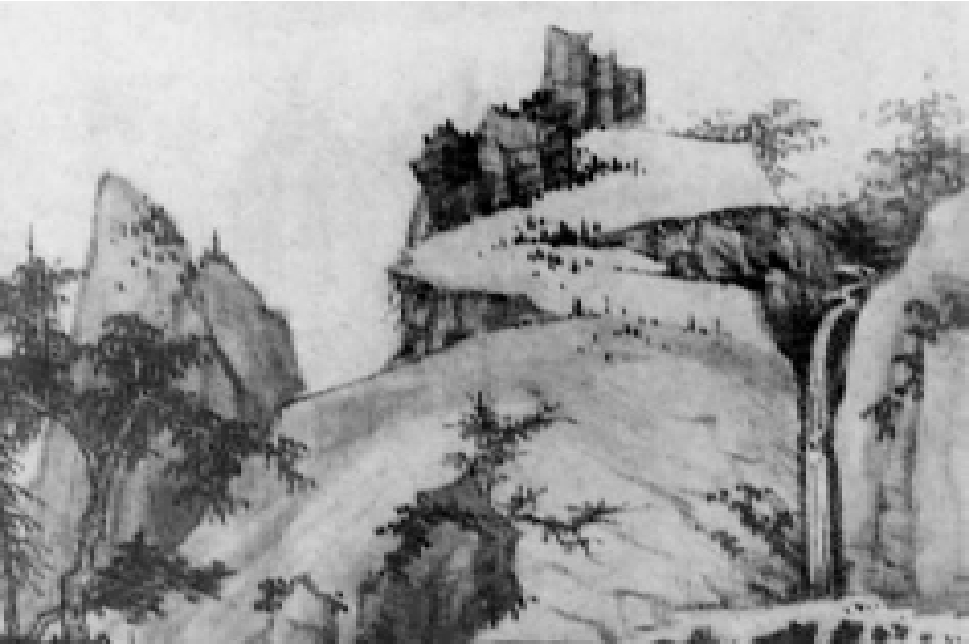第二十八章 别开生面
清初以山水画为主体的画坛,虽然是晚明风气的延续,但时事变了,人情也随之大变。原来散淡清疏的晚明文人山水画,尚古面貌浓重,一变而成“四王”、吴恽那样的“正统派”;另一变是将古传统打碎后塑造自我的“野逸派”。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壁垒分明的阵营,“正统派”也好,“野逸派”也好,都讲究笔墨,且和宋元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是风格的古近差别,个性的浅深差别,笔墨的极端和中和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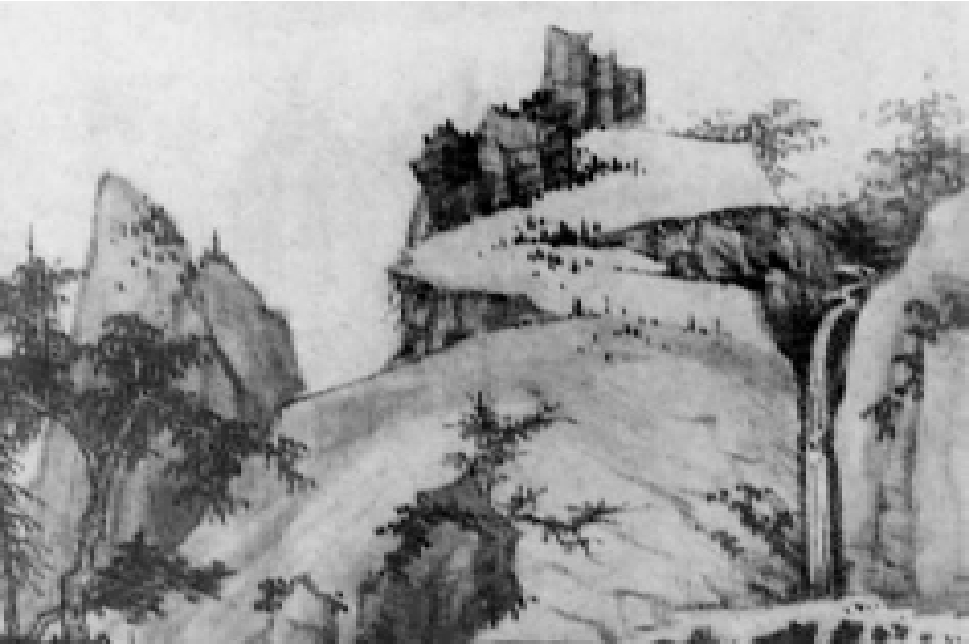

清·弘仁《山水图》(局部)
生长在黄山脚下的弘仁,本姓江,明亡后出家为僧。这位受徽州山水熏陶的画家,师承的却是惯写太湖风景的倪瓒。在“元四家”中,倪瓒是最不易学的,沈周曾在倪瓒的笔墨上,连连碰壁,原因是沈周的个性难以调和倪瓒。不知道弘仁的个性与倪瓒到底有多少相近的地方,而弘仁以徽州的高山深谷密林,以黄山的奇峰怪石、古松去迎合倪瓒疏树平坡浅岗的平远笔墨,发挥得了无痕迹,既隐约可辨出倪瓒的滋味,又全然是弘仁自己,可以说美善两尽。沈周学倪瓒的不类,问题在于刻意求似,因而牵强附会,反倒弄巧成拙地一无所获。弘仁的成功,在于不计大处,但求小节。他明白倪瓒的干笔的妙处,也明白这种干笔在倪瓒的平远山水上,可以周密结实,而移到徽州山水,一样的干毛笔法,则只能以疏当密。于是,勾和皴浑为一体,有时只勾不皴,而以疏线条支撑的画面,需要高超的运笔修养。弘仁的线条轻盈灵动,细而有劲,柔中藏刚,常常是长线连绵,平平缓缓中也充满着节奏感;他学倪瓒的方折,又兼顾了圆浑,这种笔法,用来表现高山峻岭,于清疏间依然可见幽深,再反过来画倪瓒式的平远,也有高旷的情致。在是倪瓒而非,非倪瓒而是之间,成就了弘仁自己的画风。“野逸派”的创造精神,就在于打碎传统拾其碎片来装点自己,弘仁用这样的精神,树立起黄山以及徽州山水的笔墨形象,成为“新安画派”的领袖。

清·梅清《黄山图》(局部)
作为黄山地区的弘仁,其画派只能以“新安”作称,而真正的“黄山画派”,却不以黄山脚下的弘仁为主,而是按在离黄山几百里外的宣城画家梅清身上。梅清的“黄山画派”,完全与他画黄山有关,而且,他画的黄山,自有一套用黄山烟云供养、从黄山风情中提炼出来的得黄山神韵的技巧。弘仁笔下的黄山,用黄山的标准来衡量,要逊梅清一筹,所以,“黄山画派”的主将,梅清是当仁不让的。梅清生在政治动乱的年代,甲申之变时,他二十二岁,十年后,时局趋于稳定,他应乡试,并被推为“宣城孝廉”,后试“礼部”,不第。于是,便息了做官的念头,过起田园生活来。顺治十一年(1654),应礼部试失意后,梅清第一次游黄山,他被黄山奇绝险峻的景色迷住了,不但把烦恼涤荡得干干净净,而且还和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有考证过梅清上过几次黄山,从他的画作和诗文中看,为数是不少的。他对黄山的感情很深,对黄山的一草一木都极为关注,他和未去过黄山的人谈黄山的秀美,和去过黄山的人论黄山的博大,共同交流艰辛登攀至高山绝顶的那种兴奋情怀。当年的黄山,路途险峻,有的地方要靠足够的胆魄和体力才能通过,他说百步云梯:“一线直上,三面皆空,经过许久,至今忆之犹心怖也。”(《黄山图册》《百步云梯》题跋)梅清游黄山,探险猎奇,寻幽访胜,不辞辛劳,大有“以身寻奇观,葬此抑何怍”的气概。梅清画黄山以真实为本,现在黄山的景点,说得上的,几乎他都画过,汤口、桃花峰、人字瀑、慈光阁、文殊台、天都峰、百步云梯、光明顶、清凉台、狮子林等;黄山的名松:黑虎松、蒲团松、接引松等,也是他常画的题材。我们用今天见到的上述景观来看梅清所画,外形一一契合,而神韵和风采、意趣和意境经过三百多年的风霜雨雪也竟如昨天,只是梅清的画多的是苍古和孤寂。画实景的笔墨以心境作依托,梅清画的黄山,妙在景随真实而情依己意。上述景观,在梅清的笔下常画常新,梅清的《黄山图册》,眼下能见到的有十本,也就是说一个景观,他用十种以上的角度或画法去表现。另外,梅清的画变化多端,有赖于传统笔墨功底的深厚,虽然他自立门户,自创一格,但不免时时要露底,他得力最深的是王蒙的笔法。他把王蒙牛毛皴变得粗疏,把解索皴抖得松散,这种变调,与其说在与王蒙对话,不如说是在对抗。他从王蒙中得到的和他在纸上抒发的是一种咀嚼和消化过的东西,他的尝试是大胆的,大胆来自他犷放而倔强的个性,因而,效果明显地偏袒了他的个性。他最擅长的松树,也是从王蒙的紧密中放松,既得洒脱之姿又有新奇感;梅清的苔点也作疏放之态,星星点点地洒落在线皴之间,饶有趣味,他的大而阔的苔点,浓重很见力量,嵌在墨堆里,或放在空白处,给画面增色不少。梅清的小景,精致不失豪放,大幅巨幛,豪放中不失精致,所以他的众多的册页,空灵而有着扎实的笔墨,大立轴为笔力气势所吞,可以说,在当时的画家中,能称雄奇者,当属梅清。

清·朱耷(八大山人)《山水图》

清·朱耷(八大山人)《梅雀图》

清·朱耷(八大山人)《墨荷图》
八大山人是明朝的王孙,明朝的覆灭对他来说,有着切肤之痛。在画上八大和山人连缀的款式看似“哭之”或“笑之”,真是无奈到哭也不得,笑也不得的地步,对新王朝的愤懑,极为强烈。逆境中的逆向思维造成了八大山人逆反的艺术个性,他崇拜董其昌,但他为之倾心的董式山水,到他手里,变得奇崛放浪,一派不修边幅的样子,显得异常苍凉,悲悲切切的情状,通过他苍凉的意境,造成撼人心魄的力量。完全由个性吞吐的笔墨,释放着外旷内敛的磅礴大气。
花鸟画是八大山人最擅长的题材,他不以宋元的传统为然,对明代的写意画法的接受有理有节,但对当时还不被人看好的徐渭,却是敬佩有加,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绘画,更令他醉心。生活在瓷都景德镇附近的八大山人,深受民间绘画的影响,晚明的青花瓷器上所绘的鹤、雁、鱼、鹿以及各种花卉和八大山人笔下的此类形象,多有相似处,说明文人画家感觉到民间绘画的生命力。花、草、鱼、禽,一经他的笔墨点化,形象独特而生动。八大山人的笔法拙朴却灵动活泼,墨法生硬到近似板滞的程度,却有置死地而后生的效果,造型怪诞却妙趣横生。他的花卉,以勾花点叶为多,出色的书法用笔,使所勾的花朵,简洁而富有情绪性,又寥寥数笔点叶,气盛韵足,极耐咀嚼,陈道复在他面前,简直弱不禁风。他画墨荷,疏花轻勾漫写藏露于阔叶之间,以墨见长而笔气强健,画面上墨光闪亮处,愈见笔法的精妙。《河上花图》,长卷荷花茎叶相交,墨翻笔舞,蔚为壮观,且疏密布排有致,石块、兰竹、枯枝、败草穿插其间,他在使性弄情的宣泄里,不忘理智的成分。八大山人的芙蓉、菊花、牡丹等,从简到无可再简的笔墨里,散发出丰富多彩的笔情墨趣,他甚至把勾花点叶法作在墨葡萄上,线圈葡萄,大片墨叶,间以劲爽之笔的老藤,这种小小的改制,是前无古人的,八大山人的敢为天下先的意识是出于他纵笔的胆略。八大山人的禽鸟是文人写意的经典,它完全打破了禽鸟画法框架,明代最大胆的写意禽鸟,尚要在顾及毛羽真实的表现上作一番姿态,而八大山人,却用最简练、概括的笔墨,画生动别致的禽鸟,几根墨线,一团墨色,毛羽之真,鸣啄之趣,跃然纸上。说八大山人画禽鸟有眼无珠,看来并不确切;说八大山人画禽鸟白眼朝天,却有几分实情。说有眼无珠白眼朝天是讽刺当局,也许存在这种可能,但庸俗社会学往往在社会性上大做文章而忽视了艺术家的艺术性。八大山人画禽鸟用点作眼,完全是出于画面或者形象上的考虑,他圈眼点睛,睛不在圈的正端,是禽鸟行止姿态真实而生动的表现,正是他的匠心所在。八大山人对新朝有满腔怨愤,也把怨愤尽情地发泄在画上,但艺术家毕竟不是政治家,如果将八大山人的画看作是反清檄文的话,无疑要大大地削弱它的艺术性。八大山人是位文化素养很高的画家,他的画个性鲜明,笔墨磊落,旁若无人,原本有使性宣泄孤芳自赏的因素,不期却因简练生动而受到各种审美层次的欢迎,他将极有修养的笔墨作粗野处理,是雅的通俗化,使雅得以俗赏,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

清·髡残《山水图》

清·龚贤《山水图》
髡残和弘仁一样,虔诚地礼佛,禅学的造诣很深,也一样从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画风。髡残认定“画必师古”(自题《春景图》)的道理,他心仪巨然,却没有从巨然画里摘取什么;喜欢王蒙,倒是获益匪浅。髡残、弘仁两人的异样,在传统上显现出来了,弘仁学倪瓒冷静练达,髡残师王蒙的热烈奔放;一个衣冠楚楚,一个乱头粗服,但在山水画的禅意禅境上,却是殊途同归。髡残用焦墨干笔,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然而,髡残阔略不羁,使本应慢行缓移的笔法,变得快捷,一如他风奔雷转的草书,他持深厚的书法功底,将快捷的行笔在纸上留住了干枯毛耸且凝重遒劲的线条,粗而力透纸背,乱中精彩纷呈。程正揆说:“石公作画,如龙行空,虎踞岩,草木风雷自先变动,光怪百出,奇哉;每以笔墨作佛事,得无碍三昧,有扛鼎移山之力,与子久,叔明驰驱艺苑,未知孰先。”(《青溪遗稿》)道出了髡残笔墨的动感和力度,也道出了髡残画参禅的特点。
和髡残差不多同时的龚贤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不盲从,不随波逐流,认为:“古人之书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非若今人泥粉本为先天,奉师说为上智也。然则今之学画者当奈何?曰: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取证于晋、唐、宋人,则得之矣。”(见周二学《一角编》乙册)“至理无古今,造化安知董与黄。”(《半千课徒画说》)和师古派的看法截然不同,在造化面前,今人和古人是同等的,古人用眼去观察自然,用心去体会自然,今人何尝不能呢?基于这一点,他的立足就高出他的同辈人。然而,他也承认优秀的传统,他最佩服的是五代的董源,这也和他师造化的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董源受南京地区山川风景的感染,创造了“江南画派”,董源的山水画正是他所熟悉、所热爱的地方。他学习董源的笔法,有着很深的造诣,但终掩盖不住表现真山真水的欲望,他的山水画成就,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在笔墨中注入大量写实性的因素,除了线条之外,他十分重视烘染和干擦的技巧,增加了山石的厚重感,烘染使之清润,干擦使之苍茫,这种厚重感和留白结合起来,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出现了光影的效果,山水形象恍若眼前,很贴近自然。
师法自然,表现自然,是龚贤绘画艺术的核心,他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归纳为四大要素,即笔、墨、丘壑、气韵。他说:“笔法宜老,墨气宜润,丘壑宜稳,三者得而气韵在其中矣。”(见《虚斋名画续录》卷三)龚贤山水画在“墨”和“丘壑”上构成他的特色。一般都把笔和墨合在一起,龚贤强调“墨”,并非有意要使笔墨分家,而是要突出墨的作用,把墨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烘染和干擦,即为具体的实施方法,它有效地丰富了画面的层次,表现出较强的立体感。更重要的是,为描写真实服务,南京地区的山多土,树木茂密,一派苍茫滋润的景象,透过墨,龚贤把南京地区山水的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反映出来。树叶的层层烘染,苍翠欲滴,山石反复染、擦,显得愈加浑厚幽深。另外,在墨气的映衬下,一切露白的东西,诸如云雾、泉涧、江湖、树干等皆楚楚动人。“丘壑”是龚贤的艺术术语,虽然他说:“丘壑者,位置之总名”,似乎是指构图,其实它还有一层意思,即山石树木等山水形象的造型。龚贤把自己创造的这些山水形象,在师法造化的前提下进行形体的艺术加工,刻意修炼成自己个性化的模式,他笔下树木的造型多半是下粗上细,淡枝浓叶,丛树的安排和俯仰参差都极富个性特色,山石也多呈下阔上窄状,层层叠起沉稳凝重。至于“位置”,也即构图,正是龚贤的长处。他善于调配安置山水形象,他认为:“位置宜安,然必奇而安,不奇无贵于安,安而不奇,庸手也;奇而不安,生手也。”(同上)这是一段很辩证的论述,和他的创作实践是相一致的。龚贤山水画的构图在稳健中求奇特,于险绝中见平整,他把中国画“三远”的构图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他往往提高视线的角度,“平远”构图,多采取俯视角度,这样,视野开阔,平淡中倍增缥缈的感觉,尺幅之中,山河无尽。作“高远”构图也是如此,先俯视,尔后眼光往上作仰视,打破了单一的空间透视,真有下揽深谷、上突危峰的气概。他十分注重上下的位置,这也是俯视角度带来的构图上的创新,他的画通常很“满”,但却“满”而不塞,并且恰到好处地用云带、水流等作空白透气,在“满”的构图上作纵深的刻画,用密密沉沉的笔墨造成一种幽深神秘的气氛,笔墨深处似乎隐隐约约还有更深、更大的空间,这才是龚贤的笔、墨、丘壑浑然一体的气韵。

清·石涛《山水图》
龚贤以南京地区的山水为本,创造出有地方特色的山水画,他是当之无愧的“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所谓的“金陵八家”,把龚贤列入首位。其实,“金陵八家”只是生活在南京的八位风格不尽相同的画家,他们的成就高下不一,无论从艺术水准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无法和龚贤相比。
石涛也好论画,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淋漓尽致地说着画画的道理,他说得很玄,但落实到画上,却不见了虚玄。他认为“笔墨当随时代”,于是义无反顾地用自己出色的笔墨树立了一种时代的风气。石涛的笔墨气度和格局不大,也不见得精致,然而却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很中看,很耐人寻味,很经得起推敲。他使出浑身解数来促成笔墨的变化,十分注意笔线干湿的混合,线形的破墨;对皴法的排布,更是在行,横、竖、斜、直无不如意。他又极关心点子的作用,他的散点醒目提神,聚点沉郁豪气四溢,满山遍野、铺天盖地而来的聚散无定而错落有致、大小不一而相处和谐、没头没脑而有眼有板的点子,令人惊心动魄。另外,细劲的山草,轻盈的水草,干枯的芦苇,全是为画面增色的笔墨。石涛的山水画构图丰富多彩,他抱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宗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师造化的法门,在变化多端的山川树木形象中,经营位置也变化多端,和谨守“三远”构图法的传统山水画,显然有了不同。石涛笔墨和构图的多变、丰富,使当时“正统派”的领袖王原祁也深深地折服。
石涛的花鸟画也独具一格,别开生面,在“野逸”的审美趣味里和八大山人左右相映,光彩照人。石涛的墨竹,粗阔滋润,大来大去,笔法壮实,厚重中不无清逸,说自己画墨竹如从作野战,略无纪律,以意为权衡,以情为中心。他在京师作大幅墨竹,当时最负盛名的正统山水画家王原祁为之补坡石,待遇之隆,可见一斑。石涛的墨梅,风姿绰约,笔精墨妙,双钩兰花,沉静灵活,显示他线条的功力。石涛的荷花,没有八大山人的狂肆,以自己独特的线条,勾花朵,画花蕾,出叶茎,以焦墨作叶茎参破大团淡墨,荷叶的笔情墨趣极富神采,有时双勾叶茎,淡墨画叶边,也有不同凡响的姿色,加上他那出色到无人可及的水草和令人心醉的小墨点,画龙点睛般地使整个画面生趣盎然。石涛的花卉小品,是不经意中的惨淡经营,在依情随兴、优哉游哉间,机锋迥出、逸气透溢纸间。他画的题材很多,梅、桃、牡丹、菊花、玉簪、海棠、水仙、王兰以及蔬果,造型独特,他把对形象的理解化作对笔墨的理解,也即形象地成为他体验笔墨的媒介,因此,处处涉笔成趣。

清·石涛《山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