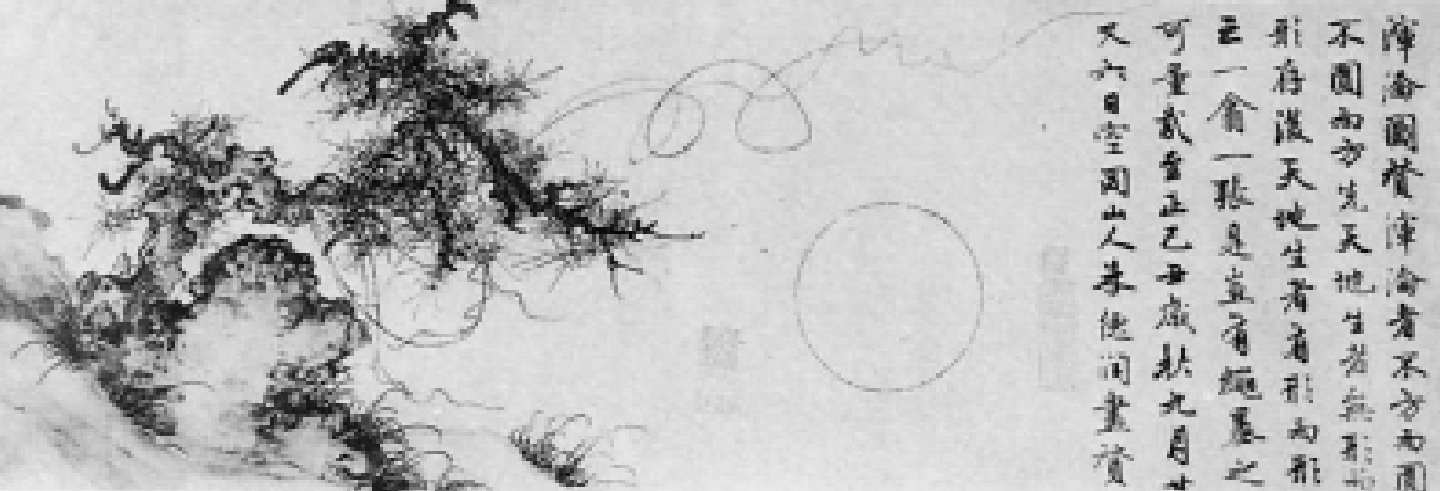第二十章 中得心源(上)

元·黄公望《山水图》
让赵孟 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山水画上改革的突破口——李成、郭熙一系的画法,被自己顺手拾起的另一种传统——董源、巨然一系的江南山水画派所超越,甚至大有掩盖、吞没的趋势。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也即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元四家”,都倾心维护董、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将江南山水画派推向了山水画发展的高峰,足以和先前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的北方山水画高峰并峙。两座高峰,熠熠生辉,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
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山水画上改革的突破口——李成、郭熙一系的画法,被自己顺手拾起的另一种传统——董源、巨然一系的江南山水画派所超越,甚至大有掩盖、吞没的趋势。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也即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元四家”,都倾心维护董、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将江南山水画派推向了山水画发展的高峰,足以和先前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的北方山水画高峰并峙。两座高峰,熠熠生辉,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
黄公望是公认的元代董巨系统的大画家。我们认识黄公望是从他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开始的,那是他八十二岁时的作品。《富春山居图》与董巨的传统有渊源,但渊源只是借鉴,或者说是发展的途径。黄公望的伟大和不朽在于他创造了自己,创造了元代江南山水画的格局,创造了可被后人继承的传统。他从传统中来而最终也成为传统,是他善于学习传统,善于化解传统,善于摆正自己和传统的关系的结果,而这些都是创造自己的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理。黄公望年轻时就认真学习董源、巨然,这一点历史几乎没有记载,谢稚柳先生《元黄子久的前期画》一文,昭示了黄公望早期学习董巨的情况。《溪山暖翠图》和《山水图》,经谢的考证确认为黄公望前期的真迹。谢说:“这两图是同一个面貌,笔墨一致,可以看出是同出一人之手的同一时期所作,与上列(指黄《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等七十岁以后的作品)的黄子久画笔相比,就显得一个苍皮老干,而一个是新条嫩枝……它的表现与晚期的不同,在于不是清空而是迫塞满纸的情景,不是简括而是繁复的描绘,不是深沉敛气于骨的而是温润柔和的笔,不是精简地惜墨如金而是一片湿晕的墨痕。”(见《鉴余杂稿》)谢文的几个“不是”、“而是”的排比,把黄公望前期成熟的风格描绘得确切无疑。黄公望早年曾从赵孟 学画,他自己曾题诗“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可见他有可能受到赵孟
学画,他自己曾题诗“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可见他有可能受到赵孟 耳提面命的指授,因此,黄公望早期画中的董巨成分,就有赵孟
耳提面命的指授,因此,黄公望早期画中的董巨成分,就有赵孟 对董巨的理解。《溪山暖翠图》迫塞满纸的构图和他后期《天池石壁图》相似,所不同的是笔墨。《溪山暖翠图》的笔墨于滋润温和中见骨力,生机勃勃,充满着青春气息,是元代江南式山水画成熟前的产物,它的总体格调倾向于董源,又有意无意地夹杂着元代初期的某些东西;《山水图》也是如此,两图的画法相近,同样显示出黄公望早年的绘画功力,从这些无可挑剔的写实笔墨中,既能领略董巨的姿色,又可细辨出成熟的黄公望的某些特征,诸如丛树的排列、树的姿态形状、空勾的矾头、圆苔点的分布、竖苔点的安插、披麻皴线的走向和疏密等等,都透露了非黄公望莫属的信息。这两幅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品,为黄公望早期的面貌提供了实物证据,让我们看到了元代江南山水画派趋于成熟的台阶。
对董巨的理解。《溪山暖翠图》迫塞满纸的构图和他后期《天池石壁图》相似,所不同的是笔墨。《溪山暖翠图》的笔墨于滋润温和中见骨力,生机勃勃,充满着青春气息,是元代江南式山水画成熟前的产物,它的总体格调倾向于董源,又有意无意地夹杂着元代初期的某些东西;《山水图》也是如此,两图的画法相近,同样显示出黄公望早年的绘画功力,从这些无可挑剔的写实笔墨中,既能领略董巨的姿色,又可细辨出成熟的黄公望的某些特征,诸如丛树的排列、树的姿态形状、空勾的矾头、圆苔点的分布、竖苔点的安插、披麻皴线的走向和疏密等等,都透露了非黄公望莫属的信息。这两幅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品,为黄公望早期的面貌提供了实物证据,让我们看到了元代江南山水画派趋于成熟的台阶。

元·黄公望《仙山图》
黄公望七十三岁时作的《天池石壁图》,它和早期的《溪山暖翠图》有着同样饱满的构图,不同的是笔墨。这种不同的笔墨与个性习惯有着关联;这种关联不仅表示时序的先和后,法度的稀疏和密致,意气的稚嫩和老练,而且是绘画意识的根本性的转变。《溪山暖翠图》在山水的写实上费尽了心思,它山中停云,树间腾雾,浓淡深浅,阴阳向背合于造化,弥漫着活脱灵动的生趣;当然它也不忘突出一些书写性的笔墨,这正是元代前期的绘画意识,造化和心源的位置是造化在先,心源在后,尽管心源的成分比宋代要多得多,但尚未越出造化。《天池石壁图》洗去了许多让人感觉逼真的细枝末节,它把借山水形象的线性笔墨的情绪宣泄放在首位。左下端作为近景的几株大松树几乎不讲究真实的结构,靠着树身和夹在树枝间的针叶,表示了他是在画松树,真实的结构已化成象征性的笔墨结构了;左和右同是近景的过度,用清晰的笔墨表现出含混的空间。至此,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黄公望的意图不在实而在意,不在景而在情,不在造化而在心源。近景后,山逐次向高,一层一层,山石夹树,山石圆方交错,皴法如写字一般,线条的疏密长短,苔点的聚散阔狭,墨色的枯润轻重,就情随意,层层高扬,间或顾左盼右。明明是在表现造化,却置造化于不顾;明明是在敞开自己的心源,则又要披上造化的外衣,黄公望在造化和心源的观念上是心源为本,造化为用,心源其里,造化其外,所以他画得轻松愉快。评者谓:寓乐于画,自大痴始。

元·黄公望《天池石壁图》
黄公望是把山水画皴法推向情感化、心绪化的重要人物。绘画线条的情感化、心绪化是绘画书写性的核心和极致。元初崇尚的绘画书写性,只看重书法线条的美观性在绘画上的运用,画家们也在此尝到了宣泄的甜头,而黄公望使心源膨胀而又不想太伤造化的作法,是赵孟 所想而未竟的事业。以披麻皴为特征的江南山水画派被黄公望出神入化的表现证实了它的优越性,不仅是因为与画家所处的造化相似,重要的是利于心源发挥,以致从元初的处在卷云皴的下风,到分庭抗礼,最终独占鳌头。
所想而未竟的事业。以披麻皴为特征的江南山水画派被黄公望出神入化的表现证实了它的优越性,不仅是因为与画家所处的造化相似,重要的是利于心源发挥,以致从元初的处在卷云皴的下风,到分庭抗礼,最终独占鳌头。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绘画巅峰时期的巅峰之作,是情感化、心绪化的代表。《天池石壁图》在《富春山居图》面前,显得呆板、木讷,《富春山居图》完全达到了情绪化笔墨的自由王国;用心源去吞吐造化,让山水形象在情绪化的笔墨里显出无比的辉煌。《富春山居图》洗练而神采飞扬的皴法令人回肠荡气。当我们细细咀嚼着图中的每一段景色、每一组形象、每一片皴法、每一根线条,都会感到精神火花闪烁的神奇力量。在那里,真正体现了沉着痛快的书法笔情和山水形象交融的风采。黄公望作此图,断断续续地费了几年的功夫,他在展卷挥毫时,把专注化为不经绘画之意的心绪宣泄之中,可见他言明的“得暇”,却实在是要等候“兴之所至”的创作最佳时机,因而完全是呕心沥血之作。我们注意到有多处只存勾勒而未能完成“填札”,多处皴法尚未再作深入,其实是碍于心绪而无法下笔的留白,它给后人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无尽的想象天地。毫无疑问,《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山水画的最经典的杰作。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与黄公望差不多同时的吴镇。
如果说赵孟 的董巨,只注意开发董源的话,那么黄公望的董巨也只开发了赵孟
的董巨,只注意开发董源的话,那么黄公望的董巨也只开发了赵孟 的董源,尽管他挖得很深,但于巨然仅能及皮毛。原因仅仅是为了突出笔线的地位。不知这种矫南宋水墨混沌之枉是否过正,他引出笔性的欢快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功绩,但不能因此掩盖其漠视墨色的瑕疵,其矫枉过了正,必有人出来矫其过,那人便是吴镇。
的董源,尽管他挖得很深,但于巨然仅能及皮毛。原因仅仅是为了突出笔线的地位。不知这种矫南宋水墨混沌之枉是否过正,他引出笔性的欢快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功绩,但不能因此掩盖其漠视墨色的瑕疵,其矫枉过了正,必有人出来矫其过,那人便是吴镇。
吴镇对董巨的热情丝毫不减黄公望,不过,他眼中的董巨的天平是倾向于巨然的。吴镇重视墨色的运用和发挥,他把墨色作为表现禅味的绝佳载体。这位自称和尚、沙弥的画家,对墨色是极为敏感的,他的山水画作品,有着极为出色的墨色分辨力和层次感,有着极为丰富的变化手段和表现方式。他施墨大处不惜重新拾起被他的前辈和同仁废弃不置的南宋院体水墨的长处,并加以改良、发展,变空旷无物的粗糙墨块为流转、富于动态、可辨五色的精美绝伦的墨色。小处与笔法交混,用小渲染去衬托大笔法,用小的墨块结构去完成笔线无法达到的表现力,用细微的墨色变化积聚成大的笔墨能量;用墨色来统摄全局,增强气氛,加深意境。他发挥笔线情绪时,注重墨的效果,所以,董巨的皴法在他手里,变得壮阔起来。而且,由于考虑到墨色的效果,他的用笔,滋润丰腴,笔线间浅深淡浓的变化十分明显,饱蘸墨色,水分充沛的笔法,需要相当深厚的控笔能力,这也说明了吴镇笔墨造诣的不凡。

元·吴镇《双桧平远图》
在元四家中.吴镇的绢本作品要多于其他三位,可以说,在元代的文人山水画家中,吴镇是最善于在绢本上演绎自己感情的画家。也许是绢上作画更能显示水分的特殊作用,也许是吴镇在绢上也能有效地突出线条的功力,也许两者的结合能更精确地表现出吴镇的审美追求。总之,吴镇在绢素上确实留下了赏心悦目的佳作。
《双桧平远图》是大幅绢本,极有北宋的气派,构图十分奇特,在突出了近景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去渲染远景,使近景的描绘坚实,且不孤单,远景开阔辽远而不空泛。吴镇以远实衬托近实,出色地运用了笔墨的浓淡和景物的大小来营造一个奇特的笔墨空间。两株桧树,顶天立地已见气势,一前一后,直凛凛向上,凌云排空,于上端分出各自的俯仰姿色;树干的画法很写实,轮廓线间有细淡的干皴,绢质地上的干笔易燥,而吴镇的干皴却画得很清秀,那是淡而轻,细而密的干笔以皴当擦,徐徐画出,复笔多处的深面为阴,留白处为阳,中间层次随着笔的多寡而丰富,加上清淡的烘染,树干的质感神色极为逼真。元代画家不把逼真当作绘画的目的,但逼真对画家来说总有一种满足感——技高于人毕竟不是丑事,而吴镇的逼真又是建立在笔性墨色美的基础上的,这就更令人心悦诚服地表明:画家追求的象外之趣,完全可以不游离于象的。既然“意足不求颜色似”,那么同样具有充足的意又不失形物的似,岂不两全其美?从两株桧树往远看:弯曲的溪流、起伏的山峦、丛树密林、村落幽径,俨然是一幅出色的水墨平远山水图。和树干一样,山石细皴和淡渲结合,苔点密集,浓淡分明,层次井然。《双桧平远图》作于泰定五年(1328)吴镇四十九岁。是他存世墨迹中最早的作品,可见吴镇的早年,在写实上是下过工夫的,也可见吴镇对元代新的绘画审美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元·吴镇《渔父图》
吴镇喜欢画水乡景色,故多有渔父、渔隐的题材。《渔父图》和《秋江渔隐图》,同是绢本大幅,前者湿笔淡皴,重渲染,笔墨滋润丰满,是董源和南宋水墨山水的调和体,用吴镇自己的情调把董源的披麻皴大规模地湿化;把南宋水墨山水的墨色大规模地收缩、精练,调和成墨色淋漓于笔法之中的吴镇样的披麻皴式山水,提高了墨的境界又发挥了笔的精神。后者干笔轻擦,淡渲染,笔墨劲爽干练,是吴镇收敛墨色、滤干水分、突出董巨、淡化南宋水墨山水的一种,看上去是他的别调,其实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水墨意识。此图中,前景三棵松树,画得骨法显眼,线条遒劲,老皮苍干,极富笔趣;山石的勾勒,也是笔法灵动而不失厚实。引笔起伏间倍见感情色彩,淡皴的微妙处处表现出他对墨色的关注,细小的墨色变化,时时在闪烁着墨色的光辉,这种光辉在重苔点的映衬下更散发出微茫中的大精神。从这两幅画中,可以看出吴镇无论是走湿润的极端,还是以干当湿,以枯作润,都是为了表现他既强调笔法又不偏废墨色的审美追求。这一点,在绢本作品上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于纸本作品,他也一如既往,执著地追求自己的审美理想。《渔父图》是他不多见的手卷形式的作品,因为是纸上作画,所以水墨渲染的成分有所减弱,他在绢素上那种淡皴淡渲的拿手戏,放到纸本上同样地得心应手。不知他有没有感觉到纸上的效果更佳?从《渔父图》中,可以看出他笔法的厚实程度和淡墨的魅力。他无须像绢本上那样用淡细皴复合兼以淡擦来以绢代纸地仿求他人纸上的笔法效果了,他的笔力得到空前的发挥,墨法也得到空前的发挥,他的淡皴笔、淡墨染兼以淡擦相配合而浑然天成,皴笔变得壮阔起来。笔墨在他手中有着心想事成般的快意,他可以用极淡的笔法去表现苍凉的意境。苔点可以淡淡地积聚,可以有层次地因地制宜随兴而下,并同皴线交相辉映,可以尽兴地用他自己轻盈而极有内蕴的线条画上十数扁舟,十数渔翁,并与画中人共同感受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的欢快,可以不用界尺画茅舍、画水榭、画楼阁,把直率寄于横线竖线的构造之中。此等自由,此等愉悦之情,在纸上似乎来得更为直接,更为彻底。

元·吴镇《秋江渔隐图》
其实,对吴镇来说,纸绢是一样的,一样能够表现,异曲同工,就不必去弄清他于纸于绢的孰亲孰疏了。不过,我们总觉得这幅《渔父图》也许是他此生的压卷之作。
李成、郭熙一系的北方山水画派,也有上佳的表现,只是因为“元四家”而显示不出耀眼的光彩。
元代李郭画派与北宋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赵孟 倡导的书法笔性线条全面介入绘画的结果,最明显的变化是画家的个性得到了突出,个人风格逐渐鲜明起来。从曹知白、唐棣、朱德润这三家看,学李郭,各见面貌。曹知白以枯淡苍秀的笔法,把卷云皴弄得干淡毛茸,一改原本清润劲爽的李郭风貌为燥辣迷茫。因为淡,所以多复笔积墨,因为干,所以皴多从藏中见露,清润消失了,静穆随之而来,劲爽消失了,浑厚随之而来。学李郭的曹知白的成功,在于他有不二的曹知白风格。另外,曹知白略参入董巨的意思,也是变李郭出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棣是赵孟
倡导的书法笔性线条全面介入绘画的结果,最明显的变化是画家的个性得到了突出,个人风格逐渐鲜明起来。从曹知白、唐棣、朱德润这三家看,学李郭,各见面貌。曹知白以枯淡苍秀的笔法,把卷云皴弄得干淡毛茸,一改原本清润劲爽的李郭风貌为燥辣迷茫。因为淡,所以多复笔积墨,因为干,所以皴多从藏中见露,清润消失了,静穆随之而来,劲爽消失了,浑厚随之而来。学李郭的曹知白的成功,在于他有不二的曹知白风格。另外,曹知白略参入董巨的意思,也是变李郭出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棣是赵孟 的同乡。他学李郭,实际是从接受赵孟
的同乡。他学李郭,实际是从接受赵孟 开始的,也就是说,他的起点在赵孟
开始的,也就是说,他的起点在赵孟 消化过的李郭。但是,唐棣又很注重画面的古气,他不仅经常使用绢本作画,而且还一改赵孟
消化过的李郭。但是,唐棣又很注重画面的古气,他不仅经常使用绢本作画,而且还一改赵孟 的清逸,以旷放劲挺的笔法去接近李郭的长松巨木,多多益壮的画风。有趣的是,唐棣时不时地要露出赵孟
的清逸,以旷放劲挺的笔法去接近李郭的长松巨木,多多益壮的画风。有趣的是,唐棣时不时地要露出赵孟 式的东西,又时不时要掩藏真正的北宋风情,在对前辈和古人的藏露之中,一股属于他自己的格调油然而生。唐棣有伟岸的气派,他说了他对李郭的崇敬;唐棣又有俊逸的神采,他用赵孟
式的东西,又时不时要掩藏真正的北宋风情,在对前辈和古人的藏露之中,一股属于他自己的格调油然而生。唐棣有伟岸的气派,他说了他对李郭的崇敬;唐棣又有俊逸的神采,他用赵孟 的新画风熔铸了自己。元代的李郭一系画法,传到朱德润,已经是能与元四家接轨的成熟而纯正的元风了。不需要躲躲闪闪地回避什么传统,也不必故作姿态去强调什么传统,无论李郭,也无论董巨,作为传统的符号已经开始通融。朱德润的《松溪放艇图》和《林下鸣琴图》的树法还留有一些李郭的形象特征,其笔法转为圆润,已参入董巨因素,山石的卷云皴中夹着似点似线的短皴,是李郭影子的董巨实质,著名的《秀野轩图》,画得温敦清润,皴法完全是卷云式的披麻化,芥叶树,圆苔点,笔随意生,至此,李郭风范已和董巨合二而一了。
的新画风熔铸了自己。元代的李郭一系画法,传到朱德润,已经是能与元四家接轨的成熟而纯正的元风了。不需要躲躲闪闪地回避什么传统,也不必故作姿态去强调什么传统,无论李郭,也无论董巨,作为传统的符号已经开始通融。朱德润的《松溪放艇图》和《林下鸣琴图》的树法还留有一些李郭的形象特征,其笔法转为圆润,已参入董巨因素,山石的卷云皴中夹着似点似线的短皴,是李郭影子的董巨实质,著名的《秀野轩图》,画得温敦清润,皴法完全是卷云式的披麻化,芥叶树,圆苔点,笔随意生,至此,李郭风范已和董巨合二而一了。

元·吴镇《渔父图》(局部)
李郭风范消解在董巨风范之中,是元代书法笔性入画的必然结果。李郭和董巨并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董巨的强大,是因为山水画仍难改它发祥时的老传统——地域。李郭画派南下后有不俗的成绩,主要是它有书法笔性方面的潜力,而一旦同样有潜力又具江南形象的董巨画派的崛起和发展,势必会出现强龙难斗地头蛇的局面。我们更应看到李郭画派给董巨画派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倪瓒的惜墨如金和李成的惜墨如金,是否异曲同工?倪瓒的折带皴是否卷云皴的刚折化?倪瓒的枯枝是否有李成的成分?王蒙的解索皴是否卷云皴和披麻皴的综合?仔细寻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否引入李郭的某些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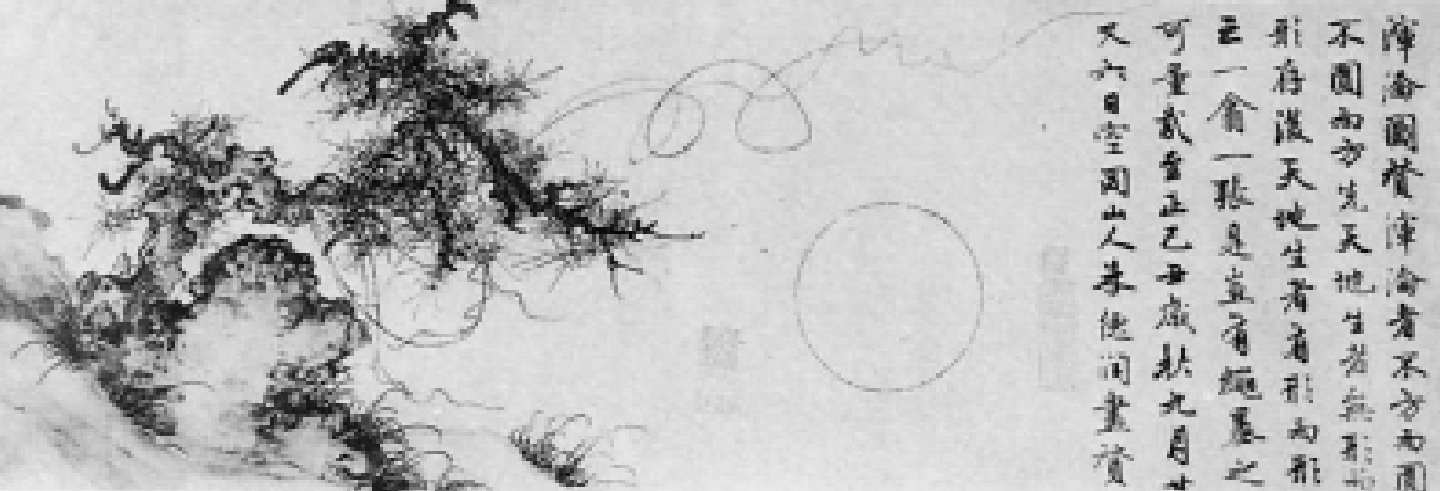
元·朱德润《浑沦图》
李郭画派在北宋独领风骚,于金代也久盛不衰,到了元代被演绎得如此出色,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至明清,它还常常出现在名家高手的作品中。

元·唐棣《雪江归棹图》

 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山水画上改革的突破口——李成、郭熙一系的画法,被自己顺手拾起的另一种传统——董源、巨然一系的江南山水画派所超越,甚至大有掩盖、吞没的趋势。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也即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元四家”,都倾心维护董、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将江南山水画派推向了山水画发展的高峰,足以和先前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的北方山水画高峰并峙。两座高峰,熠熠生辉,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
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山水画上改革的突破口——李成、郭熙一系的画法,被自己顺手拾起的另一种传统——董源、巨然一系的江南山水画派所超越,甚至大有掩盖、吞没的趋势。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也即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元四家”,都倾心维护董、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将江南山水画派推向了山水画发展的高峰,足以和先前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的北方山水画高峰并峙。两座高峰,熠熠生辉,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