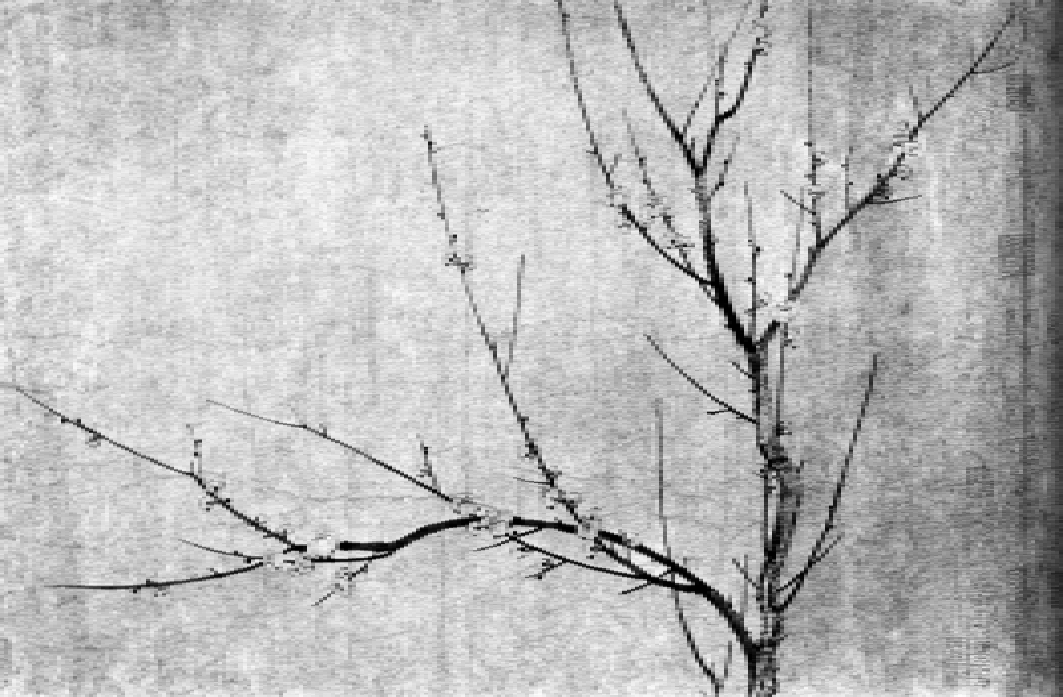第十五章 院墙内外

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局部)
徐熙在南唐独占鳌头,但江南花鸟画姿色繁多,并非徐氏一门尽掠其美。嘉兴唐希雅,多得郊野真趣,与徐熙并称“江南绝笔”;天台钟隐,“好画花竹禽鸟以自娱,凡举笔写象,必致精绝,时无拟者”。两人各有解数,纵使不能出徐熙一头,也旗鼓相当。江南花鸟画画坛呈现争艳斗辉的局面,是花鸟画成熟之际,转而追求风格的迹象。因此,徐熙曲高和寡,后继乏人,江南的花鸟画也不会因此而寂寞。但一统天下后的宋王朝,却盛行西蜀黄家花鸟画体制。这是因为以黄筌为代表的西蜀宫廷花鸟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自行完善,产生一套完整的技法体系,包括教育上的承传,它不仅是家族的,也是皇家的,更是社会的。南唐的花鸟画艺术性高,也具多样性,却缺乏体系性。北宋的第二位君主太祖也曾要求画院以徐熙为准,徐熙的技艺却没有推行,是因为不宜推行,实际上,此后的花鸟画诸多技巧中,惟独徐熙的“落墨为格,杂彩副之”没有继承者。所以,宋初的翰林图画院主持者眼力不俗,选择黄筌一系,完全是因为它具备发展的空间。
尽管翰林图画院以黄筌的画法为官方样板,尽管黄筌画法代表了写实成果,但写实的发展势头正旺,人们不会满足已有的画法。宋代初期,画家们对自然的兴趣依旧浓烈,山水画家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师古人不如师造化。花鸟画家当然不甘居后,他们也树起了师法造化的大旗。赵昌自家的园圃栽满各式花草,每当清晨,花草在朝露中的鲜艳娇美之态,难以名状,赵昌绕栏槛谛玩,调色,对花作画,备有生意,得号“写生赵昌”。赵昌首创枝折花卉,将花卉作枝折状,而姿色如沐朝露,生意盎然。他还在色彩的运用上独辟蹊径,被称作旷世无双的敷色大师。评论认为:赵昌的花卉在形似中得神似。易元吉在居所后面的空地上,挖池、凿塘,间以乱石丛花,流篁折苇,用人工造设了自然生态,蓄养水禽,每天从窗里仔细察看水禽的动静游息,以志画笔之妙。他为了画好獐、猿,在荆湖一带孤身闯入深山老林,观察猿、獐、鹿等野生动物,他跋山涉水,不避辛劳,寓宿山家,经年累月,将猿、獐之神态,惟妙惟肖地移在绢素上。

北宋·易元吉《聚猿图》
赵昌和易元吉都是宋初成功的画家。他们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师造化的结果,其内在的意识是为了超越前人,赵昌感于黄筌的成功而独辟写生,独倡敷色,独创折枝;易元吉叹服赵昌的花果,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你追我赶,争前抢先的风气,大大地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使画家发愤图强的另一因素是画成为获名得利的一种途径,当易元吉蒙诏入殿作画时,如释重负地说:“吾平生至艺,于是有所显发矣!”翰林图画院是官方的绘画机构,也是画家们梦寐以求的地方。纵观两宋的画院,容纳、造就了多少有才华的画家,使院体画成为两宋绘画的主流和代表。
北宋最富创造精神的花鸟画家崔白是宋神宗熙宁时的画院学艺,元丰时的画院待诏,他有着极为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到的笔墨写实功夫,“凡临素多不用朽,复能不假直尺界笔为长玄挺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七)。他善画花竹翎毛,熙宁初,崔白和艾宣、丁贶、葛守昌画垂拱殿御扆鹤竹各一扇,崔白技压群芳,因此,蒙恩画院学艺。宋神宗赏识崔白,崔白却并不领情,以性疏阔度,笔墨不能执事,坚持不就;宋神宗让步,“特免雷同差遣,非御前有旨毋召”,崔白才勉强应命。崔白表现出了艺术家的个性。

北宋·黄居寀《山鹧棘雀图》
宋初的画院,尽管人才济济,但未断五代的余绪。五代的花鸟画是写实上的成熟期,黄筌的《写生珍禽图》,鸟、虫、龟类的形象如真,入宋后黄居"的《山鹧棘雀图》,应是一件有完整意境的大作品,但禽鸟之间缺少呼应,缺少关系的表述,是一幅有景色场合的禽鸟栖息图,生动性不足,就无从论及意境了。黄居"的《山鹧棘雀图》所传出的信息是:北宋的花鸟画有写实的高度,却留下可深入、提高、尚待精到的空间;有意境的框架,却亟须填补、充实。

北宋·崔白《禽兔图》
画史上说:“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为程式,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宣和画谱》卷十八)崔白在画法上以更鲜明生动的写实性,精湛到几乎无懈可击的技巧,来为宋代特色的花鸟画定格;在意境上去繁缛,注重主题的深入浅出,为宋代特色的花鸟画开拓道路,如此与其说是改革,毋宁说是建设。崔白为宋代的院体花鸟画奠定了基础。崔白的《寒雀图》,以笔法老练生动的枯树寒枝为中心,一群小雀各展其姿,无一雷同,关系密切,呼应得体,浑然天成;画法十分灵秀,淡墨轻染,略敷淡色,线条勾勒与色、墨渲染融为一体。和黄筌、黄居"的禽鸟相比,显然要高出一筹。崔白的另一幅《禽兔图》,秋风劲草,竹树摇曳,双禽迎风鸣叫,老兔回首相视,以气氛烘托主题,禽与兔两组动物对应成趣,画法精湛,意境的塑造也极为成功。
崔白的艺术成就,表明了花鸟画从五代的技巧成熟,进入技巧的完善,又从技巧的完善,开始了意境方面的探索。北宋中期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文学上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影响了绘画,它将绘画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形象化的文学境界。绘画和诗结缘,使绘画获得了丰厚宽广的表现领域,同时也提高了绘画的品味,这一点在花鸟画上尤为突出。

北宋·崔白《寒雀图》(局部)
和崔白一同变革花鸟画的崔慤,是崔白之弟,另外还有崔白的学生吴元瑜。
吴元瑜是位武将,曾任光州兵马都监,武功大夫,合州团练使,却精于文墨。他不是画院中人,因其画的出色而颇具影响力。《宣和画谱》说吴元瑜“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去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可见吴元瑜比老师崔白更放逸,更重视胸臆的表露。宋徽宗赵佶,不是个称职的皇帝,但却是位很有才华的画家。由于他的误国,丢失了大片疆土;也由于他的身体力行,他的支援和倡导,北宋末的花鸟画出现了空前鼎盛的局面。赵佶倾一国之力,收罗名画,藏之内府,并时常将名画送到画院,以示学人。院内的画家有机会观摩历代名迹,对画艺的提高很有帮助。赵佶的书画造诣不俗,又明画理,因此,对画院的要求严格。一次,赵佶命画院众使画孔雀,画家们各展技艺,各极所思,画得华彩灿烂,但孔雀升腾墩先举右脚,赵佶认为是错误的,画家们愕然莫测,赵佶指出:孔雀升高,必先举左。其实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师造化的深入已达到了极至的地步。赵佶以天子的身份和花鸟画行家的眼力去治理画院,连花鸟生态的细微节情都要讲究,画家们人人骇服,当然都得竭尽精力以副上意。宣和画院可代表北宋花鸟画的最高水平,这和身兼画家的皇帝亲自参与密不可分,赵佶是功不可没的。

北宋·赵佶《腊梅山禽图》
邓椿《画继》记载赵佶画仙鹤“凡二十,题曰:《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惊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绢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赵佶的花鸟画,是极富思致,又相当写实的,他用生漆点鸟禽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得到几欲活动的效果,也是一种写实的尝试。
南渡后,宋高宗赵构在惊魂未定之际,恢复了画院。南宋的院体花鸟画,接受宣和画院的衣钵,绍兴画院有不少宣和旧人,虽然宣和花鸟画的余晖很是耀眼,但出现在南宋画家身上的变化是发展的大趋势。
李迪在宣和画院任过职,绍兴间复职,他的大幅作品如《雪树寒禽图》、《鹰窥图》,依然保持着北宋晚期宏敞的作风,但从景物的紧凑性、主题和描写对象的鲜明性来看,则是南宋的作风了。北、南宋之交的画家,多有糅合两个时代的特征。南宋花鸟画的尺幅小,突出所描写的对象,在主题鲜明的小空间里,出现了更为精致、更为细腻的表现技巧,这也是南宋花鸟画的一大特色。李迪的《鸡雉图》,一蹲一立两只雉鸡,画得细毛毕现,一丝不苟;林椿的《果熟来禽图》,取果树一角,小鸟栖于枝头,绕尾仰首,果实饱满,禽鸟羽光毛绒,精微得无以复加。
然而,艺术能够逼真,毕竟是用技巧来复述真实;艺术能够乱真,也毕竟不能与真实等同。追求真实须有限度。南宋院体花鸟画的务实写真,是花鸟画发展的成果,也是一个阶段。一旦完善了写实的手段,它必然地要利用写实的技巧成果来攀登更高的艺术层次。
其实,在花鸟画的写实发展方兴未艾的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向写实的更高层次——写意迈进的探索。这种探索开始与写实若即若离,后逐渐壮大,终于自成体系,与称之为工笔的写实画分庭抗礼,但它的真正成气候,则是后话了。

南宋·李迪《禽竹图》
写意相对写实来说,技巧上粗阔疏略,就形象的表述而言,它也始终脱离不了写实的内核,因此,后来就有工笔和意笔的称谓区别。南宋的院体花鸟画,也有受早期写意花鸟画影响的。马远的《雪滩双鹭图》,画得阔略奔放,与当时细密精微的花鸟画迥然相异,该图有数只白鹭现于山谷涧底的老树丛篁间,高枝上还有双雀作下视状。与其说是花鸟画,倒不如说是鸟雀点景的山水画。马远的另一幅《梅石凫溪图》,花、鸟相配,水、石相间,画家有那么一点画鸟的本领,竟用山水画的语言、气度来表达花鸟画的情怀,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这并不是南宋画院的专利,也不是马远的首创,相去不远的北宋即有被称为“江湖小景”的,介于山水画和花鸟画之间的一种式样,山水大背景的花鸟主题,北宋画家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便是一例。此图的花鸟形象十分工致,和同样工致的树竹、芦荻、坡石、江天相匹配,大概是马远的花鸟画渊源所在。马远的阔笔山水树石,和笔法放纵的禽鸟也是相匹配的,可见山水画的风姿决定了“江湖小景”式花鸟画的风姿,又可见山水画、花鸟画,甚至人物画以及其他画科,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被称作梁疯子的梁楷,其《秋柳飞鸦图》,笔法劲动,简练而又生趣,也是南宋花鸟画写意式的别调新装,它和梁楷粗犷豪壮的人物画如出一辙。马远《雪滩双鹭图》中的鹭、雀,《梅石凫溪图》中的凫鸟、梅花,与他山水画笔法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类具有写意意味的花鸟形象,给后来的写意花鸟以启迪。
马远等的花鸟画,是南宋精致、细腻的院体花鸟画的旁支,同属院体画的范畴,说明了南宋院体花鸟画的多样性,两者并行不悖。粗疏的花鸟画在当时没有能力改变院体花鸟画精致、细腻的主流,而只有精致、细腻的院体花鸟画走到了峰巅,没有发展空间之时,才会产生新的花鸟画审美意识,从而构筑新的花鸟画表现体系。
花鸟画的成熟和发展,皇家画院的作用举足轻重,不管统治者出于何种目的来兴办画院,也不管画院的制度是否束缚和限制了画家的创作自由,院体画家在当时成为画坛的主角,却是不争的事实。北宋的中、晚期,不甘寂寞的文人学士们,也为自己的绘画体制努力着。
水墨画起始于山水画,当山水画的水墨意识和技巧完全成熟的时候,花鸟画的色彩意识和技巧也臻完善。从绘画技巧的发展来看,水墨促进写实又是写意的源头;它的绘画意识中充满着强烈的文化因素,在写实的基础上,它可以容纳更多、更深的中国文化情趣。中国绘画发展显示出趋简、趋单纯的轨迹,就是一个不断文化化、人性化的过程。
五代时期,花鸟画的写实技巧,包括对色彩真实的表现,达到了成熟的高度,水墨山水画的巨大魅力征服了人心,花鸟画却不为所动,它把色彩看得至为重要。徐熙在极为写实的落墨形象上,还要表演他另一手色彩写实的本领;徐崇嗣的没骨画,赵昌的五色法,都将色彩的技巧弄得斑斓无比,这些也许都无可厚非。然而,减彩褪色的尝试,也在悄悄地进行中。

南宋·马远《梅石溪凫图》(局部)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榻写》说:“草木敷荣,不带舟碌之采,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花鸟画的水墨画法,没有水墨山水画那么轰轰烈烈,它只是常规下的一种别调,正途外的一种探索。而且,花鸟画的水墨意识,明显地来自山水画,一些和山水画沾边的形象,率先被水墨感染。

北宋·文同《墨竹图》
墨竹是花鸟画进入水墨领域的突破口。被白居易著名的《画竹歌》大加赞扬的萧悦,是位画竹的能手,《历代名画记》说他:“工竹一色,有雅趣。”“一色”和“雅趣”纵不作水墨看,也应是对色泽单纯的追求。
传说墨竹的始创者是五代的李夫人,她被掠后,郁郁寡欢,“月夕独坐南轩,竹影婆娑,辄起濡毫摹写窗棂上,明日视之,生意具足。”事见载于《十国春秋》,虽不足信,但竹影开启画家的心智,从而一试墨竹画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墨竹源出五代,是有根据的。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言之凿凿:“写墨竹于古无传,自沙门元霭及唐希雅,董羽辈始为之唱。”墨竹的画法,得力于毛笔的功能,竹子的形态给书法笔法绘画形象化提供了最佳的条件。元代总结为:“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完全是在表现书法的笔趣,或者说是寓书法笔法于形象之中。唐希雅的书法造诣不俗,往往以书法入画,他学李后主的金错刀行,一笔三过,“画竹木多颤掣之笔,萧疏气韵”。五代画家的墨竹,必不如元代那般圆熟,草创之时,已露出书法笔法的神韵,只待来者。
北宋名臣燕肃,《宋史》称他“图山水罨布浓淡,意象微远。尤善为古木、折竹。”黄庭坚也说:“天章阁待制燕肃始作生竹,超然免于流俗。”从“罨布浓淡,意象微远”,到盛赞他“独不为悦色”的情况来看,燕肃或许是画墨竹的先驱。他用水墨山水的心得去表现墨竹,是游刃有余的。北宋花鸟画利用山水画的成果,取得长足的进步,黄居"画中树木的枝、干,略带稚气,尚未洗净概念化,崔白手里的树木却有眼有板,老干嫩枝,一一分明。山水画树法的成熟,木本花卉由此受益,墨竹的画法,也是从山水画部件之一的丛竹中,逐步移植过来的。
文同能够画山水,毫无疑问,这是他墨竹技巧的基础。文同对竹子的表现方法下过类似宋初画家追求写实的功夫,他在陕南洋州太守的任上,于渭川$%谷千亩竹林间筑庐,观察竹的生态,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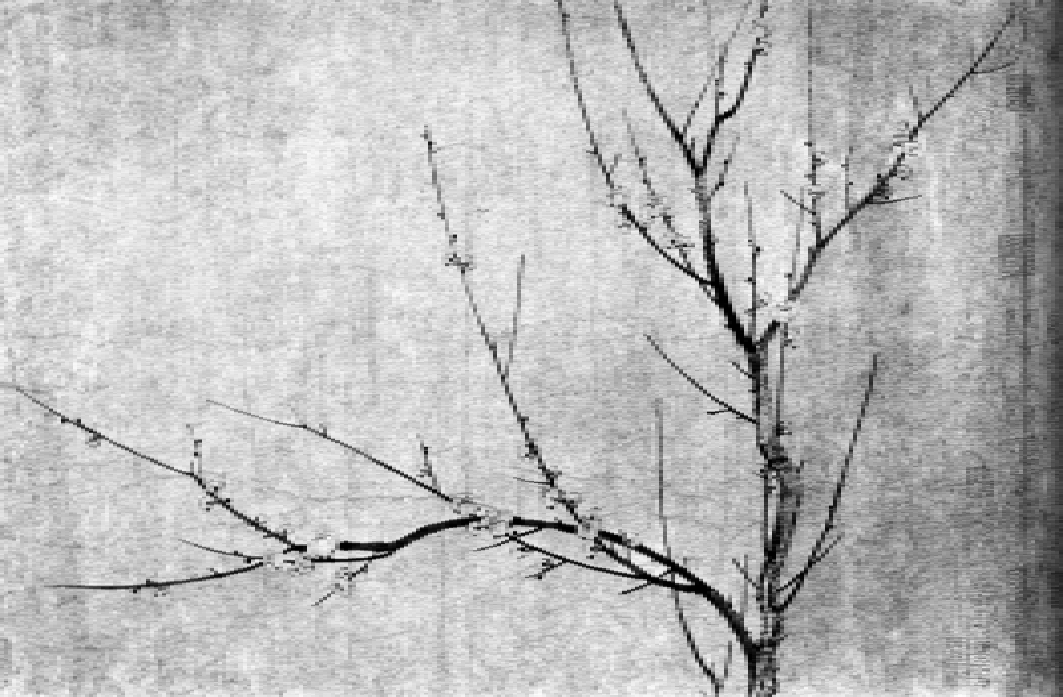
南宋·扬无咎《四梅图》(局部)
文同的墨竹法度迥然,“富萧洒之姿,逼擅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者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与宋画周密不苟的总特征是一致的。从他存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竹节的长势,偃仰的姿态,竹叶向背明暗,一一如真,是实实在在的写实体制。他完全改变了双钩的画法,以墨笔分深淡,所谓的“风格简重”,“淡墨一扫”,当是一种新的风格。真正的“文人画”即肇始于此。首先,它是文人审美情趣的产物,为悦情式的绘画敞开了大门。苏轼说:“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东坡集》卷二十)文人在诗、文不能尽兴的情况下,遂以书画遣之。文同除了诗文的才能外,还“善篆隶行草飞白”,因此,他的画,既洋溢着诗情,又将书法笔意融入其中。唐代就有“善画者必善书”的说法,但此时由于绘画发展上的局限,书法和绘画在画家个性的熔铸上尚不显著,文人与画工的分野不明确。至北宋中叶,才将书法纳入绘画,直接与心源联系起来。郭若虚说:“夫书犹画也,扬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行,君子小人见矣。”(《图画见闻志》卷一)文同的墨竹,充满着书法的笔意,丝丝缕缕都牵动着情感。黄庭坚认为:“韩退之论张长史喜草书,不治它技,所遇于世存忘得丧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发于书。所观于物,千变万化,可喜可愕,必寓于书,故张之书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与可之于竹,殆犹张之于书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当然,文同的用笔与张旭的草书,无甚大关系,但他以及苏轼那种雍容迈逸、壮实厚重的书法笔致,就是“湖州墨竹”的基本笔法。书如其人,画亦然,文同的墨竹,成为画家本人的化身。“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清新出。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苏轼《东坡集》卷十六)“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同上,卷三十一)文同的“其身与竹化”,是在理解竹子的自然属性上所作的人格化处理。这是宋画“穷理”的一个更深层次,前面说的孔雀升墩,是表现自然属性,四时风候的“物理”,反映主客事物的趣味。而人格化的处理,则是在客观的基础上赋予主观的色彩。这种寓主观于客观之中,用心源去塑造造化的意识,使画家与自然的关系,变被动为主动,他们可以观察、体会自然物,但不必拘于自然物。
苏轼从文同墨竹的写实中看到了写意的潜力,从文同墨竹的书法性用笔上看到了表现画家的胸襟心迹的可能性。于是,苏轼也跃跃欲试地玩弄起墨竹来了。然而,毕竟苏轼没有绘画基础,他自叹技不如人,却自负地认为他有笔法上的优势。流传至今的苏轼墨竹,大有争议,因此,苏轼的墨竹究竟是何等模样,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未必是坏事,留下如此诱惑人心的空白,也是有趣的。应该承认,我们在此不惜篇幅大量引用苏轼的文字,是因这些文字由文同墨竹而引发的。文同的墨竹,激发起苏轼对绘画理论的兴趣。苏轼屡屡为文同墨竹题跋,屡题屡有新的感想,发布新的惊世骇俗的绘画理论,他好像发现了绘画审美的新大陆。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画和山水画,早在六朝时期就具有了各自的理论,并在发展中完善了各自的理论,而花鸟画,从它草创到成熟,漫说有体系的理论,即便是带理论色彩的文字也不多见。苏轼的理论,虽着眼于墨竹,却可视为整个花鸟画的理论。有理论支撑的艺术,才是完整的艺术,花鸟画的品格由此而上升。

南宋·赵孟坚《墨兰图》

南宋·郑思肖《墨兰图》
墨竹的种种绘画因素,从技巧到审美,都符合文人的情趣,于是,其他题材的效法开始了。墨梅,也是从水墨山水画中演化而来的花鸟画的一种,它取树的画法为梅干,略参入些书法笔法,双钩树叶的画法为梅花圈法,点叶为梅花的点法。此外,郑思肖的墨兰,赵孟坚的类似白描的水仙,都是文人画家开拓的水墨花卉题材,这些题材的形象,大多与文人性格、情操、趣味相对应,并与文人手里的书法优势的发挥联系密切。郑思肖用兰花来表示自己的境遇,如空谷幽香的隐迹之意;更有甚者,入元后,他竟画露根的兰花,以示异族统治下无干净之土。这未免有些牵强,却是画坛上的千古佳话。
墨写的梅、兰以及水仙,开了南宋末的简练画风,北方金朝王庭均、王曼庆父子的墨竹是正统的湖州派,但也向简和散漫方面发展,这对元代的崇尚书法用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