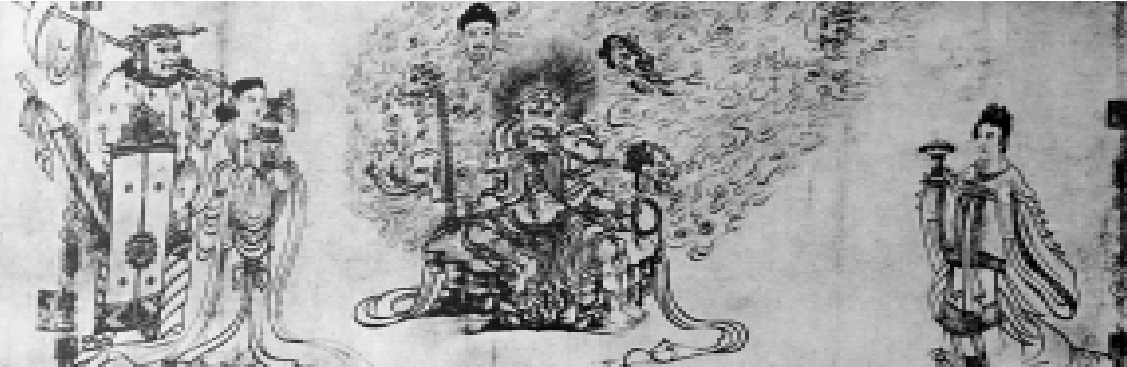第七章 吴带当风
张僧繇是划时代的,他为“疏体”开了个头;吴道子更是划时代的,他完善了“疏体”。北齐娄睿墓室壁画有“疏体”的成分,线条是简练了,但笔法上的提按,尚未见规模。应当承认,张僧繇的“疏体”,是一种摸索,一种探求,他看到了前途,却没有挟着才情去继续深入、扩大,既感奋于这种笔法的“新意”,又难分难舍于习惯的“法度”。开风气之先者尚且如此,后继者的犹豫,就无可厚非了。
从张僧繇到吴道子,“疏体”的进展缓慢。
北齐杨子华“简易标美”的画风,与张僧繇有所衔接,在北朝也许是仅有的“疏体”果实。隋收拾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本来就没有断绝交流的南北绘画,更趋统一。隋代国祚虽短,却名家辈出。绘画的兴旺,不减六朝。张僧繇的传人郑法士、孙尚子都是隋代享有盛名的大画家。李嗣真说郑法士“伏道张门,谓之高足,邻几睹奥,具体而微,气韵标举,风格遒俊。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至乃百年时景,南邻北里之娱,十月车徒,流水浮云之势,则金张意气,……江左自僧繇已降,郑君是称独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郑法士的画“气韵标举,风格遒俊”落在张僧繇的谱上,不会离得太远,孙尚子就不同了,李嗣真说:“孙(尚子)、郑(法士)共师于张(僧繇),郑则人物楼台,当雄霸伯,孙则魑魅魍魉,参灵酌妙,善为战笔之体,甚有气力,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莫不战动,惟须法独尔调利,他人效之,终莫能得,此其异态也”(同上)。战笔,即颤动的笔迹,不是线条曲曲扭扭、断断续续的形状,也不是运笔抖抖颤颤、摇摇晃晃的故作姿态,而是“甚有力气”,行笔轻重分明,起伏间呈现动感,颇具张僧繇的气派。笔法的轻重,出现的线条变化,既可作为一种别调,也可成为独特的风格。

唐·阎立本《步辇图》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初唐的绘画,和隋代紧密相连,阎立德、阎立本的父亲阎毗是隋代的大画家,当时号为臻绝,家传的画风,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变换。阎立本成为唐初最知名的画家,是才气的光芒,以致官拜右相的他让丹青淹没了自己的政绩官声,居高位却屡屡被当画工使唤。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惟认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技。’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本以画为“末技”,其实是耻于与工匠同列,若不以丹青见知,何来仕途的顺畅?从汉开始高官显宦,身怀画技者,代不乏人,由此而成的画家精英,于绘画的发展,功莫大焉。唐代少了个主爵郎中或者右丞相,无关国运,唐代绘画若没有阎立本,初唐一段便会是大空白。《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流传至今,正是阎立本“末技”不朽的见证。
《步辇图》是阎立本的传世之作,考为宋初摹本,从画法和气息上看,是忠于原作的临摹佳作。横卷,画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王松赞干布派来迎文成公主的使者禄东赞的景象,是当时的现实题材,对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生动的记录。画面很简单,四个宫女抬辇,缓缓而来,众宫女持华盖、执长扇拥簇前行。唐太宗仪态庄重,而神色亲和;身材魁伟,虽是坐姿,仍见高大英武的体相。与诸宫女的身材略失比例,是主从有别的惯例。阎立本身为李世民的重臣,对明主敬仰有加,但又对李世民的风度举止、个性情操,十分熟悉,对李世民汉藏和亲的政策十分理解,因此选择了吐蕃特使迎辇的场面。唐太宗坐在辇上的形象比高高在上地坐在龙廷宝座上的形象要随和得多,亲切慈善的神态也随接而至。李世民和禄东赞的形象真实,可作肖像画观,记载上的阎立本《凌烟阁功臣图》和《秦府十八学士图》以及今天仍可一睹的《历代帝王图》,都是肖像画。阎立本是此道的专家,画李世民、禄东赞两人,是驾轻就熟的。线条有顾恺之、陆探微的遗风,但已不再“紧劲连绵”了,线条劲而不紧;张僧繇的“疏体”在这里,只存“疏”,没有“点曳拂斫”的笔法变化,徒具“疏体”之表,未入“疏体”之里,看得出对张僧繇的态度,还是小心翼翼的。阎立本既不愿放弃由来已久的顾、陆遗风,又赞同张僧繇的疏简,《步辇图》里线条的布排,简括明了,和阎立本称许杨子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同出一辙。裴孝源认为:“阎师张,青出于蓝,人物、衣冠、车马、台阁,并得其妙,历观古今,法则巧思,惟二阎,杨、陆,张家父子,稍居其次。”(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张彦远颇不以为然,说:“二阎、杨、陆,虽则尽美,张家父子,品第居最,裴云:张在阎下,此论未当。”(同上)裴孝源为初唐人,与阎立本同时,扬阎抑张,或是当时的看法,说阎立本师承张僧繇,就不知所据了,说阎立本有出蓝之胜,指出了张、阎的不同,说明初唐尚未习惯于张僧繇的用笔方法。张彦远见过吴道子画的,深知“疏体”的妙处,他的扬张抑阎,是看到了阎以后的绘画,看到了张僧繇笔法的点滴光照在吴道子身上的辉煌。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从阎立本到吴道子的百年间,绘画发展神速,山水画的高古形式——青绿山水,被李思训收拾得像模像样了。花鸟画也蠢蠢欲动,准备独立。人物画的变法,悄然无声,却有条不紊。章怀太子李贤墓室壁画,画法于精致中不无旷逸,人物形象若生,尤其是群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序,神情和谐,把握空间的技巧十分高明,笔法娴熟,线条流利,较阎立本有更多的变化。虽然李贤墓室壁画的作者名声地位不及阎立本,但技巧显然要高出一头。这说明阎立本之后的唐代绘画水平又进了一筹。
吴道子还未亮相,他的开场锣鼓就已经响起来了。阎立本以后,出现了不少促成吴道子的迹象。张师孝对吴道子有些影响,张彦远说他“尤善画地狱,气候幽默。师孝曾死后复苏,具见冥中事,故备得之。吴道子见其画,因号为地狱变”(《历代名画记》卷九)。为吴道子的“地狱变相”作了示范,他“迹简而粗,物情皆备”(窦蒙语,同上)的画风,未准也对吴道子“疏体”作了些启示。而师法张僧繇的范长寿,“掣打捉笔,落纸如飞,虽乏窈窕,终是好手”(同上),运笔的精致高昂,快疾生色,得张僧繇之神,这条道是直通吴道子的。还有一条线是从西域来的,隋代画家尉迟跋质那来自西域,其子尉迟乙僧善画外国人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同上)。小则随顾、陆,大则类张僧繇,张僧繇曾接受过西域的某种画法,尉迟乙僧的“洒落有概”,和张僧繇应是一个渊源。这条道也直通吴道子。
另外,刘孝师的“点画不多,皆为枢要”(同上),王定的“笔迹甚快”,“往往惊艳”(同上),王知慎的“笔力爽利,风采不凡”(同上),等等,都具备“疏体”迹象,都应当看作是吴道子的先兆。
吴道子千呼万唤始出来,他是大唐盛世最耀眼的绘画明星。
吴道子将中国人物画推向顶峰,线条的写实至此完美无缺。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宗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云,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朴,可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苏轼《东坡集》卷二十三)这段长长的引文,用在吴道子的画上,就言简意赅了,任何评论都无法替代。“新意”与“法度”,“妙理”与“豪放”的论述,尤为经典。不差毫米地道出了吴道子“豪放”而“妙理”犹在,“法度”森严而“新意”撼人的“疏体”特点。
这富有“新意”的法度,是线条;那“豪放”中的“妙理”是线条造就的形象。吴道子的“疏体”,线条如“形”笔法为“质”,“形”“质”相抟,精彩纷呈。
这“形质”相望的笔线条,便是中国绘画“古今之变”的一个终端。中国绘画的主要手段是线条,线条一旦到达写意的层次,这意也就遂了人愿。吴道子一手提举起绘画质的飞跃,将成熟的线条升华。其新意,虽依据传统法度,但法度的内涵被深入了,外延也随之扩大。吴道子作画,心手相印,左右纵横,无不如意。他的豪放,是生动准确的形象、娴熟干练的线条和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气势所构成的绘画品质,它既从外表感人,又于线条笔法传达心境,舒展神采,甚至宣泄一吐为快的情绪。张彦远称此为“真画”,并认为“真画一划,见其生气”(《历代名画记》卷二)。这“生气”,已经超出了顾恺之的“传神论”对对象精神的表现,进入画家自身精神世界的表现领域。虽然,吴道子时代的主观情思还紧依着客观对象,但被线条牵动着的画家精神状态倾注在画面上,感染力是直入人心的。
吴道子一生作画无数,可惜今天已难见其真迹了。文字资料有它的可靠性,但文字毕竟不如实物,传为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又称《释迦降生图》,是宋代的摹本,也可能是仿作。此图描写印度净饭王的儿子——释迦出生的故事。画面为佛祖释迦降生以后,其父净饭王和靡耶夫人抱着他去朝拜自在天神庙,诸神朝他礼拜的场面。图中人物十余,相貌、形态、神情各异;形象生动,气氛浓烈。画家用汉族的形象来塑造净饭王、靡耶夫人、诸神、侍从,是佛教绘画汉化的具体实例。据载,吴道子在千福寺西塔院北廓的壁画中,把菩萨画成自己的样子,说明了他对神和佛的崇拜,转为对人和人性的发掘;把外来的艺术形象,用民族、时代和社会的观念加以改造。图中的净饭王、靡耶夫人和蔼可亲,诸天神威武雄壮,侍女文静妩媚,大臣沉着安详,除天神的怪异面目之外,几乎是一幅当时王室的现实图像。人物神情的刻画很微妙,线条为“莼菜条式”的描法,透露着流利舒畅、磊磊落落的韵律美感,顿挫间益见风度。不过虽然声势俱盛,但终不如文字记载中的吴道子作品那样精深博大、气象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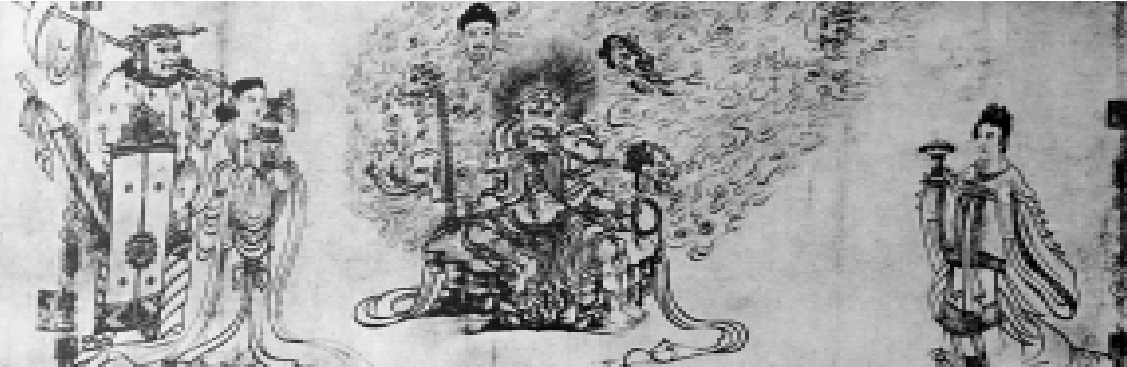
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
吴道子一生中创作了无数的作品,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地狱壁,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记,皆妙绝一时。”仅朱景玄所见,已如此丰富,可见吴道子创作量之大了。
据说吴道子画《地狱图》,把“今世作孽”的那些官僚大臣也戴上手铐脚镣在地狱中受审,表现出他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者的无情鞭笞和恶行应得报应的思想。他的创作,虽然多以佛道教义为题材,但在这些作品中,充满着现实社会的风情,充满着人性的力量,故其绘画艺术极为生动,感人至深。他画《地狱变相图》“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黄伯思《东观余论》);“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改业者,往往有之”(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的艺术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首先得力于他的写实功力,画笔在他手上左右纵横,无不如意。他画弯曲的弧线或笔直的长线,即便是精巧的宫殿楼阁也不用界尺,画巨幛大壁,不作草稿,从手臂或者腿脚先画起,顷刻间人物形象巨壮诡怪,肤脉联结,栩栩如生,须发鬓眉,往往长达数尺而凛凛然有飞动之感。“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他既把握住了写实的生动性,又把这种生动的写实性放在以得气势为主的用笔上,他开创了人物用笔的新格局,自立“莼菜条”的用笔方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疏体”的用笔形式。张彦远说吴道子之前的画“密于盻际”,“谨于象似”,而吴道子的画则“离披其点面”,“脱落其凡俗”。吴道子的用笔已经跳出过去那种线条为表现形象而作、亦步亦趋地描绘的套路,他在形象表现上的游刃有余,足以用笔的力量来制造画面的气势和抒发画家自己的情怀。米芾认为吴道子“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圆润折算,方圆凹凸”(见《画史》)。一笔之中,有粗有细,转折回旋之时,见勾见斫,其表现力远远胜过顾恺之那种以平动主,粗细如一的高古游丝描;其表现性又和刚柔相济的心理以及起伏波动的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可以变化出斑斓多姿的各种形式来完成绘画的造型写实功能,也可以在线条用笔中输送情绪,表达画家复杂的内在意度。


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
由于用笔、线条出现的新格局,设色敷彩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吴道子之前的设色法有两种:一种是流传于民间的,如墓室壁画那样勾线后随意加彩;一种是上层画家那种在细密的线描下填色,如色盖住线条,则还要复勾。这两种方法,前者流于草率,说明了绘画初期难于精工细微而粗取其意的状况;后者过于精工细微,是绘画上升时期所应有的“谨于象似”的写实作风。吴道子取两者之长,把精工细微的设色化为简淡明洁,摒去了草率和谨细。他为突出线条的特色、用笔的情韵,而不让色彩来掩盖它,发展了淡彩淡墨晕染的设色法。后人说:“其傅彩也,于焦墨痕中薄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也谓之吴装。”(见汤垕《画鉴》)这种简淡的设色,是用水将颜料化开,使色度透明而不掩盖线条,层层晕染,使之富有立体感,从而使绘画摆脱装饰趣味,进一步完善了写实的技巧。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壁画,大约作于晚唐,与吴道子相去不远。其中一幅,左边天王执剑,旁有一仕女手托香盂,中间一披甲力士手擒类似猿猴的动物,右边又一力士手持长杆兵器,向左作追赶状,形象夸张,笔法也很见气势,显然是受了吴道子的影响。吴道子在当时和对后人的影响很大,米芾说:“唐人以吴道子集大成而为格式,故多似。”吴道子能集大成,创造自己的风格,他转益多师,并不局限于张僧繇一路的“疏体”。

唐·卢棱伽《六尊者像图》(局部)
河北曲阳传为吴道子的画像石刻《鬼伯》,线条圆劲,粗细如一,大有循环超忽的风姿,可见他对顾恺之的传统也兼容并收,其弟子中之能细画者,如张藏,既“裁度粗快,思若涌泉,寺壁十间,不旬而毕”,又“亦好细画”;杨庭光“颇有似吴生处,但下笔精细耳”;卢棱伽“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卢棱伽的《六尊者像图》,是小幅作品,勾勒、设色都十分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