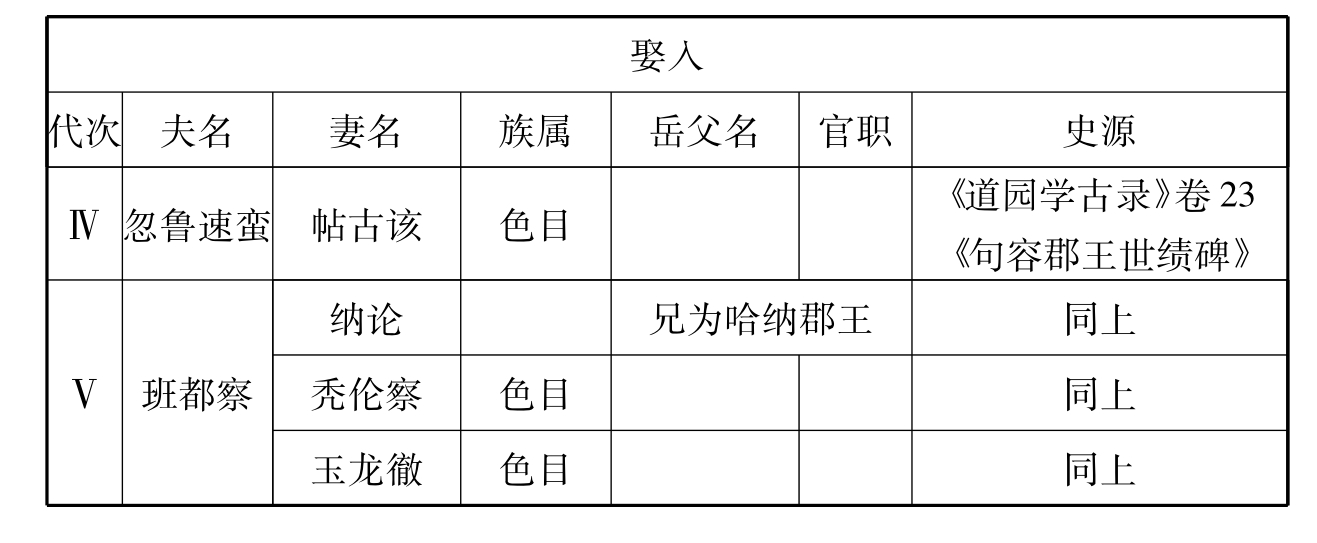-
1.1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演变轨迹述略
-
1.2导 言
-
1.3第一章 钦察土土哈家族探研
-
1.3.1一 土土哈家族的族属、居地与世系
-
1.3.2二 土土哈家族成员的军事政治活动与地位变迁
-
1.3.3三 土土哈家族的婚姻、祭祀及其文化倾向
-
1.3.4四 结 论
-
1.4第二章 康里阿沙不花家族史事辑存
-
1.4.1一 阿沙不花家族的族源、世系与居地
-
1.4.2二 阿沙不花家族的仕宦活动与地位浮沉
-
1.4.3三 以官僚为核心的社会网络
-
1.4.4四 婚丧祭祀与文化倾向
-
1.4.5五 小 结
-
1.5第三章 元代唐兀昔里氏家族研究
-
1.5.1一 族属、姓氏考辨及世系、居地状况
-
1.5.2二 昔里氏仕进与从政事迹的考察
-
1.5.3三 婚丧、宗教、交游及文化倾向
-
1.5.4四 小 结
-
1.6第四章 元代唐兀李氏家族探研
-
1.6.1一 世系与居地
-
1.6.2二 李氏家族成员的政治、军事生涯
-
1.6.3三 唐兀李氏的社会网络
-
1.6.4四 李氏家族的婚姻、丧葬祭祀与文化
-
1.6.5五 小 结
-
1.7第五章 汪古马氏家族考察
-
1.7.1一 族源、世系与居地
-
1.7.2二 马氏家族成员仕宦活动辑考
-
1.7.3三 汪古马氏的社会网络
-
1.7.4四 马氏家族的婚姻、丧葬、宗教及文化倾向
-
1.7.5五 小 结
-
1.7.6附录:马祖常之社会网络
-
1.8第六章元 代色目人家族的文化倾向与原因分析
-
1.8.1一 以汉化为主的色目人家族
-
1.8.2二 以蒙古化为主的色目人家族
-
1.8.3三 以保持伊斯兰文化为主的色目人家族
-
1.8.4四 部分蒙古化或汉化的色目人家族
-
1.8.5五 元代色目人家族不同文化倾向的原因分析
-
1.9附录:元代主要色目人家族文化表现情况表
-
1.10征引史籍文献与参考论著
-
1.11后 记
1
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