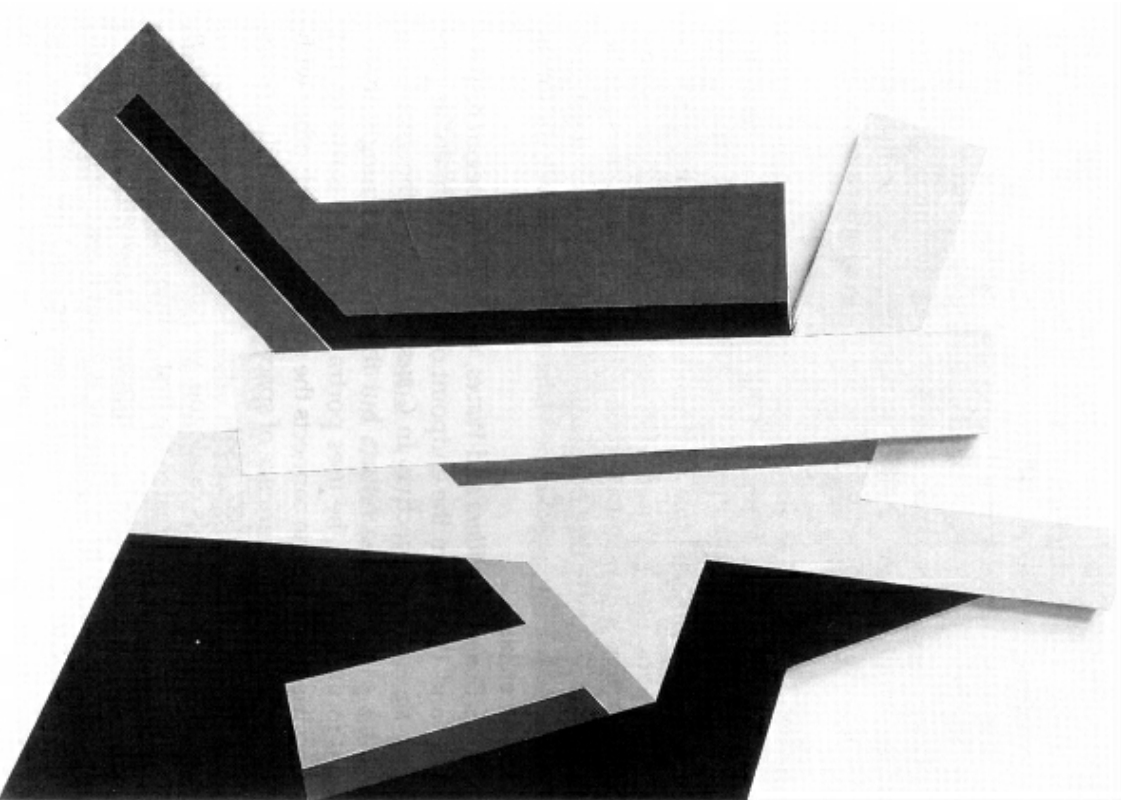-
1.1总 序
-
1.2序
-
1.3文献简称
-
1.4致 谢
-
1.5导 论
-
1.5.10.1 现代美学中的康德哲学起源
-
1.5.20.2 无法实现的浪漫主义渴望
-
1.5.30.3 浪漫主义的反讽
-
1.5.40.4 (后)现代主义之争
-
1.5.50.5 现代主义的根基
-
1.5.60.6 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VERWINDUNG
-
1.5.70.7 浪漫主义渴望的适时性
-
1.5.80.8 人类的浪漫图景
-
1.5.90.9 全书概要
-
1.61 冰封隐喻
-
1.6.11.1 冬之隐喻:隐喻之冬
-
1.6.21.2 顾蒙逊的《伟大的诗》
-
1.6.31.3 尼采和隐喻
-
1.6.41.4 固化与冰冻
-
1.6.51.5 先验的隐喻
-
1.6.61.6 悲剧的智慧
-
1.6.71.7 苏格拉底的真理和虚无主义
-
1.6.81.8 浪漫主义渴望的矛盾情绪
-
1.6.91.9 超人音乐家苏格拉底
-
1.6.101.10 多么寒冷的阿拉斯加
-
1.72 自主之路
-
1.7.12.1 皮亚杰对智力发展的研究和理性化
-
1.7.22.2 艺术的理性化与进步
-
1.7.32.3 斯特拉和现代艺术的完成
-
1.7.42.4 理性化的另一面: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反叛
-
1.7.52.5 法兰克福:理性化和现代主义
-
1.7.62.6 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斯特拉
-
1.7.72.7 从先锋派到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得不偿失的胜利
-
1.83 遗忘的艺术
-
1.8.13.1 形而上学与美学
-
1.8.23.2 叔本华的音乐美学
-
1.8.33.3 叔本华美学中的矛盾
-
1.8.43.4 尼采的《碎片本身》
-
1.8.53.5 重复和遗忘:史蒂夫·里奇的音乐
-
1.8.63.6 重复而死
-
1.8.73.7 超越现实原则?
-
1.8.83.8 永恒轮回的此刻
-
1.94 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
-
1.9.14.1 无意识的修辞学
-
1.9.24.2 言说的语言
-
1.9.34.3 无言的诗人
-
1.9.44.4 海德格尔的主体系谱学
-
1.9.54.5 去蔽和遮蔽的存在
-
1.9.64.6 永恒的缺失
-
1.9.74.7 诊疗床上的诗人
-
1.9.84.8 诗与思
-
1.9.94.9 从形而上学到隐喻:后现代哲学得不偿失的胜利
-
1.105 否认与再现
-
1.10.15.1 马格里特的烟斗:是的,我知道,但……
-
1.10.25.2 性和审美的否认
-
1.10.35.3 唯美主义的反常
-
1.10.45.4 阳具作为先验的能指
-
1.10.55.5 后现代的精神分裂
-
1.10.65.6 深层的表面
-
1.116 世上最老的贵族
-
1.11.16.1 巴特反抗偶然性的战争
-
1.11.26.2 音乐符号学和语言文字的边界
-
1.11.36.3 18世纪音乐符号学的考古学
-
1.11.46.4 奏鸣曲式和人的认识型
-
1.11.56.5 主体的音乐主导权
-
1.11.66.6 巴特的第二符号学和作曲家之死
-
1.11.76.7 凯奇的完全偶然性
-
1.11.86.8 尼采、海德格尔和偶然性(chance)世界
-
1.11.96.9 风弦琴
-
1.12后记 虚拟的浪漫
-
1.12.11 从浪漫之欲到数字之欲
-
1.12.22 (后)现代浪漫主义
-
1.12.33 (后)现代计算机
-
1.12.44 数字梦想
-
1.13参考书目
1
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浪漫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