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想象中的人权:自由与真意
——《诗性正义》与《受戒》的互动
张锦凯 行政法学院 研23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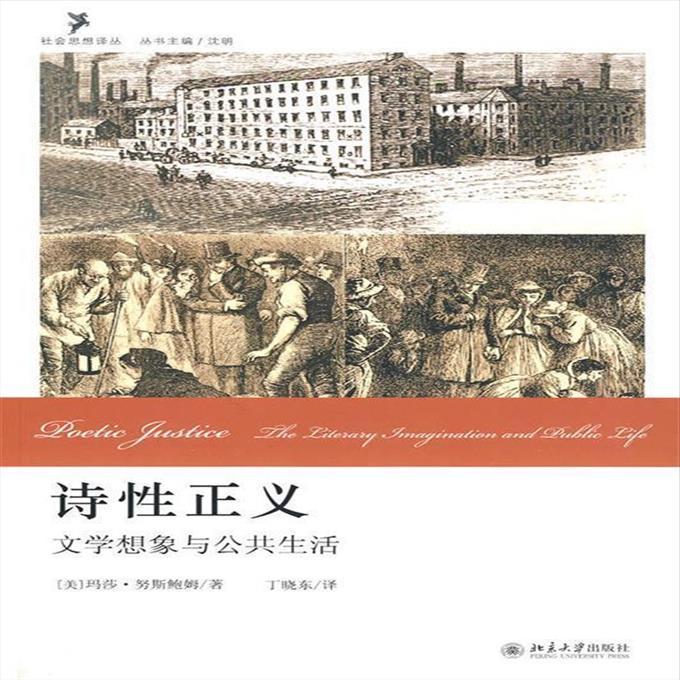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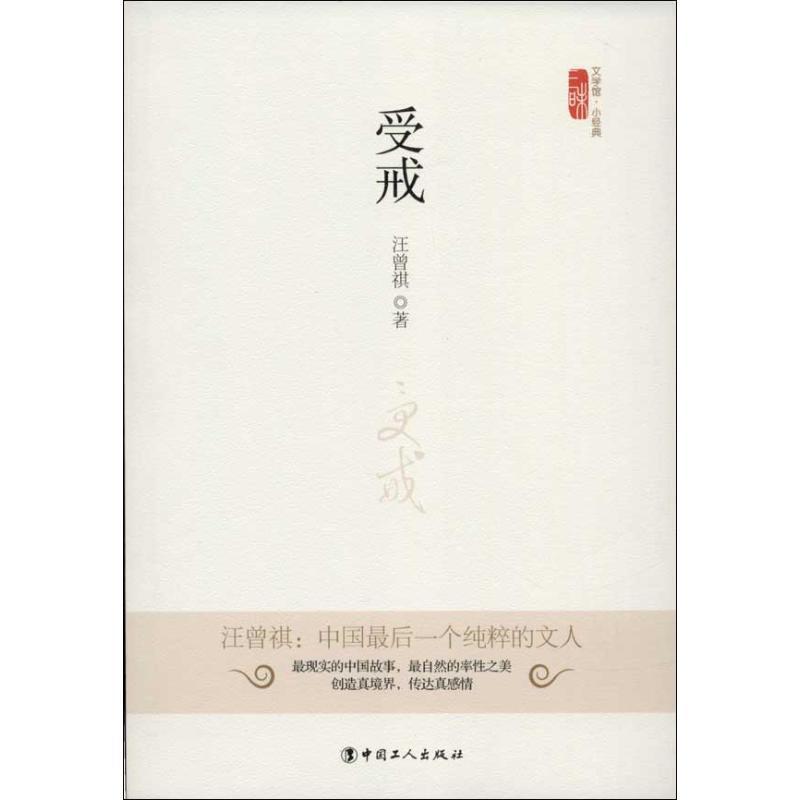
前言:
优雅的女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批判经济学和功利主义政治观的基础上,于其书——《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提出了一种“诗性正义”,即一种构筑在文学和情感基础上的正义和司法标准。努斯鲍姆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能够开启人们的想象,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物,这种理解和体验,对于形成公正的社会观念和决策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可以说,关于文学与法律的交互性分析,充满了努斯鲍姆对人性深处之正义期许的尊重。
从自然法学的权利进路出发,人权之意蕴的产生离不开人们对“普遍而又自然而然之善”的追求,其中最基本的在于“同理心”与“理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没有对他者之愿望与行为的理解,也就不能识别出“自然权利”的存在,更不会演绎出“社会契约”以促进自我保存。尽管古典自然法学家们寻求的是为政治国家的建构提供理论起底,但在领悟自然法普遍善命题的层面上,理性推演而来的“自然权利”所指涉的人权观念,与努斯鲍姆所述“异于自己的他者生活的体味与同情”表达出来的欲求基本一致,都是从“人类善”出发去探讨自由与人权的旨趣。
是故,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努斯鲍姆并没有直接讨论人权的问题,但是她的一些核心观点与人权理念密切相关。何谓人权?普遍的观点是“人之为人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有学者从尊严学说出发,认为人权是一种人应拥有的满足最低限度生活之尊严的权利;当然,也有学者在法律体系内部探究人权的意蕴,认为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宪法原则。是的,人权是一项抽象化与概括性的权利概念,但是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是如此具象。
同时,也受“重新发现人权概念的情感之维”等有关主张的启迪,基于上述种种,本文无意讨论《诗性正义》中文学想象与公共决策的关系,而是选择以汪曾祺所著《受戒》一文为分析材料,简单剖析其中所涉及的“诗性人权”特质,将“自由”作为主体内容,“想象”一种满怀“真意”的人权,尝试着探索文学想象下人权的期望。亦如努斯鲍姆女士所称,“能够想象不同于自己的人在逆境中挣扎的具体情形,这样一种能力似乎也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与公共价值。”
《受戒》——汪曾祺所著的短篇小说:一个法号明海的小和尚,一个入世未深的豆蔻少女,一段朦胧美好的感情。小说以这般微妙的感情为一条线,洋洋洒洒写下的一种快活自在的生活。题为《受戒》,但从未有人受到戒律约束。或许这样的生活如书后所言不过是一场十七岁的梦,但这样的梦却点醒出每一个人心中最为向往的自由与爱。一花一世界,这是汪曾祺的“自由”和“世俗”;一叶一如来,这是汪曾祺的“美意”与“真意”。
一、文学想象中的自由: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
常言道,入山门,受戒疤,从此便是佛教中人,受一切清规戒律。人从母体而来,入社会中去,受物质条件之桎梏,貌似我们生来的自由便是虚妄的,人性中对自由权利的渴望同社会生活体系的限制形成了不小的落差。然而,僧佛无数,每一个僧侣心中是否都明确自己踏入佛门之缘求?“小说非常强调个体作为独立的能动主题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努斯鲍姆如是说,那么暂且让我们放下疑问,于《受戒》,尝试窥见选择上的自由性。
从文学题材上来看,小说往世俗里写,就有烟火气,不仅有着喜怒悲欢,更包含有离合聚散。关于小说,努斯鲍姆认为,“小说的句子本身表达了一种对于保持超然、现实主义和公正的承诺——从句子的直率、句子的拘谨、句法的平淡无奇以及声音和韵律的生硬中都可以看出。”汪曾祺的文句就很有人间烟火,但是始终不见世俗喧嚣,先生是这么形容明海的僧侣生活的——“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箩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在这段描写里,汪先生的文笔让人觉得事体的发生和进行都刚刚好,岁月悠悠,最重要的是“生而为人”;尽是“开门”、“扫地”、“烧香”等杂活,读来也有着浓厚的天性自由的感觉,而这样的自由又是不近不远、静水流深的。在努斯鲍姆看来,选择的自由对于小说中描写的人类而言,有着一种不能简化为快乐的深刻价值,这也是成为真正人类的先决价值。诚然,明海成为小和尚是没有多少自主的空间的,但明海依然选择悠悠然地度过一天,汪曾祺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选择受限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怀抱“性本爱丘山”般的心态去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去过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
顺承这一点,私以为,人生而自由,但是否真正自由,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一个大写的“No”;不过,努斯鲍姆告诉我们,即使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纪实不能说服所有人,我们也应希望其成立,美好的事物置于丑恶的旁边,将证实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人性价值。而在这个十七岁所做的梦里,在这种梦中世俗里或许人人都是自由的——这就是想象的人权之自由。除明海以,《受戒》里有这么几个和尚,没有青灯古佛常伴,没有《华严》《梵网》常读,甚至连基本的吃斋修律都没有,好似比南怀瑾先生还世俗。这些和尚长在风日里,身上有着不规训的一面,除基本的行为规范以外,并不受太多礼法的限制。他们仅仅把和尚当做营生的一种,当作一门手艺或工作,仅仅遵守一些基本的规矩。但最为关键的是没人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他们也才能理所应当地做着打牌、娶老婆的事情。但在这背后,其实关键在于所有人的自由之思想。人权对抗的是歧视与不平等,努斯鲍姆倡导我们经由文学想象走向“诗性正义”,也正是出于对当今世界处处充斥着个体扭曲和群体排斥的担忧。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和尚身旁所遇之人都认为他们不合佛门之道,不断地批评、讥讽他们,不断地否定、排斥他们,这些和尚想必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巧妙之处就在于汪曾祺想象了一个众生自由的世界,从最开始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主人公明海的家乡很有趣,在他的家乡做和尚的概念和现在我们的参军考公差不多,不仅有饭吃,回家后工作也有了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去丧事做法等。这样的世俗之下人们总是做着最充实最诗意的事情,又到后来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众人围起仁渡让其唱些风流韵曲。不得不令人感慨,连和尚,也是有人情味的。
法律理性固然重要,但这般美好,也作为一种证明:人性心中的自由思想、情感结构的自由信念、公共生活的自由领域,这一切是多么重要。汪曾祺先写下佛教清规,芸芸众生无往不在物质生活的枷锁之中,再写到“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无疑也是在阐释这种思想,展示自由精神下的公共生活会是怎样。“偏好本身并不是社会的产物,”努斯鲍姆如是说;我们对于自由的追求仅仅是“一种个人或社会进行选择的原始材料”,所以,大胆地展示个人自治和自尊。汪曾祺的大胆与锐意就在于构建出这样一般无狭隘目光、人与人互相自由交流的世俗,在这个世俗里面只有自由的人,只有自由的日常生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也是无意讨论宗教的,他只是借佛教代指一切束缚自由与美好的东西,可以是清规戒律,也可以是世俗眼光,或许对他而言他也不想讨论世俗和宗教,汪曾祺其实只是在讨论一个自由、平淡的世界。
二、文学想象中的平等: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什么是真实的?我想说,情绪表达的就是真实的。所谓“真意”,即是真情实感。在汪曾祺这个十七岁的梦里,最重要的是爱,更是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恋爱,对于汪曾祺先生而言,这才是人性的真实。换做法言法语,或许可以表述为追求真实自我之实现的权利。
在人权的语境中,每个人都值得被平等相待,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与自由之权利会对个人的心理和情感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当个人受到关怀和保护时,他们会感到自尊和自信,这种心境有助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幸福感的提升。许多法哲学名篇或心理学著作都向我们诉说着这一“不言自明”的理论逻辑,不过在文学作品中,虽其看重情感体验,但是努斯鲍姆认为,诸多作品并没有告诉我们的社会会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阻止我们去同情不同种族、不同性别或性取向的人们,也没有告诉我们,社会不公和仇恨通过哪些方式塑造和扭曲被憎恨者的情感生活。因此,在这一部分,同努斯鲍姆一样,我想强调,当我们展开对某种生活的生动想象时,真实情感十足是一个应有部分。且先看《受戒》里的寥寥数语: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诗性正义》一书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始终关注具有质性差别的个人的情感要素,也强调着每个人彼此相互纠缠的世界,从而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写作本书时,努斯鲍姆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视角,这一视角在利益计算时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性地位,忽视了人性的真实需求和情感体验。回看此间文字,在当下人的理性观察中,成为方丈,做一庙之主绝然是前途无量的。可是,小孩儿又哪懂这些呢?他们所惦念的只有当下的两小无猜,唯是男女的情感联结。
英子活泼可爱,简单纯粹;再看明海,憨厚腼腆,包容英子的种种想法,两人间对话一问一答,却牵动丝丝真情。平白如话,简单如雪,或许能让我们回忆起心中最向往的事物。当我读到此间文字之时,我感受到的便是“纯真”二字,这样的纯真让我返回到无欲无求而又蠢蠢欲动的童年时光,让我重新感受到如丁香一般皎洁的真情流露,同时又带给我以触动后的久久怀念,如浓茶之气,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不过,童年虽被视作纯粹的代名词,但在《受戒》里,长大后的世界也可以同样简单。 “这是个很枯寂的人,一天关在房里,就是那“一花一世界”里。也看不见他念佛,只是那么一声不响地坐着”,这是老师傅普照;“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地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这是二师傅仁海和他的妻子;“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这是聪明精干的三师傅。在诗性正义观看来,小说描绘了具体社会情境下感受到的一直存在着的人类真实渴望。汪曾祺以平实的笔触写尽此种“真实渴望”,先从实践图景出发,建立非一般的真实,再由外及里传达出生活的美感。更为人惊叹的是,《受戒》建立起的这种美感,自然地表征了一个个现实社会背景下坚守浪漫之道的人,如此便将梦幻与现实完全融为一体。我们寻不见“芙蓉草”这样的符号意象,但清风徐来,在肌肤间舒柔的就是真实的。
《诗性正义》列举了许多对情感力量的反对意见,一些指责认为,情感在规范意义上是非理性的,因此它不应该用以指导我们的生活,情感也是一种盲目的力量,被描述成我们体内一种不完善的人类天性的元素。然而,正如休谟所看到的,人性由理性判断和情感伦理共同组成,在人的构成里,情感是那样真实。努斯鲍姆以“同理心”为例回应上述指摘,她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比怜悯的信念更为强烈,以支撑我们为社会正义和社会慈善而行动和冒险,拒绝怜悯则和一种冷酷与吝啬的倾向相关。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内心真实的向往所驱动着,这种真实赋予了我们感知周遭美好的能力;努斯鲍姆也论证,“它们(情感)使得主体能够感知某一类型的财富或价值”。尽管内心世界十分复杂,但在法律的建构中,我们还是可以在运用理性力量、在忠于真理的前提下,真实地操弄人类生活的情感事实与对普遍善的构想,这一点就化为了我所述的人权之“真意”。人权的出发点是生而为人的事实,人权的目标最多不过是满足人之为人的尊严感,故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天赋人权”,也没有至高的“自然法体系”,法律中的“人权”,实际上只是简单化和描述性的人性诉求。
结语:
白日初升,梦醒时分。梦虽逝,然,不变的是对一程又一程对心心所念的向往、对人性自在的追求。《受戒》中汪曾祺写下的的梦,其实是对十七岁那年时光远去但无法追及的遗憾之美,但又饱含着对人性纯真的信念与对内心深处的梦想之期盼。这样的遗憾与期盼又建立在一个充满自由烟火、充盈清幽精美的自由世俗。正因此,在这个亦幻亦真的世界中,人们所作所为皆由心动,无所谓“封建祖教”,无所谓“成规烂矩”,只所谓“自由”与“真意”。
汪曾祺道,这是一个四十三年前的梦。梦被视作虚妄,努斯鲍姆也说,“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仅仅诉诸畅想(fancy)就能够改变很多习以为常的仇恨与歧视。”但由想象而出的人权,作为一个梦,处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美好、静谧、一直沉睡着,等待我们把它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