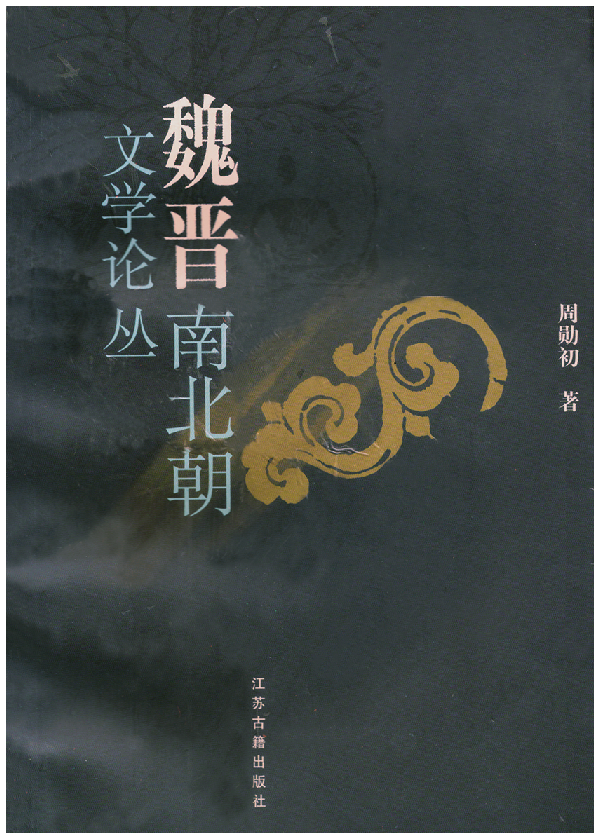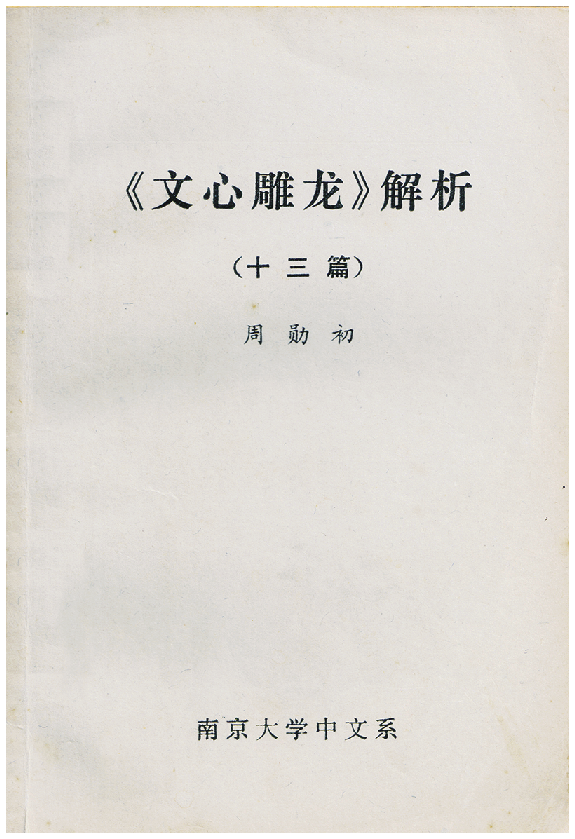【附录】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后叙
自八十年代起,我先后出版了几种有关唐代文学的著作,主持过几次唐代文学国际会议,还担负了几项编纂唐代诗文总集的主管工作,因此学术界也就确认我是唐代文学的研究人员。实则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领域中不断奔波,本无专业可言。虽曾东涂西抹,亦复难以称得上在哪些方面成绩更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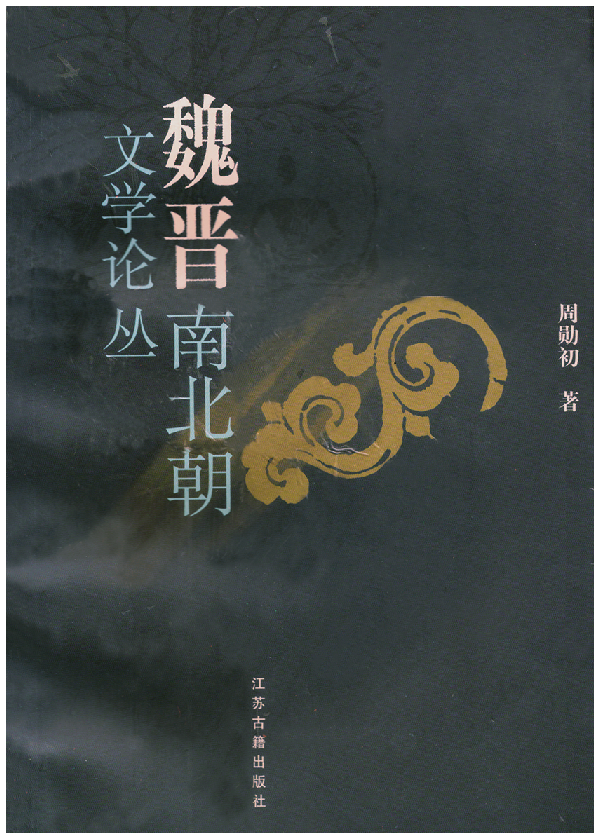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目下年事日高,回首平生,觉得早年本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有缘,只是随顺世故,身不由己,竟至无法于此投入较多精力。今蒙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好意,将我前此所写的文字汇成一册,内心的感受,真所谓欣慨交集。想到既有向学界请教的机会,不如把我写作这些文章时的情况,以及有关的一些想法,附于全书之后,供学界参考。
我于1954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曾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了两年半,后应导师胡小石之召,回校当副博士研究生。先生以为治学应该打下深厚的基础,故亲自讲授《说文》、甲骨、金文。只是这种宁静的读书生涯为时不到一年,鸣放即起。接着运动不断,什么反右派、交心、拔白旗、大跃进等等,轰轰烈烈地展开。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敲石子大炼钢铁,打麻雀“除四害”,加上平时的政治学习和大搞卫生,花去的时间比起学习的时间还要多。运动后期又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饭都很难吃饱,油水严重不足,虽然每晚仍坚持读书至十二点始就寝,但已饥肠辘辘,只能枵腹入梦。
不少人在运动中受到了无端的打击,例如学长谭优学兄仅因对无法静心读书不满,竟至划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清除出党的严惩。我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能一一渡过难关,也可算是幸事了。
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高等院校中的空气才逐渐有所缓和。这时社会主义阵营已发生分裂,中国高举反对“苏修”的旗帜,要求肃清前时苏联文艺学的影响,建设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于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重又得到重视,各校纷纷开设此课。1949年之前,这一领域中以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位先生的著作最有代表意义,此时郭、朱二先生在复旦大学任教,罗先生在我校中文系任教,再加上第一位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陈中凡先生也在我校中文系任教,因此两校阵营,本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无奈陈先生已年迈,罗先生患高血压与肝硬化,已难再上讲台,于是系里只能将我这个刚改为助教的肄业研究生驱前充数,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
其后周扬着手抓高等院校的教材建设。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将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历代文论选》的任务交给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让各编一套,这里也有促使双方竞赛的用意吧。然我校中文系正处在青黄不接的困境中,罗根泽、胡小石、方光焘等先生于六十年代初接连去世,全国有影响的学者已屈指可数;复旦大学实力本已超群,这时还得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吸收外地外校专家学者参与,组成了阵营强大的编写组,进驻国际饭店,并由上海图书馆配合,供应所需资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编出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册,后又编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中的首卷,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领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我作为一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师,对复旦大学的成绩感到钦慕,又对自己单位的现状感到沮丧。尽管有的领导还在自得其乐,我却有不胜没落之感。竞赛彻底失败,还遭到出版部门的嘲笑与奚落。那时我年纪很轻,茅庐都尚未初出,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我的职务是教师,只求在讲台上站住脚跟。
第一遍讲课,力求对讲到的内容有真切的了解,不要传播错误知识。只是批评史内容太多,自孔子到王国维,都要一一点到。当时还有很多特殊要求,例如讲到明代时还要介绍民间文学理论等等。我虽不免借鉴他人成果,但力求把握原文,而不以稗贩郭、罗、朱的现成著作为满足。
第二遍讲课,觉得应在漫长的批评史各时段中抓住重点。像其他通史一样,批评史也可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可以魏晋南北朝为重点,下半段可以明代为重点。前者承上启下,理论建树最为突出;后者内容丰富,戏曲、小说等理论均有可观。如把这两个时段的理论研究出个眉目,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可以梳理清楚了。
第三遍讲课时,我就将讲授上半段批评史时的一些读书心得慢慢写成了文章。不过在“文革”之前,只发出了两篇,其中之一即《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那时我才三十稍过,平时困处一隅,与出版界素无因缘,也无师友可以推荐。南京没有什么文史方面的专业杂志可以发表。我就贸然把它寄给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他们倒是不计名位,把我这一无名小卒的文章与诸多名家的文章并列,刊登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上。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阶段后,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我因“文革”之前教过几年文学批评史,也参加了学会的活动。诸多同行一见如故。原因何在?只是他们曾经读过那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不但此也,港台的学者也因此而对我有所了解。原来自大陆出去的杨家骆教授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讲授目录之学,他托美国的朋友买到了《中华文史论丛》。七十年代,他主编了一种《中国学术类编》,由鼎文书局出版。内有“中国中古文学史等七书”,计为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瑶《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风貌》、拙作《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夏承焘《四声绎说》、詹锳《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郭绍虞《再论永明声病说》。杨氏并在《识语》中一一介绍上述七书。其他五人,因为年辈较高,杨氏均有了解,故介绍颇详。其中说到何以不收王瑶《中古文人生活》一书,以为“实就周树人《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作,加以扩充而成,所论实为斯时士大夫之风尚,并非专指文人生活,故不取”。后又续云:“周、夏、詹、郭四作虽主题较专,然其深度实远逾王书,故并录之。”杨氏此说自是一家之见,对王瑶先生的批评过嫌苛刻,但他实际上不知我是何许人也,故在介绍时,只能泛泛地说“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探骊得珠,久称佳制”。这一褒扬,却是过分抬举了我。前已说过,截至此时,我只写过这一篇文学论文。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学风陡变,这种学院式的文章不受重视,“久称”云云,实在是无从说起。
但到八十年代,台湾大学的罗联添教授又将此文编进《中国文学史论文精选》,由学海出版社出版,见到的人就更多了。1993年,我赴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主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会议,遇到台北师范学院的刘汉初教授,他就说到前此两岸阻隔,台湾学者不易见到大陆学者写的文章,然而《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传入较早,因此台湾学者大都知道我的名字。这真是以文会友的生动事例。
1997年时,我应美国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之邀,前往讲演,他就提到《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并谬蒙赞许。可以说,我因此文而被国内外学者所接纳,取得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人员的资格。
如用夸大一些的词汇表达,我这第一篇文章可谓一炮打响,境外学者常是引用到它,而在国内却是打了一个闷炮。有的学者谈到梁代文论三派或谈到通变、新变两派时,都用表达个人研究成果的口气陈述,尽管论点与论据都与拙作相仿佛,但却好像没有看到过我这一文章似的。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文章的写作规范,那么引用他人成果时,必须注明出处,是否也应该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呢?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发表之时,政治形势已趋紧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出来后,科学研究很难进行,只能出现一系列的批判文章。我在1965年时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副标题为“与胡念贻同志商榷”,却是引起了不断的悔恨。
自1962年起到1964年止,胡念贻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讨论文学遗产批判继承的几篇文章,并举宫体诗为例而申述其意见。现在看来,他是有感于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扼制科学研究,希望能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让大家各抒己见。我这文章,则仍坚持所谓“糟粕、精华”之说,反对他开放古典文学“禁区”的主张。应该说,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无疑还是起到了“围攻”的作用,这是我一直深感遗憾的原因。批评与商讨,本是研究工作中的正常现象,但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管你写文章的主观意图怎样,事后观之,往往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想到这些心里就感到懊恼。
前几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洪顺隆教授为编《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续编》,要我复印《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一文给他。他在读过之后,来信表示赞同,说是看法跟我差不多。可能他还不太了解此间的特殊情况,因而就事论事,难得明白事情底细。当我更多地了解到其时的具体情况之后,更感到写作此文的时机与论证方式不妥。为此我在编辑论文集时,不再收入这一文字。
在当时来说,可谓不该写的文章写了,该进行的工作却不能顺利地进行。
《〈文赋〉写作年代新探》一文,“文革”前已完稿,且已寄交《新建设》杂志。“文革”中几遭湮废,全靠傅璇琮先生大力帮助,才从一堆废稿中捡回。此稿表明,我像写作《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样,重视综合研究,只是我所讨论的是陆机的文学理论,所以尤为重视哲学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大都喜欢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玄学、佛理,发生的影响很大。因此,今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而对玄学与佛理缺乏了解,也就可能难于在文学研究中有所突破。
我从《文赋》受到“言不尽意”论的影响切入,揭示陆机与玄学的关系。又从陆机对世传《易》学态度的变化上进行考察,说明他在入洛后开始学习玄学,其间还援引了陆氏兄弟夜遇王弼之鬼的传说,从文化背景上加以透视,并以此为根据而推断陆机写作《文赋》的年代。因为此文观察问题的角度有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曾经受到学界的赞誉。而我之所以能在这一老问题上提出新见,则得力于当时一些浅薄的哲学知识。
1988年时,暨南大学主办《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乃重操旧业,提交了一篇《〈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的论文,重新对玄学中的许多问题学习了一番。虽然自以为还提出了一些新见,有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或可供学界参考,但论文写得很吃力,总因平时投入的时间过少,终日为其他事务忙忙碌碌,不能进行长期的系统的考虑,因而不能驾轻就熟地操作。抽空草此论文,而又牵涉至广,又属专门之学,自然捉襟见肘了。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心雕龙》一书自当倍加重视。我总认为,若想剖析刘勰的理论体系,必须从玄学与佛理下手,特别是玄学,更具首要意义。
但不论前此抑或眼下,研究《文心雕龙》的人,说明刘勰的思想时,大都致力于参照西洋文艺理论而构拟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心雕龙》研究者,大都采择苏联的文学原理,作为参照而构拟刘勰的理论体系;八十年代之后,又有一些人参照欧美的文艺理论而构拟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我却总想从文本出发,力求按照《文心雕龙》文章中的原有格局,勾勒出刘勰的理论体系。
刘勰的理论,熔铸了前此的经史百家之学,因此我在写作有关《文心雕龙》的文章时,总是希望找出《文心雕龙》中学说的源头,根据魏晋南北朝时的风习,说明刘勰的各种建树。例如我从《序志》篇中的“唯务折衷”之说,寻找折衷这一方法的学术渊源,说明刘勰使用这一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根据《序志》篇中提到的大《易》之数,分析刘勰与《易》学的多种联系,说明《文心雕龙》中的文原之说与结构问题。根据刘勰对《春秋》学的推崇,研究刘勰何以又会遴选潘勖《九锡》为有骨之作的代表?我的研究工作,遵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虽然未必能把问题解决得很妥当,但我一直努力这样去做。
当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到这一地步时,这才体会到前此阶段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积累下来的一些先秦两汉知识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学术起于先秦,因此不论是儒、道二家的经典,还是其他诸子百家的学术,抑或《左传》《史记》等史籍,都对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士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人们如对先秦两汉的学术缺乏了解,恐怕很难深入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深层研究中去。有的《文心雕龙》研究者热衷于借助欧美的新兴学术理论构建刘勰的思想体系,而成效并不理想,可能即与他们对刘勰的主要学术渊源之一——先秦两汉学术了解不够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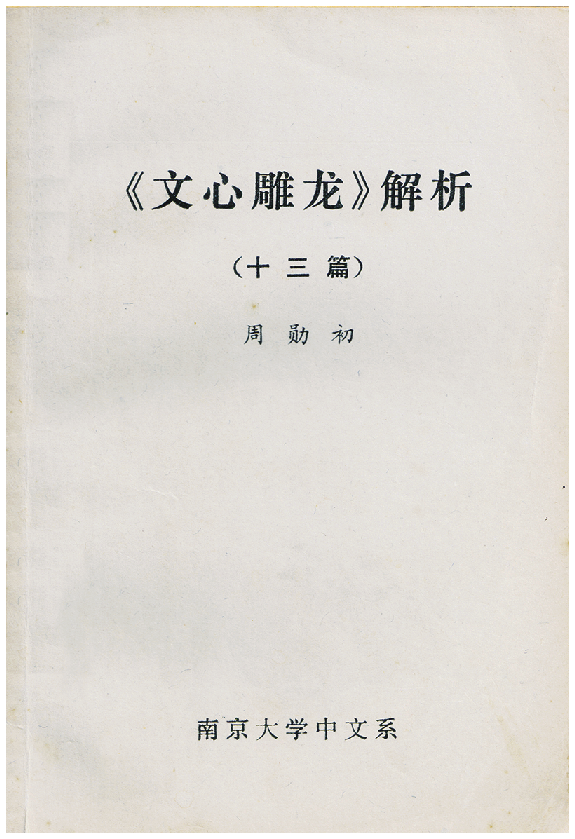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印的讲义
八十年代初期,我开过三次《文心雕龙》的选修课,遂将六十年代写的一些讲义重新捡出,挑取《原道》等十三篇有代表意义的文章,编成一种取名为《文心雕龙解析》的教学用书。我不取通论式的教学方法,而是将所选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分析。先是“解题”,因为刘勰取篇名时都很有讲究,往往与他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反映出他不偏于一端的辩证观点。中间为对正文的“分析”,按其自然段落进行讲解,这里就得注意所讲内容的学术渊源,论点展开时的内在逻辑程序,还得注意刘勰使用骈文而形成的特殊论证方式。末复作一“小结”,发表我个人的阅读心得。这一讲义,自以为还有一些特点,可惜其后因为任务转移而始终无法加工出来。
《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后一部分的理论,是从前一部分的作品研究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我本想花上一段时间认真阅读魏晋南北朝时以及前此阶段所遗存下来的各种文体的作品,相信这在探讨刘勰的成就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可惜因任务转移,这一计划也无法实现。
1995年时,我因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还写作了《“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仍然保持我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穿穴的研究方式,也曾受到好评。然因教学、行政、研究头绪纷繁,精力无法集中,始终无法在《文心雕龙》的研究领域中作全面的开拓。
过去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喜欢谈论评价问题。实则其时的研究者每依西方的某种理论为准则,而将刘勰等人的理论与之比附。相合者,评价就高;不合者,评价就低。有人为了提高中国古代某些理论的身价,还不惜婉转为之解说,使之与西方的理论相类。这样的评价,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为研究某一位古人的理论,就得恢复它的原貌,然后置之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它所起的作用。原貌尚未弄清,或者仅凭装扮过的面貌立说,又怎能谈得上什么客观评价?
也许总是由于师承的缘故吧,我的研究工作时而像是朴学家的治经史。研究的是古代文学理论,所用的方法却很少采用演绎,不喜欢根据经典作家或领袖人物的一些言论而作推导。所采用的,主要是归纳法。讨论问题时,常将研究对象分为几个方面,然后搜集积累材料,经过归纳,提炼出若干论点。《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一文,这一特点就较明显。或许我写这一文章时正处在学习古代文论的早期阶段,因而更为明显地暴露出了这一方法的斧凿痕迹。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俞铭璜同志出任我系系主任。他的思想非常灵活,一再提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人应该注意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其他艺术,如美术、雕塑、音乐等方面的成果。我在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文学的形象特点时,也就触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只是限于个人的素养,未能取得什么成果。日后更因研究方向转移,以致这方面的研究未能继续,但我以为这一方向还是正确的。研究古代理论的人不能忽视艺术领域中的一切成果,因为各门艺术之间有其相通的地方,而魏晋南北朝人更多兼通各种艺术者。
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已由另外几位教师担任,我则到处打杂,社会活动又急遽增加,只是由于缺少教师,我还教过两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课。
因为讲文学史,所以对一个个作家作过一些研究。后因参加国内外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会议,也就写下了一些文章,像《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以及有关左思、郭璞、谢灵运等文章,都是应急赶出来的。
魏晋南北朝人喜欢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警句,如“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等说,虽仅寥寥数语,底蕴却极为丰富。有人如能发此未发之覆,则对读者理解这一阶段的文化,定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虽不敏,也想于此有所尝试。《三都赋》出,“洛阳为之纸贵”;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等说,吸引我去钻研。文中作出的解释,或未妥帖,但也体现出了我的努力方向。
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时距今过远,资料遗佚过多,即使是像阮籍、左思、郭璞这样的大家名家,所能见到的诗文为数也很少。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每叹研究资料不足,在这为数很少的文献中难于推出新见。我的感受也一样。但我以为,假如我们把目光仅限于纯文学的考察,那么就会受到很多限制,比之唐、宋以下的作家,材料方面的困难要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对此进行综合的研究,则以其时社会上变化之急遽,思想上交融与冲突之激烈,文学创新的多姿多态,还是可以不断深化,予以发掘。这里可能需要更多的敏感,在各个方面的交叉关系中考虑你所研究的内容,从而提出某些他人意想不到的论点。
魏晋南北朝时的文献资料虽说为数不多,然而还没有很好地整理。过去鲁迅研究小说时,曾花大力气对这一时期所遗存的小说资料加以科学的整理,辑成《古小说钩沉》一书,沾溉后学,功德无量。不过鲁迅可能意在提供一种阅读的文本,有的地方不惜改动原文,或增加文字,以期文字畅通。这对整理古籍要求严格保存原貌来说,走的是一条新的路子。我秉性保守,又喜欢什么都试试,于是我以《文士传》为题,重新作了辑佚,希望为学术界提供一种更完整的本子。现在这书已有多种辑佚的新本子问世,读者不妨比较一下,或可看出我在体例问题上的关注。今人若欲从事编辑资料汇编之类的书,就得郑重考虑体例问题,务求存真与便用,我在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和整理《唐语林》时都曾于此再三致意。
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心雕龙》是理论方面的重镇,《文选》是文章学方面的重镇,学者必须投入很大的力量才能有所成就。
我于《文选》投入力量很少,故对《选》学不敢赞一词,而我也曾做过一件惬意的事,把流传日本的珍贵古籍《文选集注》迎归故土。这书在我国书目中一无记录,然据诸多内证,可以说明它是唐人钞本,至少是后人据唐钞转录的钞本。全书一百二十卷,内有中土已佚的公孙罗注、陆善经注与《音决》等珍贵文献,即以李善注、五臣注而言,也与目下所见者有异。诸家注本中征引材料极为丰富,有的是早已亡失的佚书与佚文。大家都在慨叹魏晋南北朝一代新发现的材料不多,那么此书的出版,当对这一方面有所补益。
民国七年时,罗振玉曾请人模写残本十六卷,以《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为名,影印行世,其时一些知名学者如高步瀛、余嘉锡等引用过此书,可能即据罗振玉影印本。只是罗本失真之处甚多,自难据为典要。其后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二博士编成《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丛书》,辑入二十三卷,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又续有所得,且请人编了几种辅助使用的材料,因此这一命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的本子出来后,相信可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史研究有所贡献。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利用此书与其他珍贵钞本,写出了不少有关《选》学的高质量的文章。我国学者困于《选》学的文献资料,有的研究工作已显得落后。这就说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闭关自守,应该虚心地向国外同行多方面地学习,才能取得进步与发展。
客观地说,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而要想发掘出大批前人未见的材料,那是不现实的,但现存材料是否已经多方发掘利用上了呢?怕也未必。还是以《文选》和《玉台新咏》为例来说明吧。
《文选》中的文体究竟分为多少类,各家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学者据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与唐钞《文选集注》卷八十八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文》中的陆善经注,以为《文选》中尚有“难”类。实则古代文献中于此早有明确的记载,《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记《文选》中有赋、诗……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其中就列有“难”类,可见宋代内府所藏《文选》中即有此类。这一上好的材料,可惜大家均未注意。
又如《玉台新咏》中的宫体诗问题,更有复杂的内容需要探究。宫体之起,可谓文坛新物,应该怎样看。往往是随社会观念的变化而采取不同视角的。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美国对同性恋者采取更宽容的态度,社会上对同性恋者不再歧视,国人的观点每随国外的动向而转移,于是便有人撰文以同性恋来解释《玉台新咏》中的一些描写。我对这些问题素无研究,故不敢妄加评论。只是根据直觉的观察,现代的同性恋者一般都能相互尊重,双方处在平等的地位上,《玉台新咏》中的那些作者,固然把娈童一类的对象描写得很美,但他们是用平等、尊重的眼光去看对方的呢,还是视作玩物?因而这种现象属于人类正常活动呢,还是一种不正常的变态的人际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既要研究彼时的同性恋问题,那么自应考察《玉台新咏》中一些作者的私人生活,看看他们有没有过同性恋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风气?可惜的是,我还没有见到过有人曾对这一问题积累过材料。前已说过,我因研究方向转移,精力无法集中,因此也没有发掘这方面的材料。然偶阅前时所作的笔记,内云《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懿(附猷子韶)传》中有“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的记载,这不是证明庾信即有同性恋的问题么?颇怪那些论证《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问题的学者何以不注意这类材料?
我很希望能对《玉台新咏》有新的正确的认识,以赎前愆。为此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更进一步敞开思想,加上严密论证,对文坛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作出新的结论。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学术上的清规戒律已大为减少,一些向被偏见所搁置的问题,这时才又受到重视,说明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已有很大的进步。例如赋这一种文体,因其具有高度综合的特点,向为前人所看重,故有“作赋需大才”之说。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因汉代大赋的内容多颂扬统治集团,小赋作者的身份类似俳优,又因其写作的方式不合西洋有关文学的定义,故而遭到否定,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一直轻视赋这一种文体。目下此说虽已很少有人相信,但如何研究这一特殊的文体,却还需要一种新的眼光。应该说,赋是一种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体,研究人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对中国的文化学术有真切的了解,才能把握赋的特殊性质。魏晋南北朝人重视作赋,在大赋与小赋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我在好几篇文章的研究中都涉及了赋的问题,路子是否正确,所言当否,希望得到学界的指正。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特具奇光异彩。尽管其时时局混乱,文士常遭不幸,然而思想上束缚较少,各个领域都有新的开拓。试将《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自汉入晋之后,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社会是一个整体,文学这一领域,自然会受到其他不同领域的影响。纵观全局,在各种关系中考察社会的变异,也可发现很多问题。我对其时的科技问题加以考察,说明这一领域的进步曾对文学产生影响,这一研究,也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我本不懂科技,自难深入了解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写作此文,也只是想在看问题时多一种视角罢了。
中国历史悠久,代有能人,在各个方面留下了众多宝贵的遗产,足以使人感到自豪。杜牧《润州》诗曰:“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多么具有吸引力。这时的一些杰出人物大都思想丰富,个性鲜明。他们思考问题时,往往更具纯文艺与纯思辨的特点。阅读与研究这一时期的作品,自能让人感到特有的愉悦。只是限于个人的条件,未能在此多所沉潜,往往陷于浅尝辄止,未能在跨出一步后再走下去。今日将此戋戋小册奉献学界,难以掩饰内心的怅惘。
但我作为一名教师,也有足以自慰的地方。1995年,我校中文系和古典文献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又联合举办了第四届辞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取得了成功。古典文学教研组和古籍所里的成员提交了不少论文,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与赞许,说明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在经历过六十年代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之后,又经历了“文革”所造成的再次青黄不接的痛苦时期,如今终于看到本学科的复兴。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新老人员的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这些成绩。这里有我投入的一份力量,那么个人的科学研究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也就不必多所感喟的了。
 【附录】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后叙
【附录】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后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