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额骨头碰到天花板的幸运
弗里曼小姐的教室充满文学的温存,就连照进教室来的太阳,也显得格外好看,没有大路上的太阳那种太亮太硬的兵气。
望着弗里曼小姐脸上那枚闪闪发光的鼻钉,陈淼淼轻轻说出“罗德岛设计学院”几个字,老师脸上就静静地笑开了花,那枚鼻钉就像花瓣上的一粒浪漫到俗气的小水珠。“祝贺你,真是幸福的时刻啊。”老师轻轻说,好像怕吓到陈淼淼一样。
弗里曼小姐真的明白像陈淼淼这种小孩,平时什么都大大咧咧的,要是心里在乎的,就加倍表现出大大咧咧的样子来。可是,要是她都装不出来无所谓的样子了,那就是十万火急的重要。此刻陈淼淼的心已经变成兔子了,禁不住弗里曼小姐大声叫好的。
陈淼淼摆着双手说:“很模糊很模糊,就是非常有兴趣,非常有兴趣。”
弗里曼小姐深深地点着头:“是的,是的,没关系,我理解。”
不过,弗里曼小姐马上指点陈淼淼去找本校的美术老师贝茨先生。
陈淼淼无声地笑了,好像她们之间做了一桩秘密的交易。
贝茨先生的教室里有股雕塑泥的气味,其实不好闻,可陈淼淼吸了一口气,把它一五一十全都咽到肚子里去存好。那气味真是难以形容,既闻所未闻,又激动人心。这就是理想国的样子。
理想国的正中央,有一大片阳光笼罩着贝茨先生和他的大工作台。他是个留着棕色大胡子的安静的年轻人,长得有点像电影里的耶稣。
理想国的窗外,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喜鹊,美国的喜鹊很大个,隆重地长了一身黑得发亮的羽毛,还有一条像纽约流行穿着那样的、黑白相间的长尾巴。
贝茨先生坐在高高的高脚凳上,正在做一个雕塑。
当贝茨先生听到陈淼淼希望申请罗德岛设计学院时,蓝框小圆眼镜后面的眼睛突然就张大了,好像它们是被心中一股突然爆发的喜悦自然而然撑大的。
这倒吓了陈淼淼一跳。她以为自己没说清楚:“老师,我要去的不是罗德岛的布朗大学,那个藤校,而是罗德岛设计学院,那个学画画的学校。”
“哈,知道啊,美国最好的设计学院!”贝茨先生紧紧捏着手里的那块泥,激动得手指甲盖都发白了。
说起来,陈淼淼还真是个幸运的孩子,她的老师们那充满喜悦的眼睛,那种对自己的学生找到自己理想的欣喜和祝贺,是那样鼓舞了她。
陈淼淼拿出一个崭新挺括的黑色硬塑料夹子,这是特地到小城唯一一家美术商店里买来的正式画夹。她打开它的时候,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害羞。那种害羞带着一股自我保护的感情,好像在催促她赶紧关上,从老师这里逃走——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可笑了,应不应该说出那所伟大学校的名字,自己的画,真是不配用这么贵重的夹子的吧。
贝茨先生欣喜的眼神按下了她的惊慌失措。
于是,陈淼淼努力镇静自己,打开画夹,里面其实只有两张画,比起画夹,画纸简直寒酸,又皱皱巴巴的。
“真不好意思啊。”陈淼淼忍不住说。
“让我看看。”贝茨先生摇摇头。
她拿出那张蓝色小花的画,又拿出那张鹿,让它们轻轻躺在老师面前的桌上。
当贝茨先生把手擦干净,放在桌子上时,陈淼淼预先就感到一种疼痛,好像他的手指要来碰触她敞开的伤口了一样。陈淼淼想起来,小时候摔破膝盖,爸爸用双氧水为她清洗伤口时,自己闻到药水气味,就先疼了起来;小时候生病去打针,护士在屁股上擦酒精时,屁股上的那块皮肤也是这样的。
“哇哦。”幸亏贝茨先生声音也很轻。
“你是不是有过阅读问题?”老师问。
“嗯?”
“就是有时候你读文字,觉得理解上有点困难——字都认识,可理解句子的意思要慢一点。”
“小时候有的,很慢,完不成作业。”陈淼淼想起妈妈用左手帮她写作业的样子,然后,又想起那些艾比让她读的诗歌,“现在好点,要是能一边读出声来,一边理解,就容易多了。”
“那就对了。你知道你的作品里有图像思维形成的结构吗?这似乎是天生的能力,你是个幸运的人,天生就是该画画,还真喜欢上画画了。”
“什么叫图像思维形成的结构?”陈淼淼怕老师搞错了,自己哪有这么高深,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
“就是你的画面不是为了记录故事,而是为了讲故事。”
那么,看字慢,默写总是错,b、d、f、k这类字母总是写反,都是天才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粗心啦?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因祸得福的事呢?陈淼淼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一定闪闪发光起来了吧,她不信自己的耳朵。
“这样的人,小时候通常会有点对读文字的障碍。”老师抬起脸来,安慰她说,“也许对弗里曼小姐来说不算好消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评判你美术天赋的一条私人标准,是好消息。”
“哟!”陈淼淼吓着了。
“能去罗德岛设计学院的,都是有天赋的人,你应该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贝茨先生并没有碰陈淼淼的画,只是把头凑得很近,好像修钟表的师傅那样小心。然后,他郑重其事地抬起脸来,脸上的喜悦更深了:“如果你信任我,我也会全力以赴帮你准备申请资料的。”
“我真的行吗?”陈淼淼摇摇自己的头发,“怎么好像做梦一样。”
“也许这两张画老师觉得好,只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了。”陈淼淼将这句话翻译成“耗子正好死在瞎猫跟前”。
贝茨先生身体向后一仰:“你是这么判断这两张画?你的处女作?”他窄长的脸变得通红,好像被打了一巴掌,“有趣!”
陈淼淼见老师恼了,赶紧解释说:“我爸爸叫我要谦虚,我有什么好事,他总是这样说我,不让我骄傲,骄傲让人落后啊。”
可贝茨先生并不释然:“那么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陈淼淼说:“我就是喜欢画画。”她想了想,“可以说非常喜欢。”
“你是有天分啊,上帝给的。”贝茨先生宣告,“你值得让罗德岛设计学院的老师好好栽培你。”
“可是,你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行。”贝茨先生警告说,“非常非常非常。你行吗?”
“我行。”陈淼淼做了一个大力水手的样子。
陈淼淼高兴得有点头晕,点头太多、太快了。
下一节课就是英文课,弗里曼小姐在讲希腊神话里那些半神半人。陈淼淼的心缥缥缈缈的,好像喝过爸爸的黄酒一样。弗里曼小姐一定看出来了,她对陈淼淼眨眼睛,但没提醒陈淼淼回过神来听课。英文课上,陈淼淼正在遥远的希腊穿行着,达芙妮讨厌阿波罗,又逃不过他的追求,所以就赶紧把自己变成一棵月桂树;达罗斯为自己和儿子伊卡鲁斯做了翅膀,是用蜡粘起来的,他们想一起飞回家,可伊卡鲁斯飞得太高,翅膀上的蜡被太阳晒化了,就掉进了大海。陈淼淼半心半意地听着,突然心里一动。她想起一个日本童话里的故事,妈妈穿上羽衣就飞走了。所以,所有的羽毛都应该固定在一件衣服上。
英文课一下课,贝茨先生已经站在教室门口等陈淼淼,手里拿着的那一沓A4纸,是他为陈淼淼打印下来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对考生作品集的要求。
就这样,陈淼淼的作品集开工了。
一个人要是在少年时代就认出了自己对将来的理想,此后的日子,就会像开一台车,油门一踩到底,日子就像窗外的风景一样,“哗啦啦啦”地飞快掠过了,因为他风驰电掣地向自己的理想奔去了。而且,刚刚找到自己理想的时候总是会万事顺利,一路上都落满了金苹果。
陈淼淼早上一醒来就去学校上课。放学了就抓紧到图书馆做功课,静悄悄的图书馆里不能出声,陈淼淼有时就在心里哼着小曲。学校要关门了,陈淼淼就赶紧回家,按照罗德岛设计学院的要求准备作品集,电脑里轻轻放着小曲。有时候几个小时过去了,飞也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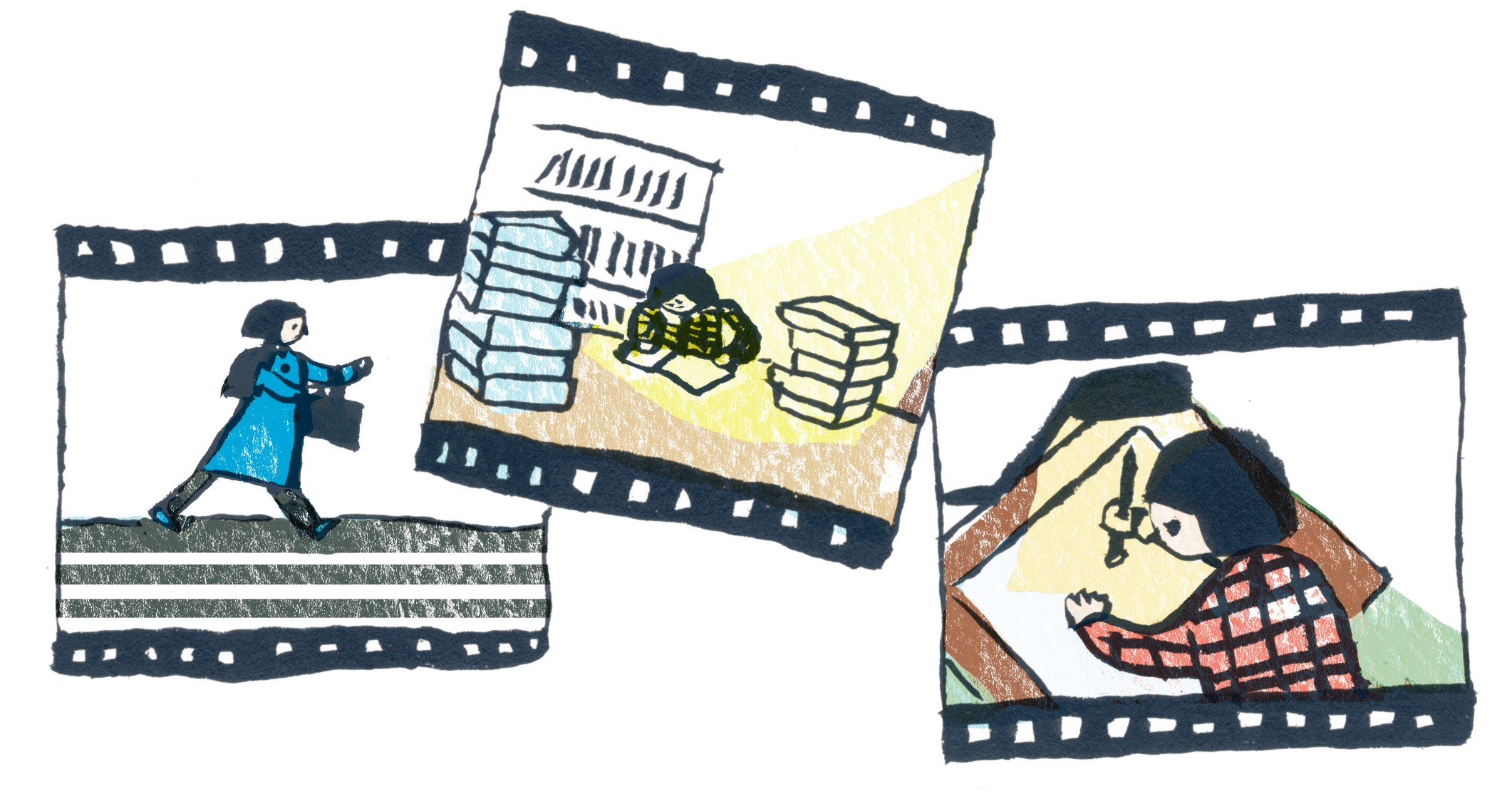
有一次陈淼淼觉得那小曲实在太好听了,就过去翻了一下曲单,这才发现那曲子竟然是古典乐《卡农》,这可吓了她一跳,她惴惴不安地想着自己,什么情况啊?难道自己竟然高级到可以跟古典音乐心意相通了?
人生突然在她面前展开了一条又大又远又美丽的大道,陈淼淼实在不敢相信,一个人心里有了一个对将来的目标,整个生活竟然会变得如此充满乐趣、充满信心、充满力量。原来一个人对将来的目标,就是一辆轰轰作响的哈雷摩托车啊。
她有时想起那条在鱼缸里一边游一边拉细条粑粑的小鱼,特别是在四周一片寂静的深夜里。大家都睡着了,只有她还精神抖擞地画着各种画,想着世界的各种形状。她的理想不是当这条懒鱼的吗?现在变成了夜以继日赶路的夸父。
有天早上刷牙,陈淼淼突然发现镜子里的那个人挺漂亮的,然后她惊奇地发现,那个人就是自己。
她告诉艾比,艾比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你干吗这么外强中干呀,你从今天起,就要确认自己是天才。”艾比握着拳头做出个罗马皇帝上朝的样子,然后说,“将来你发达了,我就公开展出你现在用过的东西,一美元参观一次。”
艾比开出了新书单,叫陈淼淼到公共图书馆去借《艺术的历史》回来读。她说,关于诗歌,她听腻了。因为陈淼淼的志向,启发了自己对艺术史的兴趣。
因此,陈淼淼知道了除了遥远的希腊雕塑很了不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也很了不起,而亚述文明中,牛有一对强壮的翅膀,羽毛在翅膀上排列得非常整齐,而且雄壮。
晚上想起艾比,陈淼淼想起从前爸爸教妈妈的一句话:“额骨头碰到天花板”,形容难以想象的幸运。那次是因为陈淼淼居然语文考了九十几分。画出艾比家的房子时,陈淼淼探索到了自己心中的感激。她想,是不是自己更应该支付艾比家庭教师费用啊。艾比用点心、诗歌、朗读、温暖,以及她自己的亲切和时不时的忧郁,让陈淼淼不知不觉摆脱了对文字的阅读障碍,特别是对《艺术的历史》这种又厚又难的书的畏惧。
所以,陈淼淼画了艾比在树林后面的房子,那个玻璃屋顶的大厨房。
然后,陈淼淼用沃尔玛的大号黑色垃圾袋和银色厚胶布制作了一条连衣裙。按照贝茨先生“尽量拓展”的教导,她决定要做一件衣服,一件在本城最贵的服装店橱窗里看见的连衣裙。陈淼淼很喜欢那件有泡泡袖的塔夫绸连衣裙,但是她不能用爸爸的钱买这么贵的衣服。她总是想,等艾比给的工资存够了,自己就来买这条裙子。可是还没等存够钱,那条裙子就从橱窗里消失了,被别人买走了。
陈淼淼就做一件。黑色垃圾袋的厚塑料天生有种塔夫绸的假象。
陈淼淼发现,这次贝茨先生拿起连衣裙的时候,自己竟然不再感到疼痛了。
贝茨先生轻手轻脚,把连衣裙平铺在工作台上。虽然它用的是垃圾袋的材质,靠的是银色封箱带把裁开的垃圾袋粘在一起,再挂在一块钱能买十只的白色简易塑料衣架上,但贝茨先生小心翼翼的样子,是富有接触艺术品的特殊训练的,富有教养的。他细心而灵巧地帮它捋平泡泡袖上的皱褶,并在工作台上摆出亚历山大·麦昆模特儿的造型。
沃尔玛的垃圾袋得到如此尊重,倒把她吓了一跳。“我竟然这么厉害了?”陈淼淼惊喜得直嘀咕。她把一双白球鞋从书包里抽出来,放在裙子下方:“应该这样配。”
贝茨先生眯着眼睛端详了半天,说:“好像你造型的空间感更好些。我不敢说是不是对,我就是这么感觉。”
“我是穿在自己身上一点点粘起来的。”陈淼淼笑了,“封箱带有时粘在身上,撕去了许多汗毛呢。”
“咦!”贝茨先生怕得牙齿都酸了。
而陈淼淼很赞许自己的英勇。
“你想过学雕塑吗?”贝茨先生问。
“我心里还想做一个更艺术化的作品,”陈淼淼被贝茨先生夸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踊跃地挖出心里的一个念头,“我想要按照小时候童话里的故事做一件羽衣。”
“什么?”
“仙女到湖中洗澡,把羽衣放在湖边。羽衣被渔夫偷了去,仙女就不能飞走了。我想要做一件羽衣。这是我们中国的故事。”
“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故事啊。”贝茨先生说。
“我想做一件真的能飞的羽衣,比伊卡鲁斯的翅膀结实的羽衣。”
“那就去做。”贝茨先生念了句耐克电视广告里的广告语。
陈淼淼备齐了大大小小的羽毛、结实的白布、蓝色的丝线、大号的缝衣针,以及固定用的白蜡,就开始做一件羽衣。她按照妈妈给的那对翅膀的样子,排列了大小不等的羽毛。渐渐,这对翅膀变成了说明书,令陈淼淼明白翅膀上,不同羽毛的分工:
那些长而坚硬的羽毛,带有挡风、飞翔和遮雨的作用。
那些短而坚硬的羽毛,在长羽毛张开的时候,会和长羽毛连成一片。在需要找准风口的时候,能像刀片一样锐利地切入风口,这是老鹰能在天空上,张着翅膀飘飘摇摇许久的原因。
那些小而柔软的羽毛,卷曲的,白色的,轻柔的,密密地贴在里面,就好像一件贴身的小棉袄。
慢慢地,妈妈来到她心中。
这是献给妈妈的羽衣。
愿妈妈能穿上它飞走,再也不用东躲西藏。
但愿妈妈飞得高时,蜡不会化;飞得远时,不会着凉;风雨来了,不必在别人家屋檐下躲藏。
完成的那天晚上,陈淼淼把羽衣平摊在地板上,羽毛都整整齐齐,密密的蓝线把根部缝得很结实,再用白蜡封住所有的针脚,那真是一件货真价实的羽衣啊。
那真是一件漂亮的羽衣啊,就像圣诞节才能盼望得到的贵重礼物。驯鹿运送了全世界的礼物,但是,驯鹿自己也应该有一份圣诞礼物吧。
陈淼淼不知道,自己是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入学考试准备这件作品的。但是,当这件羽衣完工,在桌上平铺开,羽毛在灯下闪烁着洁白的微光时,她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件给罗德岛设计学院入学考试用的艺术作品,而是给妈妈的礼物。就像妈妈给自己做冬衣时,总是密密地缝,密密地缝,陈淼淼也密密地缝,密密地缝,祝福妈妈能用它高高地飞过路易城的上空,高过所有来复枪的射程。
当陈淼淼在贝茨先生教室的工作台上,学着贝茨先生的样子,轻手轻脚地摊平这件羽衣的时候,陈淼淼发现如今自己的心里时常荡漾的已不是单纯的快乐,而是悲喜交织的复杂感情。她发现,当望着自己亲手做完的东西时,心里淤积多年的悲伤、遗憾和恐惧,变化成为仁慈——艾比老提起这个词,路易城的医院也叫这个名字——陈淼淼想,自己心里那种要张开双臂拥抱什么,想要护卫什么的感情,就是它吧。悲伤和恐惧因此而化成了一汪清水。
贝茨先生默默地看了又看,然后走过去关上了头顶的日光灯,在工作台上布了其他光源。
灯光透过羽毛,刹那间使那件羽衣散发出一种行将别离滋生蔓延的祝福。贝茨先生说:“它会让每个看到的人都静下来,都想起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艺术给予人心的幸福。”
“兄弟,你长大了。”陈淼淼轻轻拍拍自己的肚子。
又到了一年中罗德岛设计学院招生处的老师来面试学生,并指导考生准备作品集的时候了。
贝茨先生帮陈淼淼约定了在芝加哥的面试时间。和贝茨先生一起整理作品集的时候,当贝茨先生把陈淼淼的作品都拍成幻灯片,再装进罗德岛设计学院申请专用的幻灯片资料袋,夹在灯箱上时,陈淼淼才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积累了满满一画夹的作品了,这才选出二十张作品申请用。
这是一个刚刚找到自己的理想才一个月的人啊。陈淼淼暗中拍着自己肩膀,说,兄弟,你年轻有为!
贝茨先生也心满意足地感叹道:“他们怎么能不收你!”
陈淼淼实际上听不得别人表扬,别人表扬她,她就有点紧张,所以她劝慰贝茨先生说:“老师,要淡定,淡定。”
贝茨先生这次有了心理准备,没生气,只是“噗”地笑出了声:“又是你爸爸教的?怎么听上去不大真挚。”
面试时间定在周末的下午。
周五放学前,贝茨先生再三叮嘱陈淼淼路上要当心,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金色的眉毛从眼睛两边挂了下去,变成了两条倒挂的眉毛。
其实陈淼淼根本就不会开车。
所以她早已买好了从路易城图书馆底楼出发的灰狗票,灰狗公司的长途车会带她到芝加哥,然后,她再转地铁去芝加哥大学附近的面试地点。面试时间是下午四点,上午从图书馆出发,一路都是高速,中午就到了。
贝茨先生听到陈淼淼的计划,明显松了口气,眉毛这才又升了上去。
虽然他们没多说,但在双方心里,都看见了苏丝。
但是,周五晚上时,本地电视新闻里突然报了异常天气预警:明天将有龙卷风来袭。陈淼淼站在电视机前,一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其实,陈淼淼不怎么害怕龙卷风,龙卷风带来过奇迹。
这是真的,比如艾比家厨房里那棵神奇的松树。
美国的大平原上流传着不少龙卷风的传奇,听上去都不怎么坏。反而像《绿野仙踪》的故事里描写的,龙卷风带多萝茜去历险,遇见一个用洋铁皮做的人,又遇到了一个稻草做的人。而艾比和陈淼淼都是胆小的狮子。狮子最后就成了百兽之王。陈淼淼现在知道什么事都不能怕,要拼命去做,然后,希望和幸运就会降临,童话故事里总是这样写的。
陈淼淼心里总觉得龙卷风不坏,反而有点期待。
那天晚上真的开始下雨了,后来,还下了一会儿小粒冰雹。碎冰雹“哗啦哗啦”打在窗玻璃上,连林子里的夜鸟都被吵醒了,但它们鸦雀无声的。
又干爽又安静的房间在风雨声里显得格外舒服。陈淼淼在临睡前开了一罐冰激凌吃,她甚至还觉得自己要在龙卷风里飙一辆又大又长的灰狗车,像冲浪一样在龙卷风的乌云里穿梭,那真的帅死了,传奇死了,简直就像那棵松树。
人人都说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是全美国最乏味的地方了,但陈淼淼却在这里感受到中西部特有的、寂静中异想天开的浪漫。人人都说爱德华·霍普[11]画的是美国大地上特有的孤独,但陈淼淼却感受到它们特有的诗意,特别是当她认出来霍普画的如大砍刀般的阳光。
临睡前,爸爸打来电话,陈淼淼都没有提龙卷风的事。
“好吗?”爸爸问。
“好得要死。”陈淼淼嘻嘻哈哈地回答。
“艾比那里还去吗?”爸爸本来不放心艾比,他觉得世界上的事不能这么完美,后来他把艾比当成了自己最信赖的人。陈淼淼就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了。
“当然去的。艾比做焗兔子头给我吃了。赏我给她读《艺术的历史》,光那些意大利名字和希腊名字,就难死我了。”陈淼淼知道爸爸会吓一大跳,“焗兔子头是加拿大那边的法式名菜哦,一般人都没钱吃这么贵的菜。”
哪知道爸爸竟然兴高采烈地惨叫一声:“我也跟同事去吃了个粗菜坊的猪头。据说是香港人发明的,用鲍鱼汁炖的。”
“嘿嘿,我们大家都挺会放飞自我的。”
“兔子眼睛还在吗?”
“当然不在,你想点啥,爸爸,这是限制级别的哦。”
“我的猪头还微笑的呢。”
“哈哈,你的猪头。”陈淼淼抓住了爸爸的把柄,哈哈哈,这次尽欢而散。
陈淼淼想,等招生处的老师看过羽衣了,她就送羽衣给妈妈当告别礼物。等妈妈顺利飞走了,她就一往无前地去罗德岛。这些天后背不那么胀痛了,她就永远不告诉爸爸翅膀的事了。但是现在,她还真的不怕翅膀了,它是精密而美丽的物件,就像妈妈送她的那朵名叫宇宙的野花,小而精密,甚至有些脆弱,令人爱怜。
第二天,陈淼淼还在去灰狗车站的路上,就听到警报了。乌云在小城上空越压越低,闪电在乌云里闪闪烁烁,藏头露尾的,还真像童话书里魔鬼的尾巴。往天上集合的乌云那里看,就好像有许多夹着闪电尾巴的魔鬼排着队在乌云阵里穿梭不停,忙着干坏事。
到了灰狗车站,陈淼淼才发现候车室里只有一个职员,一个等车的人都没有。在这个小城里,灰狗一天只来一班,通常都有不少学生在这里等车,去周围的威斯康星大学校区,或者艾奥瓦州立大学,要不就去建阳学院。可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灰狗公司的职员是个黑人大妈,长得像面包一样软胖。“甜心,回家吧,今天没车。”她对陈淼淼慵懒地挥了挥手指。
“干吗?”
“今天赶驴不赶马呀,龙卷风比灰狗跑得快。”
“可我要去芝加哥。”陈淼淼平静地说,理所当然要去的,她都不明白大妈在说啥。
越过大妈厚实的肩膀,她看到大妈身后墙上的钟。它挂在一面星条旗旁边,响亮地走着,“咔嗒咔嗒咔嗒”,还有几分钟,车票上的时间就到了,车子就该来了呀。
“灰狗根本就没出发。”
大妈平心静气地劝说陈淼淼跟她去地下室躲躲。小城里的警报响了,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得带个枕头去地下室了。
大妈从椅子后面抽出一个软乎乎的大枕头,锁门去地下室了。
站在图书馆屋檐下,陈淼淼看到高街后面的树林,树梢全都在东倒西歪,好像有个看不见的大屁股坐在上面拧来拧去一样。
然后,一扇谁家的纱门在半空中飞过,好像一架纸飞机。
陈淼淼这才意识到,她去不了芝加哥了。去不了芝加哥,就意味着她不能参加面试了。
可她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个噩梦,就像她一直都会做考试的时候卷子上什么字也没有的噩梦一样。
她站在屋檐下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过了好一会儿,陈淼淼才想起来应该打电话。
“艾比!”叫出这个名字,陈淼淼才忍不住眼泪的。
“等着。”艾比说。
“我想去呀!”陈淼淼对着天上无声地转个不停的乌云哭了。
这时她看到摇摇晃晃地飘过来一朵小蓝花。在飞沙走石的街道上,它好像一只飞过大海的蝴蝶一样不真实。“妈妈,我想去面试。”可她转眼就看不见小蓝花了。
艾比来了,从她车里探出头来:“出发喽。”
她说,正好一起去一下芝加哥。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出城的大道只有一条,就是华盛顿街。这会儿街上已经什么人都没有了,两边楼上的窗子全都关上了木板窗,它们因此变成了一个个密封的大盒子,安静得好像每扇窗子都屏住了呼吸。
天空也是一团寂静的,但乌云却在天上转着圈,闪着电。它们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旋涡,闪电却没有带来应有的雷声,它们不是魔鬼的尾巴,还能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多萝茜的叔叔婶婶都躲得无影无踪的原因。
艾比打开车里的收音机,所有的频道都停止了日常节目,一律只报告龙卷风过境的警报,以及它的走向。
“预计四分钟后,它将要从高街转向华盛顿街,正面攻击我城最核心的街道。”
天上应声就裂开了一道口子,只一眨眼工夫,地上到处滚动着闪闪发光的冰雹。艾比的车窗上也堆起了一层冰雹。
天“咔嚓”一声就暗了下来。其实不是天黑,而是漫天的乌云都压了下来,几乎盖在街面上了。即使是在紧闭的车里,陈淼淼都能闻到一股阴森的水汽,来自高空的冰凉的水汽。
她看到高街挂在电线杆上的绿色洋铁皮街牌被风摘了下来,刹那间就飞向空中,狠狠撞在图书馆的墙上,好像一张纸。
突然就天崩地裂了。
正在这时,华盛顿街的红绿灯下突然出现了一头野鹿。
它没管红灯亮着,沿着街道中央的黄色隔离线一路飞奔过来,一直跑到车前,站下。
隔着细碎的冰粒,陈淼淼看到它破碎的鹿角。
野鹿转身开始往前面跑,带她们穿过几条小街,只是几分钟的路,她们就跟着它开进了树林里。
神秘林里虽然也是飞沙走石,但是高高的大树却像帐篷一样庇护着她们。
艾比和陈淼淼都知道它是特地来救她们的。它带她们走了一条可以避开龙卷风的小道。但是树林子里没有路可以回艾比家。
艾比熄了火:“稍等。”艾比想等风头稍停一些。
可是,野鹿跑过去站在艾比那边,直直地看着艾比。
然后,它跑到车头上,转头回来看着她们,它要为她们带路。
艾比就跟了上去。
她们在树林里越走越深,树枝“噼噼啪啪”地打在玻璃上,也打在野鹿的身上,有时还将它的身体划出血道子来。
但她们都没有停。
它跑起来有些跛,原来它有条腿瘸了。陈淼淼猜想,那条腿应该是瑞秋爸爸那天打伤的吧。
妈妈,谁给你擦红药水呢?
当它最终拐进树林深处被陈年落叶覆盖住的小路时,艾比突然轻轻拍了下方向盘,说:“这就对了!”陈淼淼看到一滴又一滴大大的眼泪从艾比眼睛里滚下来,在眼镜框边上汇成小溪,汩汩而下。

艾比说:“爸爸用外科手术帮我摘掉翅膀骨头,原本以为只是清除多余的骨头,但没想到这样伤筋动骨。我就是二级残废的正常人,但在危险天气不能开车了。”
原来艾比也是精灵的孩子。
“原来我可以。”艾比哭着笑了,鼻孔里吹出了一个大鼻涕泡泡。
这个大鼻涕泡泡把她们两个人都逗笑了。
等她们终于从另一端钻出树林时,龙卷风已经落在树林后面了。
辽阔的玉米田后面,太阳正从涌动的云层后面升起。如果没有见过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平坦无垠,就不能感受到龙卷风之后的阳光普照,会在人心中激起怎样壮丽的、再获新生后的感激之情。
野鹿止步在林边,等看到她们的车拐进了前往芝加哥的高速公路,它就转身跑回林子里去了。
“谢谢你。”艾比轻轻拍了两下喇叭,并伸出她的右手,将手掌平坦地竖起。
“谢谢妈妈。”陈淼淼也伸出她的右手,将手掌平坦地竖起。
“艾比,你让我也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陈淼淼说。
艾比的车飞快地向前赶去。
她们不知道,野鹿一直在树林边缘跟着她们,努力奔跑着,跟随着。
它不敢跑到大路上,所以,它继续在公路旁边的小道上跑。
越过树林,
越过玉米田,
越过阿米什人的村子,
越过墓地,
越过摩门教徒当年迁徙留下的古道,
直到接近芝加哥的地方,高速公路变得宽阔,树林、田地以及墓地都渐渐被房屋和工厂代替,它才停下来。
可它一直看着那辆装着它孩子的车子汇入车流,看到她将会安全到达她的面试地点。
它悄悄躲在离芝加哥最近的一棵大树后,垂下了头。
它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
第一次看到陈淼淼,是在上海,那时是她的妈妈。第二次看到陈淼淼,是在路易城,这时是一头不相干的野公鹿。
它早就知道,陈淼淼所期待的东北部,是它此生再也去不了的地方。但是,它的爱并不是要让陈淼淼留在它身边,安静地画一辈子野鹿和小蓝花。即使现在已经是一头公鹿了,它的爱仍旧是一位母亲的爱。这世界上的爱有许多种,却只有母亲的爱不希望孩子永在身边,而是祝福自己孩子的离开。
即使是一头公鹿,它也求自己的孩子能没有自己也过得幸福。
它知道自己会有一件结实的羽衣,不会像希腊人那样从太阳旁边摔下来,但它不知道自己还能有帮陈淼淼接近她的理想的幸福。妈妈从来不习惯只收孩子的礼物,只有她知道礼物对自己的孩子也好,才能心安理得地收下。它甚至觉得在神秘林里,自己因为这件羽衣,会变得太出挑了,有点不好意思。
前往芝加哥的车流“哗哗”地从这头东躲西藏的野鹿身边经过。那么多聪明的人在开车,可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头野鹿心里的幸福。《白雪公主》的故事其实早就已经告诉过人们,野鹿的心与人的心非常相似,所以,被皇后派去杀白雪公主的猎人,杀了一头野鹿,取了野鹿的心脏去向皇后交差。但是,从小听这个故事长大的人,不会去想野鹿心里装着什么。
那天,龙卷风横扫过的平原地区,约好面试的学生们都没能来。所以,当陈淼淼出现在招生处老师面前的时候,老师非常惊奇。
“我妈妈那时总说,我从小就有额骨头能碰到天花板的幸运。”陈淼淼大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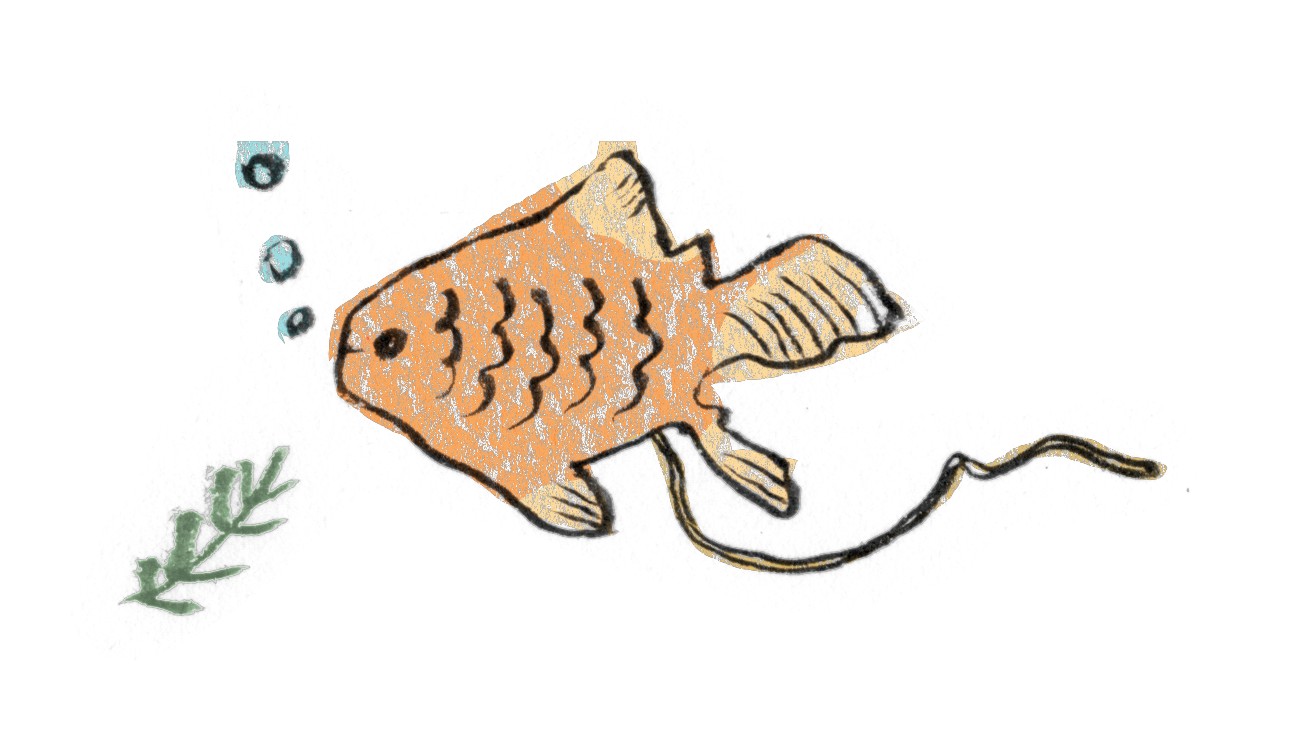
[11]爱德华·霍普(1882—1967):美国绘画大师,擅用锐利的线条和大幅的块面勾勒平凡的都市场景,画风寂静而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