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对翅膀
陈淼淼房间的窗子向着一个草坡,草坡的另一边,就是一处密密匝匝的树林子。如今她知道这个树林就是本地有名的神秘林,也就是她在飞机上看到的那片深绿色的树林,它隆起在一条长坡上,一直通向大山里的森林。长坡的另一头,连着陈淼淼的学校、她住的地方,以及四周一些零零星星的人家。沿着神秘林边缘的小路,她每天都能走去学校。
她插班进了高中。她在中国学的数学和物理比十二年级的同学学的还深,可以直接免修了,但她的英语和历史则大大不够,所以她的课表是把数学和物理课的时间都腾出来,去补文科的缺口。陈淼淼去英语教室见弗里曼老师。她一共打了六个耳钉加一个鼻钉,是从艾奥瓦大学写作系毕业的艺术硕士,一位小说家。
她笑嘻嘻地说,有时测试卷子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情况,所以陈淼淼得写一篇作文交给她。
“题目呢?”陈淼淼问。
“随便。写你想说的。”弗里曼小姐说。
哪能这么随便呢?陈淼淼反而写不来了。中国的作文课,都是题目有了以后,三段式,哪一点不到就扣分。
看到陈淼淼苦着脸,弗里曼小姐就帮着一块儿想了想,“比如说,你对自己将来的期待。”弗里曼小姐说。
就是理想是啥啰,这个容易,从小写到大了,都不用打草稿。
小时候跟着班上小孩一起写,要当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被妈妈嘲笑了。妈妈一脸不相信地问她,科学家很好玩吗?屁股坐得都扁了。企业家更不好玩,得一直一直想挣钱的事。钱是用来花的呀,还不如想想怎么花钱。
陈淼淼想了一下,就更正自己,说理想是当个玩具设计师,一边玩,一边就养活自己了。
不过,理想是一直在变的,长大一点,就变一次。现在陈淼淼被弗里曼小姐一问,反而茫然。在陈淼淼心里,理想慢慢变成了一种量子般的物质,既神秘又具体,就像童话里的白马王子一样,还带来了一个吻。最后写到这个神奇的kiss for waking up from everyday life[2],陈淼淼有点小激动,“虽然见不着它的脸,不晓得它到底是什么,却听得见马蹄声。”
弗里曼小姐给了一个大大的A+。发还给她的时候,弗里曼小姐还悄悄拍了下陈淼淼的肩膀,说:“等着,耐心,它正骑马赶来。”
接着,弗里曼小姐就递给陈淼淼一张书单:“亲爱的淼淼,等着也是等着,不如完成一下我们上个暑假已经布置给英文课学生阅读过的必读书呗。”
那张书单上列出了五本书,莎士比亚的剧本《仲夏夜之梦》,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弗罗斯特的《诗合集》,E.B.怀特的《夏洛的网》,卡佛的《大教堂》。
陈淼淼的头“嗡”地一下大了。她不是个坏学生,可她还从来没完整地读过一本英文文学作品啊,就算在上海,语文老师也没把《红楼梦》和《诗经》开在暑假书单上呀。她敢说出来莎士比亚吓住了她,至于卡佛,她可不敢告诉弗里曼小姐,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
陈淼淼觉得自己竟然还敢谈那光芒四射的理想,未免有点太不要脸了。
弗里曼小姐微微一笑:“五本里必须读完两本。还有看指定的电影,两个电影替换一本书。”
“多选题啊?”陈淼淼心中狂喜。
弗里曼小姐说:“当然,你永远拥有选择的自由。”
所以,《教父》《大鱼》两部电影顺利替换了诗集。“我这个人不大懂抒情的。”陈淼淼说。
“有种特别敏感害羞的人,就喜欢藏在大大咧咧的面具下。”弗里曼小姐说,“你读了卡佛就会明白那种感受的。所以卡佛对你来说是有益的。他是我上大学时来开讲座的作家哦,我的偶像——应该这么说,他是全美短篇小说写作者敬仰的人。”
既然这样,陈淼淼只好咽下了关于卡佛的讨价还价。
“你不用怕《仲夏夜之梦》,基本就是一群小仙人在林中飞来飞去。”弗里曼小姐两个白白胖胖的巴掌在肩膀旁边呼扇着,一副开玩笑的轻松,“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
陈淼淼点点头:“这个故事我有兴趣的,会飞的人。”
“不过,为什么会飞的人只能在树林里活着呢?”
“你写个读书笔记吧,就这个主题。”弗里曼小姐点点头,“好问题,为什么仙人们无法生活在我们的公寓里。”
“因为人们不接受仙人这个事实。”陈淼淼突然说出这句话来,连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即使是伟大的莎士比亚,也只能让他们活在树林里。
“作家们从未停止过对仙人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想象。你通过阅读最好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文学对培养一颗宽容的心所倾注的耐心。”
弗里曼小姐的眼睛闪闪发光,这是一个热爱自己理想的人,陈淼淼看懂了这一点。她突然就对文学产生了好感,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想自己也许可以读完一本全是字的书,而不感到太痛苦。陈淼淼从小就害怕阅读,每个字都认识,把它们归拢在一起也还行,理解段落大意可就费劲了。
延伸阅读的,是另两部电影《天使在人间》《柏林苍穹下》。讨论的是当天使不得不来到人间,它们要如何进入日常生活。
“但是,你要因此换掉《汤姆·索亚历险记》就太可惜了。”弗里曼小姐说,“老实说,要是你不读一遍《汤姆·索亚历险记》,许多美国形容词你听不懂呀。你可不想同学们说笑,你听不懂吧?那多尴尬。”
“不不,我不换,我要看这些电影的,我有兴趣。”陈淼淼说。
“好,我们成交。”弗里曼小姐高兴地用中指敲了敲桌子,好像她捡了多大的便宜似的。
瑞秋比陈淼淼高一年级,可她一直约着陈淼淼一起吃午饭,放学后到图书馆一起做作业,有时也一起出去吃冰激凌。每次,她都悄悄打量着陈淼淼,陈淼淼知道她把自己当成了那个死去的女孩。那个女孩叫苏丝。每当发现陈淼淼觉得尴尬时,瑞秋就很抱歉:“我忍不住啊,苏丝是我最好的朋友。请你多给我一点时间吧。”
陈淼淼就像瑞秋那样,也用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摸摸她的手臂:“我明白的啊,失去自己喜欢的人。”
“是永远失去了。”瑞秋摇着头,眼睛里涌出亮晶晶的泪水,“再也见不到了呀。”
“明白。”陈淼淼点点头。她假装没看到瑞秋哭了,因为她觉得让别人看到自己流泪很丢人,她也不相信永失所爱的痛苦是可以正视的。
“要不你忘记吧。”她有一次对瑞秋建议说。
“我也想呀,可我还做不到。”瑞秋说。
“假装嘛。”陈淼淼说,“假装着,就会变成真的。”
瑞秋“吱”的一声把车停在乡间小路中央,长叹一声说:“苏丝也常说出这样宽容的话来。你们是真的像啊。”
就这样,瑞秋成了陈淼淼在新学校交到的第一个朋友。瑞秋是觉得陈淼淼像苏丝,她也才十八岁,苏丝是她生活里第一个永别的同龄人;而陈淼淼看瑞秋,就像看见妈妈刚离开时候的自己。她们两个人就这样摸索着成了朋友。
不过,瑞秋是真的朋友吗?
瑞秋那天看到她吃葱油海蜇头时,又惊又怕的脸色,好像她在当面吃青蛙一样。瑞秋说,自己和苏丝都是蒙特勒水族馆里的美丽水母的爱好者,她不能想象有人竟然把水母盐腌,然后在嘴里“咯吱咯吱”吃掉。而且,这个人还跟苏丝长得这么像。
可是,瑞秋那天在转课换教室的时候飞奔过来,递给陈淼淼一张小告示,是她跟她妈妈去农人集市时发现的。有人要找一个朗读者,为行动不便的中年女士每周借书并朗读书籍,每小时付费十二块七毛五分。“看看,就好像是给你预备的一样!”瑞秋高兴得整个脸都闪闪发光了,点着“要求”这一栏里注明的一行小字,“有亚洲经历者优先。”瑞秋欢喜的样子,和李雨辰为她高兴的时候真是太像了。
“苏丝申请罗德岛设计学院时,就想要一个付费工作的经历,这对她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很重要。可那时她就是找不到呀。”瑞秋说。
有时放学后,瑞秋会开车带陈淼淼去森林另一边的小镇,吃一家法国人做的冰激凌,因为从前瑞秋和苏丝一起去吃过。“那是我们这个平原上最好吃的手工冰激凌。这家人世世代代做这种冰激凌,还是从法国带来的配方呢。”瑞秋每次都绕开神秘林,她说那是路易城人人都绕着走的地方,“那里的黑林子里趴着一种邪恶的力量。”
但是,按照告示上的地址看,那位名叫艾比·麦卡锡的女士就住在神秘林的另一端。
“你去她家上班,千万绕着走。”瑞秋嘱咐说。
陈淼淼跟爸爸说好,每个周末都用Skype视频一次。爸爸每次都问:“过得好不好啊?”
陈淼淼每次都说:“好得要命。”
爸爸总嫌陈淼淼说得太笼统,就问:“怎么个好法?”
“作文得了一个A+。”
“呀,天才了吗?你不是最烦写作文、看书的?”爸爸吃惊地笑。
“开什么玩笑,这学期我的必读书是莎士比亚哦。”陈淼淼很骄傲。
爸爸立刻被莎士比亚吓住了:“谁?”
“威廉·莎士比亚。”陈淼淼庄严地说出他的全名。
“哎哟喂!”
“卡佛你知道吗?”陈淼淼又说。
“不知道。”爸爸说,“他是干啥的?”
“小说家。”陈淼淼说。
爸爸看她的样子,好像哥伦布看到新大陆一样一脸懵。他想象不出来最讨厌看书的陈淼淼怎么要变成文学新秀。
有一天,爸爸突然穿了一件粉红条子的新衬衣上线,整个人好像变了一样。陈淼淼说:“啊,你怎么像新娘子一样啦。”
爸爸立刻说:“不要瞎七搭八。”
他看看自己身上,说:“就是参加医疗队去地震灾区,来不及买换洗衣服,手术室的护士长帮我去买的,买来了,总归要穿的。”
陈淼淼记得手术间的那个护士长,她一直帮爸爸干事,像他们家的田螺姑娘一样。陈淼淼这次到美国的箱子也是她帮忙选的。
“是田螺姑娘啊?”陈淼淼问。
“还有别人一起的。”爸爸说,突然他的脸显出了恍然大悟的吃惊,隔着两张显示屏,让陈淼淼看了出来。
“你总归好的啰。”爸爸转过神来问。
“很好呀,很好的呀。”陈淼淼说。
其实,陈淼淼不知道自己到底算好还是不好。人生第一次,她竟然晚上不会睡得像死掉了一样,常常醒过来。那时她第一次知道,一整夜其实很长。
有时候,半夜里被一种奇怪的忐忑惊醒,尝到嗓子里有一股鱼腥味道。原来睡着的时候,鼻子里流出血来,一直流到嗓子里。陈淼淼去问了校医,抱着听到一切噩耗的勇敢和悲哀,什么只能活三个月之类的,电影里总是这样说的。
可大胖子校医说,这些血铁定不是从她脑子里流出来的,而是从鼻子里的什么地方,一条破掉的微细血管里流出来的。
“睡觉时,你就在房间里放盆水吧。”校医教陈淼淼。
在上海长大的小孩,从来不习惯干燥的空气。晚上醒来,淼淼觉得她身体里只有许多火,根本就没有一丁点水。身体的反应如此奇怪,让陈淼淼觉得,这具身体实在是一个脱离“我”的特别的存在,充满了谜语。于是陈淼淼又开始为自己的生死问题担心了:“会死吗?难道。”她想,“我还没活够呢。”
迪士尼乐园没玩过,口红没搽过,香槟酒没喝过,没跟人亲过嘴,没爱上过一个男孩,也没被一个男孩爱过,没上过大学,没飙过摩托车,没吃过加州彩虹糖(那种把舌头都染成血红的小糖豆),没有过理想和成功,没经历过一万个人全在对她不只欢笑,而且欢呼的场面——因为自己还没来得及当豪杰,也没当成强盗——“我铁定不肯去死的。”
连那种特别高的细高跟鞋,都没穿过。也没来得及在婚礼上做惊世骇俗的事,比如全裸。
真的是铁定不肯去死的。
在床底下放了一盆水,可还是会流鼻血。
按照校医的指点,她起床到厨房打开冰箱,用毛巾包了冰块,放在前额冰镇。这是有效止血的办法。但是陈淼淼还是有点信不着笑嘻嘻的胖校医,要是鼻子里的血管破了,干吗要冰镇前额呢?那里面长着的不正是脑子吗?难道不是脑子融化了,变成血,从鼻孔里流了出来?她信不着胖校医的一个更复杂的理由,就是当她把学校要求呈交的X光胸片给校医时,他看了下,点了点头,说:“perfect(完美)。”对X光片里,肩胛骨旁边多出来的那两块对称的骨头(其实就是长大的翅膀呀!)视而不见。不过,陈淼淼也不想跟他讨论翅膀问题。
校医室里那种消毒水的气味代表了神圣的医学,这点陈淼淼还是服气的。
为了冲淡嘴里的鱼腥味道,陈淼淼挖了碗冰激凌吃,巧克力味道的。
然后,她回到蓝色小铁床上躺下。
可是还是睡不着。
许多事情就像小鱼排着队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浮游在她的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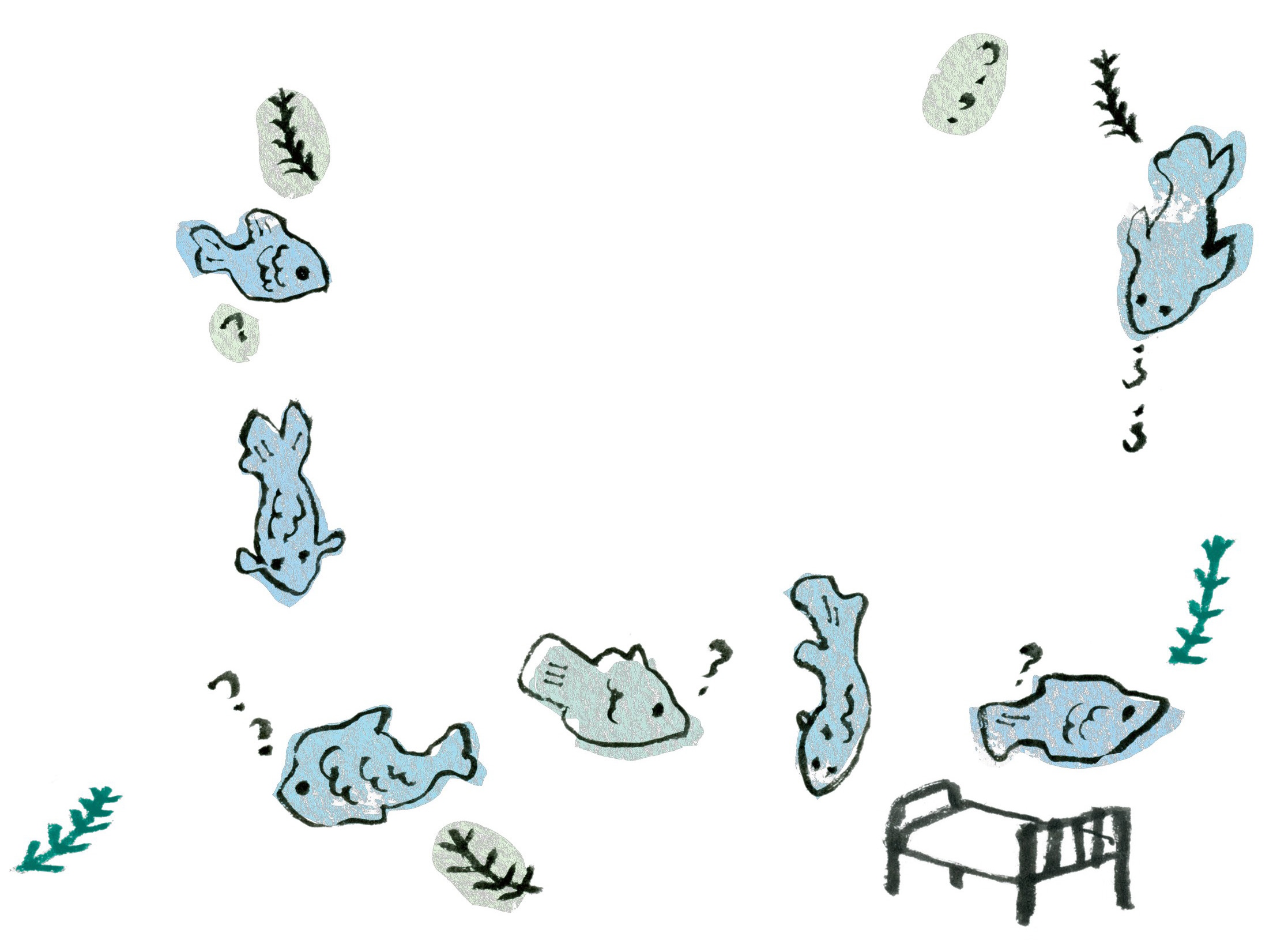
1.爸爸现在在干吗?
美国中西部的时间与上海的时差有十三小时,一算,爸爸应该从手术室出来了。她怎么也想不出,爸爸这样细腻的人怎么会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爸爸一个人生活了这些年,陈淼淼想,他还是不能忘记妈妈吧。他会后悔吗?但是陈淼淼宁可爸爸忘记妈妈,也不愿意他跟妈妈分开了,又后悔了。她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所以她从来不提这样的问题,她躲着。但她却忘不了,因此而同情爸爸。她铁定自己以后不要犯爸爸这样的错误。
还有,爸爸怎么会变得像新娘子的?
2.瑞秋真的算是自己的朋友吗?
3.每周二学校食堂里的厚底披萨那一股橡皮泥味道。
她多么想念上海普通饮食店里五块钱一碗的小馄饨呀,软得像小孩屁股一样的馄饨皮呀,鲜得直接掉了眉毛。陈淼淼想起来,从前妈妈跟爸爸学到这句上海话时,曾一把抓住陈淼淼,非常担心地尖起手指来,拉拉陈淼淼的眉毛,察察看她的眉毛结不结实。妈妈其实不怎么会做饭的,可她老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大厨,她不担心家里人嫌菜不好吃,倒是担心因为自己手艺太好,害小孩没了眉毛。
4.觉得自己孤单。
从初中起,陈淼淼就去寄宿学校了,算是习惯离开家的小孩,但是现在才生出来那么多的孤单。她本来打算假装看不见它的,可是它显得有点太大,特别是在这样刚止住鼻血的深夜。
其实,突然望见自己那无边无际的将来,会把任何一个面对它的小孩都吓一大跳的,陈淼淼也是。
陈淼淼愤愤不平地翻了个身,小铁床就应声“吱扭”地响一阵。
这小铁床可麻烦了,就像斤斤计较的小姑娘,碰一下就嚷半天。陈淼淼觉得自己一直睡不结实,全都怪它,铁和铁摩擦发出的声音真难听。在上海从来没有睡不结实过,因为不是睡这种廉价的小铁床。在路易城,陈淼淼继承了上一届学生留下来的小铁床,因为交换生都只在这里住一年多,什么都是将就用一下,扔了也不可惜的。
陈淼淼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同学们都不愿意来路易城当交换生,来的人也住不到交换期满就回家了——因为很寂寞,因为被熟悉的、安全的一切撇下了,因为这时候他们不得不突然就要长大。每个少年总以为自己有时间一点点地长大,小时候换牙齿的经历,给了他们这样的错觉——就连换牙齿,也得一个个落,一个个生出来的呀。但是长大却是突然劈头盖脸到来的。“哼。”陈淼淼又翻了个身。
神秘林在晚上还算安静,待到天要亮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鸟就开始叫了,好像小学生放学。有叽叽喳喳的鸟叫,也有呢呢哝哝的鸟叫,有长长女高音般的鸟叫,也有尖利如同粉笔在黑板上刮擦发出的刀一般的鸟叫。特别在初春时,林子里的鸟吵得陈淼淼睡不着。
有的鸟叫起来好像敲门,笃笃笃,笃笃笃,陈淼淼知道这是啄木鸟发出的声音。但是还有令人想到手指头敲门的声音。小时候在上海,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没装门铃,有客人来,都用手指头敲门的。爸爸下班回家也是这样敲门的,李雨辰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敲门的。不过陈淼淼一般不这样敲门,她要是高兴,就敲得很急,好像撒豆子一样;要是不高兴,就敲得很重,好像跟门吵架。不过,她和爸爸很快就用钥匙开门了。最初陈淼淼不想像李雨辰那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可是很快就变了。她很快知道,一个用钥匙开门的小孩,最好要把钥匙穿上条绳子,直接挂在脖子上,这样最不容易丢。外科医生的女儿,大门钥匙丢了,就得等爸爸从手术台上下来,换了衣服,下了班,回到家,才能进门。有时候爸爸的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就得等很久很久。
有的鸟叫起来好像开门,“吱扭”一声,门开了似的,其实是鸟在叫。“吱扭”一声,门关上似的,其实也是鸟在叫。黎明时候听到这种鸟叫有点吓人,陈淼淼总觉得有坏人推门进来了。路易城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瑞秋从来不相信有谁是坏人。第一次上体育课时,海勒先生带着大家绕学校跑一大圈,大家都光着脚跑步。陈淼淼问了句:要是草地上有玻璃碴,不是很容易扎坏脚啊。旁边的瑞秋吃惊地看着陈淼淼直摇头,不可能的呀,草地上哪里来的玻璃碴。那时候,陈淼淼为自己感到惭愧。
有的鸟叫起来好像老式的电话铃声,“丁零零零”,连着响三遍才歇口气,然后再响三声。这种鸟叫起来真让人紧张。
有的鸟叫好像猫在叫,而且是那种发怒的猫,边叫,边发出呼噜声。
有的鸟叫好像老人在叹气,压着嗓子,累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而有的鸟叫起来,真的好像是哑了嗓子的青蛙。
最吓人的时候,是鸟儿叫着叫着,突然好像被捂住了嘴巴似的,“唰”地静下来,连挣扎的声音都没有。那时候,夜色就突然变得又大又重。
那时候,陈淼淼就又睡不着了,翻一个身,又翻一个身,后背上有东西硌得她疼——那东西!
当然她没有告诉爸爸,她觉得爸爸不能再经历一次了。她得自己勇敢。
“皮肤总有一天要包不住它们的。”想起当年妈妈帮她洗澡时说的话,淼淼吓得都不敢去上游泳课。
在听着鸟叫的凌晨,陈淼淼在那张蓝色小铁床上“吱扭吱扭”地翻着身。
陈淼淼不知道自己独自在蓝色小铁床上度过的不眠夜,算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
可是,“等真长大了,一切都会变好的。”这是陈淼淼的信念,这也是世界上每个孩子在心里供奉的咒语,特别是无能为力的时候。
“等长大了,我就会有高奏凯歌的幸福,还要有一对高耸的乳房。”陈淼淼拍拍自己的肚子,吩咐自己要勇敢。
按照瑞秋给她的那个小告示,陈淼淼真的得到了那份小时工,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去给艾比·麦卡锡女士读一小时书。每小时的工资,正好就是美国大学申请表上的标准数字:十二块七毛五分,比麦当劳开给学生的每小时七块五毛高,因为这是智力工资的标准,比在麦当劳炸薯条要高级。
艾比·麦卡锡女士开出书单子来,让陈淼淼用她的居民卡,到城中心的公共图书馆去借书。艾比的书单子上大多数都是古旧的美国诗歌,从弗罗斯特到狄金森,有时是艾略特和爱伦·坡,有时是更现代一点的金斯堡,或者更古典一点的惠特曼。图书馆里的人总是十分尊敬地将那些很少有人借的诗集递给淼淼,然后说:“小姐,你真有教养啊。”
学校其实也警告过学生绕道走大坡,尽量不要经过神秘林。校务办公室出了个大告示:树林里也许有春天发狂的动物会攻击行人,学校里有个十二年级女生的车被冲出来的野鹿给撞了。那个女生的车被撞到对面车道上,被迎面而来的卡车压扁。
可是陈淼淼还是没听话。她觉得自己不开车,自己比鹿灵活,鹿撞不到自己。
上完最后一节课,要是走大路,赶到林子另一边的艾比家,就一定会迟到。但要是穿林子里的一条小路,时间就正好。
其实树林子里没那么吓人,陈淼淼喜欢那条林中的小路。小路两旁总是开满了高高长在绿色枝条上的白色小花,草地里则开满了白色的雏菊。在风中摇曳的白色小花好像云朵一样随风摇动,而草里的雏菊则常常围成一个圆圈,或者排着一列队伍,让陈淼淼想起自己幼儿园时候的小朋友们,那样的干净和稚气。一路走在那条小路上,对上海长大的小孩来说就像奇迹。
神秘林里处处充满了成千上万棵胞芽日夜生长、不可计数的花朵夜以继日开放所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整日都发出充满水汽的沙沙声,那是节节拔高的枝叶发出的声响。这林子里的春天是如此强悍,如此地失去控制,令陈淼淼有时魂飞魄散,有时又心潮澎湃。她觉得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身体也在发出成长的声音,小骨头“咔啦咔啦”地在背脊中央发出响声,小骨头在手腕和脚腕里“咔啦咔啦”地发出声响,就像那些分叉出去的玉米秆。
神秘林中的光线开始变成了绿色,因为再强烈的阳光都不能穿透枝叶茂密的大树。明晃晃的阳光只能像水一样,穿过一层层树叶,再滴落到林子里。于是,阳光在林子里成为一种沉甸甸的绿色,波纹荡漾。陈淼淼在小路上急急往前赶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就好像长满水草的玻璃鱼缸里的一条小鱼。就算是连走带跑着,但心里却一点也不慌。陈淼淼偏爱那种浮在水中央一动不动的小鱼崽子,肚子下面拖着一条又细又长的鱼屎。她觉得鱼那样缓慢地拉屎,实在是太舒服了。
她最喜欢的,还是按时到达艾比·麦卡锡家蓝色的小木房子,那是栋中西部古老的殖民地式样的小房子,有个红色的尖屋顶,几乎被从山上蔓延过来的树林淹没了。
第一天去上班,就是个温暖的下午。陈淼淼走进树林的时候,有一只夜莺在高大的山毛榉树丛的深处“丁零丁零”地叫着,让她突然想起妈妈为她念过的睡前故事:安徒生的故事。故事里说的什么,已经都不记得了,可是陈淼淼此刻在夜莺的歌声里想起了妈妈学夜莺叫的声音,好像隔了许多层棉布穿过来的冬天的风声,先听到,然后,在脸颊上感受到一种妈妈的气味。隔了这么多年,她才明白,虽然妈妈对世界万物的形容与理解有许多都是奇形怪状的,但是夜莺的叫声却是一点不差。在上海,陈淼淼从未听到过夜莺的叫声,她一直对妈妈的声音将信将疑。她想起自己总是怀疑地望着妈妈,说:“你又胡说了?”妈妈有时就突然“嘿”地笑了声,说:“啊,我又体会错了吗?”
那天,树林子里只有一只夜莺在高高的树影里遥远地叫着。
妈妈这次是对的呢。
有些事要过这么多年,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啊。陈淼淼在遥远的声音里想着。
到了岔路口,陈淼淼突然看到路上躺着一对翅膀。一对真的翅膀,完整的翅膀,一根羽毛也没缺。又长又硬的,带着些黑褐色的,是翅膀外部的羽毛。细小柔软的,纯然白色的,是翅膀内侧的羽毛,那里能看到一些肌肉,在翅膀根部,有一点凝固的血迹。

谁把翅膀生生地从身体里扯了下来?
疼吗?
谁又把它们端端正正放在路上,左边的翅膀在左边,右边的翅膀在右边,好像等有人来穿上它们,飞。
它们又好像是亲吻,又好像是威胁,又好像是礼物。
只有一只夜莺温柔地唱着它的歌。那些黎明时聒噪不停的鸟儿,此刻却一声不吭,统统躲在幽暗的林中深处,耸肩紧缩它们的各色翅膀,瞪着它们圆圆的、机警的、能看180度的眼睛。陈淼淼能听到它们尖锐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向自己,并在空中彼此碰撞发出的切切嘈嘈,但它们紧闭着剪刀一样尖利的嘴,被吓住了。
陈淼淼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她听到口水“咕咚”一声,好像一块石头丢进深不可测的井里。
它们又好像是遗言,又好像是预言。
在上海,家家人都在门厅换鞋,拖鞋就放在门厅地上。陈淼淼家也是一样的。妈妈走后,她那双拖鞋在门厅里放了很久,陈淼淼和爸爸都对它们视而不见,好像是拖鞋独自在等妈妈回家换上它。
这天,就像许多年前,陈淼淼在门厅前绕过妈妈的拖鞋那样,她沉默地在夜莺的叫声里绕过了这对翅膀。
然后,她把舌头顶在下颚上,顶出喉咙里的气来,从喉咙那里关上耳朵,绕过了夜莺的叫声。
树林子里的绿色,有时也实在是太绿了。高大的橡树长出一千条长长的胳膊,高大的松树戴着一千顶三角形的尖顶帽子,阳光像无数大砍刀一样从天上劈下来,照亮大树下草丛里一丛丛橘红色的蘑菇,那当然是毒蘑菇。还有一丛丛茂密的绿锯齿植物,那是有毒汁的荨麻。可是就在旁边,能看到一串串红彤彤的野草莓,一丛丛深蓝色和深红色的野莓子。高高的野燕麦草里,落着绿色的小苹果和熟透了的紫樱桃。
然后就到艾比家了。

[2]一个将你从平凡日常之中唤醒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