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科学作为天职(1)
库尔提乌斯(2)
韦伯在演说的开始描绘了一个德国学者的典型学术生涯。通过与美国大学的情况相比较,他认为德国的境况在向美国靠拢,总结道:“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在这一序言之后,接着讨论的主题就有意思多了,韦伯开始论及科学的内在天职。科学已经踏入了一个专业化的阶段,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只有通过极其严格的专业化,学术成果才可能完美而持久。“如果谁没有能力,完全蒙上双眼,不顾周围一切地想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他就尚未步入科学的门径。”所以科学要求满怀激情的献身。不过,工作激情本身并不能确保取得科学成果。一个人还需要“想法”和“灵感”。想法和灵感会不会从天而降,这是学者必须承受的又一场赌博。
青年一听到灵感对科学工作影响这么大,就以为科学里最关键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和“体验”。韦伯恰恰要打破时下风行的这两个偶像。人们现在常说的人格只是一种迷信。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心无旁骛地致力于自己的事业。韦伯指出,即便像歌德这样的人物,如果想要自由自在地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也会损害自己。
艺术与科学在要求“事情本身”(Sachlichkeit)这点上没什么分别。然而艺术领域里并不存在进步,科学却意在被超越,成为过时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着理智化的进程,科学的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的人们通常对此抱以极度否定的态度。”理智化意即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支配一切,或者换种说法,理智化意味着世界的除魔。
千百年来持续推进的理智化进程,科学决定性地参与其中的“进步”,究竟有意义吗?如此一来,论题就从“科学的职业”(Beruf zur Wissenschaft)转到更宽泛的问题,即人类的生活总体之中“科学的天职”(Beruf der Wissenschaft)。对柏拉图来说,科学是通向真实存在之道;对文艺复兴以降的时代而言,科学是通向真正艺术之道、通向真实自然之道、通向真正上帝之道、通向真正幸福之道。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科学能实现任何这些理想了。科学不能回答“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亦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可是拿这些拷问科学有道理吗?问题非得这么处理吗?
演说又一次转变了话题。韦伯提出,评价科学的关键是科学在“值得我们知道”的意义上重要与否。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依照“我们对生活所持有的终极立场”来决断。至此,韦伯已经表述了一套清晰成型的主观论,严格说来,排除了人们基于共同基础达成一致的可能。所有科学分支都预设了研究对象的价值,却没法证明其价值(难道科学不能显现这种价值吗?韦伯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描绘的世界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呢?医生努力挽救的生命值得拯救吗?艺术科学所研究的艺术王国有价值吗?抑或只是“一个恶魔支配的王国……在内心最深处与上帝势不两立,其内心深处的贵族精神,也与人类的博爱背道而驰”?历史性文化科学研究所构建的文化共同体,有值得我们参与其中的价值吗?这些问题全都没法通过科学回答。(难道哲学也不能回答?)科学这里涉及的价值问题绝非自明的。
韦伯由此得出以下结论:科学必须不做任何价值判断,避免表达一切个人的立场。这一结论背后最深的原因是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价值秩序,彼此之间处于不可解消的斗争之中。韦伯讲的这些,年轻的勒南在1849年就理解得简单明了:“神圣与真理,美与善,真理与其本身的斗争。”(3)韦伯不否认它们确实成问题,但这些都是生活问题,不属于讲台。
教授应当是一名教师,而非领袖。照美国人的话说,他就像卖菜的一样,有些知识待售而已。韦伯继而追问,那美国人这种说法就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吗?教授如果自认为有义务充当青年的人生导师,可以在私人交往当中证明自己堪当此任。
在韦伯看来,学院教师能传授给听众的最高的、最终的东西是:他能“迫使个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终极意义做出交代”。
人们可能会有种印象,觉得韦伯的演说是出于某种防守反击。年青一代对大学科学的态度,他们有些模糊的狂热,对朴素事实知识的蔑视,对即刻能达到一种绝对的渴望,在许多地方都引起了相当热烈的抗议。1919年发表演说的韦伯肯定能照他的经验理解这类情绪。但他也会提醒自己,从战场上归来的青年,心境并无先例可循。倘若年轻人兴奋不已,乱哄哄地要求大学做这做那,面对在逻辑和事实上都如此缺乏纪律的场面,韦伯准会偶尔禁不住哂笑,或者感到厌倦,无可奈何;他也可能试图自我封闭以为防御。不过,倘若他怀着爱与信任接触这些青年,就会感到竭尽所能去帮助他们是一项绝妙的使命,他会相信,最名贵的醇酒由最污浊的发酵酝酿提纯澄清而来。这项使命的责任之重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虽然韦伯在很多方面的批评都有道理,要是能让人感到他赞同现在这些青年生命中最好的意志,也许他的演讲会更富教益。不过,即便一些人会为韦伯没有肯定青年而感到遗憾,每位读者都一定能从这篇演讲中,如同韦伯的一贯立场一样,看出他那清晰成型的道德人格。一位声名如此卓著的学者,一个如此清晰鲜明的人格,他陈述自己对科学问题的看法时,哪怕透过他援引别人的方式(《以赛亚书》、《诗篇》、托尔斯泰),无意之间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就连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也难以抗拒其中的审美魅力。
韦伯的立场极具个人特点,所以对实际问题的讨论难免会相当片面。譬如韦伯采用的“科学”概念,显然仅仅指向近三百年的机械论式的自然科学以及今天对精确理想的追求。若不带入柏拉图或达·芬奇的知识理念来进一步解释,这种极其相对的科学概念极易导致误解——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关于柏拉图的新书(4)也有类似的误读。今天,如果关键在于重提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根本问题,那么,无论如何必须一开始就认识到,对知识的系统性追求而言,我们今天的科学绝非唯一的、恒久的典范。然后,人们才会意识到,韦伯似乎主张的科学持续不断地进步,不过是必须抛弃的虚构罢了。因为唯有自身始终如一的事物才可能有进步。然而,谁又敢断言古希腊的科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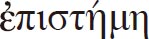 )在实质和功能上都跟现代科学是同一个东西?即使不谈这一点,科学稳定进步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韦伯似乎主张的范围,它仅对解释性的自然科学完全成立,只在有限程度上适用于历史。蒙森或兰克不会在拉瓦锡或李比希那种意义上被超越,其相对的不可超越性不仅像韦伯说的那样,靠宏大历史描述的审美或教育价值,亦有赖于历史科学的认识论结构。然而,一到哲学领域,进步理论就毫无意义了。哲学里后来者顶多有所补充,何谈进步。柏拉图不可能被超越。
)在实质和功能上都跟现代科学是同一个东西?即使不谈这一点,科学稳定进步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韦伯似乎主张的范围,它仅对解释性的自然科学完全成立,只在有限程度上适用于历史。蒙森或兰克不会在拉瓦锡或李比希那种意义上被超越,其相对的不可超越性不仅像韦伯说的那样,靠宏大历史描述的审美或教育价值,亦有赖于历史科学的认识论结构。然而,一到哲学领域,进步理论就毫无意义了。哲学里后来者顶多有所补充,何谈进步。柏拉图不可能被超越。
会不会是因为哲学本就是与科学不同的东西(当然这不意味着它更没价值)?韦伯无疑把哲学视为一门“专业学科”。这不过再一次表明他的科学概念意涵过于狭窄,且不够清晰,尚未在哲学上琢磨透彻。
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韦伯关于诸神之争的论述。虽然穆勒的哲学思想其他方面韦伯并不赞赏,但他援引“晚年穆勒”,认为价值之争植根于世界的根本,所以就应该干脆把它视为既定事实来接受。然而,这个价值论命题远非一目了然,可以不给出任何理论根据就想当然地接受——韦伯得出的那些深远推论,说服力因而就被削弱了。即便不纠结哲学的价值学说问题,至少得问问:“这种据说普遍有效的价值之争,会不会只是价值的无序状态(Wertanarchie)(5)的征兆,暴露了晚近西欧文化的某种乱象?”
韦伯提到,在科学的领域里,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的人,才具有人格。在我看来,他这样就绕开了整个讨论的关键问题,即人格在科学的认识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假如“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指的是摒除一切个人冲动,那它作为事实性的断言就已经错了。因为它仅仅适用于19世纪受康德义务伦理支配的那些人。柏拉图就足以构成反例,对他而言,认识的方法论前提源自人与知识对象之间存在爱的关系。无论如何,需要一套独立的方法论反思才能完成这一任务,重新判断每种认识方法和各类科学究竟是否要求整个人格的分有或预备性的性情倾向。例如,或许“体验”就是这样一种人格对知识的先决作用。至少,“历史性文化科学”也许都如此。宗教史研究或一般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lich)研究的成果,取决于相关学者与工作领域的价值品性之间体验到的心灵契合究竟多广多深。并且,只有他现在对此有所体验,才可能体验到往昔的心灵契合。对有些学者来说,人们可能想要引入一种“体验的义务”(Erlebnispflicht)。
假如这些异议提得不无道理,将会动摇韦伯建立那些实践性推论的理论基础。一旦省略这些推论的理论保证,就清理出了一条道路,让今天的青年针对大学科学的褒贬态度重新获得重视。
这些青年要求“人格”和“体验”,不论如何,其中的想法是颇为正当的:科学存在的意义必须有所转变,转向人本身(Menschtums)的一种意义解释。不能像韦伯那样,从一种发展史的事实状况(理智化的进程)经验地得出科学的意义与价值。更确切地说,科学的意义,只能由生命价值及其次序,从为一切奠定普遍基础的总体直观(Gesamtanshauung)中得到确定,总体直观必定是一切哲学思考的目的所在,即使在总体直观的严格哲学表达不及之处,它的基本特征也可能已经明见地给予了。即使我们都不是形而上学家,我们也晓得:有神圣,有善,有美,有真,这无须争辩;一个人越是深刻、越是广泛地觉察并且实现这些价值,就越有价值;我们必须首先是人,而后才是学者;科学的意义可以被编排进生命的意义整体;假如我们献身于科学——不论作为老师还是学生——却又在我们的科学生活和作为人的生活之间插入一道隔膜,这是不祥的、恶劣的、荒谬的。我们还知道,在专门的研究所中致力于纯粹的研究目标不错,也是必要的;然而,大学不仅是一处研究机构,也是教育机构;(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培养科学面向事情(Sachlichkeit)的教育,可以与传授精神上的诸多生命价值结合在一起;一位教师,让青年大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面向事情的训练,他们对此确信无疑,认定能从中获得其他一些更深的启迪。谁若是有意环顾我们的大学寻找这样的教师,列举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凭借其强大人格和悲剧式的紧张气质,站出来,想为一种非人格性的专门科学辩护,准会说出他的名字——马克斯·韦伯。
(1) Ernst Curtius,“Max Weber ü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Arbeitsgemeinschaft Monatsschrift für gesamte Volkshochschulwesen,1920(1):197-203.
(2) 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1886—1956),著名的罗曼语文学家,日后以论述欧洲文学传统的大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享誉于世。发表此文时他以法国文学的翻译者和文学批评家著称。
(3) Ernest Renan,Patrice,Paris:Calmann-Levy,1908,pp.5-6.
(4)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Platon,Berlin:Weidmann,1920.
(5) “无序状态”参见Max Scheler,Vom Umsturz der Werte,Leipzig:Der Neue Geist,1919:194-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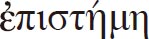 )在实质和功能上都跟现代科学是同一个东西?即使不谈这一点,科学稳定进步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韦伯似乎主张的范围,它仅对解释性的自然科学完全成立,只在有限程度上适用于历史。蒙森或兰克不会在拉瓦锡或李比希那种意义上被超越,其相对的不可超越性不仅像韦伯说的那样,靠宏大历史描述的审美或教育价值,亦有赖于历史科学的认识论结构。然而,一到哲学领域,进步理论就毫无意义了。哲学里后来者顶多有所补充,何谈进步。柏拉图不可能被超越。
)在实质和功能上都跟现代科学是同一个东西?即使不谈这一点,科学稳定进步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韦伯似乎主张的范围,它仅对解释性的自然科学完全成立,只在有限程度上适用于历史。蒙森或兰克不会在拉瓦锡或李比希那种意义上被超越,其相对的不可超越性不仅像韦伯说的那样,靠宏大历史描述的审美或教育价值,亦有赖于历史科学的认识论结构。然而,一到哲学领域,进步理论就毫无意义了。哲学里后来者顶多有所补充,何谈进步。柏拉图不可能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