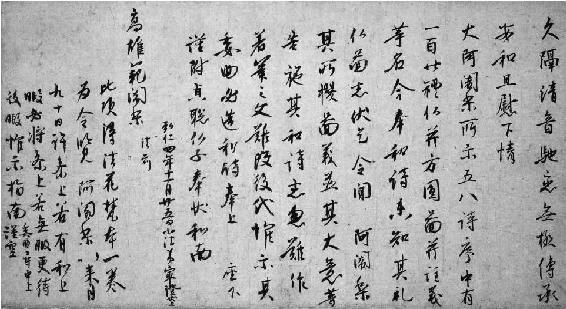-
1.1序言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
1.2第一章 方士引路,北海的探险者
-
1.2.1邹衍,古代海洋理论第一人
-
1.2.2徐福,北方航海先行者
-
1.2.3四海,秦汉时代的海洋观
-
1.3第二章 大洋开洋,黄门译使的近岸航行
-
1.3.1“路丝”与“海丝”谁先行
-
1.3.2哪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
1.3.3南海,中国最早的海洋图景
-
1.3.4跨海册封,神秘的汉赐倭奴王金印
-
1.4第三章 西帆东舶,相向而行
-
1.4.1帆船的诞生与巨大的海上商圈
-
1.4.2中国何时扬“帆”远航
-
1.4.3吴帆初航,朱应与康泰笔下的扶南国
-
1.4.4东来西去,遂溪的波斯金碗银钱
-
1.4.5隋使下南洋,常俊眼中的赤土国
-
1.4.6阿曼商船,辛伯达的“苏哈尔”远航
-
1.4.7画中丝绸,东西贸易的“大宗商品”
-
1.5第四章 僧来僧往,跨越大洋的取经传法之旅
-
1.5.1印度取经,西去取经的中国僧
-
1.5.2东渡传法,天竺高僧拘那罗陀
-
1.5.3新罗慧超,西航大唐漂洋天竺
-
1.5.4高丽僧侣,开宗传派的义通与义天
-
1.5.5东极高丽,刺马丹远航库尔德
-
1.5.6东瀛传律,大唐鉴真七闯东海
-
1.5.7搜书习字,入唐八大日本僧侣
-
1.5.8茶禅一路,最超拔的丝路文化交流
-
1.6第五章 唐宋官使,东渡西行的声教布局
-
1.6.1杨良瑶,唐使“下西洋”的秘密使命
-
1.6.2黄慎,一介海商担起的宋丽复交使命
-
1.6.3张保皋,从大唐小将到新罗海王
-
1.6.4指南针导航,徐兢奉使高丽的航海志
-
1.6.5唐宋海图,遥见阿拉伯半岛身影
-
1.7第六章 沉船密码,藏在大海深处的秘密
-
1.7.1大唐海市,唐代海船就是这个模样
-
1.7.2大食沉船,藏在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
-
1.7.3泉州宋船,香料贸易的转运商
-
1.7.4“南海一号”,南宋海上贸易的重要链条
-
1.7.5蓬莱沉船,战船、商船、高丽船
-
1.7.6新安沉船,中国、日本、高丽的海上商圈
-
1.7.7中国古船,有多少船模漂泊在海外
1
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
1.5.7
搜书习字,入唐八大日本僧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