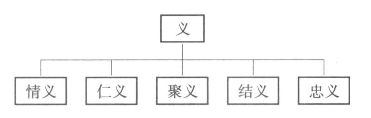含英咀华
不发展的“个人”对别人的伤害[19]
孙隆基
本节中,我们将偏重讨论不发展的“个人”对别人的损害。
1.党同伐异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而后者就是搞“党同伐异”。
中国人之间,树立不起“个人”的人,往往有“拉大旗做虎皮”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只是为了稳住自己,就顶多表现了自己没有“个性”,还不至于损害他人。然而,如果是联群结党,排除异己,就会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且,还往往使社会与国家断送人才。
“党同伐异”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一群人霸占了一些权位,为了使自己的小集团更壮大,就只援用“私人”,排除“外人”。因此,他们用人的标准不是凭才干,也不是凭公平竞争,而是看对方是不是“自己人”。在一个“个人”不能树立而又必须按“亲疏有别”层次“做人”的文化中,出现这个现象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港台的大学中,都存在这种现象。通常的情形是:院长或系主任想巩固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一党,因此只想培植“听话”的,也只援用“自己人”。笔者在台湾大学时,甚至还碰到这样的情形:连考博士班,也是凭几个老教授在背后先“内定”,录取的则是向他们磕过头的,可以成为他们的“私人”的学生,而根本不是凭既往的成绩。
还有一种情形是:在同一个单位中,也往往会形成几个派系,互相攻讦,每一个派系就更加要援用“私人”,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派系的形成,在美国的学术界也会出现,不过,还不至于做到使社会断送人才的程度。一般来说,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求职,资历不相上下的话,就多半会将位子给予有关系的熟人,否则,就凭“公平竞赛”。
这种倾向,在中国人的政治中自然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人的权力结构是一元化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搞多党政治。在后一种情形中,一个党选上了,另一个党下台了,就会名正言顺地只用自己人组阁;如果一方有人跳槽,另一方也会凭才干录用,双方都不会视之为“反骨”,因此,就根本说不上“党同伐异”。
像这类“全民”的代表,其作风往往是使国家与民族断送人才,因为,他们势必只援用“自己人”,并且打击异己,如果是有才干的人而不为他们所用,就更会施以打击,以免养虎为患。
比如,“四人帮”常向自己的党羽“封官许愿”,然而这些党羽又是一些不中用的人,因此,如果能够上台,就会令一些跳芭蕾舞的、作曲的、考试交白卷的、只在珍宝岛打过一仗的人来充任文化、教育与军事各部门的领导。然而,如果他们手头上只有这些货色,确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至于国家的命脉,则不在考虑之列。
京戏中有《大登殿》这一出剧目,内中描写薛平贵在做了皇帝后,就大量犒赏“自己人”,并打击以前的仇人。这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作风,是十足中国人的做派。想成为“人上人”的中国人,总多少会有一点儿“大登殿”思想。
2.中国人的“私心”
正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开诚布公的“逐利”行为,也没有具有尊严的“逐利”方式,才会出现大家都必须把自己说得堂而皇之及纯粹“无私”的现象,正因为大家都必须把自己说得堂而皇之,纯粹“无私”的,结果,“公”与“私”的界限就不知道划在哪里,而任何人都可以假“公”之名以遂其“私”。因此,标准定到高入云端,就往往会坠入厕所中去。
中国人在“天下为公”的国有化体制下,并没有能够消除“自留地”。本着同样的“文法”,在中国人“他制他律的人格”中,也无法去除“私心”。
这一块外力控制不到,自己也控制不了的人格中的“自留地”,在海外中国人身上的表现形态,已经比国内淡薄得多,但是只要在文化上仍然是中国人,就必定会浮现。例如,西方人与日本人在过马路时有遵守红绿灯信号的习惯,然而,不少中国人,不论他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或美国,就从不遵守讯号,只要没有车,也没有警察,也就不会有自觉的纪律。
往往越是提倡高入云端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越不能消除随地吐痰、擤鼻涕、泼污水、丢垃圾、插队、随意碰撞人等缺乏公德心的事,自然更无法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破坏国家体制的行为。
此外,在大陆与台湾的大学中,笔者都发现:有些教授将图书馆中的珍贵典籍搬回了家,变成了他们的独家资料;有时连普通的书也省得自己去买,索性将馆藏的化为私有,而且,多半是自己不看,只是占有。
因此,孙中山才会说,中国人的“自由”太多,而不是太少。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指“自我组织的人格”所能享有的自由,而是指“他制他律的人格”不受控制的一面。很不幸,这种过多的“自由”,却往往必须由集权主义去对付。
但是,小百姓在公众头上倒大便的倾向,只不过是限于上述的那些小动作。大体上来说,他们是驯良的,因为外在的纪律在大的方面仍然在发生作用。然而,这样的人格,如果“一朝权在手”的话,就是不用去看也可以想象出会有什么结果。到了那个时候,既然自己是“公”的化身,因此做任何“私”事都可以说成是为了“公”。
于是,袁世凯在做了总统后,就想做皇帝,并且还要传位给儿子袁克定。至于蒋介石,虽然没有公然地做皇帝,却也做了终身总统,并且还成功地将“中华民国”传给了儿子,也是“儿子办事,老子放心”!
笔者发现,在台湾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中正路”“中山路”以及“中华路”;而最漂亮的一条总是“中正路”,其次是“中山路”;至于“中华路”,则往往处于最暗最烂之列。这个事例很具体形象化地说明:“伟人”在公众头上倒大便的方式,确是不同凡响的。
中国人的这个“私心”,既然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倾向于化公为私的,因此也就往往是不识大体的。不识大体的人总是短视的,因为他只顾眼前的私人利益而不顾大局。然而,从长远来说,其后果最终会反弹回来损害自己。
在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治下的中国人发国难财,搞“劫收”,不只使美国盟邦皱眉,也搞到民心尽去,结果就为国民党的末运铺下了路。然而,棺材的钉子却是用自己的手敲下去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充分地利用了国民党的“私心”。国民党本来在财力、军力方面都比共产党雄厚,然而,中央与地方各军团之间却互相倾轧,往往彼此见死不救。当南京的嫡系部队在淮海一带与解放军对峙时,桂系却在武汉拥兵自雄,还认为待嫡系部队被击垮后,就是自己一显身手之日。结果,就被解放军逐个消灭。
无独有偶,清初之所以能以三十万之众征服整个中国,也正因为南明政权内部的互相倾轧。事实上,镇守武汉的左良玉就拥兵三十万之众,然而,因为与南京的中央闹矛盾,就挥军东下进行“兵谏”,结果,自然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总是必须由别人定义“自己”的中国人,一旦“他制他律”的藩篱尽去,“私心”就会像决堤一般恶性泛滥。因此,在中国文化里,“个人主义”是而且只可能是“自私”的同义词。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总是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就是“自私”的同义词。然而,我们只要分析这个观念形成的心理背景,就会发现这只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对“自私”的定义即没有“人情味”——当自己需要援手时对方不予援手,在自己需要人照顾时对方不肯照顾。因此,西方人“贵客自理”的待人态度,自然完全符合这个定义。
然而,中国人的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却总是在“自己人”之间发生的。为了在对自己有约束力的人面前“做人”,他们就往往去损害对自己没有约束力的“外人”。像“拉关系”与“走后门”一类的“人情味”动作,正是慷“外人”之慨,以肥“自己人”的。这种“内外有别”的“做人”方式,往往就将“公家”当作了倒大便的场所。然而,整个体制都搞瘫痪了,受损的人自然也会包括自己。
的确,中国人因“他制他律”失效而造成的大环境的臭化与脏化,与“他制他律”生效而搞到每一个人都不敢有吸引力,因而造成的灰色人文景色,都是对集体有损,对个人有害的。两者都是鄙视个性、反对生命的表现。
◎我思我在
1.阅读下面的句子,说说句中“文法”一词的含义。
(1)中国人在“天下为公”的国有化体制下,并没有能够消除“自留地”。本着同样的“文法”,在中国人“他制他律的人格”中,也无法去除“私心”。
(2)在中国文化行为的“文法”规则中,自然每一方都期待另一方也会恪守这个观念,亦即是预期:在自己化为对方工具的同时,对方也变成自己的工具,是之为“互助”。
2.本文选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你觉得哪些观点具有批判性?
3.在本文所提的观点中,你认为作者是站在什么视角上说的?
“义”的变质[20]
刘再复
为了避免陷入概念的纠缠与“义利之避”的老论题之中,笔者想从我国最本真、最本然的“义”现象说起。可以说,在我国远古的文化艺术史上,早就有“义”的典范。这就是古代大音乐家伯牙与他的知音钟子期之间的动人友谊。这一美好的故事,已化作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故事的记载非常简单,《吕氏春秋·本味》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是无是复为鼓琴者。”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后来成为一种纯正情义的象征。汉代蔡邕曾作《琴操·水仙操》;明阳慎的《兰亭令》则曰:“此乃高山流水之操,伯牙复生,不能出其右矣。”无论水仙般的情操,还是高山流水般的情操,都是一种完全超越世俗利害关系的纯洁情感,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最本真、最本然的“义”。这种“义”没有任何功利性,也没有时间性,它完全超越了时空界线。所以杨惊在注《荀子·劝学篇》时特别说明:“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这种“义”不知生于何代,也不知止于何代,是人类童年时期天赋的真、善、美,也是中国原始的价值理性与价值情性。这是中国“义”的原形。伯牙、钟子期这对知音的关系中没有“利”,甚至也无需契约,无需结盟,只有纯心灵的既真且美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自然向往,自然信赖,也是一种自然规范。它带有永恒价值永恒魅力。这两位古代音乐家的行为语言,比后代学者无数关于“义”的阐释和注疏都更有力量地说明中国“义”的“原形”是什么。这种超越任何功利的心灵纽带,这种相融相契的绝对倾慕与信赖,这种无目的(无世俗目的)的合目的性,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是中国还是人类世界,这种“义”永远是必须的。所谓讲义气,如果是指这种义,当然是需要讲的。
像伯牙、钟子期这种超越功利的义,带有普世价值。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讲“义”,而且都把“义”当作和“利”对立的一种大范畴。不过,从大的方向上说,西方的“义”发展为“正义”,而中国的“义”则发展为“仁义”。西方的义侧重于个体的心灵原则,中国的义则着重于人际关系准则。“义”推向社会、国家层面之后,西方的政治思想指向“正义”;中国的政治思想则指向“和谐”。仁义原则使和谐理想成为可能。孟子的天才,是他在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辩”的基础上,又提出“人兽之辩”“利义之辩”“王霸之辩”这三项伦理学的根本。古今中外,无论何国何人,皆无法逃脱这三种尺度。
从以上简略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义”,至少有两种原形,一是个人化的伯牙、钟子期式的超功利的“情义”;一是孟子提升的理想化的有别于功利的“仁义”。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利”作为“义”的对立项。把利益原则与道义原则加以区分,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义”的原形是非功利的。
但是,中国的义,经历了历史风浪的颠簸之后,却逐步变形变质。发展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义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其核心概念,变成“结义”“聚义”“忠义”。在义字前边加上一个字、一个定语,不是小事,它意味着义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宋江代替晁盖充当梁山领袖时改“聚义堂”为“忠义堂”,虽仅改了一个字,但暗示两个大原则已出现:一是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虽揭竿而起但仍忠于皇帝。二是提示梁山起义者从今天之后不可只知上山会聚,还应当忠诚于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则、共同的纪律,甚至共同的领袖。这个“忠”不仅表明忠于国家社稷,还表明忠于宋江这位老大哥。“忠义”在这里不仅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而且是个人行为的规范准则。
《水浒》中的“聚义”和“忠义”,和伯牙钟子期的情义,已完全不同。无论是聚义还是忠义,都是一个夺天下、打天下的功利目标。这种义,不是超功利,而是争功利。义只是“利”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是保证造反队伍实现大功利目标的精神纽带。聚义往往还讲小义,既带个人情感的兄弟之义,而忠义则将大义,即讲对大功利目标的绝对忠诚。因此,当李逵怀疑宋江接近女色时,他也会为了革命大义而谴责宋江。而李逵、武松虽不赞成招安,但还是服从大局,忠于宋江的“路线”。
《三国演义》讲的则是“结义”。“结义”二字,乃全书的核心价值观念。“结义”也包含着“忠义”,但重心是“结”,即结盟。如关、张的“桃园三结义”,首先是一种结盟,即组织;然后又是一种盟约,即组织原则。而其盟约的目标是谋大事,正如张飞在举行结拜仪式之前所言:“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而刘备、关羽也齐声应曰:“如此甚好。”而次日他们宣誓的盟约内容也与此相应:“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桃园这一盟约,影响中国近两千年,后来它一直成为中国民间帮会和其他秘密组织的组织原则和伦理原则,一旦“背义忘恩”,不仅违反了组织原则,而且也违背伦理原则。立下原则时是向天发誓的,所以一旦有违,便违背人理,又违背天理,于是,便有“天人共戮”的理由,“桃园三结义”就这样成为中国社团的组织模式和伦理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桃园组织模式和桃园伦理模式。
桃园模式讲的是兄弟伦理,宣示的是兄弟结盟,图谋的是天下“大事”。它所以能在后代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下层社会的生存需求。中国的上层社会,特别是贵族官僚社会,讲的不是兄弟伦理,而是君臣伦理,是上等人和下等人严格区分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中,只有“君为臣纲”的秩序,没有平等。“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伦理,把异姓的兄弟之情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下层社会的平等要求。不管参加结义的人原来是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一旦结盟,就放下等级差别,尊卑差别,一律视为兄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义打破了等级,使人获得了一种平等地位,实际上也获得了一种生命尊严与生命护卫,因此“桃园三结义”的文本中,刘备直接表明: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妻子随时可以抛弃,但兄弟不可丢掉,两种永远如手足相连。在儒家“三纲”的伦理规范中,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没有兄为弟纲。也就是说,君臣、父子、夫妻有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但兄弟关系则没有上下尊卑之分。中国的兄弟伦理特别发达,乃是下层社会逃脱三纲伦理罗网的需要。“桃园三结义”使兄弟伦理获得一种组织性的存在形式,在这一意义上,结义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历史不断证明,结义——兄弟之盟并不可靠。因为“义”最后总是受到利的考验。当兄弟全都处于贫困与患难时,也就是“利益”并不突出时,平等关系是可以维持的。然而,一旦“利”字凸显,共图的大业成功,新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关系,必定要取代兄弟关系——平等关系,否则权力结构就无法维持。像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他们起事时与周围共图大业的骨干自然都称兄道弟,而一旦事成而称帝,原先的兄弟便成了臣子,照样得跪拜三呼万岁。许多“兄弟”成了臣子之后被怀疑、被诛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当了臣子的兄弟忘记时过境迁,关系发生质变,今非昔比,往日的兄弟之义已不复存在,眼前的真实是君臣秩序,企图用过去的兄弟伦理来扰乱现在的君臣伦理,便是犯上作乱,便是大罪当诛。许多新王朝的功臣沦为悲剧人物,说明“义”是脆弱的,“结义”的盟约形式是不可靠的;也说明“义”是会变的,它不具有绝对性。
“结义”有其合理的一面,可以理解的一面,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其不合理性,关键是“结义”没有爱的普遍性,或者是,没有关怀与责任的普遍性。如果我们采用社会上的习俗语言表达,那么,无论是“桃园”还是梁山,都只是“团伙”,不是社会。结义、聚义的结果,是团伙取代社会,团伙的利益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当然也大于社会利益。所谓“义”,只是团伙原则,并非社会原则。入伙才享有“义”的保护。对于水浒梁山,一百零八将之内,才是兄弟,才有“义”字可言,一百零八将之外,则无“义”可言。鲁迅批判赛珍珠把《水浒传》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妥。就因为水浒英雄恰恰不讲五湖四海,恰恰未把普天之下视为兄弟,恰恰内外有别。一百零八之内可讲义气,一百零八之外可杀、杀、杀。凡“结义”者,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内外有别,团伙之内与团伙之外两重天。义在内,不在外,团内家族与团外异族不可混淆。禅宗所讲的不二法门,佛教所讲的无分别心,离“结义”原则最远。
◎我思我在
1.读了论著之后,你怎样看待《水浒传》?请在合适的选项前面打“√”号。
□赞同刘再复对《水浒传》的看法,作品宣扬暴力,毒害已久。
□不认同刘再复,作品十分精彩,不能以今天标准苛求古人。
□不清楚。
2.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倡导“有阅读,有思考。有见解,有生活。在茫茫的大时代里,用阅读治愈心灵”。有书评人对《双典批判》作出如下点评语:三国加水浒,一对“大毒草”。
当你读了《双典批判》后,你想写一句什么评语?
3.刘再复先生笔下的“义”的内涵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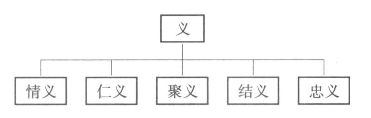
请结合图示,说说刘再复先生是如何对《水浒》中的“义”加以批判的?
◎专题研讨
刘再复先生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一是暴力崇拜,一是权术崇拜。它们影响和破坏了中国的人心,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而子遇对此提出了异议。请认真阅读下面的文字,想一想,你赞同哪一种说法,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角度展开分析。
即使是承认《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经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国民性,但就影响的程度而言,笔者亦远没有作者乐观,在这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组相对的概念来。限于书评的风格与篇幅,笔者在此只能简单介绍。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霍氏注重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把二者置于对立面,认为小传统处于被动地位,在文明的发展中,农村不可避免要被城市同化。将此一相对的概念引入中文学界而言,台湾的李亦园教授功不可没,他将此一概念运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将其相应的转换为雅文化与俗文化,具体可参见氏著《文化与行为》一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有关此大、小传统的讨论学界相当热烈,暂且不多做阐述,但在笔者看来,在此借用这组概念来区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大、小传统中的传播与影响,对于我们厘清双典是否果如刘先生所讲为“统治与危害我们国民性的文化层面”的罪魁祸首,相当具有借鉴意义。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有一批本属大传统的读书人对于《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传播与影响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批读书人的介入,比如作者书中所列举的李贽与金圣叹等人,才使得双典得以列入今日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名著中来。但这样的联系放置于以四书五经为官方意识形态与入仕资格的大传统背景下,可以讲相当微不足道,如果再注意到李、金二人在大传统中所处的相对边缘的地位的话,则即使是上文所讲的“微不足道”,也要再大打折扣了。至于讲在大传统中不乏运用双典的“暴力崇拜”与“权利崇拜”者,在笔者看来就实质影响而言同样不能高估,此点下文会有阐述,此处暂且不论。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均是由历代民间的话本与传奇不断演变而最终得以成型这一事实,我们今日客观而论,相对于大传统,双典的传播与影响,更多的是在小传统中进行与扩展的。从作者以“国民性”着眼来探讨这个问题,也不难看作者是在充分肯定小传统在此一过程中的作用的。因乎此,则可以讲双典——《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其自身即为小传统的产物,而其所能直接影响的,更多的也是小传统。
(子遇《专制之弊与“双典”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