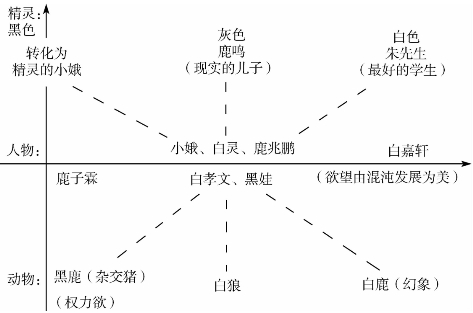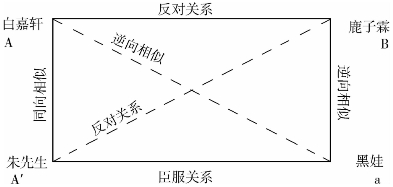-
1.1序
-
1.2目录
-
1.3不懈的“寻找” 不朽的丰碑——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
-
1.4论《白鹿原》的累积型叙事进程与审美救赎
-
1.4.1一
-
1.4.2二
-
1.4.3三
-
1.4.4四
-
1.4.5结 论
-
1.5呼唤白鹿:共在生存的人道诉求——对《白鹿原》中乡土社会共在生存的伦理省察
-
1.5.1一、鹿性之“我”:成德方能成己
-
1.5.2二、狼性之“我”:生存的异化与自我的遮蔽
-
1.5.3三、呼唤白鹿:共在生存的人道诉求
-
1.6为历史而烦——《白鹿原》的乡土生命哲学及其叙事价值
-
1.6.1一、乡土人生是与“历史”相关联的人生
-
1.6.2二、乡土生存是为历史而烦的生命过程
-
1.6.3三、乡土史诗叙事是为现实生存成长者开启生命活力渊源的探索
-
1.7《白鹿原》的关中“戏楼风景”研究
-
1.7.1一、“风景研究”与《白鹿原》研究的新视野
-
1.7.2二、作为人文景观的“关中戏楼”
-
1.7.3三、《白鹿原》的戏楼景观与文化隐喻
-
1.8陈忠实的艺术生命观
-
1.8.1一、主观体验的真实法度
-
1.8.2二、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
-
1.8.3三、批评的真实性尺度
-
1.9陈忠实文学创作观念的自觉与超越
-
1.9.1一
-
1.9.2二
-
1.9.3三
-
1.10论陈忠实作品中的关中区域和儒家文化
-
1.10.1《蓝袍先生》:儒家文化窒息关中
-
1.10.2《四妹子》:把关中非儒家化
-
1.10.3《白鹿原》:再次把关中儒家化
-
1.10.4突出儒家文化的意义
-
1.10.5把关中儒家化的后果
-
1.11陈忠实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论
-
1.11.1一
-
1.11.2二
-
1.11.3三
-
1.12生命化作浩然气 浑然一体写春秋——《白鹿原》别一种解读
-
1.13《白鹿原》性描写的象征意义和审美内涵
-
1.13.1一
-
1.13.2二
-
1.14奇观化与民族文化重塑——论《白鹿原》的视觉性书写
-
1.14.1一、意识形态、现代性、西方:奇观中的强力他者
-
1.14.2二、奇观化场景的形成及其艺术效果
-
1.14.2.1(一)全景敞视式视角
-
1.14.2.2(二)幽灵式的书写
-
1.15追述陈忠实先生三题
-
1.15.12016:陈忠实手稿管窥[1]
-
1.15.22014:《白鹿原》与关中文化[3]
-
1.15.31997:秦地小说视域中的陈忠实[4]
-
1.16《白鹿原》与中国革命
-
1.16.1一
-
1.16.2二
-
1.17论《白鹿原》中生命原欲对家族制度的侵蚀与解构
-
1.17.1一
-
1.17.2二
-
1.17.3三
-
1.18《白鹿原》中的三重空间①
-
1.18.1一、儒家文化空间——“礼法”与“圣”的空间
-
1.18.2二、原始文化空间——感性和生命力空间
-
1.18.3三、现代文化空间——革命与爱情的空间
-
1.18.4四、结语
-
1.19略论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学风格——兼论《白鹿原》的美学阐释
-
1.19.1一、关于《白鹿原》的美学风格
-
1.19.2二、《白鹿原》的社会符号系统
-
1.19.3三、“白狼来了”:“白鹿精魂”的审美意义
-
1.19.4四、当代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规定
-
1.20灞桥风雪因鹿鸣——论陈忠实的旧体诗词创作
-
1.21人性悖论的艺术呈现——《白鹿原》的个体生存伦理学阐释
-
1.21.1一、文化皈依的诱惑与奴役
-
1.21.1.1(一)《白鹿原》中彰显的文化自我认同价值
-
1.21.1.2(二)白鹿原上的悲剧映现文化与自我的矛盾
-
1.21.2二、集团归属的诱惑与奴役
-
1.21.2.1(一)集团使人获得归属感
-
1.21.2.2(二)集团遮蔽了个体自我
-
1.21.3三、肉身敞开的诱惑与奴役
-
1.21.3.1(一)爱欲是肉身生命完形的仪式
-
1.21.3.2(二)爱欲对人的奴役是生命悲剧的导火索
-
1.22试论《白鹿原》中的灾难书写
-
1.22.1一、历史与文本之间:哀民生之多艰
-
1.22.2二、传统与家族:以人物为中心
-
1.23世纪之变的文化探询——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手记》重解《白鹿原》
-
1.23.11
-
1.23.22
-
1.23.33
-
1.23.44
-
1.23.55
-
1.23.66
-
1.23.77
-
1.24《白鹿原》的创作过程
-
1.25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
1.26人格魅力、生命体验与文学创造——在“陈忠实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
1.26.1一、人格魅力与社会影响
-
1.26.2二、生命体验与文学精神
-
1.26.3三、文学创造与民族秘史
-
1.27《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
1.28《白鹿原》现实主义美学品格探索
-
1.28.1一
-
1.28.2二
-
1.28.3三
-
1.28.4四
1
陈忠实研究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