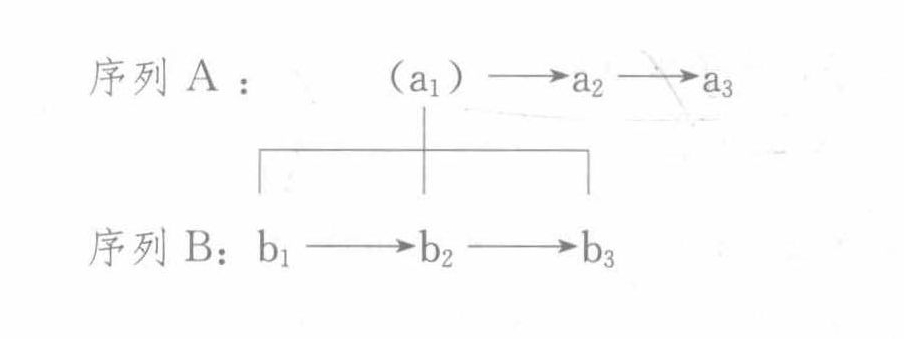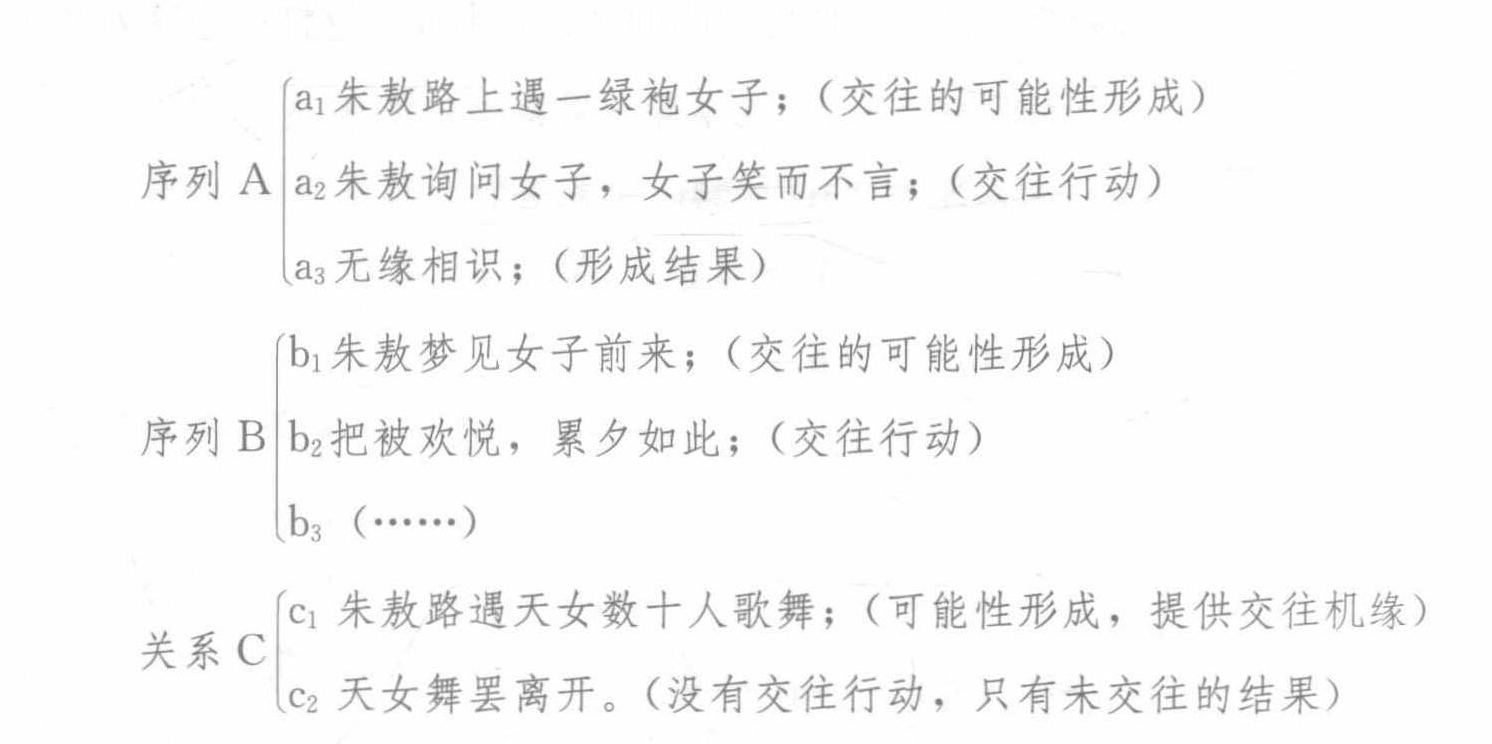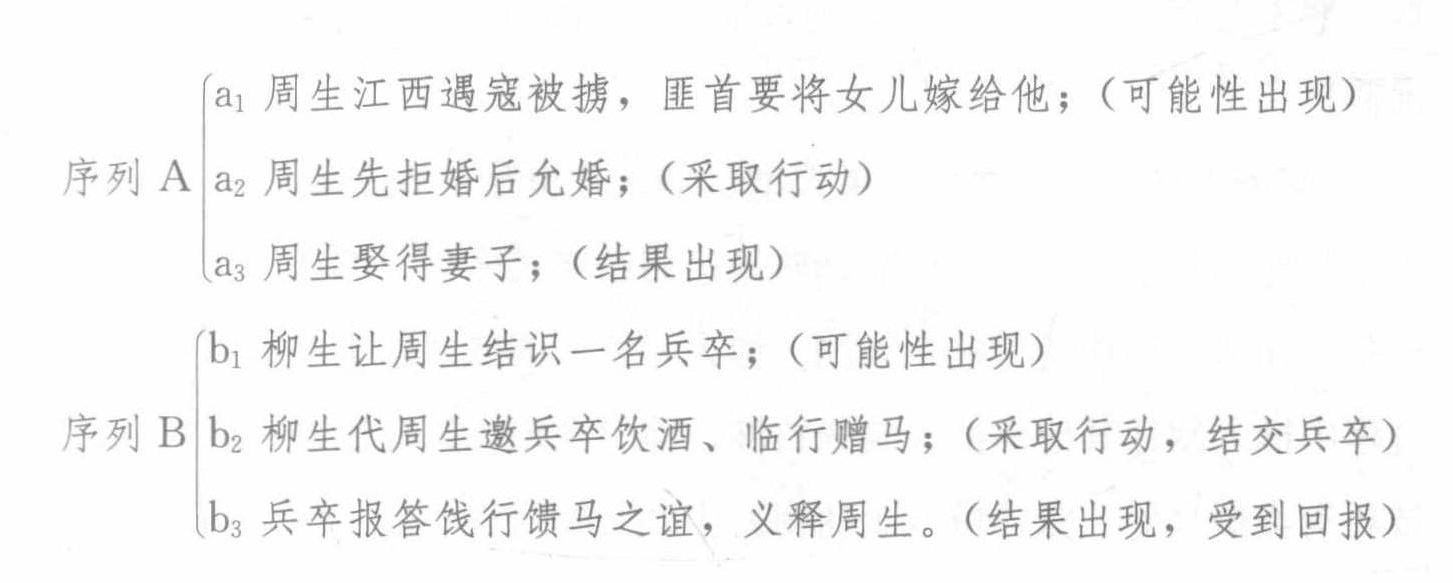-
1.1序
-
1.2目录
-
1.3第一章 绪论
-
1.3.1第一节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新创
-
1.3.1.1一、师法史传模式,大胆突破创新
-
1.3.1.2二、众体兼备,新在“传奇”
-
1.3.1.3三、人物中心转移,叙事切近民间
-
1.3.1.4四、融情志入叙事,提升小说品格
-
1.3.2第二节 《聊斋志异》叙事研究回溯
-
1.4第二章 时空叙事:变幻中的奇正相生
-
1.4.1第一节 叙事时空与时空叙事
-
1.4.1.1一、叙事时空:故事的生存形式
-
1.4.1.2二、时空叙事:讲述故事的手段
-
1.4.1.3三、文言小说的时空叙事
-
1.4.1.4四、《聊斋志异》时空叙事的新变
-
1.4.2第二节 回溯显意的追叙艺术
-
1.4.2.1一、《聊斋志异》追叙艺术的传承
-
1.4.2.2二、《聊斋志异》追叙艺术的拓展
-
1.4.2.3三、《聊斋志异》的追叙功能
-
1.4.3第三节 先期言说的预叙艺术
-
1.4.3.1一、《聊斋志异》预叙艺术的渊源
-
1.4.3.2二、《聊斋志异》预叙建构的方式
-
1.4.3.3三、《聊斋志异》预叙的功能
-
1.4.4第四节 虚实交织的空间叙事
-
1.4.4.1一、《聊斋志异》叙事空间类型
-
1.4.4.2二、《聊斋志异》叙事空间关系
-
1.4.5第五节 《聊斋志异》的第三叙事空间
-
1.4.5.1一、第三叙事空间是男女情感的自足世界
-
1.4.5.2二、第三叙事空间是情感平衡的世界
-
1.4.5.3三、第三叙事空间是礼教隔绝的世界
-
1.5第三章 叙事序列:与文体形态的肌理共存
-
1.5.1第一节 《聊斋志异》文体类型的历史关注
-
1.5.2第二节 叙事序列:审视文体形态的新视角
-
1.5.2.1一、叙事序列中的“事件”
-
1.5.2.2二、《聊斋志异》叙事序列与文体形态
-
1.5.3第三节 复合序列:《聊斋志异》的叙事拓展
-
1.5.3.1一、《聊斋志异》复合序列的基本类型
-
1.5.3.2二、环环相生:连续式复合序列
-
1.5.3.3三、交织错综:镶嵌式复合序列
-
1.5.3.4四、并进分叙:并列式复合序列
-
1.5.3.5五、一脉贯通:串珠式复合序列
-
1.6第四章 叙事修辞:体丰意腴的独特生成
-
1.6.1第一节 言约意幽的隐喻辞格
-
1.6.1.1一、语词隐喻
-
1.6.1.2二、意象隐喻
-
1.6.1.3三、行动隐喻
-
1.6.1.4四、空间隐喻
-
1.6.2第二节 疑波迭起的悬念辞格
-
1.6.2.1一、通过提出问题、摆出矛盾、强化信息创设悬念
-
1.6.2.2二、以限知叙事策略创设悬念
-
1.6.2.3三、以改变叙事节奏的方式制造悬念
-
1.6.3第三节 寓庄于谐的反讽辞格
-
1.6.3.1一、《聊斋志异》反讽修辞的性质
-
1.6.3.2二、《聊斋志异》的反讽方式
-
1.6.4第四节 复现强化的反复辞格
-
1.6.4.1一、同文反复
-
1.6.4.2二、异文反复
-
1.7第五章 人物中心移位与群体特征
-
1.7.1第一节 《聊斋志异》人物考察取向
-
1.7.2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人物中心转移
-
1.7.2.1一、清代以前的小说人物中心
-
1.7.2.2二、《聊斋志异》的人物中心转移
-
1.7.3第三节 《聊斋志异》文士人格的移位
-
1.7.3.1一、文士人格移位的群体表现
-
1.7.3.2二、文士人格移位的文化诱因
-
1.7.4第四节 《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的新变
-
1.7.4.1一、《聊斋志异》的女权倾向
-
1.7.4.2二、《聊斋志异》对男权的冲击与消解
-
1.7.4.3三、《聊斋志异》冲击男权的基础与动因
-
1.7.5第五节 《聊斋志异》、《镜花缘》文士形象比较
-
1.7.5.1一、蒲李笔下文士形象简况
-
1.7.5.2二、蒲李笔下文士群体的人格共性
-
1.7.5.3三、文士人格衰微的文化因素
-
1.7.6第六节 《聊斋志异》、《镜花缘》女性形象异同
-
1.7.6.1一、《聊斋志异》、《镜花缘》女性形象共性
-
1.7.6.2二、《聊斋志异》、《镜花缘》女性形象差异
-
1.7.6.3三、《聊斋志异》、《镜花缘》女性形象之异探因
-
1.8第六章 叙事情境:多重视角与叙事介入
-
1.8.1第一节 《聊斋志异》叙事情境简析
-
1.8.1.1一、《聊斋志异》的作者叙事情境
-
1.8.1.2二、第一人称叙事情境
-
1.8.1.3三、人物叙事情境
-
1.8.2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叙事转换
-
1.8.2.1一、叙事视角与叙述声音
-
1.8.2.2二、《聊斋志异》叙事视角转变
-
1.8.2.3三、《聊斋志异》声音转移
-
1.8.3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叙事介入
-
1.8.3.1一、《聊斋志异》叙事介入的方式
-
1.8.3.2二、《聊斋志异》叙事介入时机
-
1.8.3.3三、“异史氏曰”的介入功能
-
1.9参考文献
-
1.10后记
1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