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扫一扫,听有声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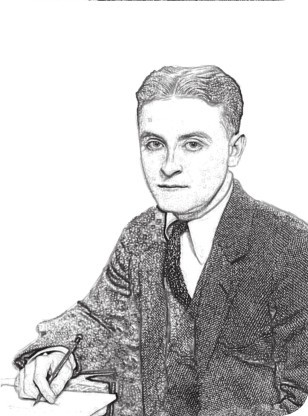
弗朗西斯 ·司皋特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最引人瞩目和最早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家。在中国,他是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他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学界和外国文学爱好者当中更是名声遐迩,备受推崇。
究其原因,首先他的功成名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无奈缀学,为了追求真爱闯入写作生涯,单凭自己年轻更事的经验而写成的第一部小说《天堂这一边》[1](Th is Side of Paradise, 1920)意外地轰动一时。当时,他年仅二十四岁,但已被公认为“爵士时代的桂冠作家”和“美国青年拥戴的国王”。遗憾的是,才思横溢的菲茨杰拉德为了应付妻子长期就医的开销疲于奔命,不得不多次把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花了不少心血写就来钱快的短篇小说。在他的影响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为了高薪去帮好莱坞修改电影剧本,结果,染上酗酒的习气,英年早逝。一生只留下四部长篇小说、一部未完稿的长篇、一本生后发表的书信散文集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生动刻画了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太平盛世到“大萧条”艰难时期之间的社会繁荣、动荡和矛盾,详尽地记载了从纵情的享乐主义到颓废的虚无主义的快速变迁,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迷惘的美国应该何去何从的难题。其次,他的作品在主题和艺术两方面终极了由西奥多 ·德莱塞和弗兰克 ·诺里斯统领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美国小说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开启了转向现代主义小说的过度,推出了展现美国新世纪的人物、文化和生活的新颖小说艺术。
一九八二年,前辈学者巫宁坤先生推出菲茨杰拉德代表作的中译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英语界备受关注,在社会上也引起一阵轰动。当时正是“文革”浩劫过后不久,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势如破竹。人们虽然踌躇满志,但是欣喜行乐之余却对自身的前途和祖国的未来充满疑虑、迷惘和失落。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急需转型,读者的需求日新月异,外国文学中的经典接踵而至,风靡一时。由此看来,菲茨杰拉德写作的历史背景和他小说中展现的时代风貌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他的作品为何能激起国内学者及读者的共鸣、并且赢得普遍的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和菲茨杰拉德的渊源由来已久。他是我酷爱的美国作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与我数十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的学习、教学和科研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说来,我选修的第一门美国文化/文学课程、我教的第一门美国文学课程、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和第一本学术专著都和菲茨杰拉德有关。记得一九七八年在复旦外语系的研究生课上,初次听到美国外教提及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一连串似曾见过、但一知半解的术语,如“盖茨比”,“爵士时代”(The Jazz Age)和“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激起我浓厚的兴趣。于是,借以自己“青年教师兼外教助理”的身份,我多次私下约谈外教,向他求索更多的相关信息。同时,我还多次在系资料室和校文科阅览室查找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和资料。遗憾的是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生平简介和作品赏析。也许,当时他的作品和其他西方文学的藏书一样还未开禁,或许复旦图书馆里根本没有。不过,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始给本科生讲授“美国文学简史”一课之后,我每次都会重点介绍菲茨杰拉德,与学生们分享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对他的肤浅却十分赏识的见解。
一九八一年秋季,我有幸经系里推荐参加了中美双方政府举办的第一期“中国美国文学高级师资培训班”。培训基地设在北大校园,为期一年,四位任课老师都是来自美国一流大学的文学教授。因为这是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后中美之间最早的学术交流项目之一,况且美方也急于在中国推广美国文学,所以美方十分重视。除了向学员赠送数十本教学所用的原著和辞书之外,还定期从使馆送来影像资料。在那个年代,英语专业人士想见上一本留着封面的英美原著机会不多。突然间一下拥有这么多原版名著,还能在美国教授的指导下一一研读、分析、讨论,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在我获赠的原版名著里,我最钟爱的就是“美国文学史”课里必读的初版《诺顿美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和“美国小说”课里必读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两门课让我初次接触和精读了菲茨杰拉德的代表性的小说和短篇小说,帮我厘清了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特色,从而认识到他对美国小说创作的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卓越贡献。一九八二年返回复旦之后,菲茨杰拉德自然成了我教“美国文学简史”一课时的重中之重;同时,我开始对其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一九八三年,我的第一篇有关美国文学的论文发表在“全国美国文学学会”主办的《美国文学丛刊》上,根据他的作品,以及他与编辑和其他作家的往来书信,阐述了他有关小说创作的独到见解。
然而,我真正能读懂和欣赏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真谛还是到了美国之后。一九八四年到哈佛访学时,我跟随萨克万 ·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教授在研究生专题课上重温《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九八五年在哈佛英语系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后,我在艾伦 ·海姆特(Alan Heimert)教授的“美国神话”(哈佛历史悠久的美国文学史课)课里担任他的助教,给美国学生讲解《了不起的盖茨比》。几年后,在伯科维奇教授和菲利普 ·菲希尔(Philip Fisher)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以菲茨杰拉德为重点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毕业不久,我在教学之余,把博士论文拓展为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在美国顺利发表。在之后的二十五年里,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偏爱可谓有增无减。他不仅是我多门美国文学专题课里的必选作家,而且一直是我研究美国小说中的重点。无论是“司皋特 ·菲茨杰拉德协会”主办的历届国际会议,还是“美国文学协会”年会上的“菲茨杰拉德专题讨论会”,我几乎每次必到。利用学术调研和会议之便,我追寻过他生前的足迹: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瞻仰他的故居,在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触摸他的手稿,在纽约、伦敦、巴黎、安第贝斯、蒙特卡洛和瑞士的洛萨纳重访他曾经住过的酒店,在马里兰州洛克威尔市搜寻他的安息之地。我还有幸聆听过他在逗留好莱坞期间所聘的女秘书弗朗西斯 ·克罗尔 ·琳恩(Frances Kroll Ring)和他的生前好友巴德 ·苏尔伯格(Budd Schulberg)追忆他的逸事和风采,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耳闻目睹了不同肤色的人们对他的赞赏和敬仰。

2007年,本书译者参加在伦敦大学英语学院举行的国际会议

2007年,本书译者参加在伦敦大学英语学院举行的国际会议

本书译者(左)与菲茨杰拉德生前秘书(右)和菲茨杰拉德协会主席(中)合影

本书译者在菲茨杰拉德研讨会会场发言

普林斯顿大学Firestone图书馆,作者的书稿都收藏在此

作者出生地故居(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与作者塑像合影(2002年,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中心广场)

作者在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墓地
作为美国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菲茨杰拉德当之无愧。迈尔科姆 ·卡奥利曾经指出,“从某种角度来看,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和短篇小说等于是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最好写照。”[2]无论是当年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如汤姆斯 ·斯特恩斯 ·埃略特 (T. S. Eliot), 还是历代推崇他的学者和读者,如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都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名字与“爵士时代”的美国分割不开,因为他的作品“带有特别的美国印记,从人物刻画到场景描绘、叙事节奏、主题意境,甚至他的桀骜不驯的创作生涯,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美国根源。”[3]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勾勒出时代的现实,传递了时代的心声,激扬了时代的精神。正如格特鲁德 ·斯坦因所说的,菲茨杰拉德“为大众塑造了新的一代。”[4]他自己既是这一代的一份子,又是这一代的代言人, 因为他不仅开创了“爵士时代”,而且亲身经历这一段大起大落的历史演变,在作品中揭示了一代人的风貌、幻想、失落和绝望。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喜欢把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跟美国文学中有关“美国梦”的阐释联系在一起。应该澄清一点,该小说发表时,“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一词还未出现。该词是由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 ·突斯娄 ·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一九三一年发表的专著《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里首先使用。在此之前,美国立国先驱和知识精英使用过不同的术语来描述他们所倡导的“美国理想”,如“山上都市”(the City on the Hill)和“美国神话”(the Myth of America)。亚当斯的术语“美国梦”与它们大同小异,但含意更加具体和深刻。他给“美国梦”所下的定义远远超出物质上的成功和发达,更多的是喻指追求完美生活的理想主义信念。亚当斯关于“美国梦”的论述得到广泛认可,这一术语由此被沿用至今。在这一问题上,菲茨杰拉德与亚当斯不谋而合,因为这正是他一再精心探索的主题。他的作品客观地、尖锐地、生动地勾勒出“美国梦”的正反两面性,不仅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性,而且在小说创作艺术上被后人尊为标新立异的楷模。历来涉及“美国神话”或“美国梦”议题的论述都会列举《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是美国文学中刻画该主题的最精辟、最动人的巨作之一。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发表轰动了当时的美国文坛,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文坛上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将他变成腰缠万贯的富豪,甚至未能帮他脱离入不敷出的窘境。该小说从一九二五年问世后到他一九四O年离世,仅仅销售了将近25,000本。然而,该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走红,销量陡增,光为军队出的专版就售出150,000本之多,而至今为止的总销量已高达2,500万册。如今,该小说已被公认为英美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先后五次被改编搬上银幕,多次在英美出版界、舆论界和学术界选定的“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的书单上名列第二,成为英美高中和大学文学课里的必读书目之一。同时,该小说已被译成数十种语言,誉满全球,其影响力经久不衰。
几十年来,海内外已经出现十多种中译本。中译本中,读者较为熟悉的小说书名有两种,一是巫宁坤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二是美籍华裔学者乔治高(George Gao)译的《大亨小传》。虽然把这两种书名看成是误译会显得过于轻率和偏颇,但是两者仅仅强调了盖芝比这一人物的个人才智和魅力,却没充分展现原著书名的另一层含意:盖茨比超凡脱俗、不同凡响。把小说的书名译成《不同凡响的盖茨比》显得更为妥帖,因为它更能概括作者的原意。首先,细心的读者都会注意到,尼克在小说里前后两次重申,他不苟同盖茨比所信奉或代表的一切。小说刚开始,尼克在表述自己从东部归来后对世态的感慨时就宣称,盖茨比“代表了他所公然蔑视的一切。”[5]临近小说结尾,在追忆他与盖茨比最后一次分别时,尼克告诉我们,他给了盖茨比唯一的一次赞扬,“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帮子全堆在一起都不如你。”[6]然而,他依然没忘再次提及,“我自始自终没赞同过他。”[7]显而易见,尼克对盖茨比的印象具有赞同和排斥的两重性。他既羡慕盖茨比对理想忠贞不渝的执着,钦佩他那敢于“誓创壮举的能力,”[8]又不心甘情愿地与他同流合污。
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给了我又一次细心品味这一杰作的机会。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时常回忆起自己以往初读原著、课堂讲解和为撰稿而考证细节的情景,重温作者精彩的文笔充满了享受。众所周知,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文学性和创意性极强,尤其是在叙事结构、修辞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他的文笔虽然言简意赅,但是内涵深邃;虽然他喜好自立行文规矩或任性地遣词造句,但是依据特定的情节、场景和人物个性来读,又显得非常细腻精巧,贴切传神。翻译中,时常觉得对原文心领意会,可是为敲定完美的译文却一再冥思苦想,费尽心机。我知道,历来译者的取舍不同,风格各异。在我看来,忠实作品的原意和文风至关重要,不能随意为了译文的优美和流畅而诉诸于“演释”(paraphrasing)或“省略”(omitting),甚至“重写”(rewriting)。尽管无人能宣称自己的译文完全彻底地与原文相吻合,但是我竭力避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埃斯卡皮特(Robert Escarpit)所说的那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9]力求在译文中尽可能地还原这一经典之作中的作者心声、时代印记、地域风貌和语言特色。
在此,我衷心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此书全文双语对照有助于读者提高精读英语文本、鉴赏文学大师创作艺术和推敲中英翻译的能力。
[1] 又译《人间天堂》。
[2] Malcom Cowley, Exile’s Return: 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 1920s (New York: Penguin, 1976), 243.
[3] Benjamin Spencer, “Fitzgerald and the American Ambivalence.”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66.3 (Summer 1967): 367.
[4] Gertrude Stein,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3), 268.
[5]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New York: Scribner, 2004), 2.
[6] Ibid,154.
[7] Ibid,154.
[8] Ibid,180.
[9] 此术语出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特(Robert Escarpit)的著作《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8). 王美华和于沛将此书译成中文,1987年由安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谢天振教授曾将这一概念推介給国内翻译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