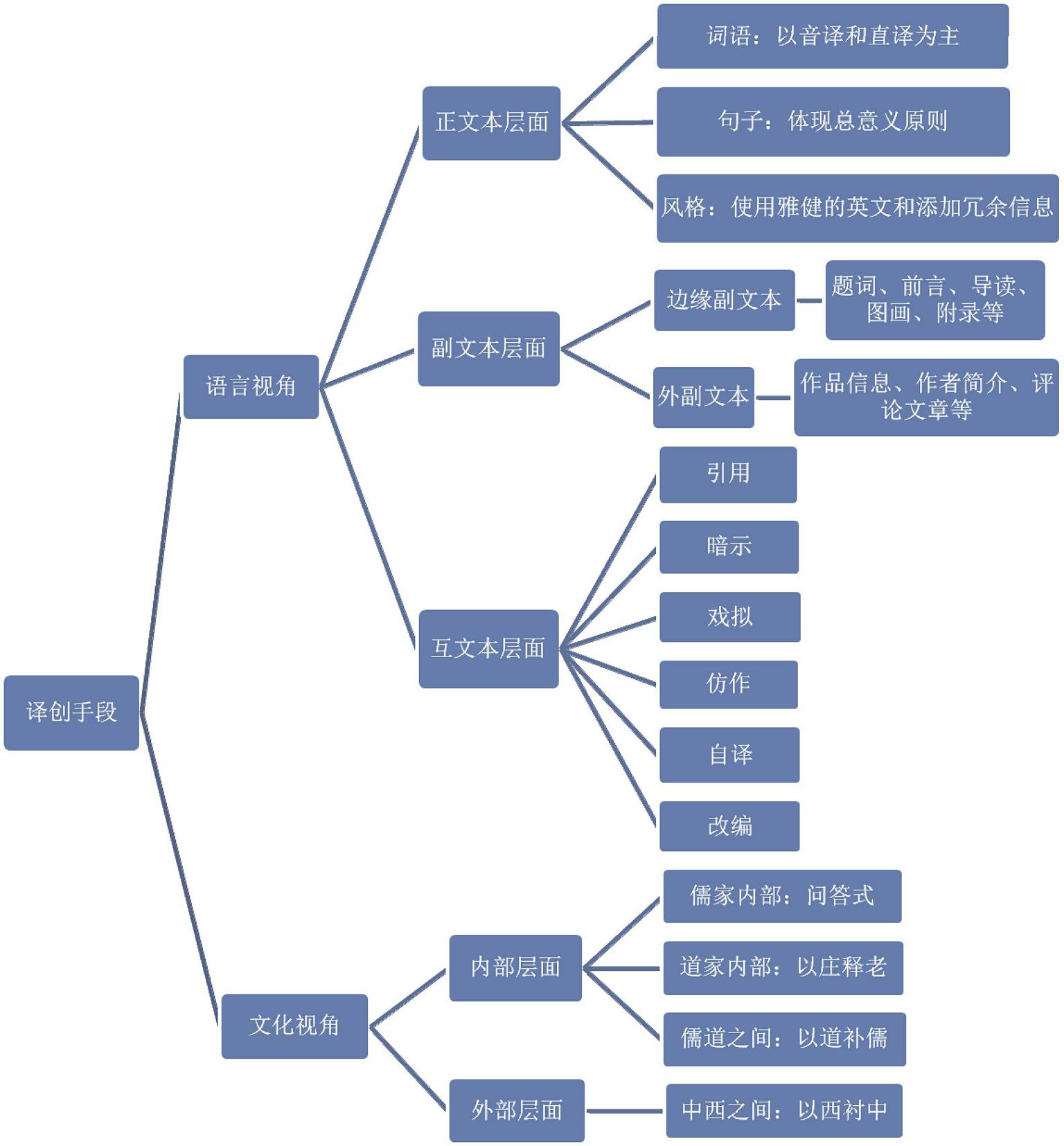-
1.1封面页
-
1.2内容提要
-
1.3序言
-
1.4目录
-
1.5第1章 绪论
-
1.5.11.1 研究背景
-
1.5.21.2 研究意义
-
1.5.3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5.41.4 研究方法
-
1.5.51.5 研究框架
-
1.6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6.12.1 译创理论概述
-
1.6.1.12.1.1 译创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
1.6.1.22.1.2 译创理论的内涵分析
-
1.6.1.32.1.3 译创者主体性分析
-
1.6.1.42.1.4 译创手段分析
-
1.6.1.52.1.5 对译创理论的批评
-
1.6.1.62.1.6 译创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及其现实意义
-
1.6.22.2 林语堂研究述评
-
1.6.2.12.2.1 中国大陆的林语堂研究述评
-
1.6.2.22.2.2 港台地区及海外林语堂研究述评
-
1.6.2.32.2.3 林语堂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1.6.32.3 本章小结
-
1.7第3章 林语堂译创动机、内容和思想研究
-
1.7.13.1 林语堂译创动机分析
-
1.7.1.13.1.1 赛珍珠的发现和《吾国与吾民》的畅销
-
1.7.1.23.1.2 纠正此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
1.7.1.33.1.3 调和中西文化,构建多元文化
-
1.7.1.43.1.4 从个人兴趣与视角出发讲述中国故事
-
1.7.23.2 林语堂译创内容分析
-
1.7.2.13.2.1 经典哲学
-
1.7.2.23.2.2 抒情哲学
-
1.7.2.33.2.3 影响译创内容的因素分析
-
1.7.33.3 林语堂译创思想分析
-
1.7.3.13.3.1 宏观视角
-
1.7.3.23.3.2 微观视角
-
1.7.43.4 林语堂作为译创主体的贡献和价值分析
-
1.7.53.5 本章小结
-
1.8第4章 林语堂译创手段研究
-
1.8.14.1 语言视角下的译创手段分析
-
1.8.1.14.1.1 正文本层面
-
1.8.1.24.1.2 副文本层面
-
1.8.1.34.1.3 互文本层面
-
1.8.24.2 文化视角下的译创手段分析
-
1.8.2.14.2.1 中国文化的内部层面
-
1.8.2.24.2.2 中西文化的外部层面
-
1.8.34.3 林语堂译创手段的贡献和价值分析
-
1.8.44.4 本章小结
-
1.9第5章 林语堂译创效果研究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
1.9.15.1 林语堂译创作品海外出版情况分析
-
1.9.25.2 林语堂译创作品读者接受情况分析
-
1.9.2.15.2.1 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书评文章
-
1.9.2.25.2.2 网络上发表的读者评论
-
1.9.35.3 林语堂译创效果的原因分析
-
1.9.3.15.3.1 西方文化语境的需要
-
1.9.3.25.3.2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
-
1.9.3.35.3.3 赛珍珠夫妇的作用
-
1.9.45.4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
1.9.55.5 本章小结
-
1.10第6章 研究绪论
-
1.10.16.1 本书研究成果
-
1.10.26.2 本书的创新之处
-
1.10.36.3 本书的局限
-
1.11参考文献
-
1.12附录1:林语堂作品总目
-
1.13附录2:林语堂生平年表
-
1.14后记
-
1.15索引
1
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