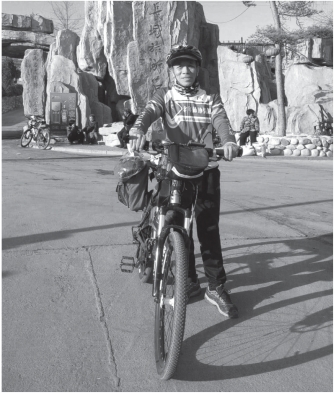-
1.1编者的话:留住知青的记忆
-
1.2目录
-
1.3历史担当 时代洪流
-
1.3.1思路心曲
-
1.3.1.1下乡——无奈的抉择
-
1.3.1.2学农——初涉人生苦涩
-
1.3.1.3生活——难咽的心酸
-
1.3.1.4“作为”——“科学种棉”和“地头春晚”
-
1.3.1.5“笑师”——只因大黑牛和小白鸡
-
1.3.1.6扎根——五彩的浮云
-
1.3.2还是那弯弯的月亮
-
1.3.3我的知青缘
-
1.3.3.1我非知青 心仪知青
-
1.3.3.2一面之缘 记忆铭心
-
1.3.3.3朝夕相处 见贤思齐
-
1.3.3.4动如参商 心有灵犀
-
1.3.4日记摘抄
-
1.3.4.1参加地区首届党代会
-
1.3.4.1.11971年4月8日
-
1.3.4.1.21971年6月5日
-
1.3.4.1.31971年6月10日
-
1.3.4.1.41971年6月16日
-
1.3.4.2参加知青回城汇报团
-
1.3.4.2.11972年1月22日
-
1.3.4.2.21972年1月24日
-
1.3.4.2.31972年1月25日
-
1.3.4.2.41972年2月10日
-
1.3.4.2.51973年1月26日
-
1.3.4.2.61973年6月16日
-
1.3.4.2.71973年6月17日
-
1.3.4.2.81973年6月21日
-
1.3.4.2.91973年7月18日
-
1.3.4.3偶遇英雄贺相魁
-
1.3.4.3.11973年5月2日
-
1.3.5追忆知青岁月
-
1.3.6我知青生涯的首站——唐山青年垦荒队
-
1.3.6.1垦荒队概况
-
1.3.6.2垦荒队的生活
-
1.3.6.3垦荒队解体
-
1.3.7我非同寻常的知青历程
-
1.3.7.1一
-
1.3.7.2二
-
1.3.7.3三
-
1.3.8邢燕子柏玉兰回唐
-
1.3.9我参加过城市动员下乡工作
-
1.3.10那个特殊年代
-
1.3.11难忘插队下乡第一天
-
1.3.12长沟流月去无声
-
1.3.12.1回乡当农民
-
1.3.12.2三级干部会
-
1.3.12.3当民办教师
-
1.3.12.4“我要上大学”
-
1.3.12.5圆梦谢恩师
-
1.3.13难忘知青生涯
-
1.3.13.1踏上征途
-
1.3.13.2鲜花盛开
-
1.3.13.3荒郊猪场
-
1.3.13.4推车挖河
-
1.3.14下乡插队那些事
-
1.3.14.1挺起胸膛
-
1.3.14.2恩重如山
-
1.3.14.3田间趣事
-
1.3.14.4较量心魔
-
1.3.15下乡记事
-
1.3.15.1到了农村
-
1.3.15.2穷则思变
-
1.3.15.3大战海河
-
1.3.15.4夜捉螃蟹
-
1.3.16抹不掉的记忆——回忆垦区文艺宣传队的难忘时光
-
1.3.16.1排演京剧《沙家浜》
-
1.3.16.2参加地区文艺会演
-
1.3.16.3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
-
1.3.16.4排演京剧《龙江颂》
-
1.3.17我在七农场当广播员
-
1.3.18回忆代课的时光
-
1.3.19重回旧地叙怀
-
1.3.20机会撞上了能忍隐的女孩
-
1.3.21乡村趣事
-
1.3.22好大一个家
-
1.3.22.1金华猪
-
1.3.22.2宣传队
-
1.3.22.3回家路
-
1.3.22.4一家人
-
1.3.22.5回“娘家”
-
1.3.23无怨无悔知青路
-
1.3.23.1煤气中毒
-
1.3.24救落井女孩
-
1.3.25“曲线”上大学
-
1.3.26难忘的岁月
-
1.3.27当年我们这么年轻
-
1.3.28烙 印
-
1.3.299名唐山知青牺牲在内蒙古
-
1.3.30渤海边上那座知青坟茔
-
1.3.31重回乌拉盖
-
1.3.32难忘的蒲台河
-
1.3.33回忆我们的创业队
-
1.3.34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
1.3.35我的知青故事
-
1.3.35.1(一)
-
1.3.35.2(二)
-
1.3.35.3(三)
-
1.3.35.4(四)
-
1.3.36“集溜子”的故事
-
1.3.36.1(一)
-
1.3.36.2(二)
-
1.3.36.3(三)
-
1.3.36.4(四)
-
1.3.37故乡的路
-
1.3.37.1记忆之路
-
1.3.37.2难忘之路
-
1.3.37.3腾飞之路
-
1.3.38下乡记忆
-
1.3.38.1参观烈士洞
-
1.3.38.2天蓝色围巾
-
1.3.38.3冬夜漏粉
-
1.3.39知青往事
-
1.3.39.1遇险
-
1.3.39.2帮助
-
1.3.39.3过河
-
1.3.39.4采药
-
1.3.40当年我是饲养员
-
1.3.41瑰丽 逆风飞扬——献给2018年唐山知青联谊会
-
1.4走出懵懂 历练青春
-
1.4.1我是北大荒人
-
1.4.1.1吹响战斗的号角
-
1.4.1.2磨砺意志的课堂
-
1.4.1.3历劫方显钢骨硬
-
1.4.1.4接触丁玲被打成右派
-
1.4.1.5农业试验场结缘园艺
-
1.4.2北疆记事
-
1.4.2.1历练苦与累
-
1.4.2.2连队的“航母”
-
1.4.3我和兵团战士的情缘
-
1.4.3.1艰难的起步
-
1.4.3.2建设新连队
-
1.4.3.3第一次大搬迁
-
1.4.3.4第二次大搬迁
-
1.4.3.5第三次搬迁
-
1.4.4在那屯垦戍边的岁月里
-
1.4.4.1草原上的新牧民
-
1.4.4.2不平常的冬天
-
1.4.4.3蒙汉亲兄弟
-
1.4.4.4兵团精神永在
-
1.4.5机运连的炊事班
-
1.4.6不释乡情伴我行
-
1.4.6.1蹉跎岁月乡情暖
-
1.4.6.2创业精神励志行
-
1.4.6.3无时无刻不关情
-
1.4.7从那片热土一路走来
-
1.4.7.1人生转折
-
1.4.7.2奋力前行
-
1.4.7.3逐梦终身
-
1.4.8开拓精神 砥砺终身
-
1.4.8.1跋涉:一条蹉跎的路
-
1.4.8.2磨砺:一股创业的精神
-
1.4.8.3尽责:一行砥砺前行的足迹
-
1.4.8.4携手:一生不了的情
-
1.4.9沧桑历练 苦涩追求
-
1.4.9.1学梦破碎
-
1.4.9.2凝筑海河
-
1.4.9.3学梦厄变
-
1.4.9.4学梦终圆
-
1.4.10秋收时节
-
1.4.10.1“杀”高粱
-
1.4.10.2割大豆
-
1.4.10.3上场(读阳平)
-
1.4.10.4尾声
-
1.4.11知青生涯第一年
-
1.4.12洪水肆虐
-
1.4.13像个庄稼人
-
1.4.13.1学会做人
-
1.4.13.2建大寨田
-
1.4.13.3深翻土地
-
1.4.13.4土托儿所
-
1.4.13.5奋战海河
-
1.4.13.6回城下井
-
1.4.14山青青 水清清——大黑汀水库遥想
-
1.4.15迁西筑路记
-
1.4.15.1出发
-
1.4.15.2开工
-
1.4.15.3上调
-
1.4.15.4办报
-
1.4.15.5村姑
-
1.4.15.6车祸
-
1.4.15.7夜路
-
1.4.15.8招工
-
1.4.16难忘的四场二队
-
1.4.17脱胎换骨的蜕变
-
1.4.18我的知青岁月
-
1.4.19命运之变
-
1.4.20难忘的回忆
-
1.4.21战天斗地第一仗
-
1.4.22激情岁月里的记忆
-
1.4.22.1挑水
-
1.4.22.2分红
-
1.4.22.3送粮
-
1.4.22.4电话
-
1.4.23伤 力
-
1.4.24累 三秋……
-
1.4.25难忘打井那些事
-
1.4.26干不完的农活
-
1.4.27知青生活点滴
-
1.4.28我选择坚强
-
1.4.29岁月有痕 青春无悔
-
1.4.30有苦涩更有感动
-
1.4.31五七干校的懵懂人生
-
1.4.31.1广阔天地的召唤
-
1.4.31.2知青生活的五味杂陈
-
1.4.32难忘的经历
-
1.5感悟真情 大爱无边
-
1.5.1岁月斩不断的情丝
-
1.5.2那无法修补的内疚
-
1.5.2.1相识
-
1.5.2.2热恋
-
1.5.2.3分手
-
1.5.2.4重见
-
1.5.3山路弯弯
-
1.5.4常想起那弯弯的身影
-
1.5.5二大爷
-
1.5.6梦中的故乡
-
1.5.7大 英
-
1.5.8终生楷模——我与两位老干部的忘年交
-
1.5.9五朵金花
-
1.5.10忆寻蔚
-
1.5.10.1老师
-
1.5.10.2兄长
-
1.5.10.3榜样
-
1.5.10.4楷模
-
1.5.11四十八载知青情
-
1.5.11.1难忘的插队情
-
1.5.11.2延续的知青情
-
1.5.12我知盘中餐
-
1.5.13农场难忘事
-
1.5.13.1粮票情缘
-
1.5.13.2患难真情
-
1.5.13.3良知民心
-
1.5.13.4心有准星
-
1.5.14从绿色的远方走来
-
1.5.15往事回想
-
1.5.16唐山知青艺术团不忘初心 用真情“致青春”
-
1.5.16.1第二故乡行
-
1.5.16.2老区行
-
1.5.16.3校园行
-
1.5.17第二故乡
-
1.5.18心系栗乡情
-
1.5.19回 城
-
1.5.20泯不去的记忆
-
1.5.21重回沙石峪
-
1.5.22小 初
-
1.5.23情窦初开的时候
-
1.5.24留在胡稍庙的记忆
-
1.5.25我们的故事
-
1.5.26他没有到照燕洲来
-
1.5.27无处诉说的解释
-
1.5.28不寻常的师生情
-
1.5.29海棠树
-
1.5.30我相识的那个小芳
-
1.5.31慧明和他的“小芳”
-
1.5.32午夜的乡音
-
1.5.33乡音
-
1.5.34不忘乡愁
-
1.5.35红绳根根闹我心
-
1.5.36广阔天地结情缘
-
1.5.37随笔三则
-
1.5.37.1杯水情
-
1.5.37.2耗油郎
-
1.5.37.3人性爱
-
1.5.38怀念感恩
-
1.5.39快乐天使刘福珑
-
1.6乐享乡韵 人生财富
-
1.6.1冰霜谁识抱关情
-
1.6.1.1冰霜抱关
-
1.6.1.2感谢开滦
-
1.6.1.3改行广告
-
1.6.1.4刷新历史
-
1.6.1.5七条好汉
-
1.6.1.6掰开硬币
-
1.6.1.7照猫画虎
-
1.6.1.8友情为重
-
1.6.1.9鼾声大作
-
1.6.1.10惟余莽莽
-
1.6.1.11有线电视
-
1.6.1.12不知羞耻
-
1.6.2燕山深处那双双渴望的眼睛
-
1.6.3今生难忘的农民结
-
1.6.3.1初次下乡务农
-
1.6.3.2大学毕业当农民
-
1.6.3.3回城到园林局
-
1.6.3.4退休不忘农村
-
1.6.4我学会了迎难而上
-
1.6.5从知青到毛体书法家
-
1.6.5.1艰苦磨炼
-
1.6.5.2如获至宝
-
1.6.5.3如鱼得水
-
1.6.5.4艺术成就
-
1.6.6我的社会大学
-
1.6.6.1第一课:失去美甲永生难忘
-
1.6.6.2第二课:开通孝道感恩父母
-
1.6.6.3第三课:伤病肆虐挑战极限
-
1.6.6.4第四课:感恩老师痛并快乐着
-
1.6.6.5结业课:知青精神成长的原动力
-
1.6.7在柏农宣传队
-
1.6.7.1我是知青“特长生”
-
1.6.7.2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
1.6.7.3迎来春色换人间
-
1.6.7.4端起龙江洒春雨
-
1.6.8“下过乡 就是不一样”
-
1.6.9最终未圆的大学梦
-
1.6.10书海无涯苦作舟
-
1.6.10.1就“好这一口儿”
-
1.6.10.2过了两次“主编瘾”
-
1.6.10.3干得最“牛”的一回
-
1.6.11北大荒精神永远激励我的人生
-
1.6.11.1献绵薄之力
-
1.6.11.2无边的母爱
-
1.6.11.3珍贵的财富
-
1.6.12下过乡的人真能干
-
1.6.13知青经历让我与沙石峪结缘
-
1.6.14回城的二次创业
-
1.6.14.1从头打拼
-
1.6.14.2找好定位
-
1.6.14.3重返机关
-
1.6.15走过,我回头一笑
-
1.6.15.1荣誉
-
1.6.15.2背后
-
1.6.15.3沉淀
-
1.6.16知青经历伴我成长
-
1.6.17要干出个模样来
-
1.6.17.1当马倌
-
1.6.17.2当猪倌
-
1.6.17.3听党话
-
1.6.17.4谱新篇
-
1.6.18我的这几十年
-
1.6.18.1情系新闻
-
1.6.18.2埋头修志
-
1.6.18.3以史知往
-
1.6.19我的知青岁月
-
1.6.19.1最难忘的那两天
-
1.6.19.2学会开拖拉机
-
1.6.19.3难忘的“堵决口”
-
1.6.19.4参加民兵预备役
-
1.6.19.5“吃小亏占大便宜”
-
1.6.19.6学当“孩子王”
-
1.6.19.7“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
1.6.20我结识的几位下乡知青
-
1.6.21永远做唐山好人
-
1.6.22我是农民的赤脚医生
-
1.6.23我眼中的孔紫
-
1.6.24无悔的选择
-
1.6.24.1命运
-
1.6.24.2追梦
-
1.6.24.3跨越
-
1.6.25我的教学生涯
-
1.6.26我当教师的起点
-
1.6.27永不服输
-
1.6.28坚强伴随我扎根迁安
-
1.6.29晚来犹自唱夕阳
-
1.6.30自强不息结硕果
-
1.6.31我是知青老来乐
-
1.6.32大地震时我在农场
-
1.6.33知青人的骄傲
-
1.6.34追 梦
-
1.6.35一张杀猪税票的回忆
-
1.7轶事风趣 感恩乡里
-
1.7.1插队乐趣
-
1.7.1.1“谁是座山雕”
-
1.7.1.2抄(chào)烟的学问
-
1.7.1.3眼镜篮球队
-
1.7.1.4捉蟹与吃蟹
-
1.7.1.5狐狸炼丹
-
1.7.2下乡散记
-
1.7.2.1啦馋
-
1.7.2.2棚车
-
1.7.2.3买车
-
1.7.3夜走狼窝掌
-
1.7.4难忘的记忆
-
1.7.4.1过年的饺子
-
1.7.4.2咸菜“展览会”
-
1.7.4.3坠井事件
-
1.7.5插队拾零
-
1.7.5.1抽烟梗
-
1.7.5.2奏哀乐
-
1.7.5.3找乐儿
-
1.7.5.4喝“鸡汤”
-
1.7.5.5过生日
-
1.7.6大兴安岭伐木二三事
-
1.7.6.1伐木小分队
-
1.7.6.2可恶的老兵
-
1.7.6.3“敌特发信号”
-
1.7.7难以忘却的趣事
-
1.7.7.1拜年时间的风趣
-
1.7.7.2突来的一顿饱餐
-
1.7.7.3巧看定亲新媳妇
-
1.7.7.4时兴的“尿素大裤”
-
1.7.8病号汤
-
1.7.9庄稼地里难忘的事
-
1.7.9.1“老盛英”发怒
-
1.7.9.2迷糊队长
-
1.7.9.3叶子秋
-
1.7.10吃嘛嘛香
-
1.7.10.1“人管猪”
-
1.7.10.2吃狗肉
-
1.7.10.3吃蛤蟆腿
-
1.7.10.4吃田鼠
-
1.7.10.5吃蛇肉
-
1.7.10.6鱼蟹乐
-
1.7.11快乐花絮
-
1.7.11.1与老大过招
-
1.7.11.2飘飘然
-
1.7.11.3烧牛粪
-
1.7.11.4绒袄当裤穿
-
1.7.12想念白菜烩饼
-
1.7.13支边轶事
-
1.7.13.1托人去支边
-
1.7.13.2偷学开车
-
1.7.13.3初学蒙语
-
1.7.13.4给家捎全羊
-
1.7.13.5厕所里遇狼
-
1.7.14黄屯轶事
-
1.7.14.1“清炒鲜菇”
-
1.7.14.2一把树剪
-
1.7.14.3捉狐狸
-
1.7.14.4兔蹬鹰
-
1.7.14.5“鸽子峪”
-
1.7.14.6黄屯石的由来
-
1.7.15十二载往事回顾
-
1.7.15.1无字之书
-
1.7.15.2跑步驱寒
-
1.7.15.3西山练胆
-
1.7.15.4正骨高手
-
1.7.15.5瞒天过海
-
1.7.16失足落井
-
1.7.17再教育拾零
-
1.7.17.1可怜的花猫
-
1.7.17.2架子
-
1.7.17.3怕蛇
-
1.7.18柏农趣事三则
-
1.7.18.1杀牛的风波
-
1.7.18.2百鸭宴庆寿
-
1.7.18.3蛙蛇蟹恶斗
-
1.7.19下乡记忆
-
1.7.19.1涮羊肉
-
1.7.19.2夜壶
-
1.7.20粗瓷大海碗
-
1.7.21农场趣事
-
1.7.21.1水压碱
-
1.7.21.2堵决口
-
1.7.21.3牵牲口
-
1.7.21.4插苇子
-
1.7.22米心肉
-
1.7.23我在农村“战备”的岁月
-
1.7.23.1听战备动员 搞战备宣传
-
1.7.23.2强渡芦坑 奔袭韩城
-
1.7.23.3挖防空洞 打大口井
-
1.8代跋 知青——我们有同一个姓名
-
1.9后记
1
我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