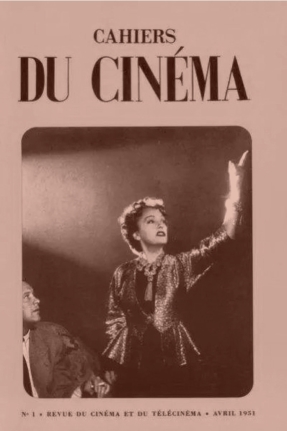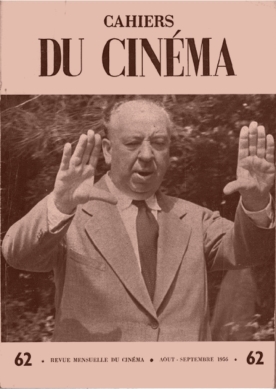-
1.1目录
-
1.2拉斯·冯·提尔 没有他,戛纳就不热闹
-
1.3小津安二郎 这个鬼子差点娶了个艺伎
-
1.4李天济 他被上官云珠单独传艺,又写出了中国电影最闷骚的剧本
-
1.5埃尼奥·莫里康内 没有他,西西里就没有美丽传说
-
1.6昆汀·塔伦蒂诺 只要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就一定会再次败给他
-
1.7马龙·白兰度 二十个私生子、两尊小金人、一场谋杀案,串起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
1.8谢尔盖·帕拉杰诺夫 他只拍了四部长片,就被认为难以超越
-
1.9王羽 “独臂刀王”的江湖往事
-
1.10莱妮·里芬施塔尔 长寿对她而言就是苦役
-
1.11莱奥·卡拉克斯 直接把黑帮金库拍“爆”了的小个子
-
1.12田中绢代 每次脆弱茫然,我都会想起她的奋争
-
1.13哈维·韦恩斯坦 又一个大佬倒在了道德的枪口下
-
1.14赵丹 他是第一个在银幕上骂“册那”的电影巨星
-
1.15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过去他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他是中国文青的偶像
-
1.16让娜·莫罗 她在银幕上创造了最著名的三角恋
-
1.17泰伦斯·马力克 他二十年没拍电影,一出手就是一座“金熊”
-
1.18杨延晋 风流才子情债高筑
-
1.19吉尔莫·德尔·托罗 他在洛杉矶郊外有一座黑暗庄园
-
1.20奥逊·威尔斯 第一次拍电影,电影公司就让他随便拍
-
1.21英格丽·褒曼 地下情重创银幕形象,她一度被好莱坞除名
-
1.22大卫·欧·塞尔兹尼克 没有他,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成色减半
-
1.23是枝裕和 影迷做着做着就拿了威尼斯大奖
-
1.24杨德昌 他可以十年没有性生活
-
1.25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他吸毒滥交家暴,我们却用电影节向他致敬
-
1.26德里克·贾曼 77分钟全屏蓝色是他临死的至善之言
-
1.27徐枫 她是胡金铨的女侠,也是张国荣的贵人
-
1.28约翰·巴里 他曾经丢弃了怀孕中的妻子,最终找回了生命的宁静
-
1.29詹姆斯·卡梅隆 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只有他敢说自己是世界之王
-
1.30马克·穆勒 他究竟是中国电影的恩人还是恶人
-
1.31邹文怀 小弟叛变,自立门户,两巨头香江厮杀半生
-
1.32克里斯托弗·诺兰 说他是大师,好像还早了点
-
1.33霍伊特·范·霍特玛 他就是诺兰离不开的新欢
-
1.34阿尔·帕西诺 二十六岁还在做保安,五年后他被提名奥斯卡
-
1.35克劳斯·金斯基 他是银幕上的魔鬼,也是生活中的魔鬼
-
1.36科恩兄弟 求求他们,千万不要变成姐妹
-
1.37冯小刚 这回他是在演戏吗
-
1.38让-吕克·戈达尔 电影史因他分成了上下两册
-
1.39艾曼努尔·卢贝兹基 他用镜头玩死影迷
-
1.40英格玛·伯格曼 他总能把痛恨他的女人拉回来拍电影
-
1.41李翰祥 他庄可为历史存照,谐可作风月宝鉴
-
1.42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早年拿奥斯卡,晚年酿葡萄酒,他一直是我们的榜样
-
1.43路易斯·布努埃尔 他就像黄梅天,让资产阶级发霉
-
1.44李屏宾 他是铁汉,却有柔情
-
1.45罗曼·波兰斯基 女人比李小龙对他更有效
-
1.46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他是意大利最离经叛道的导演
-
1.47加斯帕·诺 你怎么能把他看成是个A片导演
-
1.48拉夫·迪亚兹 看他的电影,你要准备面包、水和靠枕
-
1.49斯坦利·库布里克 他是电影大师,也是猫和狗的勤务兵
-
1.50安德烈·巴赞 他没有拍过一部电影,却影响了世界电影的发展
-
1.51代跋 《世界影史50名人传奇》诞生记
1
世界影史50名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