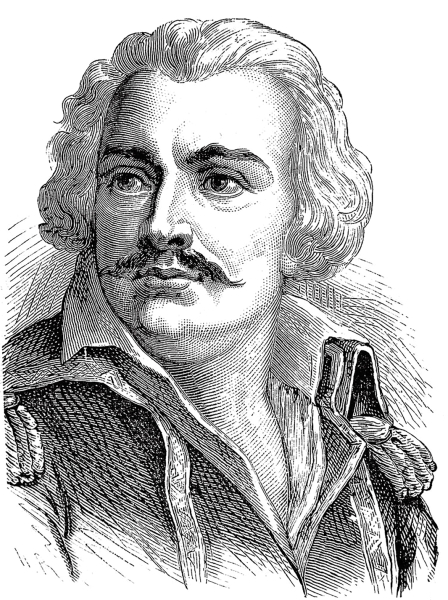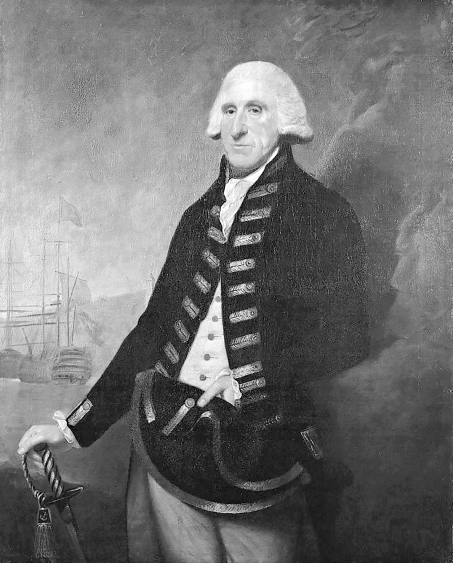第14章 土伦平叛(1793 年9 月——1794 年3 月)

精彩看点
拿破仑·波拿巴回军团——《博凯尔的晚餐》公费出版——错误的指控——土伦围城——土伦司令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拿破仑·波拿巴担任炮兵指挥官——新司令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穆尔格雷夫要塞争夺——法朗山——土伦城陷——腥风血雨——拿破仑·波拿巴不赞成屠杀——拿破仑·波拿巴开始变冷漠——围城轶事一则——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初见拿破仑·波拿巴——让-保罗·马拉之喻——盛宴庆功——结识让-安多什·朱诺——不实的指控——拿破仑·波拿巴晋升为准将——卢西恩·波拿巴又出场——拿破仑·波拿巴否认指控——出逃——交好国民公会代表——受到部下爱戴——加入自己不愿加入的小团体
1793年6月中旬,拿破仑·波拿巴重返军队。军队有一部分部队驻扎在意大利边境,于是,拿破仑·波拿巴随军来到尼斯。拿破仑·波拿巴的职责是监管海岸上的弹药武器。当时,大不列颠舰队已开到地中海,面向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虎视眈眈。法军很有必要在海岸布好炮阵。拿破仑·波拿巴结束了在阿维尼翁协助守城的任务,刚回到军队,就向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托马斯-奥古斯丁·德·加斯帕兰和其他随军来到普罗旺斯镇压叛乱的议员们展示了自己写的宣传册《博凯尔的晚餐》。众人看过之后啧啧称赞,并用财政部的公款帮拿破仑·波拿巴联系印刷发行。1793年8月,《博凯尔的晚餐》由阿维尼翁的《日报》正式发行。根据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1]的叙述,拿破仑·波拿巴将用于印刷册的费用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应付印刷商的钱一直拖欠着,直到后来拿破仑·波拿巴当上皇帝,印刷商的遗孀才不得不将债务一笔勾销。[2]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的这一记叙是否可信。

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
在托马斯-奥古斯丁·德·加斯帕兰和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这两座靠山的庇护下,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兄弟们都跟着沾到了光,连舅舅约瑟夫·费什都脱下了教袍,穿上军装,去阿尔卑斯军团军需部就职了。卢西恩·波拿巴在圣马克西曼领到了类似的美差。约瑟夫·波拿巴任马赛一级国防委员,待遇更丰厚。事实上,依据法规,国防委员这样的职位只能由军人担任,而且军衔必须在中校以上。根据这一条件,波拿巴全家没有一个人符合任职条件。但这点小事算什么困难?对波拿巴家族来说,开一张军人身份的证明还不是小菜一碟?拿破仑·波拿巴将自己任科西嘉岛中校的证件给约瑟夫·波拿巴用,约瑟夫·波拿巴便立刻上任,简单到连名字都不用改。别忘了,他们兄弟二人连出生日期都可以交换使用。受洗的登记簿上,他们的名字都是“拿布里奥尼”,对吗?[3]
十年后,拿破仑·波拿巴有意擢升约瑟夫·波拿巴为上校时,毫无愧色地写了以下的证明。我们来看看没有一天从军经历的约瑟夫·波拿巴是怎么在军中“服役”的:
1768年,炮兵学员。
1792年,参谋。
1793年,营队副官。
1796年,即共和五年,立法军团成员。
第四防线军团上校。
1793年至1794年间,参加战役,于土伦战役中受轻伤。
上述每条证明都是假的。在炮兵学校学习的是拿破仑·波拿巴,不是约瑟夫·波拿巴。约瑟夫·波拿巴也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副官,甚至没有一天的从军履历。1792年,约瑟夫·波拿巴在倒卖石油,之后便一直担任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的秘书。土伦战役中,约瑟夫·波拿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受轻伤的当然也只能是拿破仑·波拿巴。倘若有人细查约瑟夫·波拿巴的“从军经历”,只要出示受洗证明就可以反驳,追查的人也会信以为真。为受洗证书弄个副本也不是什么难事。
在马赛时,约瑟夫·波拿巴结识了商人弗朗西斯·克拉里,两人关系很好。约瑟夫·波拿巴和拿破仑·波拿巴初到马赛时就住在弗朗西斯·克拉里的家中。弗朗西斯·克拉里有两个女儿,玛丽·朱莉·克拉里和伯纳丁·欧仁妮·德西雷·克拉里。两个女儿后来都成为王后。大女儿玛丽·朱莉·克拉里嫁给了约瑟夫·波拿巴,小女儿伯纳丁·欧仁妮·德西雷·克拉里则嫁给了让-巴蒂斯特·朱尔·贝纳多特[4]。

玛丽·朱莉·克拉里与女儿泽奈德·波拿巴

伯纳丁·欧仁妮·德西雷·克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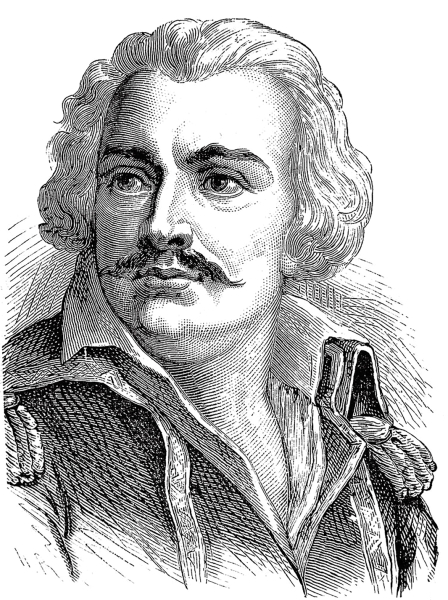
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
军队如汹涌的浪潮般向土伦袭来。这支军队中不仅有国民公会革命军,还混有极端主义分子。军队声势浩荡,士兵冷血疯狂。1793年10月9日,他们刚刚平息了里昂的保王党叛乱。将里昂的保王党屠戮殆尽后,趁手上血迹未干,这支军队便马不停蹄地奔向下一个保王党的汇集地——土伦。军队司令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指挥革命军来到土伦城外。土伦城城门紧闭。与大不列颠人勾结的保王党宁可暗中向大不列颠海军敞开港口,也决不会放革命军进城。城内几乎已成为叛党的世界,充斥着来自马赛、里昂等地的逃亡者。立宪派、温和派、反动派、保王党,各路政治派别遍布城中。可想而知,护守堡垒的卫军成分也相当复杂,有撒丁人、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对革命和共和的仇恨将他们凝结在了一起。革命军兵分两路,沿着俯瞰土伦城的法隆山分道而行。法隆山以西是圣安托万堡,圣安托万堡再往西便是奥利乌尔。奥利乌尔是土伦附近的一个市镇,西路军司令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将指挥部设在奥利乌尔。东路军的部队大都是意大利军团,还有一部分来自里昂的志愿军。一小部分来自马赛的极端分子也混迹在东路军中。他们凶狠残暴,只等攻陷土伦城后进城烧杀抢掠。
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根本不懂军事。他准备炮轰英格兰舰队,于是命令士兵架起大炮。但他做事非常谨慎,担心敌方的炮火打到自己,于是进行了精细的计算,将大炮架设在英军炮火的射程之外。这样做的唯一问题是,他自己的火力也打不到英军。[5]

围攻土伦

拿破仑·波拿巴在土伦战场
1793年9月,攻城正式开始。直到1793年10月,革命军都没能成功攻下土伦城。革命军指挥官身后,还有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如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安托万·路易·阿尔比特、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和托马斯-奥古斯丁·德·加斯帕兰。他们前来土伦督战,但他们和曾经是画家的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一样,并不懂得统兵打仗。无论是指挥军队,还是运送军需物资,他们都毫无章法。必不可少的急需物资总是断供,连军粮都渐难支应。指挥小组中的诸位特派员,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指挥没有任何问题,同时觉得其他人的指挥永远都会出错。
在如此混乱的指挥中,拿破仑·波拿巴抵达土伦。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向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介绍了炮兵军官拿破仑·波拿巴。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如获至宝,当即任命拿破仑·波拿巴在炮兵岗位上就职。拿破仑·波拿巴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军将大炮架得太远,根本打不到英格兰舰船。此等“专家意见”使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心悦诚服,他觉得拿破仑·波拿巴来得正是时候。

让·弗朗西斯·科尔尼·德·拉波普

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
正当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在浪费炮弹,炮轰远离联军要塞的海面时,让·弗朗西斯·科尔尼·德·拉波普率领东路军,在特派员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和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6]的监察下,已取得大捷。东路军首先攻下了法隆山地,但很快被联军夺回。即便如此,让·弗朗西斯·科尔尼·德·拉波普带领的军队也算表现不俗。他们占领了拉马尔格堡前面的战壕。拉马尔格堡扼住土伦港一角,勒吉耶蒂要塞扼住土伦港另一角。拉马尔格堡和勒吉耶蒂要塞只要攻得其一,便可一举占领整个土伦港。
国民公会的特派员终于明白,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并不适合指挥作战。于是,他们将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撤职,任命弗朗西斯·阿梅代·多佩特为革命军总司令。弗朗西斯·阿梅代·多佩特过去是一位医生,在指挥作战方面并不比做过画家的让·巴蒂斯特·弗朗西斯·卡尔托更在行。1793年9月26日,弗朗西斯·阿梅代·多佩特接到委任状,担任革命军总司令。但还不到一个月,他也被撤职了。医生和画家都不是打仗的材料。接任弗朗西斯·阿梅代·多佩特的是风烛残年的老将军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1793年11月25日,战时委员会召开。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让·弗朗西斯·里科尔、奥古斯丁·邦·约瑟夫·德·罗伯斯庇尔、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和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出席会议,诸位委员一致同意拿破仑·波拿巴出任革命军炮兵指挥官。

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

1793 年11 月的土伦战场
革命军总司令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很快发觉自己是个傀儡。他想执行任何作战计划,都要先向战时委员会委员请示,还要向他们论证该计划为何可行。战时委员会命令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全力攻城。但全力攻城需要六万兵力,而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手中只有不到两万五千人。因此,全力攻城不可行。如果将战线拉得过长,会为联军反攻留下空当。联军一旦反攻,打退革命军简直易如反掌。任何略懂军事的人都可以依据常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即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但依据经验,无论任务有多困难,有多不可能实现,都要尽力达成——联军不好对付,战时委员会也能得罪。违抗委员们的命令,下场只会更惨。革命军只得努力达成目标,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否则,结局一定惨不忍睹。

拿破仑·波拿巴将自己的作战观点写成请愿书,递交到国防部。国防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批准了拿破仑·波拿巴的作战计划,并授予他执行该计划的全部权限。
与此同时,拿破仑·波拿巴也绞尽脑汁,对军需供给的管理进行了梳理。他从马赛、里昂和格勒诺布尔搜集各式火炮、弹药。大战当前,这些补给都必不可少。拿破仑·波拿巴以卓越的行动力重新整合了所有资源。跟他有过接触的将士都受他影响颇深。拿破仑·波拿巴用行动力建立了威信。事实上,大家已经将他当成第一指挥官了。

马尔格雷夫伯爵亨利·菲普斯
按照拿破仑·波拿巴的部署,革命军全体围城部队向英军驻守的勒吉耶蒂要塞发起猛烈炮攻。英军驻军在司令官马尔格雷夫伯爵亨利·菲普斯[7]的率领下顽强抵抗。1793年11月17日,革命军在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将军的指挥下发动突袭,想将要塞一举攻下,但最终未能成功。革命军只得暂时退兵。但没过多久,革命军得到了援军补充,于是再次发动进攻,打败了守军中力量较弱的西班牙部队,从西班牙部队的防线上撕了一个口子,冲入要塞。于是,革命军内外夹击,侧面攻击英军,彻底摧毁了英军防线。在此次战斗中,英军死亡人数达三百人。
革命军占领勒吉耶蒂要塞后,联军很难继续维持局面,只得放弃土伦城的外围防御。英明的英军司令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于是联军趁着夜色,悄悄从海角撤回土伦城内。
同时,拿破仑·波拿巴亲自指挥了一次进攻,拿下了法隆高地,并在高地上升起三色旗。
革命军面临的形势依旧险峻。反法联盟在城内仍拥有一万驻军,几个城防堡垒也都被联军牢牢地把控着。不过,已经占领了勒吉耶蒂要塞和法隆高地的革命军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土伦港已进入革命军炮火打击的范围。英军中队指挥官塞缪尔·胡德向联军强烈呼吁,这个海岬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是两军必争之地,一定要将它从革命军手里夺回。但联军总指挥安贝尔男爵一心撤离,没有同意塞缪尔·胡德的这一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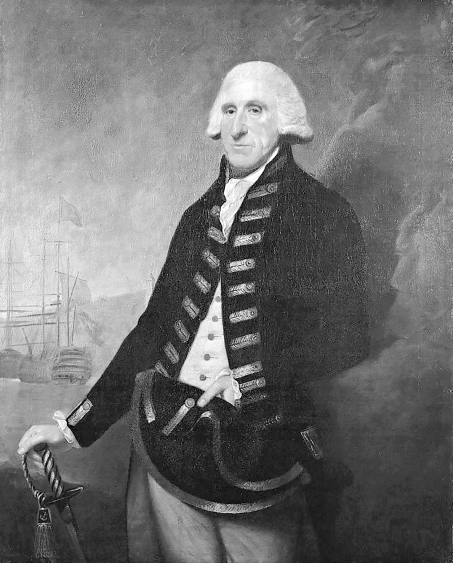
塞缪尔·胡德

土伦人逃离土伦
得知联军要撤走,土伦城内的人慌乱如麻。保王党对革命党的辣手无情再清楚不过。他们一旦落入革命军手中,会有怎样的下场,真是想都不敢想。因此,联军撤退时,码头上一片哀号。土伦人不分男女,都惊恐地挤在码头,哭天抢地,要求和联军一起登船离开。正在此时,拿破仑·波拿巴下令开炮。只见炮台上炮火纷飞,人群四散。有时炮弹打偏,人群还来不及散开,就被炮弹砸中。土伦人跳上一艘艘小船,将小船填满,希望跟着联军的大船一起逃走。海港里停着几艘联军缴获的法军大船,此时成了土伦人的救命稻草。最终,一万四千人由小船换上大船并成功逃走。拿破仑·波拿巴看到土伦人借小船准备逃离时,立即下令,将革命军的枪炮对准满载土伦人的小船。有一些小船就此沉没。船上的人多半是保王党,他们就这样手无寸铁地葬身海底——带着对新政权深深的不满和对旧制度的深切怀念。
1793年11月18日,土伦城内也一片大乱。监狱里的囚犯趁机引发暴乱,越狱后冲入土伦人的房舍,挨家挨户地掠夺一空,然后纵火离去。绝大多数土伦人已经弃房逃走,未来得及离开的,便成了暴徒手下的冤魂。
1793年11月19日,革命军进驻土伦城,标志土伦收复成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数百名未及逃离的保王党人全部被带到旷野。他们未经审判便被执行死刑。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大喜过望道:“土伦城中大火熊熊,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成功逃走的人应该庆幸,因为留在城里的人都难逃一死。我们要用他们的鲜血祭奠我们战死的勇士。”[8]约瑟夫·富歇[9]从里昂匆匆赶来,目睹了这一幕。他致信身在巴黎的让-玛利·科洛·德赫布瓦[10]道:“再见了我的朋友。喜悦的泪水从我的双颊滚落,像河水一样,汩汩地流过我的灵魂。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庆祝胜利,那就是今夜的枪声。今夜,二百一十三名叛乱分子将在枪声中死去。”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说:“要狠一点。断头台总要有人上。如果我不送别人上去,别人就要送我上去。”另外还有人被错杀。平乱成功的革命军杀红了眼,将城内的二百多雅各宾派成员一起杀了。真是大错特错啊,雅各宾派成员其实是前去欢迎革命军进城的。
一连数日,“流剑飞闸”日日上演。人们不是做了刀下鬼,就是成了无头尸。革命军已经进驻土伦城。不戴标志雅各宾派身份的红帽子,就是在找死。然而,国民公会从来“明察秋毫”。戴着红帽子的人不见得真是雅各宾派成员。因此,在让·安托万·巴里埃[11]的“英明”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并公布了法令:作为滋生叛乱的罪恶之城,土伦理应寸草不生!于是,一个新的委员会得以成立,由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和奥古斯丁·邦·约瑟夫·德·罗伯斯庇尔组成,势将清洗进行到底。在这样的时期,有钱也买不到命。一位八十四岁的老商人捐出了所有财产,只留给自己八十万里弗尔养老,但正是这八十万里弗尔让他命丧绞架。法官一直在觊觎这八十万里弗尔,索性给这位老商人判了死刑。如此一来,老商人连八十万里弗尔也不能留给自己。

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埃塞·德·马尔蒙
后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时回忆:“我看到这位老先生被绞死时,觉得那真是世界的末日,人性的荒原。”
据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埃塞·德·马尔蒙[12]说,拿破仑·波拿巴极其反感随便处死人的暴行,因此,拿破仑·波拿巴救出了一些人。这个说法倒符合拿破仑·波拿巴的个性。他本质上并不是嗜血的杀人狂,并且非常反感无谓的杀戮。拿破仑·波拿巴认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必要大开杀戒。在达成目标的前提下,他乐得表现出更大方、更宽仁的一面。可惜的是,拿破仑·波拿巴心中很清楚,他正在与恶狼为伍。恶狼吃人嗜血,他自然无法不同流合污。在《博凯尔的晚餐》中,拿破仑·波拿巴下定决心,对国民公会的滥杀行为表达了深深的抵触。在“深深抵触”和“深恶痛绝”之间,是他在普罗旺斯受到的震撼。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的夫人回忆了一桩轶事。从这件轶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拿破仑·波拿巴的心已如枯井一般干涸、麻木。这件事是这样的:
那是1795年5月,我们第二次从德意志回来后不久。有一天,我们遇见了拿破仑·波拿巴。我记得就在几天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残忍的经历,令人不寒而栗。我对这样的叙述憎恶极了,因此未及听完整个故事,我就开始讨厌他。拿破仑·波拿巴讲的是他去土伦之前,还在炮兵部队当指挥官的时候。有一天,有位女子来到军营,那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手下一位军官的妻子,他们正值新婚燕尔。几天后,军队接到攻城的命令,这位军官也要奉命前去。军官的新婚妻子找到拿破仑·波拿巴,泪水涟涟,苦苦哀求拿破仑·波拿巴为她的丈夫批准一天的假期。拿破仑·波拿巴冷酷地拒绝了这位女士。甚至他自己都觉得,他不仅冷酷,还近乎野蛮。拿破仑·波拿巴亲口告诉我们,当进攻来临时,这位军官,这位真正的勇士——拿破仑·波拿巴对这一点非常确信——似乎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在这场战役中战死,面色苍白,浑身颤抖。这位军官在拿破仑·波拿巴身边随行。忽然,城内守军向外密集开炮,拿破仑·波拿巴向他大声喊:“小心!有炮弹。”这位军官还没来得及躲开,就被炮弹扑倒在地,生生被炸成了两截。拿破仑·波拿巴一边描述这些恐怖的细节,一边邪恶地大笑起来。
拿破仑·波拿巴按规矩行事,决不会被一个女人的眼泪左右。但他讲述整件事情时的冷漠态度令人毛骨悚然。拿破仑·波拿巴并非天生暴虐的人,但从这件事情看,他也算够冷血了。[13]
收复土伦期间,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与拿破仑·波拿巴相识。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初次见到拿破仑·波拿巴时,拿破仑·波拿巴正在胳膊底下夹着一沓《博凯尔的晚餐》小册子,向周围的军官和士兵分发。
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拿破仑·波拿巴的行为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尽职尽责,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患难中易见真情,我们惺惺相惜。于公于私,他的所有要求我都全力支持……很快,我们开始一起讨论时局问题,而他总是站在我的角度上赞同我的观点。世人多亲善,人们总喜欢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的人,甚至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赞赏。拿破仑·波拿巴便是这样内心强大的人,他的灵魂比肉体更挺拔,更美丽。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位年轻的炮兵中尉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强大的灵魂。当然,我不是危言耸听,也没有神化他的意思。在他身上展现的不仅有英勇、无畏,还有思想的跳跃、震颤和升华。这个小个子军官的身体里有一种悸动,那是灵魂永恒的思考。在我看来,拿破仑·波拿巴和另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位革命者堪称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他像流星一般掠过革命时代的舞台。那个人就是让-保罗·马拉。”[14]

让-保罗·马拉
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并不是说拿破仑·波拿巴和让-保罗·马拉的外貌有什么相似之处,而是说他们拥有相同的心和坚毅的品质,他们是一样的人。
收复土伦期间,忙碌的断头台下是举行欢宴的好地方。革命党的领袖和各位公民代表在此相聚。共同前来庆祝的还有城内的共和党和厨师们。[15]士兵、爱国者和无套裤汉也济济一堂。但几位特派员似乎无意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冷漠地坐在较远处的一张桌子前。

让-安多什·朱诺
在土伦平叛的事件中,拿破仑·波拿巴还有另一份收获——他寻觅到了一份珍贵的、至死不渝的友谊。这个友人就是让-安多什·朱诺。让-安多什·朱诺那时还很年轻,是个掷弹兵。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在土伦平叛期间与他结识的。
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攻势猛烈,拿破仑·波拿巴要发派一个重要口令,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记录,因为他的书写观感实在太差。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让-安多什·朱诺出场了。他一边听拿破仑·波拿巴口述,一边做笔记。这时,一颗子弹射到他身边,扬起厚厚的尘烟,两个人都是一身尘土。
让-安多什·朱诺说:“这太棒了,长官。我好久没见过飞扬的尘沙了。”
拿破仑·波拿巴说:“你挺勇敢的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让-安多什·朱诺回复道:“我想当军官,长官。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让-安多什·朱诺遇到了伯乐。拿破仑·波拿巴闻言,立即提拔他做了军士长。不久后,让-安多什·朱诺得到了委任状。1796年,让-安多什·朱诺晋升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侍卫官,后来受封为阿布兰特什公爵。让-安多什·朱诺金发碧眼,性情温和。他出身行伍,遇到拿破仑·波拿巴后青云直上。他后来娶了德·佩尔蒙家的小姐劳雷-阿德莱德-康斯坦茨·佩尔蒙。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要诚挚地感谢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劳雷·朱诺的回忆录。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我们得以将拿破仑·波拿巴的早期时代了解得更清晰透彻。
土伦战役中,拿破仑·波拿巴人中之龙的雏态初现。雅克·弗朗西斯·迪戈米耶将军在一封信中报告:“这位年轻军官的态度举足轻重。他支持哪一边,天平就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赢。
为了嘉奖拿破仑·波拿巴的英勇,1794年2月16日,拿破仑·波拿巴荣升准将。
拿破仑·波拿巴就任准将前,免不了要例行公事,做个人背景调查。为了应付调查,之前改过日期的受洗记录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拿破仑·波拿巴成功地把年龄改为二十五岁。这个年龄对应1768年在科尔特的出生证明,而不是1769年在阿雅克肖的那一份。拿破仑·波拿巴登记的出身是“非贵族”,也就是说,他不是贵族出身。他想得很清楚,现在科西嘉全岛暴动不休,想查询一份出生证明几乎不可能。鉴于时局更迭,也不会有任何军事机构仔细调查。况且只有十五岁零五个月的路易·波拿巴也在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的手下升任了炮兵副少校。拿破仑·波拿巴让路易·波拿巴冒用同事的假名才得以入伍。当然,这件事一定要瞒着那位同事。可未曾想,炮兵部门竟然坚持原则,以“违反常规”为由拒绝批准。最终,路易·波拿巴只好折中,选择去沙隆的军校读书。炮兵兵部的原话是:“他不符合条件,没有继续留任炮兵军团的资格。”后来,路易·波拿巴同他的几位兄长一样,假装有从军经历,假装曾经在战争中负伤。这真是波拿巴家族的光荣传统啊!正如荣格上校所言,波拿巴家族的座右铭就是“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是为了家人”。

克里斯蒂娜·博耶
当时,卢西恩·波拿巴在圣马克西曼,负责搜集军需物资。如此狡诈的人在做公事的时候当然不会忘记从中分一杯羹,自然也不会忘记将自己的名字改得更高大。他现在的名字是卢西恩-布吕蒂斯·波拿巴。[16]现在,卢西恩-布吕蒂斯·波拿巴正与小酒馆老板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博耶陷入热恋,后来他们结婚了。舅舅约瑟夫·费什,这位未来的大主教,此刻还一心扑在工作上,想着如何能算清楚军需物资的账目。他在这个时期打交道的对象都是面粉、豌豆之类的。埃利萨·波拿巴已长大成人,是一个翩翩少女。波莱恩·波拿巴也快十四岁,卡罗琳·波拿巴十二岁,热罗姆·波拿巴只有九岁。
拿破仑·波拿巴负责南部海岸防御。有一次,他在查探地形的时候,遇到一处非常险峻的地方,拿破仑·波拿巴差点丢了性命,于是他便记录下了这一句话:“塔尔皮亚岩石危险陡峭。”
拿破仑·波拿巴初到马赛,就能凭借军人的敏锐洞察力,一眼看出优势所在,知道哪些地方还需要加固加强。1794年1月4日,拿破仑·波拿巴致信国防部,说他要重新装备大炮,重建城防工事。这个计划在马赛引起了一番热议。大家一致表示抗议:“巴士底狱刚刚摧毁几天,现在又要在此重建吗?为什么要修建炮台?是想将炮弹射向守法的公民吗?”
国民公会将拿破仑·波拿巴和让·弗朗西斯·科尔尼·德·拉波普将军召回公审,让他们二人对此事给个说法。让·弗朗西斯·科尔尼·德·拉波普将军老老实实地回去了,拿破仑·波拿巴则逃到土伦,在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的保护下躲了起来。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公开为拿破仑·波拿巴辩护。在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的帮助下,这场风波没有损伤拿破仑·波拿巴一丝一毫。
土伦是拿破仑·波拿巴事业开始的地方。在土伦,拿破仑·波拿巴第一次有机会展现出与生俱来的军事天才。他在土伦崭露头角,最终大放异彩,赢得了他人的赞誉和尊重。后来,那么多人甘愿为拿破仑·波拿巴效力、誓死追随,这一切都源于土伦战役中拿破仑·波拿巴展现出来的天才。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个来自孤岛的青年,是一个异乡人。他甚至不能算是法兰西人因为他法语说得并不地道,书写的文法也一塌糊涂。拿破仑·波拿巴和土伦、法兰西人没有血缘关系,他的家人在法兰西也只是领取津贴的寓客。拿破仑·波拿巴知道,他要一展雄才干出一番伟大辉煌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只有坚忍,绝不能虚弱;他要控制情绪,绝不能再乱发脾气;他要放弃尊严,要谄媚当权的政客。这些都是必需的。
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讲述了拿破仑·波拿巴献媚的故事。拿破仑·波拿巴向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和其他委员深深鞠躬,“几乎是屈膝到地”。拿破仑·波拿巴还“向委员让·弗朗西斯·里科尔的夫人献殷勤。他服侍周到,无微不至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他会捡起让·弗朗西斯·里科尔的夫人掉落地上的手套,给她递上扇子。她上马时,拿破仑·波拿巴帮她拉着马辔、扶好马镫。陪她散步的时候,拿破仑·波拿巴会帮她拿好帽子,非常绅士”。[17]
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是,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虽然城府老道,但确实有智慧和才能。拿破仑·波拿巴拼命取悦和讨好大权在握的委员们,比如奥古斯丁·邦·约瑟夫·德·罗伯斯庇尔——刚刚问鼎权力巅峰的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西斯·玛利·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18]的弟弟、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在督政府一言九鼎、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雾月政变和葡月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正如麦考利对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的称呼一般,这个“雅各宾毒瘤”有能力在督政府终身任期的职位上执掌大权。对于拿破仑·波拿巴来说,取得这些政坛领袖的信任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获得年轻官兵们的热爱和崇拜。拿破仑·波拿巴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当时的法兰西庸才泛世,拿破仑·波拿巴能够保持清醒,清楚地知晓自己心之所向、志之所存,还知道应该如何出手才能谋到权力,这在懵懂的世人中也算得上奇才。拿破仑·波拿巴能够轻而易举地迷倒他愿意结识的人。他的博才多学令众人惊服。他宅心仁厚、笑语甜美——这些性格都能为他赢得人心。他是科西嘉岛的流亡贵族,家里的房子都被烧毁。他的名字和马泰奥·布塔福科同出同现,一定有与马泰奥·布塔福科类似的人品。他渴望交朋结友,在寻觅友情的过程中抑制了性格中尖锐的部分,发挥出所有魅力来慑服人心。拥护拿破仑·波拿巴的年轻官兵大都前途不凡。他们对拿破仑·波拿巴忠心耿耿,并狂热地尊崇他。官兵们众星捧月般地汇聚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周围。
从记述拿破仑·波拿巴性格发展的角度,土伦之战也可谓墨彩千秋。自童年以来所有郁结于心的伤怀、失望和人生的悲怨自此一扫而光。土伦是拿破仑·波拿巴走向新生的起点。土伦的意义不止于此。经历过土伦平叛的拿破仑·波拿巴已经威严赫赫。他学会了使用共和派的词汇和理念为自己的辩论打开道路。尽管在内心深处,他早已失去对共和的信仰。“俱乐部演讲”一旦付诸实施,不知又会让多少人失去生命。
一直以来,拿破仑·波拿巴都在勉力地谋取家乡科西嘉岛的福祉,为科西嘉岛的独立大业努力奔走。只有当他意识到科西嘉岛的独立是一场梦幻,并不可能实现时,他才转变了立场,投向了他曾激烈反对和抵抗的法兰西人的怀抱。而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科西嘉岛很有可能步土伦、里昂、阿维尼翁和马赛的后尘。这些地方发生的血腥平叛事件随时可能在科西嘉岛上演。拿破仑·波拿巴并没有选择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才干都赋予保卫科西嘉岛的大业。他选择投靠法兰西人,效忠自己民族的敌人。他做出如此选择的时候,也将自己曾经深爱的故乡放在砧板上,等待法兰西人的宰杀。
看起来,拿破仑·波拿巴的早期生涯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三次蜕变,每蜕变一次,拿破仑·波拿巴就离道德远一些,他的真心和真情也就淡漠了几分。在第一个阶段,拿破仑·波拿巴还是一个少年。他有真诚的梦想,有与生俱来的远大志向。他青涩的热望还没有化作日后不灭的野心,没有如后来一般,只剩下冷漠和苍凉。后来的他,背弃了巴斯夸·帕欧里,忘记了军职,甚至将家乡从心上抹去。他将这一切当作负担,统统丢弃。在第二个阶段,拿破仑·波拿巴失去了远大的志向,只剩私利的追逐。他遗忘了奋斗的热情,只留下腹黑和阴谋。但他还有仅存的信仰,那是一丝道义。他渴望成功,还留有一丝敬意。然而,追求越高尚,现实就越显绝情。拿破仑·波拿巴理智的人格告诉他,一些政策非常不合情理,依据这些政策根本不会成功。但他投机的人格也会说,要抓住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哪怕泯灭真心、背叛真情。在第三个阶段,拿破仑·波拿巴经历了人生中痛苦的背叛。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抛却了正义、辜负了真诚,但更痛苦的是他背弃了理想、远离了正道。
现在,拿破仑·波拿巴已经不再相信革命的原则。他决意以刀剑开路,维护现存的政权。从剑锋上滴下的都是无辜的鲜血。从人性方面来说,拿破仑·波拿巴并非滥杀无辜的恶徒。他反感滥杀,认为无意义的滥杀是严酷的错误,堪比罪行。他不想犯错,却不得不犯;他不想杀人,却不得不杀。当拿破仑·波拿巴在码头上用炮弹封死叛军的最后一条出路;当满载妇孺的小船在炮击中永远沉入大海,再也不会绕过勒吉耶蒂海峡,靠近英军的大船;当拿破仑·波拿巴敞开土伦城的大门,迎接国民公会委员入城,却丝毫不考虑随后的腥风血雨,不考虑会有多少人死在弹雨之中,殒命断头台上时,拿破仑·波拿巴依然笑立着、谄媚着,恭敬地脱帽致礼,殷切地与国民公会委员同席就餐——冷酷的时代麻木了冷酷的心。英雄齐格弗里德[19]杀死恶龙后,将自己浸在龙血中,他的身上生长出一个个龙角,从此刀剑不入。同样,土伦战役中死去的人,他们的鲜血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心灵飘荡过的地方,自此之后,寸草不生。
经历过战争的人会老得很快。在土伦战役后不算太久的一天,拿破仑·波拿巴感慨道:“历经战事,果然容易衰老啊。”其实,他没有说出口的是:“失去道义的心灵,早已是一片荒芜。”
【注释】
[1]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Paul François Jean Nicolas,vicomte de Barras,1755——1829),出身普罗旺斯贵族。支持法国大革命,参加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当选国民公会议员。成立督政府后,为督政官之首。是督政府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雾月政变后权势被削弱,后被逐出巴黎。拿破仑·波拿巴当政期间不得志。1815年隐退。著有回忆录。
[2]参见《保罗·巴拉斯回忆录》(英译版),1895年,第1卷,第143页。——原注
[3]任命书上说:“各位人民委员……鉴于南部王党叛乱益重,部队急需军官前去平乱(原文如此),擢升陆军中校约瑟夫·波拿巴为一级国防委员。”当时是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签字同意的。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明知约瑟夫·波拿巴没有从军经历,却对波拿巴兄弟造假一事只字不提。——原注
[4]让-巴蒂斯特·朱尔·贝尔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1763——1844),1804年封法兰西元帅。1810年选为瑞典王储。1818年以卡尔十四世·约翰(Karl XIV Johan)和卡尔三世·约翰(Karl III Johan)的名号加冕瑞典国王与挪威国王。1844年在位时去世。妻子为伯纳丁·欧仁妮·德西雷·克拉里,相传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初恋情人。
[5]“卡尔托夫人随军至此。她为人矫揉造作,待人颐指气使。平日大肆参与政务,目前指挥作战。据不止一位军中人士的明述……当日如此不堪的命令实际出自卡尔托夫人。且不知是过于狂傲还是纯属无知,她竟然在军令上签署了‘卡尔托夫人。’”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保罗·巴拉斯回忆录》,第1卷,第143页。——原注
[6]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Stanislas Freron,1754——1802),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曾与拿破仑·波拿巴的二妹波莱恩·波拿巴有过恋情。当时,路易-玛利·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隆已过不惑之年,波莱恩·波拿巴仅十五岁。
[7]马尔格雷夫伯爵亨利·菲普斯(Henry Phipps,Earl of Mulgrave,1755——1831),英国将军,在法土伦战役期间,马尔格雷夫伯爵亨利·菲普斯曾短期接管英军在土伦的军队。
[8]参见共和二年雪月五日,即1793年12月25日《通报》,《圣诞欢庆——来自推翻了国王的革命者》。——原注
[9]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59——1820),1799年任公安部长,雾月政变中支持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第一帝国警务大臣,负责建立了法兰西警察组织。1807年后阴谋反对拿破仑·波拿巴。1809年受封奥特朗特公爵。拿破仑·波拿巴倒台后,受路易十八冷遇。拿破仑·波拿巴百日统治期间,再度出任公安部长。滑铁卢战役后,劝拿破仑·波拿巴同意第二次退位。后在路易十八朝廷不受重用。1816年后流亡。
[10]让-玛利·科洛·德赫布瓦(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1749——1796),法兰西演员、戏剧家、散文家和革命家。
[11]让·安托万·巴里埃(Jean Antoine Barrière,1752——1836),法兰西政治家,“五百人议会”成员。
[12]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埃塞·德·马尔蒙(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Viesse de Marmont,1774——1852),1793年升上尉。在土伦战役中与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挚友。1805年升上将。1808年封拉古萨公爵。1814年在法兰西战役中背叛拿破仑·波拿巴。百日王朝期间随路易十八流亡。波旁王朝复辟后,任皇家卫队元帅。1830年镇压七月革命失败后流亡欧洲。
[13]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回忆拿破仑·波拿巴》,第1卷,第31页。——原注
[14]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保罗·巴拉斯回忆录》,第1卷,第146页。虽然此部为英译本,我读来仍要精炼语句,提纯语义,皆因译本多有赘述之处。不过,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本就文风晦涩,译成英文后更显生硬难懂。——原注
[15]人们流传,那天委员们评论说,这当中共和党和厨师们是“城中仅有的好人。”——原注
[16]如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西斯·让·尼古拉所言,卢西恩·波拿巴此举“口出不敬”“玷污先贤”。——原注
[17]《保罗·巴拉斯回忆录》,第1卷,第161页。——原注
[18]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西斯·玛利·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法兰西革命家,法兰西大革命时期重要领袖人物,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1794年国民公会一致推举他为主席。在热月政变中阵亡。
[19]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日耳曼神话中的英雄。他杀死了一条龙,后来又被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