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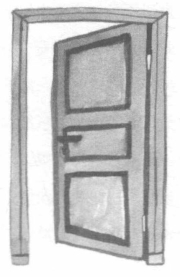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没有让他滚出我的房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个问题竟然不是“你是谁”。大概是因为他看上去非常迷茫;我记得我只想了这么多。他从花园走进来,显得格格不入,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实际上,对于贸然闯入,他露出了表示抱歉的表情。
我不认识他的制服,但我想我当时一定以为他是个军人,因为我隐约记得这样想过:“天哪,要是他有枪怎么办?”不过我显然没有慌张,否则我肯定逃跑了,或者把他推到门外。总之,我一定会这么做的。然而依我看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处境下会做出什么事情,等到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采取行动了。大脑让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变得合情合理。记忆也是错综复杂的。
他说了些什么,但似乎不是对我说的。我想或许他在对着一个被隐藏起来的无线电台讲话。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也听不出他说的是哪种语言,我的脑海中确实闪过一个念头,也许他在自言自语,这样做应该会让我们两人都感到尴尬。我还记得我出于某种古怪的原因,开始盘算要不要表现得坚决一点、振作一点。似乎我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厨房里,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
我把肩膀往后收了收,勉强问了一句:“有什么能帮你的?”你知道,就像是他径直走进了一家店,而我是那里的店员。就好像每天随时都会有军人跑到我家里来——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紧接着我意识到,如果他刚才的喃喃自语算是一种提示的话,他可能不讲英语,于是我只好笑了一下,希望我的笑容看上去不像在学校合影上摆出的那副假笑。我妈总是说我在学校合影中看起来像个傻瓜。她在这样的事情上一向说话口无遮拦。我确信,如果这个人大半夜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吓她一跳,她一定会让他滚出她的厨房。不知怎的,这也是我想让他留下来的原因。
“你好。”他刚才没有回答我,于是我又开了口。
他回敬了我一个微笑,这笑容表示他并不想开口回应,却又不显得粗鲁无礼。他的沉默并没有冒犯我。恰恰相反。他挪了挪他的鞋,那双棕色的鞋擦得锃亮。他看上去很体面。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我脱下戴在手上的橡胶手套,朝冰箱走去。“我们家有……嗯……只有一些炖菜了。”我耸耸肩,忽然想知道为何自己没有做一顿四道菜的大餐。“我们有一些剩饭……詹姆斯今晚不是很饿。”我能听见自己在喋喋不休地说话,直到我强迫自己停下来。就像这样,寂静无声。你想填补这沉默,因为它空洞得可怕,吞噬了周围的一切。像一个黑洞。
这个人又笑了笑,然后开始在房间里走动。他在梳妆台前停了下来,拿起一个蓝色的花瓶。
“噢,那是我妈妈的,”我一边把炖菜舀到碗里,把碗放进微波炉,一边说,“她以前常常去跳蚤市场淘回来一些没用的旧东西,而我又不忍心把它扔掉。真傻,是不是?”
没有回答。
我又试了一次,看着他的制服说:
“你是不是要去……去那里,去,嗯……?”我的声音渐渐变小了。大家都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那天早上的报纸就摆在桌上,头条指向天空。
他放下花瓶,从身体两侧抬起双臂,伸展开来,像一个十字架。我眨眨眼。然后恍然大悟。
“噢。一架飞机。”我点点头,浑身上下感到一阵轻松;现在我明白了。一架飞机。他开飞机。在某个地方,为了某个人,为了某件事。他的制服是天空的伪装色。“我喜欢飞机。”我听见自己傻乎乎地说道,“好吧。不是,其实并不喜欢。我对飞行没有一点儿兴趣。抱歉。”
微波炉发出“叮”的一声。我吓了一跳。
“给。”我把碗和餐叉放在我俩之间的餐桌上。“请一定吃一些。你懂的,为飞行保存体力。”我发现我也学着他展开了双臂,根本来不及阻止自己。就像一个去度假的英国游客令人尴尬地大声嚷嚷,以为这样就能让其他国家的人听明白。我妈一定在某个地方翻了个白眼。
然而,他似乎笑了起来,还拿起了碗和餐叉。他打量着它们,表现出某种兴趣,然后开始吃了起来。他匆匆把食物送进嘴里,不过动作还是一点都不粗鲁,甚至颇具魅力,好像他只是很久没有吃到东西了。他如此爱吃我做的饭,这让我很骄傲,我以前从没觉得自己做饭好吃。
他没有坐下,依然站在那里,抬头看了一眼电灯泡。这个飞行员就这样站在我的厨房里。
“你从哪里来?”我拉开一把椅子,坐在椅面的边缘,碰运气似的问道。
他好奇地看了看我,继续进食。
“我儿子在楼上睡觉,”我换了个话题,以免他觉得不自在,“你有孩子吗?”
我无法保持沉默,继续追问道:“你是从法国来的吗?”我试着回忆了一下我的中学法语。我承认,当他露出迷茫的表情时,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德国?荷兰?俄罗斯?”我开始列举欧洲的一些国家,然后是亚洲、南美洲……我想起了詹姆斯的地理作业,于是我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的世界地图拿来。就像在玩蒙着眼睛给小毛驴贴尾巴的游戏[1],全靠猜,不过这样做似乎不太礼貌。飞行员用餐叉刮着碗底,还皱了皱眉,仿佛他能听见我的想法。
他坚定地放下碗,点了点头。我觉得这一定是个表达谢意的点头。他掸掉了身上的面包屑,然后朝门走去。
“你要走了吗?”我站起身问道。
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想到也许他根本不是飞行员,而是一个强盗,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来到这一带踩点,他只会在我睡熟后回到这里,把我家洗劫一空。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可此时此刻,有什么不可能呢?
“你不能就这样离开,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笑着说,虽然这一点也不好笑,“我是说,这算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到我家来?我记得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没有说出口。为什么找上我?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
他在后门那里停了下来。我记得那时我想,也许他真的听得懂我说的话。也许他比表现出来的样子要懂得更多,只是不愿说罢了。他路过这里,像一个被交换了人生的人,想看一眼另一种生活是怎样的存在,那是他无法真正体验到的生活,然后潜入夜色中。我颤抖了。那一刻,他让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人,他走在繁华街头,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写着“末日将至”。他跺着脚,高声叫喊着世界末日,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对他视而不见。假装他们听不见。
就在这时,飞行员的眼中似乎有些什么,不过如果有人要问我,我知道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想我很可能不会将他的来访告诉任何人。我明白,我会对此只字不提。那一刻,我感觉到,他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就在那短短的一秒之间,然后他踏出我的家门,不见了踪影。某种忧伤弥漫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在这黑暗中谁也未曾将它说出口。
【注释】
[1]一种英美国家孩子玩的游戏,在墙上挂一幅小毛驴的画,唯独缺少尾巴,参加游戏的人蒙住眼睛,手中拿着带图钉的驴尾巴,然后将其按在图片上,看谁能把尾巴放在正确的位置。游戏名作为惯用语还用来嘲笑盲目进行毫无意义或不得要领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