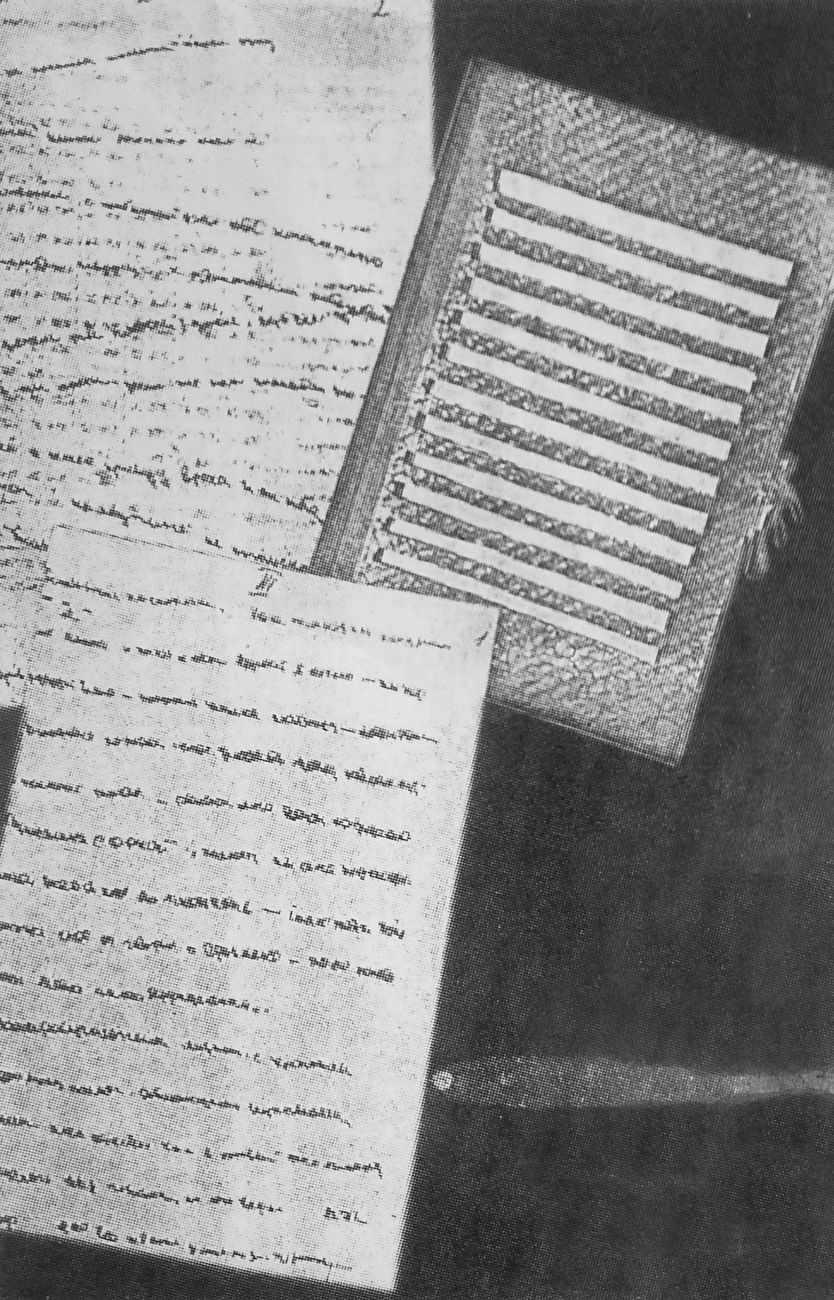第25章 两个尼古拉
没错儿,房子调拨下来了。不过,准确些说,只有半间房。
数月内,拉依萨耐心地各处奔走,不怕碰钉子,不怕遭回绝,到过区苏维埃,找女代表诉说,也去了中央医疗委员会,请专家出力。尼古拉让她直接去见雅罗斯拉夫斯基,详谈丈夫的经历和困境,提出要求。拉依萨虽然没能见到雅罗斯拉夫斯基,但另一位首长接待了她,倾听了她的陈述,并当即用公文纸给一个区的不动产管理局局长写了几句话,建议优先为病残严重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调拨住房。拉依萨带着便条,怀着希望,去了不动产管理局……
拉依萨来到医院,院方通知她:“你丈夫的病目前难以治愈,还是把床位腾出来,让别人入住吧。”
“但是我们还没地方可去。请宽限那么三四天,等落实了房子,一定马上就走。”
“不行!如果不马上腾位置,我们就要把他抬到走廊上去了。”
拉依萨眼泪都急出来了,她无奈地把院方的意思告诉了尼古拉。
“这样,拉依萨,你别慌。三天,你三天别出现,看谁敢把我抬出去!”
“我能不来吗?他们要是真把你抬出去了,可怎么办呢?”
“那好,你照常来。”尼古拉觉得,自己再没办法,此时此刻,身为丈夫,也必须抚慰拉依萨,让她感到有依傍,不忧虑。“但你把‘勃朗宁’放在我手边。你会看到,一切都能顺利解决的。”
他们不是小孩子了,当然知道话可以这么说,办法还得想。不约而同,俩人都记起了俄罗斯谚语“有勇气,必胜利”,于是,俩人互相鼓励一番,商量一番,分析一番,继续行动了。
对医院,用不着太担心。这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未必真会动手,把病人抬到走廊上去。尼古拉让自己千万别发火,急躁、恼怒、使性子,于事无补。比水沉静比草低,往往反而表明内心强大,能把事情办妥。
有些地方,有些人,不靠谱,别再浪费时间去找、去托、去求。接连几日,拉依萨到医院来之前,总是先跑一趟不动产管理局。果然,这天局长笑着对又一次到来的拉依萨说:“行!给你半间房的居住证。”
拉依萨兴冲冲地按着地址找去一看,不免有些失望。
房子肮里肮脏,墙壁上沾着不少臭虫的血迹。原本是间大屋子,当中用破帷幔一隔为二。破帷幔那边的一张床上,有个老婆婆躺着,是一家邻居的母亲,病重得快要咽气了。这样子,怎么能让尼古拉搬过来呢?至少要用板壁隔一隔,屋子也得修理一下,打扫干净,添置最简单的桌椅之类,否则真没法住。
拉依萨不得不再到不动产管理局,求他们帮忙。
这回运气不错,碰到一位中层女干部,是个先进工作者。她同情尼古拉夫妇的处境,愿意出把力。她主张,尽管只有半间很差的房子,但应该先接受下来。她会设法送去一些拆旧房时剩下的木板,并安排工人,帮他们把板壁装好。木板不收钱了,只要支付一点儿辛苦费给工人师傅就可以。她还弄来了一些廉价的旧床旧桌椅呀什么的。拉依萨非常感谢这位热心人……
翌日,有辆救护车顺着大街行驶。刚下过雨,车轮底下,水光闪烁的柏油马路飞速后移。车内,躺着的是尼古拉,坐着的是拉依萨。每次接近十字路口,尖利的笛声响起,尼古拉就觉得刺耳,禁不住浑身哆嗦。他那已经看不清东西的双眼,似乎紧盯着纯白的顶棚。一些关节受到震动,一阵阵疼得钻心,但他强忍着,一声不吭。他已习惯用思绪“转移法”来抗击剧痛。此刻,他这样想:要我呜呼哀哉吗?不,我一定得活下去,跟那些博学的医生开开玩笑。他们横检查竖检查,说我身患这种病那种病。没错儿,那些病我全有,可他们如果下结论,说我已百分之百地既残又废,那就大错特错喽……我的美好的梦想要变成现实,要从遥远的后方转向前沿阵地……成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进行创作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我憧憬着劳动、进步和成就。为此,必须努力再努力,同时学习再学习。除非心脏停止搏动,否则,布尔什维克永远可以学习和工作……对了,我该去封信,鼓励鼓励洛卓奇卡。她是通过诺维科夫的介绍认识我的。她年轻,却病得不轻。我要劝她抓紧治疗,丧失健康等于丧失一切。瞧瞧我吧,凡是你所向往的,我全部向往,然而一旦失去了力量,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如果你正面临着丧失劳动力的危险,那么赶紧抛下一切工作,修补健康。这健康,是一名战士用什么也换不来的财富……
这样充满信心的、乐观的深思默想,逼退了疼痛。
突然,车子一个急刹,打断了尼古拉的思索。拉依萨也霍地一惊。原来已到目的地,救护车停住了。正是苗尔特维胡同口。
一群人围了过来。奇怪,到处都有那么多闲人,不懂得珍惜光阴,不担心上班迟到,喜欢看热闹,还互相打听出了什么事,闹哄哄的。
尼古拉紧锁双眉,催促卫生员动作快些。他被抬下车,进胡同,上了12号的二楼,穿过宽宽的长廊,进入狭长的屋子。
啊,到家了,在莫斯科有个家了!
板壁是仓促间安装的。板条抹上灰浆还不久,像个硕大的棋盘。这幢楼房原先属于一个贵族,那么多的房间,现在住满了各种各样的房客,仿佛蜂巢,挤满蜜蜂。公共厨房在另一头,嘈杂的声音从清晨响到深夜,好在离得较远,干扰不大。
房间里搁着一张旧铁床、一只呢面破旧的小牌桌和一把破椅子。还有一张用木箱和板条搭成的“床”,是给拉依萨睡的。还有两个厚实粗大的木头墩子,权做木凳。这便是全部“家具”了。
头天晚上,夫妻俩一直谈到半夜,许多事情要商量、决定。
最初一些日子,生活过得特别困难。拉依萨继续上班,她不可能辞掉工作,留在家中照料丈夫。不仅经济上不允许,丈夫也不赞成她离开工厂这个集体。这段时间,尼古拉的母亲奥里加独自住在索契,儿子让母亲每月去领他的抚恤金过日子。当然,母亲是节俭惯了的,往往只花掉三分之一。拉依萨去厂里上班,要走一个半小时。每天早晨5点起来,先帮尼古拉漱口洗脸,重新铺床,喂他吃早饭,摆好小棍子,这样忙到6点,才可以出门。她临走时会把门锁上。
尼古拉独自留在家里,唯一能使用的工具是那根小棍子——一端缠着纱布的细木棍。当时,他还剩下一点点视力,如果别人俯下身去,凑近他的眼睛,他可以勉强看到对方的面孔,甚至分辨出上衣的花纹;如果是一张信纸,他可以借助放大镜,看清纸上的字句。然而,他无法这样写字,因为他只能直挺挺地仰面躺着,动弹不了。实在需要,就只能瞎摸着写。
在写,在写,上肢的关节经常酸疼,他依旧在写,在写,在写……
拉依萨在厂里,作为积极分子,带头苦干巧干;下班了,步行一个半小时回家。一开门,看见丈夫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她眼眶内便不由蓄满泪水,喉咙里哽咽着,讲不出话来。反倒是尼古拉微笑着安慰她:“别难受,拉依萨,我不寂寞。在幻想中消磨时光,很有乐趣的。快弄点儿饭给我吃吧,饿坏啦。”
妻子破涕为笑,利索地喂丈夫吃饭,做完家务,她就坐在铁床边,读报给他听。俩人议论时事,谈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新成绩、新胜利,也谈妻子工厂里的各种人和事。尼古拉总能提出一些切实的建议。
他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精神上非常快乐。1930年7月16日,尼古拉在给日吉廖娃的一封信里这样说:“拉彦卡作为一个党员,在工作,在成长,方向对,步子快。这女孩像小伙子一样干练。我和她亲密无间,日子过得很好。”
那是4月的一个晚间,拉依萨下班回家,刚进门,尼古拉就兴奋地冲着她说:“快把家务做完,帮我誊清写好的几页东西。”
“是信吧?”拉依萨随口问。
“不,不是信。”
她看出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不由得振奋起来。她一边誊清一边想,这是他的心血、他的希望。
从这时起,妻子每天下班回家,就把丈夫白天写的文字抄录一遍。那个年代,纸张匮乏,拉依萨征得厂长的同意,拿回了许多废弃的切边纸,装订成一本本笔记簿。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写完以后,他们又搞到一点儿红色道林纸,就用它做成了封面,从旧报纸上找出需要的印刷体字母,剪下来,拼成书名和作者的名字,贴在封面上——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这是后话。
丈夫开始写作,拉依萨自然更忙了。清早离家前,把几支铅笔削好,插在一个粗重的茶杯托里,搁到床边的旧椅子上,便于尼古拉取用。写作之初,他还可以自己伸手摸索着拿笔。傍晚回家,妻子把散落在地的、已写满了字的纸页捡起来,整理,誊录。次日黎明,再留下一些空白的纸页。她心里完全清楚,文学创作是尼古拉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必须长期努力,攻克万难,才有可能成功的,自己要全力支持。
春去夏来,屋内逐渐热起来,驶过近处的载重卡车和拉货马车发出的噪声,由打开的窗户传送进屋,显得越发刺耳烦心。尼古拉睡不安稳,要进行创作也难以集中心思。
他思念体弱多病的妈妈了。恰好有人可以同行,沿途照顾,尼古拉就乘坐火车,前往索契,跟母亲奥里加一起过了数月。
索契温暖宜人的气候,母亲的全天护理,使他烦躁的心情得以舒缓,但亲友们经常登门探望和小住,又让他白天忙于接待、聊天,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安静地躺着,不受干扰,犹如孕育胎儿般,脑子里紧张地琢磨,安排小说的结构、情节和人物,直至某个场合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在脑海中浮现,清晰又逼真,他才莞尔而笑,沉沉入睡。尼古拉挺累,也挺快乐。
可竟如晴天霹雳,他遭受了一次新的、做梦也想不到的重大打击。
原来,当他在莫斯科住院之时,索契正进行着一场全面清党的工作。尼古拉以为,自己的往昔与当下,所有的生活历程,绝对经得起调查与检验,根本无须担忧。然而,久久没人来找他本人谈话和了解情况,忽然有一天,仿佛突然袭击似的,蓦地传来一个消息——他被视作自动脱党了!
索契清党委员会的这一决定使他无比震惊,两日两夜没有合眼,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了,全身的健康状况随之恶化,连眼部的炎症也明显发作得更厉害了。他闷声不响,痛苦地思索着:清党委员会里的人,竟然懒得审查,便草率地、武断地把一个忠诚的党员推到党外去了。从表面看,似乎他们也并无过错,没有违背规章。一般讲,在党代会后,未经审查的党员即视为自动脱党。可他呢,重残重病,身在遥远的莫斯科……这样的一个年轻党员,怎能不经审查便收去党证呢?他还年轻,却已被各种磨难损耗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但他保住了清醒的头脑和钢铸铁打的心。这是最珍贵的,恰似未毁坏的发电机,尚可启动,尚可贡献力量!与脱党相比,什么病,什么残,什么痛,什么苦,全是细枝末节,不值一提,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是的,决不脱党,决不脱党!
尼古拉重新振作精神,为恢复党籍而努力奋斗。但这件事情办起来十分艰巨,况且他的健康状况如此之糟糕。难能可贵的是在艰辛地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他仍不断地进行申诉,终于在两年后获知,有关方面已做出结论:恢复党籍,并确定已通过审查[1]。
1930年10月17日,尼古拉由二姐卡佳陪同,返回莫斯科,抓紧时间,继续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
当初,他曾经考虑写成一本回忆录,记述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来偶然结识杂志编辑考斯特洛夫[2],在交谈中谈起此事。考斯特罗夫从专业角度,诚恳地建议他写成小说,塑造一些优秀工人的形象,着力描写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革命的憧憬与追求、青年时代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与充满激情的劳动态度。
这个建议,正中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下怀,他大受启发。当然,实施起来要艰难得多。
如今,每天每日,他都抓紧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视力越来越差,写作速度奇慢,常常写得字跟字重叠,行跟行重叠,连自己也辨认不清。
尼古拉让拉依萨找来硬纸板,割出一条条空格,配合夹子,做成特殊的写字板。夹子夹住白纸,尼古拉摸索着镂空格子写字,就方便多了。速度快了些,文字也整齐了些。开始并不顺手,几天后才熟能生巧。他的膝关节僵化,双腿怪异地呈弯曲状,这是病症,是畸形,如今恰好可以斜斜地“放置”镂空写字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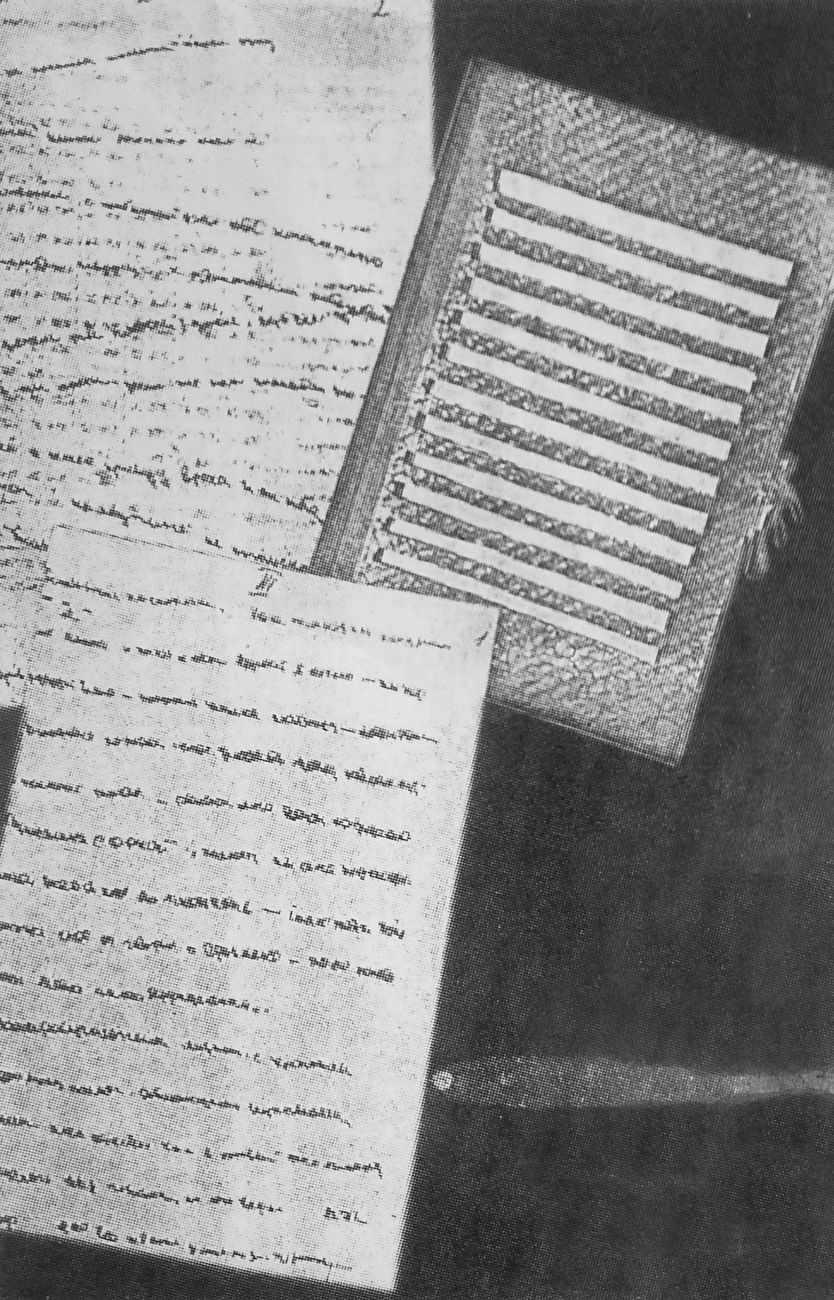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几章所使用的镂空写字板和部分手稿原件。
尼古拉抓紧时间写作,可病魔再次凶狠地袭击了他,上肢关节的炎症恶化,别说写字,稍稍动弹一下也酸痛得厉害。只能等拉依萨下班回来,他口述,妻子记录。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次日拉依萨还得上班。
他俩在首都莫斯科有了住所,尽管是小小的半间,狭长得跟走廊似的,亲友们闻讯都为他们高兴,纷纷来访、小住。有一阵儿,除了尼古拉两口子,小屋里还挤住了这些亲戚——尼古拉的母亲奥里加、二姐卡佳带着女儿喀秋莎,拉依萨的母亲留保芙、弟弟沃洛佳和妻子叶莲娜、姐姐廖利娅和她年幼的儿子,总共十口人。其中,两个学龄前儿童常会瞎吵瞎闹,谁管得住?沃洛佳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也缠绵病榻。两位母亲,各有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儿子,内心都很悲酸。在这种氛围中,尼古拉老是不得安宁,进行创作,难上加难。
不过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即便整天都闹哄哄的,尼古拉的创作仍在进行,人多他的助手也多了。沃洛佳一度发病住院,出院后,他和妻子叶莲娜在楼房的同一层,另租了半间低矮阴暗的屋子住下,成了尼古拉家的“近邻”。那些日子里,拉依萨、沃洛佳和叶莲娜都帮尼古拉抄录过书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的前四章,共有底稿500页左右。白天得上班的拉依萨抄了约100页;叶莲娜抄了100多页;其余将近300页,全是心脏病严重的沃洛佳抄的。不久,母亲奥里加来长住,挑起了做家务的重担,尼古拉的写作就又加快些了。
每天每日,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着,写着。无论多种疾病轮番来袭,还是“自动脱党”通知如五雷轰顶,都未能使他中断写作。
不料,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邻居家有个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活泼又调皮,大家管他叫尼古尔卡[3]。
一天傍晚,小男孩尼古尔卡推开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家的房门,走到屋子中间才开口问:“可以进来吗?”
“可以,可以,快进来吧。”
“我已经进来了。”
尼古拉不由笑了起来,说:“已经进来了,还问什么呢?大家都是在门外就问可不可以进来的。”
不料,尼古拉话音刚落,尼古尔卡小小的身影转过去,箭一般地跑出了房门。这么一来,尼古拉反倒觉得有点儿尴尬了。
“瞧瞧,怎么会这样呢?”他嗫嚅着跟拉依萨说,“小家伙儿怎么这样容易生气?怎么一溜烟儿跑了呢?”
就在这一瞬间,门外又传来尼古尔卡脆生生的童音:“可以进来吗?”
“请进,快请进来吧。真是好样儿的。”尼古拉快乐地夸赞,“你已经改正了缺点。”
话音刚落,孩子已坐在未来作家的床边了。两个尼古拉亲热地聊起来。
“你以前怎么不来我家做客呢?我老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冷冷清清的。”
“老没空来呀。”小客人满脸愁苦,还叹了口气。
“哦,这么着,那的确来不了……尼古尔卡,我总觉得,你老早就想跟我认识了。好几次了,是谁在我家门口弄出挺响的声音,还哼哧哼哧地喘气?”
“那是老鼠,”尼古尔卡不假思索地回答,还反问了一句,“那你为什么也不来我家做客呢?”
“是呀,那是因为我也老没空哦。”尼古拉学着小客人的口吻答道,也叹了口气。
尼古尔卡忽然眯缝起两眼,一脸机灵,怪逗人的。他也来了个反问:“那么,在我家门口弄出挺响的声音的,又是谁呢?”
这下,尼古拉憋不住了,被小家伙逗得大笑起来。
“哦,这我可不知道啊!大概是鳄鱼,它想跟你交朋友吧?”
“不对,鳄鱼不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它是在河里游来游去的。爸爸告诉过我,你不会走路,只能躺在床上,整天整天的看不到什么人。”
“正是这样。那你怎么还问我为什么不去你家呢?”
“我故意这样问的呀。”尼古尔卡天真地回答,紧接着,他一本正经地、十分关切地提出成串的问题:“你怎么会变成盲人的?怎么会走不来路的?怎么要一直躺在床上呢?”
“你想知道,是吧?好,我给你讲讲。”
于是,大哥哥尼古拉尽量晓畅易懂地、具体生动地给小弟弟尼古尔卡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
尼古尔卡认认真真地听着,还不时发出惊叹。
从这时起,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尼古拉常给小家伙讲有趣的小故事,非常真实,又非常夸张,每每让尼古尔卡惊喜得一愣一愣的。这小家伙呢,一张小嘴唧唧呱呱,能说会道。为了引发尼古拉的兴趣,他还善于发挥自个儿的优势——把看见的,听到的,刚刚发生在院子里、胡同内的大事情小情况,一件件一桩桩,讲给尼古拉听。有时候兴之所至,他居然会凭着想象,添枝加叶,讲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这种添枝加叶,完全是孩童式的,透露出稚气的愿望、奇妙的创意。尼古拉一听便知“其中有诈”,但他根本无意点穿,宁可全盘接受,并对小弟弟的想象力表示赞赏。
一天,尼古尔卡捏着几块黏糊糊的赤膊糖,笑嘻嘻地对尼古拉说:“这糖是我送给你吃的。妈妈给了我5戈比,我就给你买了糖啦。”
一大一小两个尼古拉,越来越要好了。如果尼古尔卡哪天没来,尼古拉就会牵挂,甚至着急起来,催促拉依萨去瞧瞧,小家伙家里是否出了什么事儿。
拉依萨拗不过他,一般都会去看看,好在每次都没什么事儿。第二天小家伙就又来尼古拉家了。
可有一天,拉依萨下班后,刚进家门,尼古拉就急巴巴地说:“尼古尔卡一整天都没来,你去瞧瞧,小家伙会不会生病了啊。”
拉依萨忙着做家务,过了一会儿还没去。不知怎么的,尼古拉烦躁不安,焦虑地说:“你先去瞧瞧孩子嘛,他们家好像有异常的响动,或许发生了什么情况。”拉依萨被他说得心慌意乱,赶紧过去探望。
哦,尼古尔卡果真病了,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拉依萨安慰了孩子的父母几句,慌忙回来告诉尼古拉。这个夜晚,尼古拉心神不宁,简直没合眼。
次日清早,他让妻子上班前再去探望一下,看看尼古尔卡的病好些没有。
原来,医生已经做出诊断,说尼古尔卡病情严重,必须动手术。尼古拉闻讯,那副忧心忡忡的神态,真像家长一样。
次日,尼古拉整天焦灼不安,因为尼古尔卡当晚便要接受手术了。
拉依萨下班回家后,尼古拉心不在焉地吃过晚饭,不声不响地静躺着,屏息谛听邻居家传出的所有细微的声音。直到凌晨1点多钟,走廊里响起急促而杂沓的、不祥的脚步声。尼古拉那难以动弹的躯体似乎哆嗦了一下,显然,他一直清醒着。此刻,他视力丧失殆尽的双眼睁得好大,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躺在简易卧榻上的拉依萨也被惊醒了。
正在此时,尼古尔卡的母亲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叫,紧跟着便是一片杂乱的恸哭声。
“拉依萨,快开灯!”尼古拉大喊。
妻子开了电灯,只见丈夫双目“凝视”着天花板,那样子,就像是灯亮了自己却仍一无所见似的愣怔着。
“尼古尔卡死了?”尼古拉恍若低声自问。
“尼古尔卡死了。”与其说是妻子的回话,倒不如说是自己问话的回声。
……
可爱的小男孩被安葬了。
接连数天,铁骨柔肠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沉浸在悲伤中。
[1]1929—1930年,苏联党内进行第二次清洗。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正在莫斯科长期住院,区委会没有对他进行审查,而未经审查的党员是一律被留在党的队伍之外的。为此,奥斯特洛夫斯基提出申诉,至1932年,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他在莫斯科通过了审查。
[2]塔拉斯·考斯特洛夫(1901—1930),1928—1929年,任《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他建议奥斯特洛夫斯基,别把丰富的素材写成回忆录之类的作品,而是写成小说。
[3]这孩子也叫尼古拉,和本书传主同名。尼古尔卡是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