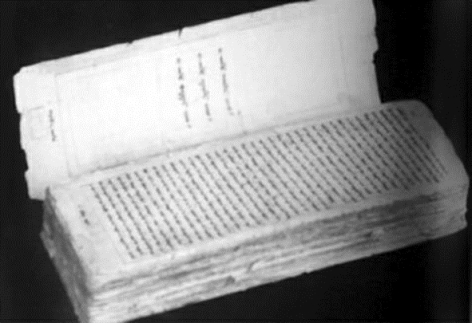-
1.1前言
-
1.2目录
-
1.3第一章 印度远古文明
-
1.3.1一、印度的自然环境
-
1.3.2二、史前居民与石器分布
-
1.3.3三、哈拉巴文明
-
1.3.4作者点评:
-
1.4第二章 雅利安文化的冲击
-
1.4.1一、雅利安人与《梨俱吠陀》
-
1.4.2二、五河时期的雅利安人
-
1.4.3三、后期吠陀与史诗
-
1.4.4四、恒河流域的开发
-
1.4.5五、种姓制度初现
-
1.4.6六、梵语和俗语
-
1.4.7作者点评:
-
1.5第三章 摩揭陀王国的兴起
-
1.5.1一、从十六国到四雄争霸
-
1.5.2二、摩揭陀统一恒河流域
-
1.5.3三、印度的“百家争鸣”
-
1.5.4作者点评:
-
1.6第四章 孔雀王朝的统一
-
1.6.1一、波斯占领西北印度
-
1.6.2二、亚历山大入印
-
1.6.3三、旃陀罗笈多建立孔雀王朝
-
1.6.4四、阿育王
-
1.6.5五、种姓的演变
-
1.6.6作者点评:
-
1.7第五章 贵霜王国
-
1.7.1一、孔雀帝国遗产的继承者
-
1.7.2二、泰米尔三邦
-
1.7.3三、西北外族
-
1.7.4四、贵霜王国
-
1.7.5作者点评:
-
1.8第六章 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时期
-
1.8.1一、笈多王朝的兴衰
-
1.8.2二、哒人进入印度
-
1.8.3三、戒日王时期
-
1.8.4四、公元6世纪后的南印度
-
1.8.5五、公元7世纪后的北印度
-
1.8.6六、社会状况
-
1.8.7七、种姓制度的确立
-
1.8.8作者点评:
-
1.9第七章 印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
1.9.1一、古代印度与西部世界的交流
-
1.9.2二、古代中印交流概述
-
1.9.3三、中国西藏与印度的交流
-
1.9.4四、印度与东南亚的交流概况
-
1.9.5作者点评:
-
1.10第八章 古典时期的印度文化概述
-
1.10.1一、文学、艺术、哲学
-
1.10.2二、科学
-
1.10.3三、宗教的演化
-
1.10.4作者点评:
-
1.11第九章 德里苏丹
-
1.11.1一、穆斯林进占印度
-
1.11.2二、德里苏丹五王朝
-
1.11.3三、注入新的因素
-
1.11.4四、北印度的地方政权
-
1.11.5五、南印度的地方政权
-
1.11.6作者点评:
-
1.12第十章 莫卧儿帝国
-
1.12.1一、巴卑尔建国
-
1.12.2二、胡马雍的颠沛流离与舍尔沙的苏尔王朝
-
1.12.3三、阿克巴的武功
-
1.12.4四、阿克巴的文治
-
1.12.5五、查罕杰时期(1605—1627)
-
1.12.6六、沙·贾汉时期(1627—1658)
-
1.12.7七、奥朗则布时期(1658—1707)
-
1.12.8八、莫卧儿帝国的瓦解
-
1.12.9九、中世纪的印度文化
-
1.12.10作者点评:
-
1.13第十一章 欧洲人东来及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
1.13.1一、葡萄牙在东方的海上霸权
-
1.13.2二、英、荷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和英荷之争
-
1.13.3三、英法争霸印度
-
1.13.4四、印度东北地区的沦陷
-
1.13.5五、德干和南印度地区及印度斯坦的沦陷
-
1.13.6六、西北印度的沦陷
-
1.13.7作者点评:
-
1.14第十二章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及印度社会向近代转型
-
1.14.1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状况(1600—1773)
-
1.14.2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后期状况(1773—1858)
-
1.14.3三、印度农村在掠夺中蜕变
-
1.14.4四、备受摧残的印度手工业、商业
-
1.14.5五、转型中的印度农村和城镇
-
1.14.6六、政治结构中的近代因素
-
1.14.7七、印度近代意识的开端
-
1.14.8八、殖民当局对印度附属国的政策
-
1.14.9九、印度大起义(1857—1859)
-
1.14.10作者点评:
-
1.15第十三章 殖民地化与印度近代化初型
-
1.15.1一、殖民地的统治体制和统治政策
-
1.15.2二、近代产业的出现及初步发展
-
1.15.3三、近代宗教改革运动
-
1.15.4四、民族主义的萌芽
-
1.15.5五、印度国大党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
1.15.6六、印度穆斯林的近代启蒙及文化教育运动
-
1.15.7作者点评:
-
1.16第十四章 第一次民族运动高潮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1.16.1一、国大党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
1.16.2二、寇松及孟加拉分省案
-
1.16.3三、穆斯林联盟的建立与青年一代的崛起
-
1.16.4四、1916年勒克瑙的团结聚会
-
1.16.5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的影响
-
1.16.6作者点评:
-
1.17第十五章 甘地与民族运动第二次高潮
-
1.17.1一、甘地及其思想
-
1.17.2二、战后英印政府的政策
-
1.17.3三、哈里发运动
-
1.17.4四、甘地与不合作运动
-
1.17.5五、真纳与穆斯林联盟的崛起
-
1.17.6六、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
-
1.17.7作者点评:
-
1.18第十六章 国民不服从运动与艰难的自治之路
-
1.18.1一、青年激进派及国民不服从运动
-
1.18.2二、1935年《印度政府法》
-
1.18.3三、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纷争
-
1.18.4作者点评:
-
1.19第十七章 自由与分治
-
1.19.1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印度局势
-
1.19.2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印度局势
-
1.19.3三、英国接受印度独立的要求
-
1.19.4四、蒙巴顿与印巴分治
-
1.19.5作者点评:
-
1.20第十八章 从自治领到共和国
-
1.20.1一、自治领政府的建立
-
1.20.2二、教派冲突及甘地证果
-
1.20.3三、土邦的归属
-
1.20.4四、《印度宪法》
-
1.20.5作者点评:
-
1.21第十九章 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印度
-
1.21.1一、议会民主制进程
-
1.21.2二、建设印度式的社会主义
-
1.21.3三、印度的工业发展模式
-
1.21.4四、印度的农村建设
-
1.21.5五、世俗主义
-
1.21.6六、印度的主要政党及其概况
-
1.21.7七、尼赫鲁的外交政策
-
1.21.8八、遗憾的结局
-
1.21.9作者点评:
-
1.22第二十章 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的印度
-
1.22.1一、夏斯特里的短暂执政
-
1.22.2二、英迪拉·甘地初掌政权
-
1.22.3三、渐露峥嵘
-
1.22.4四、1971年大选及英迪拉·甘地大权在握
-
1.22.5五、经济、政治危机与英迪拉·甘地下野
-
1.22.6六、人民党执政时期及英迪拉·甘地东山再起
-
1.22.7七、教派冲突与英迪拉·甘地殉难
-
1.22.8八、英迪拉·甘地政府的外交政策
-
1.22.9作者点评:
-
1.23第二十一章 从拉吉夫·甘地政府到拉奥政府
-
1.23.1一、突如其来的接班
-
1.23.2二、缓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
1.23.3三、传承与革新
-
1.23.4四、拉·甘地政府的外交
-
1.23.5五、拉·甘地的困境
-
1.23.6六、维·普·辛格与谢卡尔的执政
-
1.23.7七、拉奥政府的锐意进取
-
1.23.8八、拉奥政府的外交
-
1.23.9作者点评:
-
1.24第二十二章 全国阵线与全国民主联盟
-
1.24.1一、1996年大选
-
1.24.2二、组阁风波及联合阵线政府
-
1.24.3三、经济改革与社会治理
-
1.24.4四、印度的核能政策
-
1.24.5五、联合政府的外交政策
-
1.24.6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
1.24.7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
-
1.24.7.1一年半的执政状况
-
1.24.7.2任重而道远
-
1.24.8作者点评:
-
1.25主要参考书目
-
1.26后记
1
印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