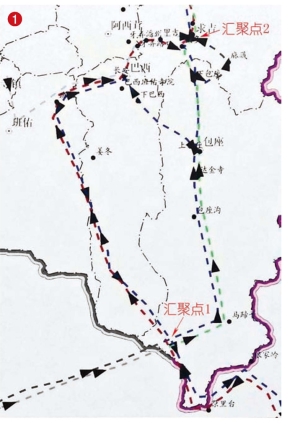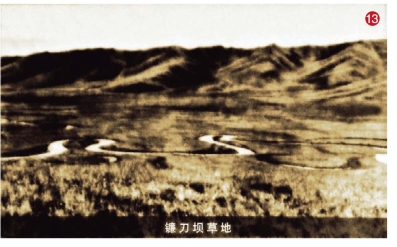1
2
重走长征路. 红四方面军
-
2.1目录
-
2.2开篇 自驾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
-
2.3第001站 万源市
-
2.4第002站 王坪村
-
2.5第003站 通江县城
-
2.6第004站 巴中市
-
2.7第005站 阆中市
-
2.8第006站 苍溪红军渡
-
2.9第007站 江油市
-
2.10第008站 禹里镇
-
2.11第009站 墩上乡
-
2.12第010站 土门镇
-
2.13第011站 茂县县城
-
2.14第012站 汶川县城
-
2.15第013站 理 县
-
2.16第014站 卓克基
-
2.17第015站 两河口
-
2.18第016站 猛固桥、马鞍桥
-
2.19第017站 小金县城
-
2.20第018站 达维镇
-
2.21第019站 夹金山
-
2.22第020站 硗碛镇
-
2.23第021站 宝兴县城
-
2.24第022站 芦山县城
-
2.25第023站 双石镇
-
2.26第024站 蒙顶山
-
2.27第025站 荥经县
-
2.28第026站 天全县
-
2.29第027站 程家窝村
-
2.30第028站 泸定县城
-
2.31第029站 道孚县城
-
2.32第030站 炉霍县城
-
2.33第031站 甘孜县城
-
2.34第032站 新龙县
-
2.35第033站 班玛县
-
2.36第034站 阿坝县
-
2.37第035站 丹巴县城
-
2.38第036站 金川县城
-
2.39第037站 卓木碉
-
2.40第038站 马尔康县城
-
2.41第039站 达古雪山
-
2.42第040站 黑水县城
-
2.43第041站 沙窝寨
-
2.44第042站 索花村
-
2.45第043站 松潘古城
-
2.46第044站 川主寺
-
2.47第045站 日干乔
-
2.48第046站 班 佑
-
2.49第047站 巴西乡
-
2.50第048站 牙弄村
-
2.51第049站 钦多路口
-
2.52第050站 包 座
-
2.53第051站 求吉乡
-
2.54第052站 高吉村
-
2.55第053站 茨日那村
-
2.56第054站 腊子口
-
2.57第055站 哈达铺
-
2.58第056站 三十里铺村
-
2.59第057站 鸳鸯镇
-
2.60第058站 榜罗镇
-
2.61第059站 通渭县城
-
2.62第060站 大墩梁
-
2.63第061站 会宁城
-
2.64附 篇 七里坪乡
-
2.65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