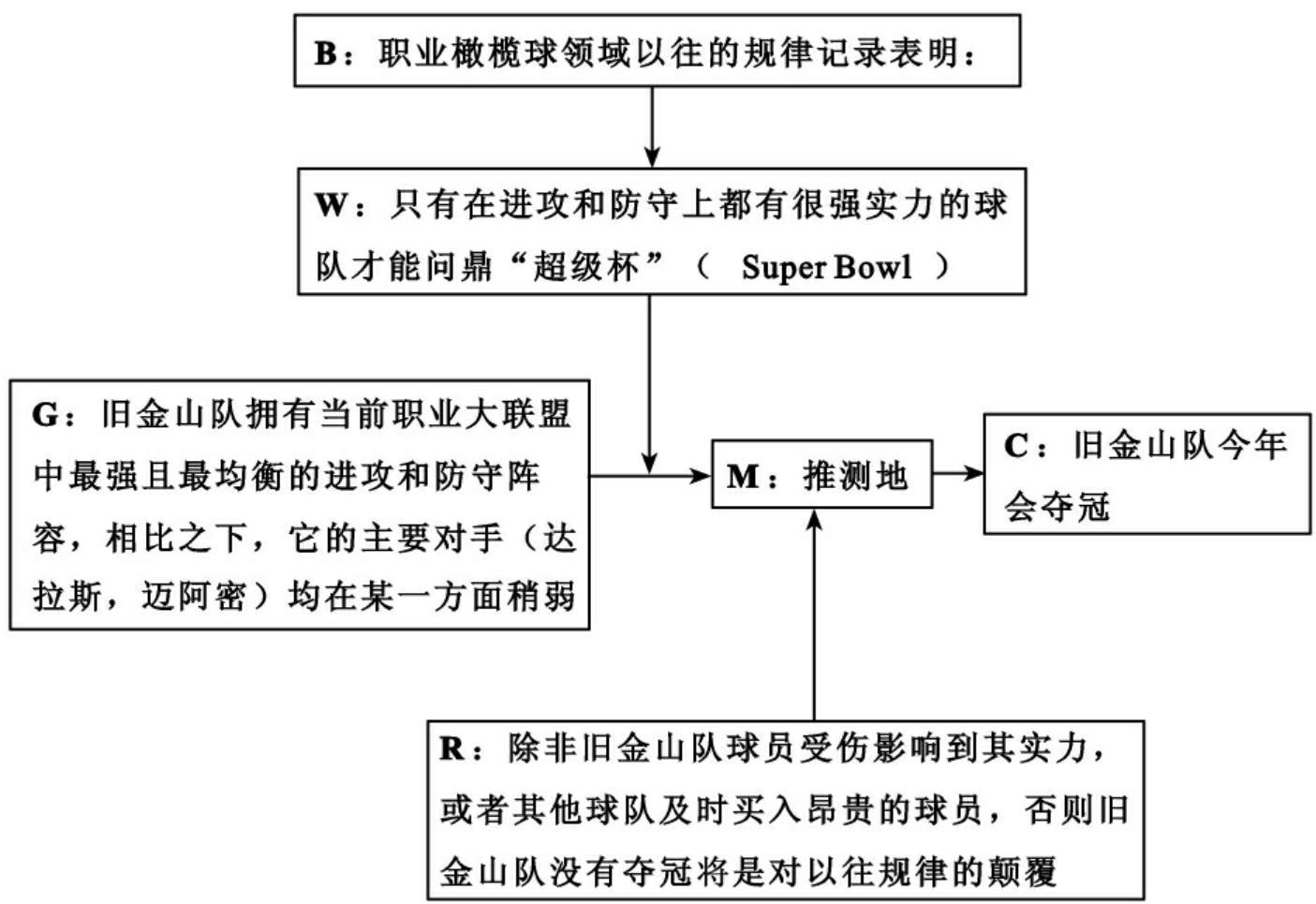-
1.1第一编 导 论
-
1.1.1第一章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历史
-
1.1.1.1第一节 法学与法理学
-
1.1.1.1.1一、法学的概念和品格
-
1.1.1.1.2二、法理学的性质与沿革
-
1.1.1.1.3三、学习研究法理学的重要意义
-
1.1.1.1.4四、法理学的课程体系
-
1.1.1.2第二节 法理学史纲
-
1.1.1.2.1一、古代法理学思想
-
1.1.1.2.2二、近代的法理学
-
1.1.1.2.3三、西方现代法理学
-
1.1.1.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
1.1.1.3.1一、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创立
-
1.1.1.3.2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
-
1.1.1.3.3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丰富与创新
-
1.1.1.3.4四、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主要内容
-
1.1.1.3.5五、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重大意义
-
1.1.2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1.1.2.1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1.1.2.1.1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
-
1.1.2.1.2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构成
-
1.1.2.1.3三、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渊源
-
1.1.2.1.4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特征
-
1.1.2.1.5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意义
-
1.1.2.2第二节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1.1.2.2.1一、治国方略根本原则的历史考察
-
1.1.2.2.2二、“三者统一”是我国民主法治的科学总结
-
1.1.2.2.3三、“三者统一”的辩证关系
-
1.1.2.3第三节 尊重与保障人权
-
1.1.2.3.1一、人权属性上的突破
-
1.1.2.3.2二、人权主体上的突破
-
1.1.2.3.3三、人权内容上的突破
-
1.1.2.3.4四、人权实现上的突破
-
1.1.2.4第四节 创新社会管理与法治的保障
-
1.1.2.4.1一、创新社会管理与法治理念的更新
-
1.1.2.4.2二、创新社会管理与法的功能的发挥
-
1.1.2.4.3三、创新社会管理与法治价值的实现
-
1.1.3第三章 法学方法论
-
1.1.3.1第一节 法学方法概述
-
1.1.3.1.1一、法学方法的含义
-
1.1.3.1.2二、法学方法的作用
-
1.1.3.1.3三、法学方法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
1.1.3.1.4四、法学基本方法
-
1.1.3.2第二节 法律推理
-
1.1.3.2.1一、法律推理概述
-
1.1.3.2.2二、形式推理
-
1.1.3.2.3三、辩证推理
-
1.1.3.3第三节 法律论证
-
1.1.3.3.1一、法律论证的含义与作用
-
1.1.3.3.2二、法律论证的理论模型
-
1.1.3.3.3三、法律论证的方法
-
1.1.3.3.4四、法律论证的基本要求
-
1.2第二编 本 体 论
-
1.2.1第四章 法的本质
-
1.2.1.1第一节 法的词源与词义
-
1.2.1.1.1一、“法”的中文词源
-
1.2.1.1.2二、“法”的西文词源
-
1.2.1.1.3三、现代汉语中的法的词义
-
1.2.1.2第二节 法的本质
-
1.2.1.2.1一、中国古代礼法传统观念与法的本质
-
1.2.1.2.2二、西方主要法学流派对法的本质的认识
-
1.2.1.2.3三、当代中国法理学对法的本质问题的认识
-
1.2.1.3第三节 法的基本特征
-
1.2.1.3.1一、法是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
-
1.2.1.3.2二、法是出自国家的社会规范
-
1.2.1.3.3三、法是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社会规范
-
1.2.1.3.4四、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
1.2.1.4第四节 法的分类
-
1.2.1.4.1一、法的一般分类
-
1.2.1.4.2二、法的特殊分类
-
1.2.2第五章 法的本原
-
1.2.2.1第一节 法的本原的重要性
-
1.2.2.1.1一、对法的本原的不同态度
-
1.2.2.1.2二、正确认识法的本原的重大意义
-
1.2.2.2第二节 经济基础——法的本原
-
1.2.2.2.1一、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
1.2.2.2.2二、法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
1.2.2.2.3三、法服务于经济基础
-
1.2.2.3第三节 法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
-
1.2.2.3.1一、商品交换与法的产生
-
1.2.2.3.2二、商品经济与法的发展
-
1.2.2.3.3三、市场经济与法律体系的形成
-
1.2.2.4第四节 法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
1.2.2.4.1一、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
1.2.2.4.2二、法在规范微观经济行为中的作用
-
1.2.3第六章 法的要素
-
1.2.3.1第一节 法的要素释义
-
1.2.3.1.1一、法的要素的定义与形成
-
1.2.3.1.2二、法的要素的学说与分类
-
1.2.3.2第二节 法律概念
-
1.2.3.2.1一、法律概念释义
-
1.2.3.2.2二、法律概念的分类
-
1.2.3.2.3三、法律概念的特征与要求
-
1.2.3.3第三节 法律规则
-
1.2.3.3.1一、法律规则释义
-
1.2.3.3.2二、法律规则的结构
-
1.2.3.3.3三、法律规则的分类
-
1.2.3.4第四节 法律原则
-
1.2.3.4.1一、法律原则释义
-
1.2.3.4.2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
1.2.3.4.3三、法律原则的分类
-
1.2.3.4.4四、法律原则的形式与适用
-
1.2.3.5第五节 技术性事项
-
1.2.3.5.1一、法律技术性事项的由来
-
1.2.3.5.2二、法律技术性事项的类别
-
1.3第三编 发 展 论
-
1.3.1第七章 法律发展概论
-
1.3.1.1第一节 法律发展的概念与特征
-
1.3.1.1.1一、法律发展的概念
-
1.3.1.1.2二、法律发展的特征
-
1.3.1.2第二节 法律发展的过程
-
1.3.1.2.1一、法律发展过程的种种解说
-
1.3.1.2.2二、当代中国法理学对法律发展过程的阐释
-
1.3.1.3第三节 法律发展的依据
-
1.3.1.3.1一、外部因素
-
1.3.1.3.2二、内部因素
-
1.3.2第八章 法律的起源与演进
-
1.3.2.1第一节 法律的起源
-
1.3.2.1.1一、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1.3.2.1.2二、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
-
1.3.2.2第二节 法律的演进
-
1.3.2.2.1一、奴隶制法
-
1.3.2.2.2二、封建制法
-
1.3.2.2.3三、资本主义法
-
1.3.2.2.4四、社会主义法
-
1.3.2.3第三节 法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
-
1.3.2.3.1一、法律的现代化
-
1.3.2.3.2二、法律的全球化
-
1.3.2.3.3三、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
-
1.3.3第九章 法律发展的路径
-
1.3.3.1第一节 法律继承
-
1.3.3.1.1一、法律继承的含义
-
1.3.3.1.2二、法律继承的内容
-
1.3.3.1.3三、法律继承的依据
-
1.3.3.2第二节 法律移植
-
1.3.3.2.1一、法律移植的含义与依据
-
1.3.3.2.2二、法律移植的原则与方法
-
1.3.3.3第三节 法律改革
-
1.3.3.3.1一、法律改革的基本依据
-
1.3.3.3.2二、法律改革的主要原则
-
1.3.3.3.3三、法律改革的基本内容
-
1.3.3.4第四节 法律革命
-
1.3.3.4.1一、法律革命的含义与本质
-
1.3.3.4.2二、中国的法律革命
-
1.4第四编 运 行 论
-
1.4.1第十章 立法
-
1.4.1.1第一节 立法概述
-
1.4.1.1.1一、立法的由来
-
1.4.1.1.2二、立法的概念与特征
-
1.4.1.1.3三、立法的形式和分类
-
1.4.1.2第二节 立法的基本原则
-
1.4.1.2.1一、合法性原则
-
1.4.1.2.2二、民主性原则
-
1.4.1.2.3三、实效性原则
-
1.4.1.3第三节 立法体制
-
1.4.1.3.1一、立法体制的概念和类型
-
1.4.1.3.2二、我国现行的立法程序
-
1.4.1.3.3三、我国的法律冲突与解决
-
1.4.1.4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
1.4.1.4.1一、宪法及其相关法
-
1.4.1.4.2二、民商法
-
1.4.1.4.3三、行政法
-
1.4.1.4.4四、经济法
-
1.4.1.4.5五、社会法
-
1.4.1.4.6六、刑法
-
1.4.1.4.7七、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
1.4.2第十一章 执法
-
1.4.2.1第一节 执法的概念与原则
-
1.4.2.1.1一、法的实施与执法的概念
-
1.4.2.1.2二、执法的分类
-
1.4.2.2第二节 执法的原则
-
1.4.2.2.1一、合法性原则
-
1.4.2.2.2二、合理性原则
-
1.4.2.2.3三、效率原则
-
1.4.2.2.4四、应急性原则
-
1.4.2.3第三节 执法的体系
-
1.4.2.3.1一、政府的执法
-
1.4.2.3.2二、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
-
1.4.2.3.3三、法律、法规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执法
-
1.4.2.3.4四、行政委托的社会组织的执法
-
1.4.2.4第四节 执法的基本要求与保障
-
1.4.2.4.1一、执法的基本要求
-
1.4.2.4.2二、执法的保障
-
1.4.3第十二章 司法
-
1.4.3.1第一节 司法的概念
-
1.4.3.1.1一、司法的含义
-
1.4.3.1.2二、司法的特征
-
1.4.3.1.3三、司法的功能与价值
-
1.4.3.2第二节 司法的过程
-
1.4.3.2.1一、启动
-
1.4.3.2.2二、审理
-
1.4.3.3第三节 当代中国司法体制及改革
-
1.4.3.3.1一、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概况
-
1.4.3.3.2二、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要点
-
1.4.4第十三章 守法
-
1.4.4.1第一节 守法的概念、要素
-
1.4.4.1.1一、守法的概念
-
1.4.4.1.2二、守法的要素
-
1.4.4.2第二节 守法的动机和理由
-
1.4.4.2.1一、守法的动机
-
1.4.4.2.2二、守法的理由
-
1.4.4.3第三节 守法的途径
-
1.4.4.3.1一、以普法教育塑造公民守法精神
-
1.4.4.3.2二、以良法理念培植公民守法内在信念
-
1.4.4.3.3三、以完善的法律适用提升法律公信力
-
1.4.5第十四章 法律监督
-
1.4.5.1第一节 法律监督释义
-
1.4.5.1.1一、法律监督的含义与特征
-
1.4.5.1.2二、法律监督的意义
-
1.4.5.1.3三、法律监督的原则
-
1.4.5.2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律监督体系
-
1.4.5.2.1一、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
-
1.4.5.2.2二、社会的法律监督
-
1.4.6第十五章 法律解释
-
1.4.6.1第一节 作为立法活动的法律解释
-
1.4.6.1.1一、作为立法活动的法律解释的含义
-
1.4.6.1.2二、现行中国法律解释体制
-
1.4.6.2第二节 作为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
-
1.4.6.2.1一、作为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的含义
-
1.4.6.2.2二、作为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
1.4.6.2.3三、作为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的目标
-
1.4.6.2.4四、作为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的方法
-
1.5第五编 范 畴 论
-
1.5.1第十六章 权利与义务
-
1.5.1.1第一节 权利与义务释义
-
1.5.1.1.1一、权利与义务的含义
-
1.5.1.1.2二、权利与义务的类型
-
1.5.1.2第二节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1.5.1.2.1一、权利与义务的相关相存
-
1.5.1.2.2二、权利与义务的互补互促
-
1.5.1.2.3三、权利与义务的等量等值
-
1.5.1.2.4四、权利与义务的对立一致
-
1.5.1.3第三节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
1.5.1.3.1一、依存
-
1.5.1.3.2二、区别
-
1.5.1.3.3三、冲突
-
1.5.1.4第四节 法律关系、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
-
1.5.1.4.1一、法律关系概述
-
1.5.1.4.2二、法律关系的要素
-
1.5.1.4.3三、法律责任
-
1.5.1.4.4四、法律制裁
-
1.5.2第十七章 人治与法治
-
1.5.2.1第一节 人治及其主要历史形态
-
1.5.2.1.1一、神治
-
1.5.2.1.2二、德治
-
1.5.2.2第二节 法治及其历史表现
-
1.5.2.2.1一、法治的思想脉络
-
1.5.2.2.2二、法治的制度演变
-
1.5.2.3第三节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
1.5.2.3.1一、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基本范畴
-
1.5.2.3.2二、依法治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
1.5.3第十八章 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
-
1.5.3.1第一节 法律规范
-
1.5.3.1.1一、法律规范释义
-
1.5.3.1.2二、法律规范与相关概念辨析
-
1.5.3.2第二节 法律事实
-
1.5.3.2.1一、法律事实的含义与特征
-
1.5.3.2.2二、法律事实的分类
-
1.5.3.2.3三、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
1.5.3.2.4四、法律事实的认定
-
1.5.3.3第三节 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关系
-
1.5.3.3.1一、事实的法律意义
-
1.5.3.3.2二、法律的事实意义
-
1.5.3.3.3三、法律事实与规范的连接方式
-
1.5.3.4第四节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
1.5.3.4.1一、基本要求
-
1.5.3.4.2二、内在根据
-
1.5.4第十九章 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
-
1.5.4.1第一节 法律意识
-
1.5.4.1.1一、法律意识的界定
-
1.5.4.1.2二、法律意识的类型
-
1.5.4.2第二节 法律行为
-
1.5.4.2.1一、法律行为释义
-
1.5.4.2.2二、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
1.5.4.2.3三、法律行为的类型
-
1.5.4.3第三节 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关系
-
1.5.4.3.1一、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相互区别
-
1.5.4.3.2二、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相互联系
-
1.5.5第二十章 法的应然与实然
-
1.5.5.1第一节 法的应然与实然范畴的历史演变
-
1.5.5.1.1一、自然法学说对法的应然的追问
-
1.5.5.1.2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法的实然的探究
-
1.5.5.1.3三、现代西方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的争论
-
1.5.5.2第二节 法的应然与实然的法学意义
-
1.5.5.2.1一、道德与法律
-
1.5.5.2.2二、价值与事实
-
1.5.5.2.3三、规律与法律
-
1.5.6第二十一章 法的实体与程序
-
1.5.6.1第一节 实体法与程序法
-
1.5.6.1.1一、实体、实体法与程序、程序法的定义
-
1.5.6.1.2二、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
1.5.6.2第二节 法律程序的意义
-
1.5.6.2.1一、程序性是法的基本特征
-
1.5.6.2.2二、正当性是衡量法律程序的独特标准
-
1.5.6.2.3三、正当程序具有独立价值
-
1.6第六编 价 值 论
-
1.6.1第二十二章 法的价值的一般理论
-
1.6.1.1第一节 法的价值的释义与分类
-
1.6.1.1.1一、法的价值的释义
-
1.6.1.1.2二、法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
1.6.1.2第二节 法的价值的功能与流变
-
1.6.1.2.1一、法的价值的功能
-
1.6.1.2.2二、法的价值的流变
-
1.6.1.3第三节 法的价值冲突与整合
-
1.6.1.3.1一、法的价值冲突界定
-
1.6.1.3.2二、法的价值冲突的原因
-
1.6.1.3.3三、法的价值冲突的表现模式
-
1.6.1.3.4四、法的价值冲突的整合
-
1.6.2第二十三章 人权
-
1.6.2.1第一节 人权的基本含义
-
1.6.2.1.1一、对“人权”一词的不同解说
-
1.6.2.1.2二、人权的定义与构造
-
1.6.2.2第二节 人权的本质属性
-
1.6.2.2.1一、西方学者的观点
-
1.6.2.2.2二、人权的本质属性
-
1.6.2.3第三节 人权的分类
-
1.6.2.4第四节 人权与法律的相互关系
-
1.6.2.4.1一、人权和法律相互结合的历程
-
1.6.2.4.2二、人权法律化的内在根据
-
1.6.2.4.3三、法对人权的作用
-
1.6.3第二十四章 正义
-
1.6.3.1第一节 正义理论的历史回顾
-
1.6.3.1.1一、古代法哲学时期
-
1.6.3.1.2二、中世纪法哲学时期
-
1.6.3.1.3三、近代法哲学时期
-
1.6.3.2第二节 正义的法律价值
-
1.6.3.2.1一、作为法律价值批判标准的正义
-
1.6.3.2.2二、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正义
-
1.6.3.3第三节 法律正义的当代主题
-
1.6.3.3.1一、宪政人权
-
1.6.3.3.2二、多样宽容
-
1.6.3.3.3三、形式平等
-
1.6.3.3.4四、社会利益
-
1.6.4第二十五章 法律与秩序
-
1.6.4.1第一节 秩序
-
1.6.4.1.1一、秩序
-
1.6.4.1.2二、社会秩序
-
1.6.4.2第二节 法律秩序
-
1.6.4.2.1一、法律秩序
-
1.6.4.2.2二、法律秩序的基本特征
-
1.6.4.3第三节 法律的秩序价值
-
1.6.4.3.1一、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
-
1.6.4.3.2二、法律对秩序的作用
-
1.6.4.4第四节 秩序与自由
-
1.6.4.4.1一、法律自由
-
1.6.4.4.2二、法律自由的存在形式
-
1.6.4.4.3三、秩序对自由的功能
-
1.6.4.4.4四、自由对秩序的功能
-
1.6.4.4.5五、秩序与自由的冲突与整合
-
1.6.5第二十六章 效率
-
1.6.5.1第一节 效率与法律的效率分析
-
1.6.5.1.1一、效率的含义
-
1.6.5.1.2二、法律的效率分析
-
1.6.5.2第二节 效率与法律的关系
-
1.6.5.2.1一、法律对效率的功能
-
1.6.5.2.2二、效率对法律的价值
-
1.6.5.3第三节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1.6.5.3.1一、公平的含义
-
1.6.5.3.2二、公平的分类
-
1.6.5.3.3三、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与协调
-
1.7第七编 关 联 论
-
1.7.1第二十七章 法与政治
-
1.7.1.1第一节 法与政治的一般关系
-
1.7.1.1.1一、政治的概念
-
1.7.1.1.2二、法与政治的联系和区别
-
1.7.1.2第二节 法与政策
-
1.7.1.2.1一、政策的概念
-
1.7.1.2.2二、法与政策的一致性和区别
-
1.7.1.2.3三、法与政策的相互作用
-
1.7.1.3第三节 法与民主
-
1.7.1.3.1一、民主的概念及其分类
-
1.7.1.3.2二、法与民主的关系
-
1.7.1.4第四节 法与政治文明
-
1.7.1.4.1一、政治文明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1.7.1.4.2二、法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
1.7.1.4.3三、法治国家对政治文明的意义
-
1.7.2第二十八章 法律与道德
-
1.7.2.1第一节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由来
-
1.7.2.1.1一、西方法学史上有关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观点
-
1.7.2.1.2二、“二战”后围绕法与道德关系的几次重要论战
-
1.7.2.2第二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
1.7.2.2.1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
-
1.7.2.2.2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
1.7.2.2.3三、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作用
-
1.7.3第二十九章 法与文化
-
1.7.3.1第一节 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
1.7.3.1.1一、文化的定义
-
1.7.3.1.2二、文化的内在结构
-
1.7.3.1.3三、文化的外在分类
-
1.7.3.2第二节 法与文化的关系
-
1.7.3.2.1一、作为文化现象的法律
-
1.7.3.2.2二、法律的文化解释
-
1.7.4第三十章 法律与科学技术
-
1.7.4.1第一节 法律与科学技术的联系与区别
-
1.7.4.1.1一、科学技术概说
-
1.7.4.1.2二、法律与科学技术的联系
-
1.7.4.1.3三、法律与科学技术的区别
-
1.7.4.2第二节 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
1.7.4.2.1一、科学技术对法律意识的影响
-
1.7.4.2.2二、科学技术对法律规范的影响
-
1.7.4.2.3三、科学技术对法律运行的影响
-
1.7.4.2.4四、科学技术对法学教育的影响
-
1.7.4.3第三节 法律对科学技术的作用
-
1.7.4.3.1一、法律为科学技术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1.7.4.3.2二、法律引导、组织和管理科技活动
-
1.7.4.3.3三、法律促进科技成果的合理利用
-
1.7.4.3.4四、法律推动国际科技合作
-
1.7.4.3.5五、法律防范与消解科技的负面效应
-
1.7.4.4第四节 依法治国与建设创新型国家
-
1.7.4.4.1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确立
-
1.7.4.4.2二、依法治国方略与创新型国家战略
-
1.7.5第三十一章 和谐与法律
-
1.7.5.1第一节 和谐与法律的思想渊源
-
1.7.5.1.1一、西方的和谐法律观
-
1.7.5.1.2二、中国历史上的和谐法律观
-
1.7.5.1.3三、当代中国的和谐法律观
-
1.7.5.2第二节 和谐的立法观
-
1.7.5.2.1一、从斗争法律观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
-
1.7.5.2.2二、从形式正义向社会公平立法观的转变
-
1.7.5.2.3三、从利益分化向多元利益整合的立法观转变
-
1.7.5.3第三节 和谐的执法观
-
1.7.5.3.1一、和谐司法观
-
1.7.5.3.2二、和谐执法观
-
1.7.5.4第四节 法律对和谐的意义
-
1.7.5.4.1一、法律促进主体维度的和谐
-
1.7.5.4.2二、法律促进客体维度的和谐
-
1.7.5.4.3三、法律促进空间维度的和谐
-
1.7.5.4.4四、法律促进时间维度的和谐
-
1.7.6参考文献
-
1.7.7后 记
1
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