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暨南哲学文库》总序
-
1.2综合研究是先秦诸子研究的创新之路(代前言)
-
1.3目录
-
1.4文本解读与历史语境:《大学》格致说本义探析
-
1.5客卿政策与周秦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以韩非、李斯为例
-
1.5.1一 秦客卿制度与韩非、李斯之客秦
-
1.5.2二 秦始皇时期客卿政策的三次变化
-
1.5.3三 李斯之死与秦二世时期客卿政策的变化
-
1.5.4四 秦代文学思想与风格的变化
-
1.6子书编集、经典生成与“轴心时代”的再认识——以《韩非子》为个案的考察
-
1.6.1一 “经典生成”视野下的古书体例
-
1.6.2二 《韩非子》成书诸说平议
-
1.6.3三 《韩非子》的二次编集
-
1.6.4四 《初见秦》与《存韩》的意义
-
1.6.5五 “轴心时代”的再认识
-
1.7诸子文献与子学研究
-
1.7.1一 诸子文献之界定
-
1.7.2二 诸子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情况
-
1.7.3三 诸子文献在子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
1.7.4四 诸子文献在子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
-
1.8从出土文献看先秦“圣”观念的起源与演变[1]
-
1.8.1一
-
1.8.2二
-
1.8.3三
-
1.8.4四
-
1.8.5五
-
1.8.6六
-
1.9关于孔子办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
1.9.1一 孔子办学的时间地点
-
1.9.2二 孔子办学的层次规模
-
1.9.3三 孔子办学的组织管理
-
1.9.4四 孔子办学的经费来源
-
1.10孟子“久假而不归”的王霸之辨
-
1.11《春秋》的文本性质及记事原则[1]
-
1.11.1一 《春秋》的作者群体和时间框架
-
1.11.2二 《春秋》:鲁国的告庙文本
-
1.11.3三 《春秋》的记事原则
-
1.11.4结 语
-
1.12再论《中庸》的成书及作者问题
-
1.12.1一 关于《中庸》文本的争议
-
1.12.2二 文本特征
-
1.12.3三 余论
-
1.13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
1.13.1一 弃同求和:西周到春秋时代政治学的演进
-
1.13.2二 和而不同:孔子的协调政治论
-
1.13.3三 尚同:墨子的服从政治学
-
1.13.4四 人性之“同”与政治之“和”:孟、荀的政治学
-
1.14墨家三书略考
-
1.14.1一 《胡非子》小考
-
1.14.2二 《缠子》小考
-
1.14.3三 《田俅子》小考
-
1.14.4三 余论
-
1.15“学”、“术”之间:梁启超的墨学观及其思想主张的演变
-
1.15.1一 墨家精神与“新民”的塑造
-
1.15.2二 东方文化视野下的墨学观
-
1.15.3三 小结
-
1.16老子哲学的生存论特征及与儒家的分判
-
1.16.1一
-
1.16.2二
-
1.17《老子》第三十六章新研[1]
-
1.17.1引 言
-
1.17.2一 上下两段与古之谚语的关系
-
1.17.3二 战国秦汉时期对这两组谚语的解释
-
1.17.4三 老子对于上下两段谚语的哲学提炼
-
1.17.5余 论
-
1.18语词损益与哲理变迁——读《老子》札记
-
1.18.1一 “天下”与“神器”
-
1.18.2二 “知常”与“袭常”
-
1.18.3三 “袭明”与“曳明”
-
1.18.4四 “知”与“智”
-
1.18.5五 “声”与“圣”
-
1.18.6六 “圣”与“知”(智)
-
1.19道家无为观的思想内涵、诠释倾向与现代转化
-
1.19.1一 无为观念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
1.19.2二 无为观念的诠释倾向
-
1.19.3三 无为观念的现代转化
-
1.20公孙龙“指物论”新解
-
1.20.1一 公孙龙“指物论”研究现状
-
1.20.2二 《指物论》疏解
-
1.20.3三 “指”、“物”概念之辨析
-
1.21今本先秦诸子书与《庄子》之关系
-
1.21.1一 《管子》与《庄子》之关系
-
1.21.2二 《慎子》与《庄子》之关系
-
1.21.3三 《鹖冠子》与《庄子》之关系
-
1.22论《庄子》内篇中“圣人”的基本涵义
-
1.22.1一 《逍遥游》与《齐物论》中的“圣人”
-
1.22.2二 《人间世》到《应帝王》的“圣人”
-
1.22.3三 内篇所论“圣人”的主要涵义
-
1.23楚简《恒先》分章与语译
-
1.23.1一 缘起
-
1.23.2二 分章
-
1.23.3三 语译
-
1.23.4四 说明
-
1.24《论语》“君子”意义分疏
-
1.24.1一 “君子”指称有官位者
-
1.24.2二 “君子”指称兼有德位者
-
1.24.3三 “君子”泛指有道德者
-
1.24.4四 “君子”指称兼有道德和生活理性者
-
1.25先秦文献中的“太一”概念及相关问题
-
1.25.1一 “太一”与“道”——作为哲学的终极概念
-
1.25.2二 “太一”概念在战国时期的发展演变
-
1.25.3三 《文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太一”引发的思考
-
1.26《汉志·诸子略·农家》通考
-
1.27《吕氏春秋》的阴阳五行思想[1]
-
1.27.1一 “四时教令”思想
-
1.27.2二 “五德终始”思想
-
1.27.3三 “祥符应”思想
-
1.28谈谈《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三秋”思想——兼论杂家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
1.28.1一 杂家代表人物之特殊身份与立场
-
1.28.2二 诸子融汇于杂家之内在逻辑
-
1.28.3三 《吕氏春秋》的兵刑农战之说
-
1.28.4四 杂家与中国文学观念之确立
-
1.29论《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
-
1.29.1一 《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1.29.2二 “兼儒、墨”——《吕氏春秋》对儒、墨的学术批评
-
1.29.3三 “合名、法”——《吕氏春秋》对名家和法家的批评
-
1.29.4四 《吕氏春秋》对从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的学术批评
1
先秦诸子研究论文集
 ”“
”“ ”“
”“ ”,亦作
”,亦作 ”“
”“ ”“
”“ ”,或支作“
”,或支作“ ”,(后上七·一〇);帛书《老子》乙本作“
”,(后上七·一〇);帛书《老子》乙本作“ ”,《古文四声韵》与之相近;《华岳碑》作“
”,《古文四声韵》与之相近;《华岳碑》作“ ”。从“口”从“耳”,或从双“口”并从“耳”(
”。从“口”从“耳”,或从双“口”并从“耳”( )。(二)甲骨文(乙五一六一)作“
)。(二)甲骨文(乙五一六一)作“ ”,《克鼎》作“
”,《克鼎》作“ ”,从“口”“耳”下为“人”。(三)作“
”,从“口”“耳”下为“人”。(三)作“ ”,如《师望鼎》《睡虎地秦简·日乙》,郭店楚简《语丛一》《成之闻之》《老子》甲本等;上博简多写作“
”,如《师望鼎》《睡虎地秦简·日乙》,郭店楚简《语丛一》《成之闻之》《老子》甲本等;上博简多写作“ ”,是“耳”下之“人”演化为“壬”而成,后世繁体“聖”即由此而来。(四)甲骨文(粹一二二五)作“
”,是“耳”下之“人”演化为“壬”而成,后世繁体“聖”即由此而来。(四)甲骨文(粹一二二五)作“ ”,乃声(聲)之初文。赵诚先生认为“像以殳击
”,乃声(聲)之初文。赵诚先生认为“像以殳击 。会声闻于耳之意,当是声之本字”[2]。
。会声闻于耳之意,当是声之本字”[2]。 ,从口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之动作则为听。圣、声、听均后起之字也。《左传》圣姜,《公》《谷》作声姜,知声、圣为古今字,后乃引申为贤圣字,三字遂分化矣。”[3]于省吾先生解释:“
,从口耳会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为声,其得声之动作则为听。圣、声、听均后起之字也。《左传》圣姜,《公》《谷》作声姜,知声、圣为古今字,后乃引申为贤圣字,三字遂分化矣。”[3]于省吾先生解释:“ 亦作
亦作 ,从二口与从一口同,古文有繁省耳。魏三体石经《书·无逸》‘此厥不听’,古文听作
,从二口与从一口同,古文有繁省耳。魏三体石经《书·无逸》‘此厥不听’,古文听作 。《古文四声韵》下平十八青引《义云章》听作
。《古文四声韵》下平十八青引《义云章》听作 ,是以
,是以 为听也。又去声四十七‘劲’引古《老子》,圣作
为听也。又去声四十七‘劲’引古《老子》,圣作 ,是以
,是以 为圣也。又下平十七清引《华岳碑》,声作
为圣也。又下平十七清引《华岳碑》,声作 ,是以
,是以 为声也。金文圣字,早期作
为声也。金文圣字,早期作 ,晚期加壬为声符作圣。此以形证之知古听、圣、声之本作
,晚期加壬为声符作圣。此以形证之知古听、圣、声之本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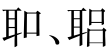 也。”并广引《礼记·乐记》、秦《泰山刻石》《墨子》《史记》等,以传世载籍证之,“古听、圣、声之通用也”,谓“契文聲字僅一见,《粹》1225有
也。”并广引《礼记·乐记》、秦《泰山刻石》《墨子》《史记》等,以传世载籍证之,“古听、圣、声之通用也”,谓“契文聲字僅一见,《粹》1225有 字,上已残,应补作
字,上已残,应补作 ,从
,从 ,殸声,即古声字”[4]。“听”“圣”“声”三字相通之说,郭沫若、于省吾、顾颉刚、李孝定、唐兰等先生都作了文字学的研究[5],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紧扣先秦思想文化背景与近年出土简帛文献,对“圣”的使用情况做综合考察,把他们的努力推向深入。
,殸声,即古声字”[4]。“听”“圣”“声”三字相通之说,郭沫若、于省吾、顾颉刚、李孝定、唐兰等先生都作了文字学的研究[5],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紧扣先秦思想文化背景与近年出土简帛文献,对“圣”的使用情况做综合考察,把他们的努力推向深入。 ”
” ”“听”“圣”等不同写法[6]。
”“听”“圣”等不同写法[6]。 ”“
”“ ”
” ”等字形本身已经透露了文字出现以前某些文化观念的消息。从上举第一类字形来看,“圣”之初义应是“入于耳而出于口”、或“出于口而入于耳”,乃是指口语交流中的“口有所言,耳得之”之“声”,或者“其得声之动作”之“听”,抑或同时包括两个方面的“口口”交流与“口口相传”,故楚简称“人苟有言,必闻其圣(声)”(《缁衣》40背)。因此,“
”等字形本身已经透露了文字出现以前某些文化观念的消息。从上举第一类字形来看,“圣”之初义应是“入于耳而出于口”、或“出于口而入于耳”,乃是指口语交流中的“口有所言,耳得之”之“声”,或者“其得声之动作”之“听”,抑或同时包括两个方面的“口口”交流与“口口相传”,故楚简称“人苟有言,必闻其圣(声)”(《缁衣》40背)。因此,“ ”“
”“ ”
” ”正是对文字出现以前的上古口传文明的概括和无意识记录。
”正是对文字出现以前的上古口传文明的概括和无意识记录。 字用法有二……一
字用法有二……一 为听(
为听( )闻之听。《后》下三〇·一八:‘方亡
)闻之听。《后》下三〇·一八:‘方亡 。’言方国无所听闻。……《续》一·一三·五:‘
。’言方国无所听闻。……《续》一·一三·五:‘ 方亡.
方亡. (闻)。’听闻同义。《藏》二·三:‘归其
(闻)。’听闻同义。《藏》二·三:‘归其 (有)
(有) 。’亡听与有听,语有反正耳。一
。’亡听与有听,语有反正耳。一 为听治之听。《书大传·周传》:‘诸侯不同听。’注:‘听议狱也。’《书·洪范》:‘四曰听。’疏:‘听者受人言察是非也。’《周礼·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注:‘听平治也。’《荀子·王霸》:‘要百事之听。’注:‘听治也。’《王制》:‘听之绳也。’注:‘听,听政也。’是古谓听为议狱为平治为听政,均听治之义也。《前》六·五四·七:‘王
为听治之听。《书大传·周传》:‘诸侯不同听。’注:‘听议狱也。’《书·洪范》:‘四曰听。’疏:‘听者受人言察是非也。’《周礼·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注:‘听平治也。’《荀子·王霸》:‘要百事之听。’注:‘听治也。’《王制》:‘听之绳也。’注:‘听,听政也。’是古谓听为议狱为平治为听政,均听治之义也。《前》六·五四·七:‘王 。’言王听治也。《戬》四五·九:‘王
。’言王听治也。《戬》四五·九:‘王 不隹
不隹 。’契文言
。’契文言 与《易》言咎同。言王听不隹咎也。《戬》四五·十:‘王
与《易》言咎同。言王听不隹咎也。《戬》四五·十:‘王 隹
隹 。’言有
。’言有 则不利于听治也。《
则不利于听治也。《 》一·九:‘王
》一·九:‘王 不隹于唐∂。’言王之听治唐不
不隹于唐∂。’言王之听治唐不 王也。殷王之动作,无事不占,况临朝听治之大事,岂能无所贞卜乎。……
王也。殷王之动作,无事不占,况临朝听治之大事,岂能无所贞卜乎。…… 古听字。听从壬声,乃后世所加之声符。”[7]而《尚书》有关“听”政的记录也很多,如《虞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疏云:我欲闻知六律,和五声,播之于八音,以此音乐察其政治与忽怠者,其乐音又以出纳五德之言,汝当为我听审之。我有违道,汝当以义辅成我。《商书·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其中的“视”、“听”,即政治治理上的鉴察是非、识知善恶。不难看出,文字还未通行的上古“听政”,包括以八音等音声、乐歌来察辨政治忽怠与否、以视听来分辨是非善恶和评断狱、讼等多方面的内容。
古听字。听从壬声,乃后世所加之声符。”[7]而《尚书》有关“听”政的记录也很多,如《虞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疏云:我欲闻知六律,和五声,播之于八音,以此音乐察其政治与忽怠者,其乐音又以出纳五德之言,汝当为我听审之。我有违道,汝当以义辅成我。《商书·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其中的“视”、“听”,即政治治理上的鉴察是非、识知善恶。不难看出,文字还未通行的上古“听政”,包括以八音等音声、乐歌来察辨政治忽怠与否、以视听来分辨是非善恶和评断狱、讼等多方面的内容。 、
、 )来统称文字产生以前的口传文明。《礼记·乐记》说得很明确:“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能“识”、能称述、复述已经存在的(礼乐)文明就叫“述”,显然,这个“述”仅仅是指用语言文字对口传文化中实际施用的制度和文明进行整理和记录。[11]
)来统称文字产生以前的口传文明。《礼记·乐记》说得很明确:“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能“识”、能称述、复述已经存在的(礼乐)文明就叫“述”,显然,这个“述”仅仅是指用语言文字对口传文化中实际施用的制度和文明进行整理和记录。[1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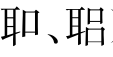 )”这个字,记录、沉淀着如此多的文明因子,同如此多的文化巨擘联系在一起,这是它具有超凡和神圣性的原因之一,也是未有文字的语音时代、口传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而且,“出于口而入于耳”、“声入心通”的独特能力在那个大部分人尚未开化的文明起步时代是如此不同凡响——语音能力意味着拥有至高的权威,“语言就是权力本身”,而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或权力的一部分:话语权。拥有话语的能力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已经启蒙、开化的思想的能力,这是可以同武力相提并论的力量。巫师正是因为拥有垄断性的话语能力而赢得了同王权和野蛮武力相抗衡的地位,甚至成为师、王合一的独特“巫王”——当然“巫”还必须有一种能沟通神人的独特话语能力。因此,拥有话语,正是“圣(
)”这个字,记录、沉淀着如此多的文明因子,同如此多的文化巨擘联系在一起,这是它具有超凡和神圣性的原因之一,也是未有文字的语音时代、口传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而且,“出于口而入于耳”、“声入心通”的独特能力在那个大部分人尚未开化的文明起步时代是如此不同凡响——语音能力意味着拥有至高的权威,“语言就是权力本身”,而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或权力的一部分:话语权。拥有话语的能力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已经启蒙、开化的思想的能力,这是可以同武力相提并论的力量。巫师正是因为拥有垄断性的话语能力而赢得了同王权和野蛮武力相抗衡的地位,甚至成为师、王合一的独特“巫王”——当然“巫”还必须有一种能沟通神人的独特话语能力。因此,拥有话语,正是“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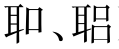 )”拥有超凡性和神秘性的基本原因,并成为口传文化的符号性表征。
)”拥有超凡性和神秘性的基本原因,并成为口传文化的符号性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