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与历史语境:《大学》格致说本义探析
常 森
《大学》云:“古之……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格物”、“致知”究为何意,是前儒颇为懵懂且争拗甚多的重要问题。我们先检视一下前人的代表性观点。
郑玄(127—200)释“致知在格物”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郑玄的解读有一个严重问题,即颠倒了“致知”和“格物”的逻辑关系。钱穆批评道:“此则说成‘格物在致知’矣。可证‘格物’一解,汉儒已失其义。”[1]——汉儒失却“格物”、“致知”本义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失却了这一学说的历史语境,这一点下文再作细论。
郑注之后,影响深远也备受争议的,是朱子章句及补传。朱子注“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云:“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注“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云:“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朱子补传则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钱穆曾经评价说:“……朱子格物补传,实为尊信程朱学者之圭臬。今纵谓朱子补传无当于《大学》原本之真相,然自朱子以来七百年,此格物补传固已与旧本《大学》凝成一体,已为一尽人必读之经典矣,固不应忽昧而不知。”[2]从思想史角度看,钱氏此说堪称的评,可是对《大学》本旨而言,至少其立场有一点暧昧。本文更关注的是朱子补传在多大程度上掘发了《大学》本义。从现有材料来看,说《大学》原有这一部分文字固然缺乏实证,可朱子释“致知在格物”为“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旨当不谬,惟不够具体明晰而已。刘宗周《大学杂言》云:“朱子之补传,善会之即古本之意也,以为支离而斥之者,亦过也。”[3]殆是。
朱子格物补传之大旨是循物求知,反其意者则往往倾向于遗物而求心。王阳明释云:“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4]又云:“‘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5]简言之,王氏以为格物即格意念所在之事,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王阳明还强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6]。刘宗周认为朱熹、王阳明所代表的两条路径,均有缺失。他说:“自格致之旨晦,而圣学沦于多歧:滞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离耳目而言知者,遗物者也。徇物者,弊至于一草一木亦用工夫,而遗物求心,又逃之无善无恶,均过也。故阳明以朱子为支离,后人又以阳明之徒为佛、老,两者交讥而相矫之,不相为病。入《大学》之道者,宜折衷于斯。”[7]刘氏之批评颇有可取之处,但仍未回归《大学》文本所确立之系谱。实际上,王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就《大学》所立系谱而言,“格物”一节尚未及“知止”、“知至”阶段,何以论正与不正、善与不善呢?
而湛若水(1466—1560)《答阳明》书称:“鄙见以为,‘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随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8]此论之弊,与上揭阳明之说颇类。就《大学》所立系谱而言,“格物”一节尚未及“知止”、“知至”,道为何物尚且未知,何有“造道”可言呢?
刘宗周《大学杂言》综评,云:“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约之亦不过数说。‘格’之为义,有训‘至’者,程子、朱子也;有训‘改革’者,杨慈湖也;有训‘正’者,王文成也;有训‘格式’者,王心斋也;有训‘感通’者,罗念庵也。其义皆有所本,而其说各有可通,然从‘至’为近。”复云:“诸生讲《大学》。一夕,偶思而得之,因谓诸生曰《大学》一篇是人生全谱。试思吾辈坐下只此一身,渐推开去,得家、国、天下,渐约入来,得心、意、知。然此知不是悬空起照,必寄之于物,才言物,而身与家、国、天下一齐都到面前,更无欠剩。即尔诸生身上,此时知在起居,便有起居之物理可格;知在饮食,便有饮食之物理可格。推此以往,莫不皆然。物无不格,则知无不至,至于意得诚,至于心得正,至于身得修,至于家得齐,至于国得治,至于天下得平,而先后之序,自不容紊,真是天造地设规模,一了百当道理,非人道全谱而何?”[9]《大学》“格物”之“格”确当为至之义,然刘氏似将“格物”解为“物格(至)”,将“物格而后知至”解为“知至而后物格”,而基于“格物”之“知至”,则与夫“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混同为一了。
宋翔凤(1779—1860)在郑玄释“致知在格物”的基础上,引祥瑞之说,解“格物”之意,云:“郑君释此文云,‘格,来也’;言‘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是格物者,诚、正、修、齐、治、平之效验也。故言‘在’而不言‘先’,言其效验无往不在。‘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此格物之谓也。”[10]这是完全不顾《大学》本旨的想象,尽管号称“古义”,在旧说中可能是最为怪异的。就《大学》所立系谱而言,“格物”尚未及“知止”、“知至”阶段,更无论诚、正、修、齐、治、平,何有“诚、正、修、齐、治、平之效验”可言呢?宋氏一如郑玄等学者,直把入道成德过程之始端当成了终了。
要之,自汉迄清,论“格致”之意者甚多,然犹治丝而棼之也。现代学者依违于旧说之间,左支右绌,往往不能免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之窘境。饶宗颐先生一九五〇年作《格物论》,云:饶先生之论究竟是否得《大学》“格物”本义,恐怕还需要商榷。《大学》所陈系谱始言“格物”,至“致知”一节方及知所止,亦即于格物阶段,礼乐为何物尚且未定,何者为正且亦未明,更无论持之守之了,故认为“言‘格物’而礼、乐赅其中”或“‘格物’必先齐之以礼”,认为“‘格物’者,谓成于物,而动不失其正也”或“‘格物’者,物来而应之以正”,等等,终究与《大学》原意有隔。
“格物”者,谓成于物,而动不失其正也。《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千古阐“格物”之义,无如此段之深切。“格物”者,物来而应之以正。必也能化物而别物。化物者,乐之事;别物者,礼之事。是言“格物”而礼、乐赅其中矣。夫化物斯能和,别物斯能序。和,故百物不失节而合爱;序,故百物皆纳轨(《左传》所谓纳民轨物)而合敬。爱自中出,敬由外作,如是则物罔不格矣。《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斯即明明德矣。故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以是立己,则物来无碍(格物之格之训来,犹庶民来子之来,谓不期而至,不期而会,不期而得。格物亦犹不期而有得于物,以本乎天道,循乎德性,故能如此。仁民爱物,物我之间,固一致也。益知郑注陈义之精)。以是化民,则民诚悦而有格心;是格物者,其事必先乎礼。《仲尼燕居》云:“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礼所以治事,物犹事也;事治则物格,物格固莫尚于礼矣。故曰格物必先齐之以礼。以《礼记》证《礼记》,则《大学》“格物”一义,可了然无滞碍矣。[11]
钱穆一九五三年撰《大学中庸释义》,其论有曰:“‘格物’一义,自明儒以下,纷纷无定论。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古书如此‘物’字甚多,如曰‘言有物而行有则’,又曰‘孝子不过乎物’。不过于物,即‘格物’也。‘格物’,即‘止于至善’也。‘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此即君与臣之至善。在未能致知以前,尚未能真知其为至善之义,则变其辞曰‘格物’。”[12]案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礼记·缁衣》)[13]孔子又说:“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礼记·哀公问》)郑玄注云:“物,犹事也。事亲、事天,孝、敬,同也。《孝经》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举无过事,以孝事亲,是所以成身。”疏云:
“仁人不过乎物”者,物,事也;言仁德之人不过失于其事,言在事无过失也。〇“孝子不过乎物”者,言孝子事亲,亦于事无过也。〇“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者,言仁人事亲以敬,如与事天相似,言敬亲与敬天同。〇“事天如事亲”者,言仁人事天以孝爱,如人事亲孝爱相似,言爱亲与爱天同。〇“是故孝子成身”者,上称“仁人”,则“孝子”也,据其泛爱,则称“仁人”,据其事亲,则称“孝子”。内则孝敬于父母,外则孝敬于天地。其间无所不行孝敬,故云“孝子成身”也。
钱穆基于传世儒典所载“孝子不过乎物”等说法,将《大学》“格物”解释成“止于至善”,认为只是因为“在未能致知以前,尚未能真知其为至善之义”,变其辞而曰“格物”。然而据《大学》本文,“止于至善”当指“明明德”(具体落实为格→致→诚→正→修)与“亲(新)民”(具体落实为齐→治→平)两面均达至善之地而不移,“格物”仅仅为“明明德”一面遥远微细之始端,将“格物”等同于未被真知的“止于至善”,还是抹杀了《大学》强调“先后”之意,有本末倒置之弊。
那么,《大学》“格物”、“致知”两个具有生成性关联的环节究竟为何义呢?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以下两点:
一是回归《大学》文本所含的小语境。既然要阐释文本,那么文本就是第一义的,要善于把握其中互相关联、互相发明、互相证成的元素。毛奇龄《大学证文》卷一有云:“予读《大学》,以为‘格物’、‘致知’安有如后儒之纷纷者乎?既而读‘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之文,亦恍然曰,格致之义前圣自解之矣……”[14]毛奇龄的认知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具体说解仍有待完善。
依《大学》本文,格物致知,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格物使知至(原文申说部分尚存留着结语“此谓知之至也”,惜乎前面的申说亡佚)。《说文解字·木部》云:“格,木长貌,从木各声。”段注称:“木长貌者,‘格’之本义。引伸之,长必有所至,故《释诂》曰‘格……至也’,《抑》诗传亦曰‘格,至也’。凡《尚书》‘格于上下’、‘格于艺祖’、‘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也。此接于彼曰‘至’,彼接于此则曰‘来’。郑注《大学》曰:‘格,来也。’凡《尚书》‘格尔众庶’、‘格汝众’,是也。”究其实际,“格”虽有“来”义,郑解《大学》“格物”之“格”为“来”,却并不确当。《大学》“格物”之“格”当为“至”义,强调的是主体接物(即段注所谓的“此接于彼”),而非物来接于主体。朱熹补传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以“即”释“格”,同样强调主体之接物,堪称得之。战国学者对认知之机理有所认识。《墨子·经上》篇谓“知,接也”,就是说知意味着人以其智与物(即认知对象)交接;《墨子·经上》又谓“知(智),材也”,是说智是人所以知的资质。在传世《大学》文本中,“格物”的具体申说虽然缺失,但其本旨还是有迹可寻的。要之,“格物”即主体主动接物以考察、探究之,为“致知”之门径(揆之以理,“格物”未必能“致知”,但欲“致知”,则必须“格物”,故曰“致知在格物”)。论及这种意义上的“格”以及“格物致知”,需要高度关注《尚书·大诰》篇所谓“格知”。其文曰:“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一般认为《大诰》为周公作[15],其所谓“格知”常被理解为度知。实际上,“格知天命”可以理解为交接天命,探究而知之。《大学》“格物”、“致知”,与《大诰》之“格知”当不无联系。其所格之物,既包括主体之身心以及主体之外的天地万物,也包括典籍、圣言、师教等等[16]。以前者为对象之格物致知,可称作“直接格物致知”;以后者为对象之格物致知,可称作“间接格物致知”(乃是通过探究典籍或他人言语中呈现之物,达成对价值的认知;或说是藉助典籍与他人之言谈,获取他人格物所得之价值)。“致知”一词原本不难理解,这里仅仅强调,《大学》所欲致之知为何,在文本中落实于“知止”与“知本”(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于止,知其所止”以及“此谓知本”)。前者之要删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后者之要删为:“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17]“致知”在过去同样遭到滥解,但它在文本中的界定和立意是相当明确的,即不是指追求一般、普泛的知,而是指追求安身立命、修齐治平之知。这种取向,在孔子那里已经显露了端倪。《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荀子·儒效》篇云:“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先秦儒家所谓“致知”之要本,由此亦可知矣。
《大学》云:“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前三语意谓,富有则其屋修饬,有德则其身修饬,心宽宏则体舒泰。此三事皆可证成“有实于内,显见于外”(郑玄注),一如其上文所说“诚于中形于外”,故结之以“君子必诚其意”。这是《大学》中直接格物致知的显例,观照的是世间富者之事象、有德者之事象、心宽者之事象,证成的是内心与外形的必然性关联以及“诚其意”的重要性。《大学》又说:“《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段文字,主要是通过探究经典及圣人言教,来达成人不可不知所止的认知,为《大学》中间接格物致知的显例[18]。
二是将《大学》格致观念放到它形成的大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该语境部分地见于传世文献,而主要见于出土简帛。如此,其意指才更加确切和显白。宋明儒者将其过度形上化,玄而又玄,葛藤胶戾,不过是师心立说罢了。
毫无疑问,直接格物致知在学说创立时期十分重要,故儒家创始人孔子致力于此。古人尝评论道:“求诸孔圣之言,惟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一句最于致知格物极其渊妙。盖松柏,物也;察其因何而岁寒之际独后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则‘然后知’之三字为真致其知矣。何以见其格之正?如《礼器》所谓如松柏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则知其为得气之本而岁寒后凋矣,是也。”[19]事实上,认定孔子“岁寒”一句“最于致知格物极其渊妙”,至少有一点偏狭、不全面。孔子屡屡论析“君子”、“小人”德行之异,如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等等,彰显了他对芸芸众生的深刻认知;——千百年来,以及千百年后,世人之基本人格绝不外乎“君子”、“小人”两种。其他如孔子谓子夏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彰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凡此之类,均可见孔子直接格物致知之功,而在《论语》诸儒典中俯拾皆是,毋庸一一举列。
需要说明的是,直接格物致知应当包括主体对己身以及他者的省察。孔子论仁与恕,均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卫灵公》),又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意味着以己之所欲、所不欲,为对待他者的准则,把他者当成另外一个自我来体贴,其前提自然是针对己身的格致[20]。对早期儒家学者来说,只有以确立政教伦理价值为目的来探究己身,才有格致的意义。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种自省,主要是根据原已确认的价值,省察己身是否与之契合,大致当归结于《大学》八目中的修身。而孔子所谓“见贤思齐”,包含从他者发现价值的意义,此即以他者为对象的格物致知。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知柳下惠之贤”便属于这一类格致。
孔子自创立儒学时,便高度重视间接格物致知。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以传旧好古为职志,实即以往古典籍或圣贤为知之源。他光大了《诗》《书》《礼》《乐》《易》等经典的一部分价值,辅之以儒学价值转换,且又属辞比事撰作了《春秋》,将这六部经典建构为儒学价值之渊薮,用以教育三千弟子,并开化世间众生。郭店、上博儒典对孔子这番事业有极明确的总结。比如《眚自命出》上篇云:“凡 (道),心述(术)为宔(主)。
(道),心述(术)为宔(主)。 四述,唯人
四述,唯人 为可
为可 也。亓(其)厽(三)述者,
也。亓(其)厽(三)述者, 之而已。《时(诗)》《箸(书)》《豊(礼)》《乐》,亓
之而已。《时(诗)》《箸(书)》《豊(礼)》《乐》,亓 (始)出皆生于人。《时》,又(有)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豊》《乐》,又为
(始)出皆生于人。《时》,又(有)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豊》《乐》,又为 (举)之也。圣人比亓頪(类)而仑(论)会之,雚(观)亓(之
(举)之也。圣人比亓頪(类)而仑(论)会之,雚(观)亓(之 )〔先后〕而逆训(顺)之,体亓宜(义)而即(节)
)〔先后〕而逆训(顺)之,体亓宜(义)而即(节) (文)之,里(理)亓青(情)而出内(入)之,肰(然)句(后)复以教。教,所以生惪(德)于中者也。”(同样的文字也见于上博《眚
(文)之,里(理)亓青(情)而出内(入)之,肰(然)句(后)复以教。教,所以生惪(德)于中者也。”(同样的文字也见于上博《眚 论》)而《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
论》)而《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 (道)人
(道)人 也。《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豊(礼)》,交之行述(术)也。《乐》,或生(性)或教者也。《书》
也。《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豊(礼)》,交之行述(术)也。《乐》,或生(性)或教者也。《书》 者也。”凡此皆可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上博《诗论》当即孔子以《诗》教的记录。[21]总而言之,孔子视六艺为真知之渊薮,六艺被他确立为间接格物致知的核心对象。孔子尝曰:“(加)〔假〕我数年,(五十)〔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还对伯鱼(孔鲤,前532—前482)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作为致知之门径,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从孔子创派之初就被确认了,儒家经典建设和授受的基础也由孔子奠定。上博《诗论》第五章云:
者也。”凡此皆可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上博《诗论》当即孔子以《诗》教的记录。[21]总而言之,孔子视六艺为真知之渊薮,六艺被他确立为间接格物致知的核心对象。孔子尝曰:“(加)〔假〕我数年,(五十)〔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还对伯鱼(孔鲤,前532—前482)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作为致知之门径,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从孔子创派之初就被确认了,儒家经典建设和授受的基础也由孔子奠定。上博《诗论》第五章云:
孔子曰 (吾)
(吾) (以)《
(以)《 》得氏(祗)初之訔(志),民眚(性)古(固)然,见丌(其)
》得氏(祗)初之訔(志),民眚(性)古(固)然,见丌(其) (美),必谷(欲)反丌本。夫萭(葛)之见诃(歌)也,则
(美),必谷(欲)反丌本。夫萭(葛)之见诃(歌)也,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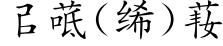 (绤)之古(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
(绤)之古(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 文、武之惪(德)也。
文、武之惪(德)也。
 《甘棠》得宗
《甘棠》得宗 (庙)之敬,民眚古然,甚贵丌人,必敬丌立(位),敚(悦)丌人,必好丌所为,亚(恶)丌人者亦然。
(庙)之敬,民眚古然,甚贵丌人,必敬丌立(位),敚(悦)丌人,必好丌所为,亚(恶)丌人者亦然。 《木苽》
《木苽》 (得)
(得) (币)帛之不可
(币)帛之不可 (去)也,民眚古然,丌
(去)也,民眚古然,丌 (隐)志必又(有)
(隐)志必又(有) 俞(喻)也。丌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
俞(喻)也。丌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 (触)也。
(触)也。
 杜》得雀□之不可无也,民眚古然,□□□□女此可,斯雀之矣。
杜》得雀□之不可无也,民眚古然,□□□□女此可,斯雀之矣。 (御)丌所㤅(爱),必曰:
(御)丌所㤅(爱),必曰: 奚舍之?宾赠氏(是)也。
奚舍之?宾赠氏(是)也。
这是孔子间接格物致知的显例。他基于人性省察《周南·葛覃》《召南·甘棠》《卫风·木瓜》以及《唐风·有杕之杜》,确认了德之重要性以及宗庙、币帛诸礼之根源。
在阅读经典以外,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之传播特赖口耳授受,故通过“闻”而知“道”分外重要。仅就《论语》所记,樊迟、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问仁(见《论语·雍也》《颜渊》《子路》《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见《论语·阳货》),鲁大夫孟懿子、其子孟武伯以及子游、子夏问孝(见《论语·为政》),林放问礼之本(见《论语·八佾》),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见《论语·学而》),樊迟问知(见《论语·雍也》),原宪问耻(见《论语·宪问》),子张问行(见《论语·卫灵公》),子贡问友(见《论语·颜渊》),子路问成人(见《论语·宪问》),子贡、司马牛问君子(见《论语·为政》《颜渊》),子贡、子路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见《论语·子路》),子贡问为仁(见《论语·卫灵公》),季路“问事鬼神”、“问死”(见《论语·先进》),子路、冉有问“闻斯行诸”(见《论语·先进》),子张问“崇德、辨惑”(见《论语·颜渊》),子路问事君(见《论语·宪问》),颜渊问为邦(见《论语·卫灵公》),子张问“何如斯可以从政矣”(见《论语·尧曰》),子贡、子张、子路、仲弓、子夏、叶公、季康子、齐景公问政(见《论语·颜渊》《子路》),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见《论语·为政》),鲁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见《论语·八佾》),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见《论语·为政》),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见《论语·子路》),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见《论语·卫灵公》),凡此之类,不一而足,孔子每每因其材、就其事而施以不同的教诲。
作为认知道术的途径,“听—闻”异常重要,尝以高度理论化的形态出现在儒、道诸家之体系中。《五行》经文第十八章云:“闻君子道,悤(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而)〔天〕道〔也〕。知而行之,(圣)〔义〕也。行之而时,德也。”《五行》说文第十八章释之曰:“‘闻君子道, (聪)也’:同之闻也,独色然辩于君子道,(道)〔
(聪)也’:同之闻也,独色然辩于君子道,(道)〔 也〕;〔
也〕;〔 也〕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亓(其)天之道也,是圣矣。圣人知天之道。道者,所道也。‘知而行之,义也’:知君子之所道而
也〕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亓(其)天之道也,是圣矣。圣人知天之道。道者,所道也。‘知而行之,义也’:知君子之所道而 然行之,义气也。‘行之而时,
然行之,义气也。‘行之而时, (德)也’:时者,和也。和也者(惠)〔
(德)也’:时者,和也。和也者(惠)〔 〕也。”这是说以“听—闻”获取对道的认知,而后付诸道德之修为。庄子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耳〕止于(耳)〔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内篇·人间世》)[22]“听之以气”实即秉持心之虚来听,看似玄奥,但说到底还是以听为获取道的途径。显然,在儒学授受的历史交接中,听师教或圣言以获取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道术,也是间接的格物致知。
〕也。”这是说以“听—闻”获取对道的认知,而后付诸道德之修为。庄子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耳〕止于(耳)〔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内篇·人间世》)[22]“听之以气”实即秉持心之虚来听,看似玄奥,但说到底还是以听为获取道的途径。显然,在儒学授受的历史交接中,听师教或圣言以获取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道术,也是间接的格物致知。
在学派成熟以后,因为其观念、价值体系臻于成熟和完备,负载该体系的经典臻于定型,直接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自然会有所下降,而以经典授受为核心的间接格物致知则愈发占据主导地位。儒家以六经为教材始于孔子创派之时,至孔门七十子,六经的位置已牢固确立(新见郭店、上博儒典可以为证)。其后,孟子进一步突出《春秋》,曾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对孔子本人及天下之意义,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荀子之时,六经地位已经坚确无疑。故《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明显以读经为第二义,以为士、为君子、为圣人为第一义,然而他并不脱离第二义来空谈第一义,因为不读经,第一义便无着手处。荀子又将“经”与《礼》相对,置《礼》于群经之上,推《礼》为学之终竟、“道德之极”,称《书》《诗》《乐》《春秋》诸书为“经”,但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礼》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礼》说到底也是“经”。故《荀子·大略》篇云:“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诗》《书》《礼》《乐》《春秋》诸经均为“道”之渊薮。因此《荀子·儒效》篇更明确地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读经以知“道”,与《大学》所说格物以致知同趣。《荀子》并不漠视《易》。其《大略》篇云:“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杨注云:相,谓为人赞相焉),其心同也。”拿《易》来与《诗》《礼》两经并列,当非偶然。总之自孔子至荀子,六经逐渐成为儒家核心典籍,读经以致知越发成为格物以致知的根本方式。正如徐复观所说,“在先秦时代,由孔子所开创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教化集团,是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中心而展开的”[23]。
朱熹云:“读书是格物一事。今且须逐段子细玩味,反来覆去,或一日,或两日,只看一段,则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后,却见头头道理都到。这工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个晓悟处出,不容安排也。书之句法义理,虽只是如此解说,但一次看,有一次见识。所以某书,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说定,一番看,一番见得稳当,愈加分晓。故某说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尔。然用工亦须是勇做进前去,莫思退转,始得。”又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还说:“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24]朱子把读书以致知的道理说得十分明白和透彻。
师教作为间接格物致知的重要一途,至荀子时也已确立。《荀子·修身》篇云:“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智)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其《性恶》篇也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顺服)使然也。”毫无疑问,以师教为致知之途,与以读书为致知之途有很高的同一性,因为师教的核心也是经典。
以上史实,从一定程度上证成了《大学》“格物”、“致知”的本意。而确认这些论断,需要特别关注见于新出简帛、与《大学》差不多同时代的儒典。
在以载录孔子《诗》说为核心的上博《诗论》中,有不少材料堪为间接格物致知的注脚。比如,《诗论》第五章记载,孔子透过《周南·葛覃》《召南·甘棠》《卫风·木瓜》《唐风·有杕之杜》,而认知人性的各种面相,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宗庙、币帛诸礼之所以然。这是间接格物致知的显例。而《诗论》第一章云:
孔子曰:《訔》,丌(其)猷塝门与?戋(残)民而 (逸)之,丌甬(用)心也
(逸)之,丌甬(用)心也 (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已。民之又(有)
(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已。民之又(有) (戚)
(戚) (惓)也,上下之不和者,丌甬心也
(惓)也,上下之不和者,丌甬心也 可女?曰《少
可女?曰《少 》氏(是)已。□□□□□□可女?曰《大
》氏(是)已。□□□□□□可女?曰《大 》氏已。又城(成)工(功)者可女?曰《讼》氏已。
》氏已。又城(成)工(功)者可女?曰《讼》氏已。
孔子通过读《诗》,读《邦风》《大雅》《小雅》以及《颂》,认知政教伦理之得失与民心之向背,也是间接格物致知的典型个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载录子思体系的《五行》直接凸显了《大学》“格物→致知”的本旨,或说基于《五行》,可以发前人千百年未发之覆。《五行》经文第二十三章云:“目(侔)而知之,胃(谓)之进之。”其说文第二十三章曰:《五行》经文第二十三章文字极为简括,然而很明显,所谓“目(侔)而知之,胃(谓)之进之”即落实为说文第二十三章中的“目(侔)万物之生(性)而知人独有仁义”、“目人 (体)而知亓(其)莫贵于仁义”,此二说堪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具体呈现。具体说来,《五行》说文第二十三章一系列申释和论证,如“循……(某某对象)则知……(某某道理)”、“源……(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等等,均亦呈现出“格物→致知”的理念和模式。《五行》经、说第二十三章中的“目”通“侔”;“目……(某某对象)而知……(某种道理或价值)”,意指主体接物,比较之而达成某种认知,如“目(侔)万物之生(性)”即主体交接草木、禽兽以及人之性而比较之,“目人
(体)而知亓(其)莫贵于仁义”,此二说堪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具体呈现。具体说来,《五行》说文第二十三章一系列申释和论证,如“循……(某某对象)则知……(某某道理)”、“源……(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等等,均亦呈现出“格物→致知”的理念和模式。《五行》经、说第二十三章中的“目”通“侔”;“目……(某某对象)而知……(某种道理或价值)”,意指主体接物,比较之而达成某种认知,如“目(侔)万物之生(性)”即主体交接草木、禽兽以及人之性而比较之,“目人 (之性)”即主体交接耳目、鼻口、手足以及心之性而比较之。《五行》说文该章中,“遁(循)”和“源”意指探究;“遁……(某某对象)”和“源……(某某对象)”意指主体接物而探究之,比如探究草木之性、禽兽之性、人之性(概言之即万物之性),探究耳目之性、鼻口之性、手足之性、心之性(概言之即人体之性)等等。“目(侔)”、“遁(循)”、“源”三字之义均可包括在《大学》“格物”之“格”中,均可呈现“格物”之“格”的实际意涵。而此处所格之“物”包括草木、禽兽、人类以及人体,后者又具体化为作为大体的心与作为小体的耳目、鼻口、手足等等。
(之性)”即主体交接耳目、鼻口、手足以及心之性而比较之。《五行》说文该章中,“遁(循)”和“源”意指探究;“遁……(某某对象)”和“源……(某某对象)”意指主体接物而探究之,比如探究草木之性、禽兽之性、人之性(概言之即万物之性),探究耳目之性、鼻口之性、手足之性、心之性(概言之即人体之性)等等。“目(侔)”、“遁(循)”、“源”三字之义均可包括在《大学》“格物”之“格”中,均可呈现“格物”之“格”的实际意涵。而此处所格之“物”包括草木、禽兽、人类以及人体,后者又具体化为作为大体的心与作为小体的耳目、鼻口、手足等等。
“目(侔)而知之,胃(谓)之进之”:弗目也,目则知之矣;知之则进耳。目之也者,比之也。“天监在下,有命既杂(集)”者也,天之监下也,杂命焉耳。遁(循)草木之生(性)则有生焉,而无(无)好恶焉。遁禽兽之生,则有好恶焉,而无礼义焉。遁人之生,则巍然知亓(其)好仁义也。不遁亓所以受命也,遁之则得之矣。是目之已。故目万物之生而知人独有仁义也,进耳。“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之胃也。文王源耳目之生(性)而知亓好声色也,源鼻口之生而知亓好 (臭)味也,源手足之生而知亓好勶(佚)余(豫)也,源心之生则巍然知亓好仁义也。故执之而弗失,亲之而弗离,故卓然见于天,箸(著)于天下。无他焉,目也。故目人
(臭)味也,源手足之生而知亓好勶(佚)余(豫)也,源心之生则巍然知亓好仁义也。故执之而弗失,亲之而弗离,故卓然见于天,箸(著)于天下。无他焉,目也。故目人 (体)而知亓莫贵于仁义也,进耳。
(体)而知亓莫贵于仁义也,进耳。
《五行》经文第二十四章云:“辟(譬)而知之,胃(谓)之进之。”说文第二十四章解释道:
“辟(譬)而知之,胃(谓)之进之”:弗辟也,辟则知之矣,知之则进耳。辟丘之与山也,丘之所以不如名山者,不责(积)也。舜有仁,我亦有仁,而不如舜之仁,不责也。舜有义,而我亦有义,而不如舜之义,不责也。辟比之而知吾所以不如舜,进耳。
这是以丘因不积而不如名山,类比而得知“我”之仁义因不积而不如舜之仁义,以此确认积仁义之为要务,简单言之“辟比……(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这是《五行》“格物→致知”的又一种具体形式。
与此相似,《五行》经文第二十五章“谕而知之”以及说文第二十五章给出的说解、《五行》经文第二十六章“鐖(几)而知之”以及说文第二十六章给出的说解,也都与《大学》格致观念密切相关。
以上所举是直接的格物致知。在《五行》体系中,以言教为认知对象的间接格物致知也有所表现。比如其经文第十七章云:“未尝闻君子道,胃(谓)之不悤(聪)。未尝见贤人,胃之不明。闻君子道而不知亓(其)君子道也,胃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亓有德也,胃之不知(智)。见而知之,知(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知(智)也。壑壑,圣〔也〕。‘明明在下,壑壑在上’,此之胃也。”该章有一个论断是见贤人而知其有德谓之智,即“见……(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或价值)”,这是直接的格物致知;另有一个论断则是闻君子道而知其君子道谓之圣,即“闻……(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或价值)”,这是间接的格物致知。《五行》在这两个层面上均承袭了孔子及其弟子认知道术的模式,其德行生成的系谱往往基于此建构。战国末期,《荀子》偏重于张扬基于“见—知”而践履价值、提升人格的一面。故其《儒效》篇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杨注:行之则通明于事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杨注:见而不知,虽能记识,必昧于指意);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杨注:苟不能行,虽所知多厚,必至困踬也)。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杨注:虽偶有所当,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杨注:言偶中之道,百举而百陷,无一可免也)。”
除《五行》之外,郭店竹书《 惪义》之系谱
惪义》之系谱 (察)→智(知
(察)→智(知 (己)→智人→智命→智道→智行”、《语丛一》之系谱“智忌(己)→智人→智豊(礼)→智行”等,亦莫不蕴含格物致知之意。
(己)→智人→智命→智道→智行”、《语丛一》之系谱“智忌(己)→智人→智豊(礼)→智行”等,亦莫不蕴含格物致知之意。
所有的历史都有其土壤;找不到历史的土壤,就找不到真正的历史。将《大学》格致观念孤立于其前后的传世文献之外,尤其是孤立于大致与它同时的新出儒典之外,显然是不科学的。《大学》文本与上博《诗论》、郭店及马王堆《五行》等新见儒典的互证关系,为上文对《大学》格致观念的诠释提供了力证。
道德修为无法摸着石头过河,必须先达成认知,才能进一步将它落实到修为或践履中。由格物而致知未必轻松简易,《中庸》第二十章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便是“致知”的一系列工夫。而知之不当,则行之必妄。《论语·阳货》篇记:
子曰:“由(仲由,子路)也,女(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又记: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凡此均夫子矫正弟子之知也。故前人或评价说:“搔着子路痒处,亦搔着子路痛处,亦搔着天下万世痛痒处。”[25]而朱子云:“子路之勇,夫子屡箴诲之,是其勇多有未是处。若知勇于义,知大勇,则不如此矣。”[26]一言以蔽之,知有偏差,则践行愈笃实卖力,问题便愈大。“格物→致知”作为《大学》八目及儒家道德修为之始基,良有以也。
朱熹解“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见其补传),或者“穷至事物之理”(见其章句),解“致知”为“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见其章句),其说在思想史上自有极重要之价值。徐复观云:
朱元晦对致知格物的补义……实含有两大意义;尽管未必为《大学》原义所有,但亦可谓为《大学》原义的引申推拓;最低限度,这是儒家重知识一面的重大发展,所以并不必为《大学》原义所拒绝。……第一,他把求知识的知性,及求知识的对象,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并且在“即物而穷理”的这句话里,把道德的主观性所加于求知的制约,与以取消或压小;因之,使知性从道德主体的主观性中完全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客观之物而活动,这便为求知识开出一条大路。第二,因为上述知性的解放,于是把求知的对象,从“伦理”、“事理”,扩充到“物理”;伦理不待说,即是事理的“事”,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向客观对象的活动而成立;若此种客观对象,只限于身、家、国、天下,则此时的“事理”,是在伦理与物理之间所成立的理。这若完全站在知识的立场说,此时的事理,便算是不纯不净,对于知识自身的发展,即形成一限制。中国传统所说的理,多半是属于此种性格。程朱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说“即物而穷其理”;这里所说的物,已突破了《大学》原有的范围,而伸向“凡天下之物”,连一草一木,都包括在内的自然方面;理之客观性,始彻底明了,求知的限制亦随之打破;这是中国文化,由道德通向科学的大关键。必如此,而学问的性格乃全,且亦为孔子思想所蕴蓄而未能完全展出的。[27]
这些论述相当正确。可凡事往往都存在另外一面。从先秦儒家立场上说,朱子章句及补传只能说是得其大略,其严重缺陷,在于未意识到先秦儒家讲格物致知,绝非泛言致一般之知识,而是聚焦于致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事君、敬长、使众、与国人交等修齐治平之知。徐复观说“朱元晦因未能把握性理而偏重事理、物理,故其释《大学》,使‘正心’、‘诚意’二辞落空”[28],准确地提挈了朱子诠释《大学》“格物”、“致知”的弊端。以朱说为代表的对《大学》“格物”、“致知”的新认知、新观念,暗含了格致学说蜕变为科学性求知而偏离安身立命之本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后来成了大势所趋。1876年2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上海创办《格致汇编》,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完全以科技知识为内容的报刊”[29],它被命名为“格致”,可以说就是前一偏向的自然发展。前进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在科学日益进步的同时,安身立命问题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1]钱穆《大学中庸释义·大学古本》,《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2]钱穆《大学中庸释义·例言》,《四书释义》,第278页。
[3]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9页。
[4]王阳明《大学问》,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三册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页。
[5]《传习录上》,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一册语录一,第7页。
[6]分别参见《传习录下》,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一册语录三,第136页;《年谱一》,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四册,第1354页。
[7]刘宗周《大学古记约义》“格致”条,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六,第648—649页。
[8]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68页下。
[9]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七,第657、654页。案:杨简(1141—1225),世称慈湖先生。王守仁(1472—1528),世称阳明先生,卒谥文成。王艮(1483—1541),号心斋。罗洪先(1504—1564),号念庵。
[10]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上篇,《续修四库全书》159,经部四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下。案:其所引瑞应,见载于《礼记·礼运》篇。
[11]饶宗颐《选堂文集·格物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文录、诗词,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2—53页。案:饶文上引《礼记·缁衣》篇记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郑注:“格,来也;遁,逃也。”又谓:“《学记》论为学程序,而殿以语云:‘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注:‘怀,来也’。是大学之道,其效不离齐之以德,使人心悦诚服而来归已耳,而其道莫重于格物。”(同前注,第51页)所谓“郑注陈义之精”即对此而言。“庶民来子”当作“庶民子来”,见《诗经·大雅·灵台》。
[12]钱穆《大学中庸释义·大学古本》,《四书释义》,第300页。
[13]郭店简文《缁衣》所载为:“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 (格),此以生不可敚(夺)志,死不可敚名。”
(格),此以生不可敚(夺)志,死不可敚名。”
[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一〇册,经部第二〇四册四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0页上。
[15]杜勇列三条内证,证明《史记·周本纪》《书序》说周公作《大诰》之可信,并判断《大诰》为“周公东征前发布的政治宣言书”(见氏著《〈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4页),可以参考。
[16]许慎《说文解字·牛部》:“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裘锡圭《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一文(《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五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315页),采摭相关文献甚富,颇可见“物”字无所不包之义。
[17]案:传世《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后有“此谓知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谓“四字衍”(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0页),是。又:“子曰听讼”以下一段文字,旧说往往就听讼一事作解,郑玄《礼记》注、朱熹《大学章句》等,莫不如此。笔者以为当系三事,其意为:“听讼”固然重要,使民不起争讼才是根本。“情”之于“辞”为根本,故“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周易·系辞传下》“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可证成“情”与“辞”之关系。《尚书·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分别见《左氏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前542〕所记穆叔引《大誓》、《孟子·万章上》所记孟子引《太誓》以及《诗经·大雅·烝民》郑笺引《书》,——正义以为《泰誓》文)。凡此足见“民志”之为根本。故《大学》谓“必也使无讼”、“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三者为“知本”。
[18]徐复观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见氏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大学》未受西汉学术思想之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儒家以经典为中心建构学问体系,自孔子创立儒家之时便开始了,至战国中晚期,六经业已被确立为学问之核心,《大学》之“格物→致知”实亦包含自经典获取价值的一面,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面。
[19]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一“致知格物”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20]孔子对仁的如下诠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回答的是子贡所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所谓“近取譬”,是就相对于“人”之远的“己”之近而言的,指言本“己欲”而事人。徐复观提出:“‘能近取譬’的‘近’,是指可以具体实行的工夫、方法而言。仁的自觉的精神,必须落实于工夫、方法之上;而工夫、方法,必定是在当下生活中可以实践的,所以便说是‘近’。‘近’是针对博施济众之‘远’而言。”(见氏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85页)其解“近取譬”显然是一大误会。《中庸》第十三章载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之后即倡言“违道不远”之“忠恕”,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云云。孟子则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凡此均是将践行推己及人之恕道作为求仁德最近之途径,均可为孔子“近取譬”一说之注脚。简单地说,对于孔、孟而言,践行仁取则在自身,故或谓其“方”为“近取譬”,或谓“强恕而行”为求仁最近之途,其所谓“近”,与“博施济众之‘远’”无涉。
[2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可知孔子又曾以《春秋》教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孔子传《易》于瞿(鲁人商瞿),瞿传楚人 臂子弘(前儒疑为子弓之误),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则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臂子弘(前儒疑为子弓之误),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则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二说之差别主要是第三世第四世互易,而孔子以《易》授徒一事则确凿无疑。要之,六经均在孔门授受之列。
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二说之差别主要是第三世第四世互易,而孔子以《易》授徒一事则确凿无疑。要之,六经均在孔门授受之列。
[22]“听止于耳”原当为“耳止于听”,参阅俞樾《诸子平议·庄子一》。
[2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70页。案:徐复观认为:“六经的成立,是先有《诗》《书》《礼》《乐》;到了孟子,才加上了《春秋》。而《周易》之加入,恐在荀子以后。《荀子·儒效》篇‘《诗》言其志也’一段,总言五经而未及《易》。但这是《易》的重要性尚未被荀子这一派人所承认,并非《易》尚未成为传习的教材。”(同前注,第70页注2)徐复观又说:“……六经的成立,可能是在秦博士之手,或其并世的儒者。”(同前注,第326页)徐复观显然缺乏新出战国儒典的知识背景,也忽视了《荀子·大略》篇将《易》与《诗》《礼》并列的重要性,因此严重偏离了事实。
[2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学》四《读书法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7、161页。案:刘宗周《大学杂言》云:“朱子格物之说,其大端从《诗》《书》六艺穷讨物理,原是学问正项工夫,士舍此无以入道者。但其工夫已做在小学时,至十五而入大学,则自小学之所得者,由身而达之天下国家,其第一义在格物,即就此身坐下言。通《大学》一书,何尝有学文游艺之说?”(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七,第656页)
[25]李贽《四书评》,《论语》卷之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8页。案:此书颇有学者怀疑为叶昼所作,反驳的意见可参考刘建国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1页。
[2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七,《论语》二十九《阳货篇》,第1191页。
[2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72—273页。
[2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82页。
[29]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道),心述(术)为宔(主)。
(道),心述(术)为宔(主)。 四述,唯人
四述,唯人 为可
为可 也。亓(其)厽(三)述者,
也。亓(其)厽(三)述者, 之而已。《时(诗)》《箸(书)》《豊(礼)》《乐》,亓
之而已。《时(诗)》《箸(书)》《豊(礼)》《乐》,亓 (始)出皆生于人。《时》,又(有)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豊》《乐》,又为
(始)出皆生于人。《时》,又(有)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豊》《乐》,又为 (举)之也。圣人比亓頪(类)而仑(论)会之,雚(观)亓(之
(举)之也。圣人比亓頪(类)而仑(论)会之,雚(观)亓(之 )〔先后〕而逆训(顺)之,体亓宜(义)而即(节)
)〔先后〕而逆训(顺)之,体亓宜(义)而即(节) (文)之,里(理)亓青(情)而出内(入)之,肰(然)句(后)复以教。教,所以生惪(德)于中者也。”(同样的文字也见于上博《眚
(文)之,里(理)亓青(情)而出内(入)之,肰(然)句(后)复以教。教,所以生惪(德)于中者也。”(同样的文字也见于上博《眚 论》)而《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
论》)而《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 (道)人
(道)人 也。《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豊(礼)》,交之行述(术)也。《乐》,或生(性)或教者也。《书》
也。《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豊(礼)》,交之行述(术)也。《乐》,或生(性)或教者也。《书》 者也。”凡此皆可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上博《诗论》当即孔子以《诗》教的记录。[21]总而言之,孔子视六艺为真知之渊薮,六艺被他确立为间接格物致知的核心对象。孔子尝曰:“(加)〔假〕我数年,(五十)〔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还对伯鱼(孔鲤,前532—前482)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作为致知之门径,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从孔子创派之初就被确认了,儒家经典建设和授受的基础也由孔子奠定。上博《诗论》第五章云:
者也。”凡此皆可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上博《诗论》当即孔子以《诗》教的记录。[21]总而言之,孔子视六艺为真知之渊薮,六艺被他确立为间接格物致知的核心对象。孔子尝曰:“(加)〔假〕我数年,(五十)〔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还对伯鱼(孔鲤,前532—前482)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作为致知之门径,阅读经典的重要性从孔子创派之初就被确认了,儒家经典建设和授受的基础也由孔子奠定。上博《诗论》第五章云: (吾)
(吾) (以)《
(以)《 》得氏(祗)初之訔(志),民眚(性)古(固)然,见丌(其)
》得氏(祗)初之訔(志),民眚(性)古(固)然,见丌(其) (美),必谷(欲)反丌本。夫萭(葛)之见诃(歌)也,则
(美),必谷(欲)反丌本。夫萭(葛)之见诃(歌)也,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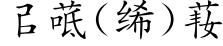 (绤)之古(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
(绤)之古(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 文、武之惪(德)也。
文、武之惪(德)也。
 《甘棠》得宗
《甘棠》得宗 (庙)之敬,民眚古然,甚贵丌人,必敬丌立(位),敚(悦)丌人,必好丌所为,亚(恶)丌人者亦然。
(庙)之敬,民眚古然,甚贵丌人,必敬丌立(位),敚(悦)丌人,必好丌所为,亚(恶)丌人者亦然。 《木苽》
《木苽》 (得)
(得) (币)帛之不可
(币)帛之不可 (去)也,民眚古然,丌
(去)也,民眚古然,丌 (隐)志必又(有)
(隐)志必又(有) 俞(喻)也。丌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
俞(喻)也。丌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 (触)也。
(触)也。
 杜》得雀□之不可无也,民眚古然,□□□□女此可,斯雀之矣。
杜》得雀□之不可无也,民眚古然,□□□□女此可,斯雀之矣。 (御)丌所㤅(爱),必曰:
(御)丌所㤅(爱),必曰: 奚舍之?宾赠氏(是)也。
奚舍之?宾赠氏(是)也。 (聪)也’:同之闻也,独色然辩于君子道,(道)〔
(聪)也’:同之闻也,独色然辩于君子道,(道)〔 也〕;〔
也〕;〔 也〕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亓(其)天之道也,是圣矣。圣人知天之道。道者,所道也。‘知而行之,义也’:知君子之所道而
也〕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亓(其)天之道也,是圣矣。圣人知天之道。道者,所道也。‘知而行之,义也’:知君子之所道而 然行之,义气也。‘行之而时,
然行之,义气也。‘行之而时, (德)也’:时者,和也。和也者(惠)〔
(德)也’:时者,和也。和也者(惠)〔 〕也。”这是说以“听—闻”获取对道的认知,而后付诸道德之修为。庄子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耳〕止于(耳)〔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内篇·人间世》)[22]“听之以气”实即秉持心之虚来听,看似玄奥,但说到底还是以听为获取道的途径。显然,在儒学授受的历史交接中,听师教或圣言以获取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道术,也是间接的格物致知。
〕也。”这是说以“听—闻”获取对道的认知,而后付诸道德之修为。庄子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耳〕止于(耳)〔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内篇·人间世》)[22]“听之以气”实即秉持心之虚来听,看似玄奥,但说到底还是以听为获取道的途径。显然,在儒学授受的历史交接中,听师教或圣言以获取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道术,也是间接的格物致知。 (逸)之,丌甬(用)心也
(逸)之,丌甬(用)心也 (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已。民之又(有)
(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已。民之又(有) (戚)
(戚) (惓)也,上下之不和者,丌甬心也
(惓)也,上下之不和者,丌甬心也 可女?曰《少
可女?曰《少 》氏(是)已。□□□□□□可女?曰《大
》氏(是)已。□□□□□□可女?曰《大 》氏已。又城(成)工(功)者可女?曰《讼》氏已。
》氏已。又城(成)工(功)者可女?曰《讼》氏已。 (体)而知亓(其)莫贵于仁义”,此二说堪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具体呈现。具体说来,《五行》说文第二十三章一系列申释和论证,如“循……(某某对象)则知……(某某道理)”、“源……(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等等,均亦呈现出“格物→致知”的理念和模式。《五行》经、说第二十三章中的“目”通“侔”;“目……(某某对象)而知……(某种道理或价值)”,意指主体接物,比较之而达成某种认知,如“目(侔)万物之生(性)”即主体交接草木、禽兽以及人之性而比较之,“目人
(体)而知亓(其)莫贵于仁义”,此二说堪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具体呈现。具体说来,《五行》说文第二十三章一系列申释和论证,如“循……(某某对象)则知……(某某道理)”、“源……(某某对象)而知……(某某道理)”等等,均亦呈现出“格物→致知”的理念和模式。《五行》经、说第二十三章中的“目”通“侔”;“目……(某某对象)而知……(某种道理或价值)”,意指主体接物,比较之而达成某种认知,如“目(侔)万物之生(性)”即主体交接草木、禽兽以及人之性而比较之,“目人 (之性)”即主体交接耳目、鼻口、手足以及心之性而比较之。《五行》说文该章中,“遁(循)”和“源”意指探究;“遁……(某某对象)”和“源……(某某对象)”意指主体接物而探究之,比如探究草木之性、禽兽之性、人之性(概言之即万物之性),探究耳目之性、鼻口之性、手足之性、心之性(概言之即人体之性)等等。“目(侔)”、“遁(循)”、“源”三字之义均可包括在《大学》“格物”之“格”中,均可呈现“格物”之“格”的实际意涵。而此处所格之“物”包括草木、禽兽、人类以及人体,后者又具体化为作为大体的心与作为小体的耳目、鼻口、手足等等。
(之性)”即主体交接耳目、鼻口、手足以及心之性而比较之。《五行》说文该章中,“遁(循)”和“源”意指探究;“遁……(某某对象)”和“源……(某某对象)”意指主体接物而探究之,比如探究草木之性、禽兽之性、人之性(概言之即万物之性),探究耳目之性、鼻口之性、手足之性、心之性(概言之即人体之性)等等。“目(侔)”、“遁(循)”、“源”三字之义均可包括在《大学》“格物”之“格”中,均可呈现“格物”之“格”的实际意涵。而此处所格之“物”包括草木、禽兽、人类以及人体,后者又具体化为作为大体的心与作为小体的耳目、鼻口、手足等等。 (臭)味也,源手足之生而知亓好勶(佚)余(豫)也,源心之生则巍然知亓好仁义也。故执之而弗失,亲之而弗离,故卓然见于天,箸(著)于天下。无他焉,目也。故目人
(臭)味也,源手足之生而知亓好勶(佚)余(豫)也,源心之生则巍然知亓好仁义也。故执之而弗失,亲之而弗离,故卓然见于天,箸(著)于天下。无他焉,目也。故目人 (体)而知亓莫贵于仁义也,进耳。
(体)而知亓莫贵于仁义也,进耳。 惪义》之系谱
惪义》之系谱 (察)→智(知
(察)→智(知 (己)→智人→智命→智道→智行”、《语丛一》之系谱“智忌(己)→智人→智豊(礼)→智行”等,亦莫不蕴含格物致知之意。
(己)→智人→智命→智道→智行”、《语丛一》之系谱“智忌(己)→智人→智豊(礼)→智行”等,亦莫不蕴含格物致知之意。 (格),此以生不可敚(夺)志,死不可敚名。”
(格),此以生不可敚(夺)志,死不可敚名。” 臂子弘(前儒疑为子弓之误),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则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臂子弘(前儒疑为子弓之误),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则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二说之差别主要是第三世第四世互易,而孔子以《易》授徒一事则确凿无疑。要之,六经均在孔门授受之列。
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二说之差别主要是第三世第四世互易,而孔子以《易》授徒一事则确凿无疑。要之,六经均在孔门授受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