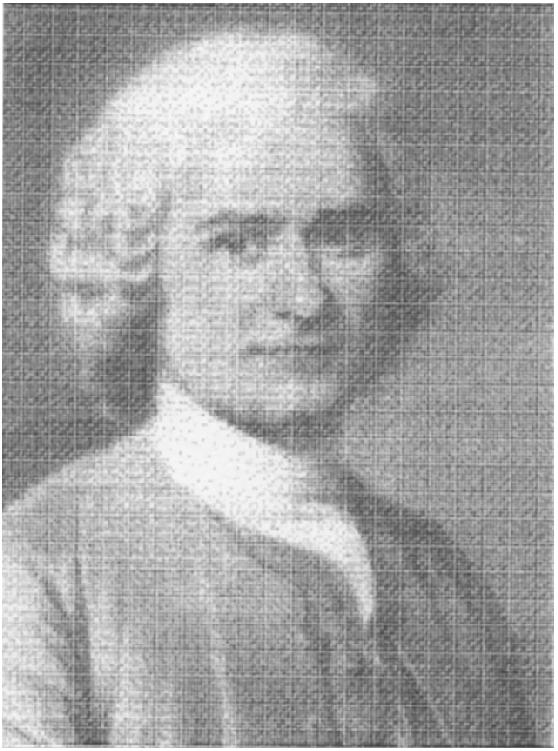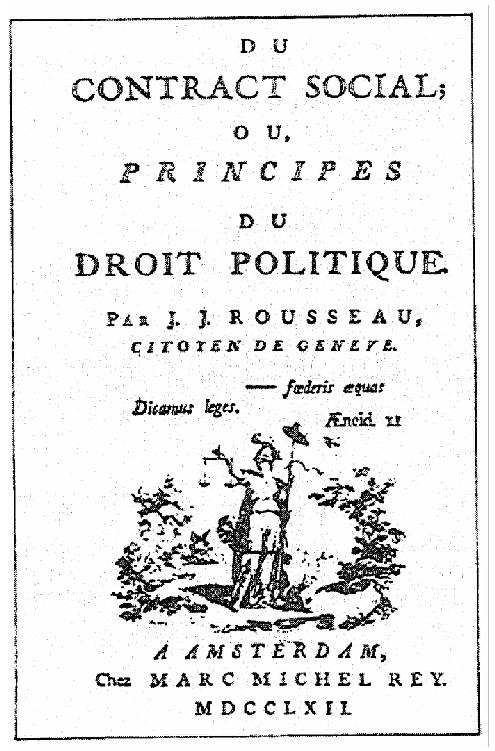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
——卢梭政治哲学分析
朱学勤[42]
[摘要] 本文为当年金重远先生指导作者的博士论文《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核心章节。文章从卢梭政治哲学的基石——社会契约论进入,论述其如何失落契约论关键一方,从民主的起点走向专制的终点;与此同时,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此也发生重要转折,从彼岸神学救赎论走向此岸道德理想国,政教合一,建立教士与帝国一致的一元化制度;此一理论为此后雅克宾专政奠定了思想基础,并由此对世界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发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神学救赎;此岸重建;社会契约;教士与帝国合二而一;道德理想国;红色恐怖
伟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事物。
——柏拉图[43]
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是最可怕的制度。
——伏尔泰[44]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近代社会开始了世俗化过程。
在政治领域内,这一变化首先意味着中世纪神学政治论有可能转化为近代早期的一个过渡性形式:政治神学论。若完成这一转折,则必须论证人能够代神立言、替神行圣的正当资格:人的道德能力。而这一论证即由卢梭对神正论原罪说的重大改动而完成:原罪的载体并非个人,而是社会;社会对人心本源的逐渐疏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异化史。因此,社会历史必须退回零度为起点重新出发,不再追寻彼岸神性天国,而是折过头来,在此岸重建道德理想国。重建道德理想国的过程不仅发生于人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它还要发生于社会之中,发生于道德选民与道德弃民之间:“正义”与“邪恶”争战,“美德”与“罪恶”争战。
于是,神人和解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神性救赎话语延伸为世俗的观念话语(discourse of idea)。也就是在这一国度、这一时刻,法国人特拉西(Tracy,1754—1836)第一次启用了idéologie这一法语单词。拿破仑则启用了idéologue这一法文单词,以埋怨卢梭及其后裔——迷恋观念形态的知识分子给他造成的无穷麻烦。从此,idéologie不胫而走,它不仅塑造了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内战性格,也预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神学将取代神与人之间的神学政治。这一取代将意味着马丁·路德之后,一个后神学时代的来临——idéologie,ideology,即“意识形态”时代的来临。
一、“公共意志”——卢梭哲学的发生进路
我们从“公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这一概念,进入后神学时代意识形态的起源。因为卢梭自己说:
正像在人的构成方面,灵魂对于身体的作用乃是哲学的尖端,同样在国家的构成方面,公意对于公共力量的作用问题则是政治学的尖端。[45]
1762年,卢梭《社会契约论》发表。他酝酿七年之久的人类进入道德状态的进路,终于得到一次全面阐述:
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主动时,就称为主权者,当它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46]
我们可从这里依次抽出三个问题。作为本节或以后诸节逐一讨论的对象。第一,是本节讨论的“公共意志”如何产生问题。
第二,“一瞬间”问题。必须追问的是:什么样的“一瞬间”?哪些人参加了这“一瞬间”?是两方“约定”,还是三方“约定”?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路易丝·阿尔图塞(L. Althusser),曾把这“一瞬间”拉长为充满疑点的“一片段”,捉住了卢梭在这“一瞬间”暴露的四只马脚。这一问题,我们留待第二节讨论。
第三,语言转换问题。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语言转换的标本:几乎所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共和国、共同体、政治体、主权者、国家、人民、公民、臣民,都被卢梭用“公共意志”这一道德网络一网拉尽,统统转换为道德符号来讨论。卢梭道德理想国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是这场语言转换的结果。语言转换在理论上带来的后果,我们将在最后一节评述。
让我们先回到第一个问题。卢梭的“公共意志”(以下简称“公意”),是作为“众意”的对待之物出现的。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的民主要求,在逻辑上是以“众意”而非“公意”为基础。卢梭不满英国政治思想,提出“公意”为法国新型民主的基础。卢梭“公意”的产生过程,就是“众意”的克服过程。《社会契约论》说:
公意与众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47]
假如普遍社会存在于什么地方,而不是存在于哲学家的体系里;那末,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就会是一个道德的生命,有着它自身固有的品质而与构成它的那些个体生命的品质截然不同,有点像是化合物所具有的特性并非得自构成化合物的任何一种混合物那样。[48]
这里有两步:从私意到众意,是“一度聚合”,为物理变化;从众意到公意,是“二度抽象”,为化学变化,从中化合产出一种新的物质——“公共人格”,或称“道德共同体”。第一步,是英美政治哲学的典型性格;第二步,是卢梭开启先河的大陆政治哲学的顽强追求。一步与两步之差,预示着后来英美与大陆政治思潮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第一步——众意从私意中聚合产生,洛克、伏尔泰都不会反对。这正是他们为之论证的资产阶级近代社会的民主基础与世俗图像,也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共处于一个平面利益板块,双方不能凌驾对方的存在模式。洛克、伏尔泰之平庸,亦在于此。他们永远满足于只做世俗社会的物理学家,不敢奢望再做世俗社会向道德理想国化合飞跃的化学家。卢梭凌空蹈虚,向前多跨一步——从众意中化合产生公意。正是这个向前多跨的一步,把近代社会世俗化、近代政治制度化的两个根基抽象净尽。
首先是个人存在空间,这是近代社会挣脱中世纪宗法共同体走上世俗化进程的根基。卢梭说:
只有私人意愿与公共意志完全一致,每一个人才是道德的。[49]
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实现吗?那就使所有的个人意愿与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样的事情可以换句话说,那就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50]
其次是众意的联合空间——民间社团党派,这是近代政治挣脱中世纪神学体系走上制度化过程的根基。卢梭说: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侯,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末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
因此,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51]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传统政治向近代政治转型期间,是政治参与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政治参与扩大如果不同时伴以制度化,那么,参与扩大极易走向参与爆炸,导致社会动乱。参与扩大制度化的重要方面,是参与者以个人为单位逐渐发育为以社团党派为单位,走向集团参与。经过这样的“二次组合”,近代政治转型期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近代政治的规范、制度才能发育成熟。英国政党制度在英国革命的中、后期逐渐形成,对保持革命后期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两党制在美国革命后期的类似作用,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对,法国革命则提供了相反教训。1789年革命之后,社会长期震荡、难以稳定的根本原因,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即在于雅各宾派接受卢梭上述反社团党派、反政党政治的理论,明令禁止民间结社组党,本身亦自我束缚,自限于政治参与的低级阶段——聚散无常的俱乐部阶段,拒绝向政党阶段发展。
从另一方面说,卢梭在社会层面抽空个人利益主体,在政治层面又放大个人政治符号——“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用以排挤社团党派的政治空间,这种逻辑若走入政治实践,则会出现一种高度统一乃至极权的政治局面。无数失去恒常的利益主体立场的个人,极易受政治允诺的蛊惑,旋聚旋散,暴涨暴落,最终还会匍匐于某个以公意为号召的奇理斯玛之下,成为无数供人驱使的政治侏儒。用卢梭自己的语言总结,那就是:
在一个完美的立法之下,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政府本身的团体意志应该是极其次要的,从而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永远应该是主导的,并且是其他一切意志的唯一规范。[52]
这种公意指导下的民主,后来成为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大陆国家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在散漫无常的动沙流水之上,直接矗立着公共意志的最高主宰;下面的极端民主制与上面的绝对权威对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团体结构作为支撑。
更危险的,是公共意志的人格化,不管这个人格化的公共意志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出现。卢梭虽然一再否认,订约的双方需要一个可以裁决他们之间分歧的共同上级[53],但是他那样的公意理论在实践中却内在地需要一个第三者,一个可疑的牧羊人……
二、“社会契约”——卢梭哲学的逻辑脱漏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被阿尔图塞抓住的那个可疑的“一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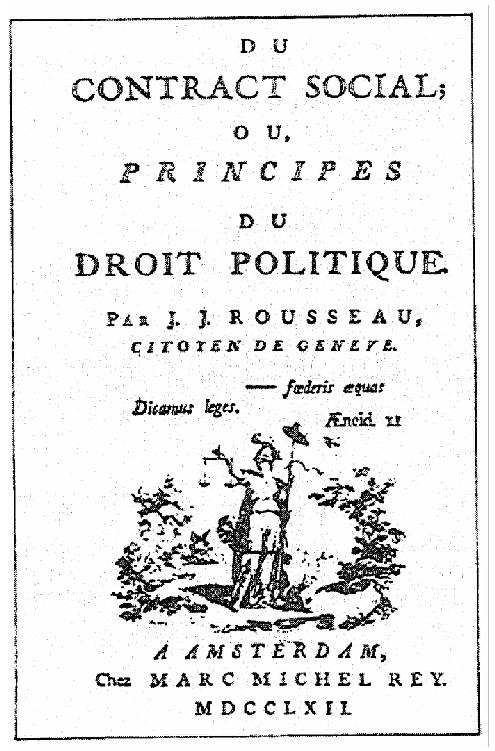
《社会契约论》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然阿尔图塞却加以攻击。图为该书初版(1762)封面。
阿尔图塞声称,卢梭论述社会契约行为时,出现有四大脱漏(discrepancy):契约第二方不明确;契约承受方不在场;主权交换同义反复;公益私利混淆不分。[54]
由于卢梭明确陈言,公益就是要克服私利,故讨论第四项脱漏可能会被他奚落,属节外生枝,因此本文对此项删略不论。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可能过于干涩,我们可以把卢梭在其他三方面的逻辑脱漏,改换为与洛克、霍布斯对比研究来讨论。
先与洛克相比。在洛克的小契约论里,订约者是社会居民的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双方转让主权与第三方,第三方按约行使权力。但是,转让出去的不是全部权力,而是部分权力,余有更多权力留于个人。个人权力既是隐私空间的屏障,又是市民社会利益组合的自治单位。但在卢梭的大契约论里,订约者是个人与公共集体,转让出去的是全部权力。故而阿尔图塞在这里抓住第一只马脚。质问卢梭:这个契约第二方——公共集体如何界定?是超于社会一个实体,还是那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式的“人人”道德集合体?按卢梭之回答。恐怕是后者,不是前者。但是如此回答又生了一个问题:人与人人订约,兜了一大圈,最终岂不是人与人自己订约,是个什么都交出去、什么都返回来的主权者,在原地踏步?这就是阿尔图塞抓住的第二只马脚——主权交换是同义反复。问题还不在逻辑结构上的再三脱漏,结构主义者可能在这里过于挑剔,技痒难耐;问题首先在于——主权全部转让后,将带来什么实践后果?个人的法权独立身份与社会利益的单位空间如何安置?这是对比洛克小契约论以后,卢梭大契约使人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再与霍布斯相比。卢梭的主权全部转让说与洛克有异,但与霍布斯正好吻合。尽管逻辑来源不一,但卢梭至少在这里可以得到霍布斯逻辑形式上的支援。然而,差异马上就发生了: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约论都是三方契约,两方订约让渡主权(有全部与局部让渡之分),第三方承受两方让渡过来的主权,组织政治;而卢梭的契约论却是两方订约,没有第三方承受!这就是阿尔图塞抓住的第三只马脚——契约承受方(recipient party)不在场。无怪西方有学者挖苦卢梭,说他的这一主权让渡理论是个“没有守门员的球门”[55]。在这里,人们自然产生第二个疑问——权力全部转让后,竟无第三者具体承受,政治国家的制度层面如何安排?
我们面对这两大疑问,可以看到英国学派提不出卢梭这类道德政治观、美学政治观,却提得出一个低调而又实际的逻辑前提——制度化层面得以安排的逻辑前提:主权授受双方会否冲突?如果冲突,有何制度化的技术手段予以解决?这一问题貌似平庸,恰恰是近现代政治生活的关键所在。
霍布斯回答:会发生冲突,但那必定是订约者悔约,主权承受者,即第三方可自上而下镇压之,于是便发生绝对主权之制度性安排。
洛克回答:有摩擦,有张力,但不会冲突为全民起义或全面镇压。因为第三方是市民社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孤岛既受外部制约,又受内部权力分立之牵制,不会把摩擦、张力恶化为冲突。于是,在洛克的第三方层面也就发生有代议制、宪政制之类的制度性安排。
但在卢梭这里,他要么通向无政府主义,要么通向道德化的政治全能主义,却提不出中立化的制度性技术手段,因为他失落了整个国家形态的制度安排。
在这里,我们如果需要某种形象隐喻来概述以上三人对政治国家的理论设计,那么蒂利希(Paul Tillich)在《政治期望》一书中正好提供了这三种隐喻,移用过来,略有增删,即十分切合。霍布斯所说的国家是一个“魔鬼”,尽管霍布斯曾说过国家是一个“终有一死的上帝”,但我们不得不说,国家很像一个不愿去死的“魔鬼”[56]。
洛克所说的国家是一个“看守人”(watchman of state)。它是一个庸俗的人间机器,不具有神性。它只有世俗功能,不承担高尚的精神事务。精神事务归教会,功利分配归社会。它只看守被看守者,绝无权力侵入被看守者,更无奢望全盘改造被看守者。正像它的内部有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它的外部恰好也有议会、教会、社会的“三会分立”。议会管政治,教会管灵魂,社会管俗务,各司其职,不得互侵。
卢梭的国家是一个“世间的上帝”。它是作为精神价值的承担者获得神性的。它的存在方式确如上帝之存在方式;不可能作为物化形式而存在,存在为一种制度系统或科层结构;它只能以一种精神形式存在,存在为一种价值符号、理想系统,或干脆结构硬化为意识形态。作为可视对象,它是被否定的,正如上帝不能有形、现形;作为可感觉对象,它是被肯定的,正如上帝万能,全视全觉,无所不在。它比霍布斯坦率的地方在于从来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永恒性——终无一死。至于这一神性承担者如何通过奇理斯玛这一人间形态,从上帝转化为嗜血者,突然与霍布斯的“魔鬼”接通,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悖论,在雅各宾史、法国革命史、中国“文化革命”史里,皆有详细佐证。
很显然,卢梭的政治国家是个对待之物,它在两个方面分别以英国学派的对待之状而存在,正好满足卢梭对英国学派的对抗式:内部不作霍布斯的制度安排,外部不作洛克式的边界限定。这个独具卢梭风格的巨无霸,一旦从理论形态进入实践形态,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第一,在常态情况下,政、教合一,政、社合一。政治国家的边界无限扩张,淹灭市民社会,更淹灭个人存在。此时可谓有道德国家熔铸一切,无市民社会利益分殊。
第二,在非常态情况下,政治参与突然扩大,国家内部无制度层面可以吸纳,只能听任参与扩大走上参与爆炸,走上革命一途。此时可谓有市民社会参与突起,无政治国家制度约束。
这两种局面,都是灾难性状态。个人始终没有立足之地,制度安排亦无法落实,只有道德的日常状态与道德的非常状态交替出现,周期震荡。而这样的周期震荡,推移往复,既稳定不住政治国家的宪政权威,又稳定不了市民社会的自治机制,恰恰正是1789年之后大陆国家屡次革命、反复起义的典型概括。
三、“第三者统治”与“第四种法律”——卢梭政治哲学中的道德国家
在这一节里,我们讨论第一节提出的那个可疑的牧羊人问题,并问答上一节留下的这一问题:公共意志不具制度形态,又将以什么形态出现?摸清这两个问题,卢梭如何把政治国家道德化,也就豁然开朗。
第三者即牧羊人的需要,首先来自公意从众意中产生这一过程的神秘性。公意与众意的区别,卢梭说得清楚。但是公意如何产生?产生后如何既高于众意,又对立于众意,然后最终又能为众意接受?卢梭语焉不详。他宁可进入神秘状态,也不愿进入英国学派的技术状态。
显然,能够解决神秘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者,必是天赋神性者,至少是一个先知型半人半神者。这样的人物俯视众生,只听从内心的召唤(calling),而他个人的内心独白经过广场政治的放大,却能对全社会产生暗示性催眠效果,用卢梭的话来说,就是使大众处于“不知道德的道德状态”。这样的第三者只能是韦伯所说的奇理斯玛型统治者。
卢梭当时尚不知奇理斯玛。但是,在他对“公意立法者”的具体描述中,一个奇理斯玛人物原型已呼之欲出——
奇理斯玛的必要:“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正是因为如此,才需要一个立法者”,“总之,简直是需要一种神明,才能为人类制定良好的法律”[57];
奇理斯玛的地位:“立法者是非凡人物。这一职务创造了共和国,但又决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就像是一个牧人对他的羊群具有优越性那样”[58];
奇理斯玛的职责:“公共权威取代父亲地位,并履行父亲的重要职责,通过履行他们的责任,获得他们的权力”[59];“主权力量代表着头脑,公民则是身体和组成部分,使得这一机构能够运转、有生气,并且工作。”[60]
这就是卢梭最满意的第三者——牧羊人统治,一个在公共意志中时隐时现的奇理斯玛。它依靠什么进行统治?卢梭走到18世纪通行的法律三分法后面,再提出一个第四种法律,即政治法、刑法、民法之后的第四法——“内心统治法”[61]:
在这三种法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者代替那些法律。……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按:指孟德斯鸠)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黑体字乃作者所加)
《论政治经济学》中,卢梭说得更为露骨:
如果说,能够按照人的本身的状态去驱动人们是高明的话,那末,能够按照需要他们成为的样子去驱使人们,则更高一筹。最高的权威是能穿透人们内心的权威。[62]
反过来,针对英国政治学派和英国政治制度,卢梭鄙夷地说,只有道德崩溃,统治者才“不得不求助于他们称之为国家制度和内阁的诀窍种种不足道的卑劣伎俩”[63]。
卢梭显然认为,统治权力的合法范围不能局限于公民外在行为的约束,而应再深入一步,深入公民内心深处,管理公民内心的道德活动。第四种法律是软性法、隐形法、不成文法,但是它比前三种法律更有穿透力。它是一场政治学的“革命”,革“政治”的命——它第一次把统治范围从公民的外在行为扩及公民的内心领域,第一次把“政治统治”改变为“道德统治”,第一次把政治国家改选成为在俗而又离俗的道德国家。这不是中世纪绵延千年的神学政治论的延展,又是什么呢?考虑到卢梭理论的世俗面目,人们需要作出的改动,只是把神学政治论改为政治神学论就可以了。
卢梭的进一步深入,是他政治哲学中最为冒险的一步。第三者统治加第四种法律,完成了政治国家的道德改造——实质上是一场后神学改造。这样的政治国家承担起神学功能,用伏尔泰的说法,“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是最可怕的制度”,用泰纳(Taine)的说法,则“是一个世俗的寺院”,“在这个寺院里,个人一无所有,而国家则掌握一切”[64]。
四、“公民宗教”——卢梭的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
历史不幸被伏尔泰、泰纳言中。卢梭之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对雅各宾专政推崇备至,在某种程度上起而仿效的大陆其他国家革命党人的实践,都曾建立过一个“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一个“世俗的寺院”:国家管教育、管信仰、管观念、管精神世界发生的一切,直至接过教皇、教会的所有管辖范围,重建一个不穿法衣、不设主教的教会。他们的领袖人物,都不以政治领袖为满足,在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只愿保留或追求那个最接近牧师、牧羊人的称号——思想导师。这一点,几乎是不约而同。对这类国家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神学时代的来临,就是意识形态统治的来临。
后神学时代意识形态统治的实践性格,当然有更多的国别差异、地区差异,但我们可以卢梭政治思想为文本,从意识形态统治的逻辑根据、社会状态、对外闭锁、对内斗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在实践中逐渐显示的普遍特征。
第一,倒果为因,观念先行——意识形态统治的逻辑根据。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为了使一个新生的民族能够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律,便必须倒果为因,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凌驾于制度本身之上,并且使人们在法律出现之前,便可以成为本来应该是由于法律才能形成的那种样子。这样,立法者便既不能使用强力,也不能使用说理;因此就有必要求之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了。[65]
这段文字表明,卢梭陷入了这样一种逻辑循环:一方面他认为“一切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66];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又总是由人来制定。那么,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在18世纪,这是一个困扰着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的重大问题,以至卡西勒(E. Cassirer)评价:“这里裸露着18世纪思想生活的心脏。”[67]当时,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方向,突破这一逻辑循环:一是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坚持的属人的方向拒绝神性的干预,即由人产生的问题只能由人自己解决,由此设计了种种理性普及的教育方案;卢梭摸索上另一个属神的方向,求援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这“另外一种权威”,只能类似于牛顿世界的那个第一推动力——从外面踢进来的一脚。只有让上帝踢一脚,牛顿的世界才能从静止走向运动;也只有让神性踢一脚,卢梭的世界才能中断循环,跃上新的一环。这个从外面踢进来的一脚,或是神明,或是人间先知先觉,几乎是柏拉图以来,所有以先验论为哲学基础的道德理想国得以运转的前提,也是后来大陆国家普遍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逻辑根据。这一点,后来在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政治学说中,俄国革命党人的无产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等理论中,曾反复出现过。
第二,“公民宗教”——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社会状态。
后神学时代,统治者一端出现奇理斯玛,被统治者一端则必须呼唤一种世俗性宗教。卢梭活着的时候,对此即有深谋远虑。他给这种宗教取有一个十分恰当的名字——“公民宗教”,并且规定:
要有一篇公民信仰的宣言,条款由主权者规定。它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68]
这样的安排——上有奇理斯玛,下有世俗宗教,足以击穿中间任何科层制秩序与个人隐私空间,两者一旦在广场短路,就出现令人激动不已的革命场面——后来被称为盛大的节日:钟声长鸣不已,市场变成广场,广场变成教堂,定期集会,不断示威,伟业与暴行并举,镇压与殉道共生,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理想救赎压倒功利经营。满街都是圣徒,全民涌现奉献热潮,奇理斯玛高耸入云,大众随之超凡入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岸进入彼岸,天国就在人间——所有这一切,用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研究巫魅现象的话来说就是:“这里真正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和他平时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使他像触了电一样直到疯狂程度时才能进入的世界。前者是世俗的世界,后者是神圣事物的世界”[69]。
即使是在革命以后,那些思想导师还会真诚迷恋这种公民普遍信教、殉教的政治狂欢节状态,当群众逐渐从广场退回厨房的时候,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把群众驱回广场。他们既是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反过来,在制造过程中浸淫日久,又是意识形态的自我中毒者。历史上,那些卷入1789年潮流的革命党,迟迟难以放弃意识形态统治,结束后神学时代,本身亦难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这一历史性转变,其重大障碍,即在这里。
第三,道德孤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对外封锁。
卢梭的神学化心态、对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后出现普遍世俗化潮流怀有抗拒。他的历史观是:“罗马的倾覆,大批蛮族的入侵,造成所有民族的融合,毁灭了各民族的道德和习俗;十字军东征、贸易、寻找印度、航海、长途旅行,延续并加剧了这一混乱。”[70]他在给波兰政府建议时说:“对波兰人的感情要给予另一种导向:你们要给他们的心灵烙上民族的面貌特征,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使他们不致混合于其他民族,这样才能保持幸福并团结他们。”[71]论及白人进入非洲的历史过程,他甚至这样说:“如果我是那些黑人民族的领袖,我将发誓,在国家的边界上竖起一个绞刑架,在那里,我将毫无例外地绞死任何一个胆敢进入我国的欧洲人,以及任何一个胆敢离境的第一个本国公民。”[72]
这种带有道德孤立倾向的历史观、文化观,后来在俄国民粹党人那里发生强烈呼应。从民粹党到革命党,俄国思想史上的这一重要线索尚未得到清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卢梭所欲树立的国界上的绞刑架后来是大大扩展了,扩展为“一个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冷战铁幕之所以出现,当然具有卢梭不能负责的更为直接的政治史因素。不过有一点人们应该思索:在冷战铁幕出现以前两百年,欧洲近代思想生活的某一支脉已出现冷战性格:这一冷战性格先出现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分裂,后出现于19世纪流贯大陆的革命理论,最后表现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闭锁,并与其他历史因素交汇在一起,方凝结成为那道现实生活中的冷战铁幕。
第四,道德肃清——意识形态统治的内部斗争。
1762年6月10日,卢梭在逃亡途中读到《圣经·士师记》最后一章利未人受辱复仇记,为此激动,并创作了以此为题材的诗篇。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作品,表达了他一生坚持的中心思想:一个道德受到玷污的民族有权报复它的仇敌,哪怕灭绝对方部落。这种道德复仇倾向,也在卢梭的其他作品中如低沉的背景伴奏反复响起。如《科西嘉宪法草案》:“要保存国家就不能容忍他,二者之中必消灭一个;当邪恶者被判处死刑时,他已不是公民,而是一个敌人……”[73]又如《忏悔录》结尾处:“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末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74]
对待政治生活中的差异,经验政治学是彻头彻尾的世俗立场。差异双方都是世俗中人,多为是非之争。即使有善恶,也不存在善恶之争。狄德罗甚至说:“恶就存在善的本身,我们无法消灭这一个而不同时消灭另一个。”[75]因此,双方只能以对方的存在为己方存在的前提,为己方的存在方式。先验政治哲学从彼岸而来,承继了中世纪神学的巨大热情,也承继了中世纪神学的不宽容传统,并把这种传统发展为近代意识形态统治的道德清洗。在经验政治学以是非之争处理的地方,先验政治哲学总能发现为善为恶的道德内容,必引进道德法庭严加审判:是者为德为美,非者为恶为罪。是者道义热情高涨,非者为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也反激起同样的道义热情,回过头来审判另一方,双方俱以消灭对方为己方存在的前提,为己方的存在方式。所谓法兰西性格的“内战”风格之所以发生,逻辑机制可能就在这里。
五、“政治与道德相连”——卢梭政治哲学的道德灾变
现在要问:卢梭为什么会从道德救赎之宏愿悲怀,走向“世间上帝”“世俗寺院”,开辟了后神学时代的理论起源?
应该说,道德救赎即使以神学形态出现,也自有它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理应合法存在。然而如果建立起下面两个中介联系,道德救赎就很难避免不滑向“世俗寺院”的怀抱:
(1)道德目的与国家行政权力相连,换言之,神学与政治相连,让政治学承担神学的功能。
(2)政治学错位为政治哲学,换言之,政治学概念转换为政治哲学概念,以政治哲学伦理语言讨论政治学问题。
卢梭思想前半段,在《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充满忧患。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的历史性变化,使他坐立不安。那种超乎常人的道德敏感使他走在了同时代人前面,提前发出了人类异化的预警报告。这一警告经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海德格尔到萨特,历时两百年才汇成20世纪大陆学派系统的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尽管他发出这一警告的姿态是前倾后顾的复合姿态,却正应《圣经》所言,那走在最后的人,恰是最前面的人。卢梭思想的这一功绩不该埋灭。
卢梭对历史已然状态的怀疑,使他产生对社会自发演变的强烈不信任心理。而返回森林的道路已被遗忘,人类的社会化状态已不可避免;为了避免社会化走向异化,就必须切断社会自发性流变。正是在这里,他对重经验沉积的历史进步观投以鄙夷的眼光,把视线转向政治国家——自发性社会的唯一对待之物,可以注入主观理想的控制者、操纵者和改变者。他把所有的道德理想寄望于国家,让国家承担过去由教会承担的责任,为社会道德立法;同时,又在国家之上安排了奇理斯玛,在督率社会道德化过程中实现国家机器本身的道德化。这就是卢梭化合国家与社会于道德一炉的社会化学工程,也是卢梭所有政治运算的如意算盘。如此一来,这个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要求推动下,无意中转过了身子,成了一个最强烈的国家主义者、政治全能主义者。走在最前面的人又成了走在最后面的人:他的政治理论,听上去活像中世纪教俗之争中教会一方反复出现过的政教合一论。天才的“异化”理论本身也未逃脱“异化”的作弄——异化论本身发生了异化。
另一方面,卢梭既然面向中世纪而立,他就始终不能接受身后的时代背迁。其时政治学通过英国学派的自觉、不自觉摸索,正在突破神学、伦理学的母胎,发育成为一门非价值化的独立学科。与此同时,政治哲学接受神学、伦理学的遗产,发育成为另一门价值化的独立学科。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是近代社会世俗化、分殊化在学科类别划界分工的正常反应。对此,卢梭是背道而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坚持“把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贯注于理论运思,就是一生坚持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努力以前者取代后者。这样,他对神学政治论的中世纪遗产,就不是有边界意识的分流接收,而是无分界、无分流的整体接收;其间经过世俗化改造的过程,但是这样的改造,也只能是把神学政治论整体改造为政治神学论,把彼岸的上帝改造成为此岸的、世间的上帝,由此在理论上开辟一个后神学时代——意识形态时代。
在上述背景下,自然发生一场语言大转换——卢梭政治语言的道德磁化现象:几乎所有的政治概念都经过道德磁化处理,以道德词语讨论政治命题,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以伦理审美代替操作设计。如第一节引述卢梭的那段道德理想国的“进路”,共和国、共同体、政治体、主权者、国家、人民、公民、臣民八个政治基本概念,皆受道德磁化处理,转换为道德语言来讨论,成为语言转换的一份高密度标本。这样,卢梭政治哲学表面上呈道德—政治的宽泛面貌,内里却陷于道德词语的无边界讨论。阿尔图塞仅从技术角度分析卢梭理论逻辑脱漏,当然别具新意,却忽略了造成卢梭逻辑脱漏的方法论原因。无边界或跨边界讨论,是卢梭政治理论发生逻辑脱漏的一个根本失误。它既是卢梭从道德救赎走向“世间上帝”“世俗寺院”的语言桥梁,也是一代天才越界筑路时,“一瞬间”露出那么多马脚的基本原因。
这场语言大转换,是价值判断对事实判断的大换算,是政治哲学能指对政治学所指的大换算。大换算引起大逃亡,逃离道德理想的疯狂追捕。就在政治学逃亡所剩的空白地上,卢梭开始营建他的道德理想国——此岸的彼岸天国,在俗的离俗寺院,一个没有上帝却有神性的世俗寺院。后来的历史证明,政治哲学对政治学在学理上的大规模入侵,在政治实践中,必然“换算”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入侵;起于反异化理论的道德理想一旦与权力结合,本身亦发生异化——从神人同敬的理想试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
六、结语
这是神学史在政治史中的延长,是神正论在意识形态中的延长。
谁也没有理由把1789年以来大陆国家政治史中的阴暗面全部归咎于卢梭。像伯特兰·罗素那样把卢梭说成是纳粹先锋队的先导、斯大林主义的始作俑者,未免言过其实。以思想史解释政治史,使后者成为前者的注脚,如今正成为时髦,而这恰恰是当年卢梭所犯的错误。本文讨论的只不过是诸多背景线索中的一根线索,而这一线索上的每一环节都会与其他方向来的其他线索发生横向联系。作者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本身的思想清理,还是外部环境的认知定位,清理这一线索可能会比其他环境中的人们更为紧迫。而学人所能者,也只不过是从学理上疏浚这这一线索的上游来源。
政治史不能简化为思想史,但思想史的清理却可以走在政治史的前面。
[本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3年10月号,总第19期]
[42]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重远先生1989级博士研究生。
[43]柏拉国:《理想国》注47,479d。
[44]Voltaire,Philosophical Dictionary,Vol. 2,New York,1962,p.433.
[45]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页。
[4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25页。
[47]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页。
[48]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92页。
[49]Rousseau,Oevres Complètes de Rousseau,Vol. 3,Paris,1964,p.254.
[50]Ibid.
[51]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9—40页。
[52]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3页。
[53]卢梭:《爱弥儿》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9页。
[54]L. Althusser,Montersquieu,Rouseau,Marx:Politics and History,London,1982,其中评论卢梭部分可参见: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Views — Jean-Jacques Rousseau,Yale University,1988,pp.83-117。
[55]J.G. Merquiors,Rousseau and Weber:Two Study in the Theory of Legitimacy,London,1980,p.76.
[56]蒂利希:《政治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页。
[57]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9—53页。
[58]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3—55页。
[59]Rousseau,Oevres Complètes de Rousseau,Vol. 3,p.260.
[60]Ibid. p.245.
[61]卢梭:《社会契约论》,第73页。
[62]Rousseau,Politics and the Arts — Letter to M. D'Alembert on the Theatre,Illinois,1960,p.67.
[63]Ibid.,p.251.
[64]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mtemporaine,Vol. 1:L'Ancien Régime,Paris,1896,pp.323,321.
[65]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7页。
[66]卢梭:《忏悔录》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00页。
[67]卡西勒:《启蒙哲学》第4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8]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7—58页。
[69]转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80页。
[70]Rousseau,Overes Complètes de Rousseau,Vol.2,p.966.
[71]Ibid.,p.962.
[72]Rousseau,Overes Complètes de Rousseau,Vol.2,p.91.
[73]Rousseau,Oevres Complètes de Rousseau,Vol.3,p.259.
[74]卢梭:《忏悔录》下卷,第809页。
[75]勒费弗尔:《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商务印务馆1985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