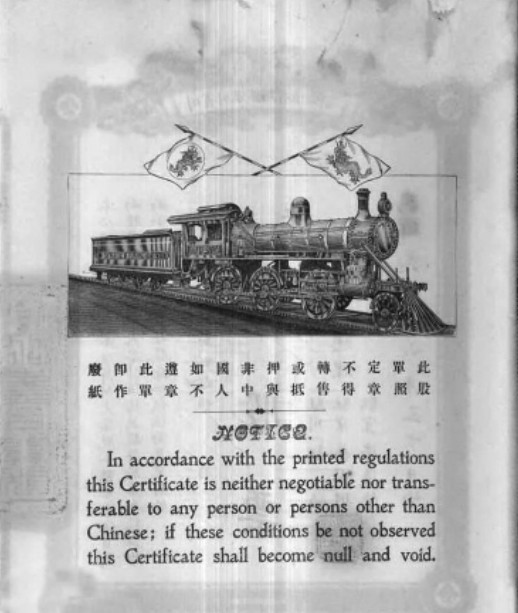一、清政府“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出台
“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是1911年5月9日的上谕中发布的。此外,5月11日批准邮传部关于取消商办铁路前案的奏折和5月22日的停收川、湘两省租股上谕也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在这几道谕旨中,清政府罗列了商办铁路的诸种弊端,认为继续下去“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所以“干路均归国有”,“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川、湘租股“系巧取诸民”,故“一律停止”,“以稍纾民困”。而在同月20日,盛宣怀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600万英镑修路的合同。
清政府并未从正面论证铁路国有之“是”,只是从反面指责商办铁路之“非”。而这些指责看似言之凿凿,仔细考察,则大谬不然。
首先,清政府指责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路工太慢,“开局多年,徒资坐耗”。这一指斥不尽符合事实:广东的进度就不能说慢。1910年,詹天佑担任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后,工程进展迅速,到1916年就全线贯通,而美国合兴公司几年时间也不过修了几十里支线。其他几省,湖南修路102里,四川修路34里,湖北寸路未修,是可以说进展不够快。但路工迟缓是不是仅仅因为商办所致,我们以由官办转为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为例细加分析。
1903年,锡良由热河督统调任四川总督,赴任至正定途次,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创设伊始,锡良即开始调派人员,筹集款项。从用人看,公司督办、会办均由总督奏委,且委任者皆为政府官员,如几任督办中冯煦、许涵度为藩司,赵尔丰为永宁道,会办沈秉堃为成绵龙茂道。公司“财政隶属于藩司”,股东“不得干预公司用人行政之权”,只可“条陈听候选择”。显然,此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行政、财政、人事诸大权均操于政府之手的官办公司。这个官办铁路公司在筹款上却全无起色,至1904年10月,仍“资本久未鸠集,工程久未兴行”。有鉴于此,四川留日学生300余人在东京召开同乡会,自募、劝募银共30余万两,并上书锡良,提出了他们的集股办法,主张改官办公司为官商合办公司。锡良仅采纳了“因粮摊认”的建议,并未接受官商合办的主张。
1905年,四川绅商强烈要求改川汉铁路公司为民办。在留日学生和在川绅商的内外呼应下,锡良于同年7月奏称,川汉铁路“官民各股,即应官绅合办”,并奏派官绅总办各一人。川路公司虽表面上成了官绅合办,但股东并未享有当时公司法所规定的权利,实权仍操于锡良为首的官府之手,四川绅民当然不满意。1907年3月,在四川留日学生和四川绅民的进一步斗争下,川路公司遵《商律》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制定了《川汉铁路公司章程》。但公司的总理、副理仍由川督奏派,公司遇重大事件,仍禀呈总督办理。此时的川路公司实际上是官督商办公司。
1909年11月,川汉铁路公司于成都召集第一次股东会,次月成立董事局。至此,川路公司才真正获得了商办性质。
从1904年1月到1909年12月,经六年时间,川路公司方具商办规模。商办公司成立后,还不到一年半时间,朝廷便颁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故把“路工迟缓”的罪名加于商办头上,显然是不公正的。
其次,上谕申斥各商办铁路公司“侵蚀”、“虚糜”股款,尤其提到川汉铁路公司“倒账甚巨,参追无着”。这里具体所指是重庆铜圆局案和上海施典章倒款案。
先分析铜圆局案。1905年1月《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把股份分为四种: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股之股,公利之股。其中公利之股系川路公司筹款开办别项利源、收取余利作为股本之股份,当时着手进行的只有试办铜圆。按“集股章程”规定,提借存放在当铺、盐局的公款银100万两,在票号借银50万两,由川路公司会同机械局于重庆设厂试办。
从这一规定看,铜圆局所需经费与川路股款无涉,只是利润充做川路股份,但实际上确由川路已筹股款中拨付银200余万两给铜圆局,遂惹得议论纷纷,指责官府违背了“无论异日有何项急需,决不挪移”的承诺。但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第2期中,已载明此款项为借款,而且此项借款基本收回,至1907年10月尚欠款仅1.9万余两,邮传部并已令“四川督臣饬局设法还清”。即便是亏损,也与商办公司无涉。
再看施典章倒款案。1905年《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订立后,一年可收股款300多万两。由于一时间铁路不能开工,各类股票均要按时付息,所以川路公司遂将股款存入商号生息,所选以成都、重庆、汉口、上海等地为主,基本存在钱庄里,另有少量借拨给政府部门、企业以生息。
1910年7月,上海正元、谦余、兆康三钱庄破产,进而引起大批钱庄倒闭。此次钱庄倒闭风潮系由于各钱庄竞相参与“橡胶股票”投机所致,川路股款也因此大受损失,所涉款项包括存在10家钱庄的银140万两。此外,又有购买兰格志股票的银85万两在此次风潮中也受损失。
暂时不用款项放于钱庄生息,是寻常办法,此点邮传部亦承认。因钱庄倒闭而受损,只能说是商家胜败常情。1910年上海有钱庄91家,1911年倒闭42家,几近半数。况三家钱庄中洋款被倒也有银140万两,上海道在钱庄中所存公款也大受损失。
钱庄倒闭,不等于所存款全部化为乌有。“三庄股东家产素称殷实,本有自行清理之议”,并非邮传部所说的“本非上等商号”。况三钱庄倒闭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即令上海道台蔡乃煌出面,向各国银行借款350万两以维持市面,应该说能挽回很大一部分损失。但具体经办的上海道台蔡乃煌却横生枝节,令三钱庄先还洋商存款,导致川路股款损失不能挽回。
至于投资股票,行情本有涨落,也不能以此作为铁路不能商办的证据。
当然,从重庆铜圆局占用股款到施典章倒款,川路公司所筹股款在保管、使用上不能说没有漏洞。拨款至铜圆局确实违背了“集股章程”,投资铜圆局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施典章在存款和投资股票中也确有营私舞弊的行为。问题在于,这应归责于谁。
铜圆局案发生在川路公司官办时期,当时主管的商部、户部和外务部就有所怀疑,在对川督锡良奏折的复议中就说:“所提当铺盐局公款百万两,究竟是何公款,提用后有无窒碍,臣部所凭悬疑,应令该督转饬查明,详细声复。”而铜圆局亏本和官场腐败有直接关系,当时铜圆局经办人之一蔡乃煌就颇受非议。若非四川绅民的斗争,此项亏挪不知要到何时。
同样,施典章也系1907年由川督奏派。若不是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提出议案和随即召开第一届股东会,还不会有查账的决定。
其三,清政府认为川湘路租股扰民,“名为商办,仍系巧取诸民”。租股一宗,为川、湘两省独有。湘省收取租股很晚,1910年始征收,筹款数额也不大。川省租股,为时既久,范围又广,数额巨大,为川股大宗,引致争议也大。其在川汉铁路筹建、修建中作用突出,亦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中央与四川地方矛盾的焦点之一,实非“巧取诸民”所能概括,亦非“一律停止”所能打发。
川路公司于1904年初创办后,筹资无路,锡良遂于1905年初采纳留日学生建议,在《川汉铁路集股章程》中作出抽收租股的规定,又在同时颁布的《川汉铁路按租抽谷详细章程》作了进一步规定,并于当年秋忙后开始征收,涉及全川140余府、厅、州、县。1907年颁布的《商办铁路公司续订章程》中,又出台了提高租股年息(4厘增至6厘),增加方便租股的股票面额,改变付息方式(在次年租股中坐扣),预定租股总额上限(占川路总额预算的五分之二),设定租股股东权利等意在刺激租股交纳者积极性的新规定。
租股对川路股款筹集的作用是巨大的。1905年当年即征收达290万两。有据可查的1908年和1909年,坐扣上年利息后亦达到151万余两和134万余两,分别占当年全部股款的80%和81%。到1911年停收租股,六年合计的租股数额达928余万两。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无租股即永不可能有川路。是故,虽各界对征收租股议论纷纷,但始终未能停收。
至于租股扰民,也确非虚言偏见。晚清举办新政,其费主要来源于增加捐税。清末四川全省主要征收税目有28项之多,征收额数亦巨,“川省财赋,占全国十分之一,滇、黔、甘、新四省协饷,皆仰于川,川糜烂,四省不保”。以一省养五省,已属支绌,而租股又大大超过此前任何一种捐税。由于租股征收情况是考核地方官的一个尺度,同时“许各地就本地情形据实禀请酌夺更改”,在征收过程中自然会有各种弊端。即使支持租股的人士也并非不清楚这一点,但考虑到租股对于川路,进而对于国家主权的重大意义,“租股可废而不能废”。只言扰民,不顾大局,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更重要的,租股虽是强制征收的,但本质上实大不同于各类新捐旧税。早有研究指出,租股有股息,租股股票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价证券,租股股东享有《公司律》规定的权利,故川路租股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独特方式。因此,清政府把租股当成寻常捐税,一纸上谕,一免了之,反认为是皇恩浩荡,实是指鹿为马,李代桃僵,当然不能服人。
以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民间实力,自筹资金修建铁路确有些勉为其难,力所不逮。那为什么各省绅民热切要求自办铁路呢?这充分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清政府又日趋软弱的形势下人民的爱国热情。看待各省人民有些“自不量力”地争办本地铁路的问题,不应该不考虑到这个大背景。一部分中央大员、地方大吏,也产生了利用民众的热情和财力以保存或收回利权的认识。这也是收回利权运动能开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早在1898年11月19日,矿务总局公布的《矿务铁路章程》即说:“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此后总以多得商办为主。”不到一个月,这个措施就和其他的维新政策一起被慈禧太后废除了。
在新政中,商办铁路的提议再度被提起。1903年,商部尚书载振上奏,认为侨商张煜南请办潮汕铁路,可“开风气而保利权”,地方官“不得以事属商办,稍存漠视之意,致拂舆情”,尽管他仍认为商办只适宜工费有限的铁路。
如果说最早提议地方自筹资金修筑铁路的是一些商人,锡良奏请筑造川汉铁路则表明各地督抚开始赞同这个主张。锡良上奏中说:“四川天府奥区,物产殷富,只以限于运转,百货不能畅通,外人久已垂涎,群思揽办,中人亦多假名集股勾结外人,若不及早主张官设公司,必致喧宾夺主,退处无权。”随即,各省纷纷请办铁路。1904年11月,江西京官李盛铎等请准开办全省铁路,认为“近年铁路之利,觊觎者多,江西完善之区,尤宜及早自行筹筑”。1905年8月,浙江京官黄绍箕也请办浙路,他说:“浙江商埠繁盛,倘非及时筹筑铁路,殊不足自保利权。”1907年8月,河南官绅王安澜等表达了更急切的心情:“铁路为生民命脉,中州绾铁路枢机,非急筹自办,不足以杜觊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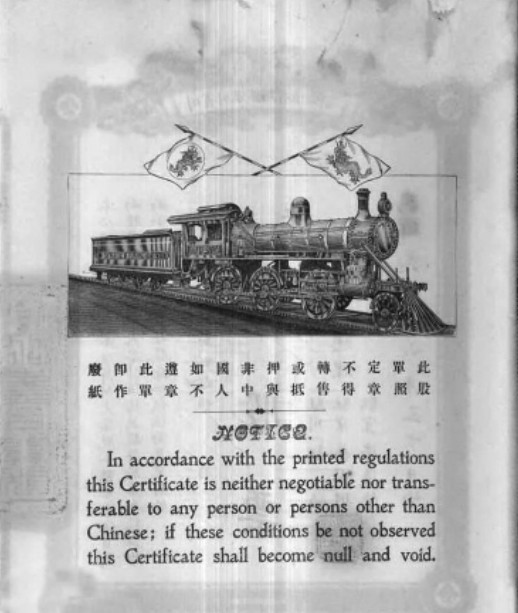
川汉铁路公司股票背面印有 “不得转售或抵押与非中国人” 的字样
各省铁路公司章程也详细落实了自办的主张。《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国人股份;其非中国人股份,一概不准入股,并不准将股份售与非中国人。”湖南省开办粤汉铁路的招股章程中也规定:“公司股票只招华人,凡洋人概不得附股。如有代购或转售抵押与洋人,以及本为华人,而购票后改注洋籍者,均作为废纸。”其他各省铁路公司的章程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单纯看各省铁路公司对洋股的态度,似乎太过极端,有盲目排外之嫌,但结合列强强修中国铁路的咄咄逼人之势和一些中央官吏的“保”利权之法,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困难处境和良苦用心了。
如前所述,1895年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加上新兴的日本掀起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掠夺筑路权是列强瓜分中国主权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其具体手法就是强迫中国向他们举借筑路款,同时获得出售原料、设备,提供工程技术人员和开采沿线矿产等特权。其目的在于扼住中国的生命线,路到一处地方,即控制一处地方。即使在各省已开始筹划自办铁路后,列强仍不放弃,以各种手段,包括威胁、恫吓来进行阻挠。如川汉铁路公司甫一成立,英法美三国立即要求让与该路贷款权。英国公使在1904年向外务部提出按照1903年7、8月往返函件,“所需外款皆在英美两国借用”。驻重庆法国领事也在同年7月向锡良要求由法商包揽路款和路工。
面对危局,有些人提出了“均利止贪”、以夷制夷的办法。盛宣怀的主张最为典型,他认为:“各国窃保护之名,分占边疆、海口,渐入腹地。一国起争,数国效尤。牵制之法,不足破其阴谋;通商之利,不足抵其奢欲。处今日而欲散其瓜分之局,惟有照土耳其请各国同保护。凡天下险要精华之地,皆为各国通商码头。特立铁路矿物衙门,统招中国及各国股份,聘请总铁路司、总矿物司,职分权力悉如总税务司。似此悉毕路成,英、德不患俄独吞;缅滇路成,俄、法不患英独噬。”此种办法,不啻开门揖盗,引虎驱狼。虽然盛宣怀接着又列举了大局定后一系列自强之法,但实际上举国被瓜分之后,再好的设想也终是虚言。
可见,包括川路公司在内的各省铁路公司在明知自筹资金有困难的情况下,仍坚决抵制外款实在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是在以一种很悲壮的,甚至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方式护卫国家主权。上谕对官民的爱国热情只字不提,实则予以否定,联系清廷以前的态度,实是出尔反尔。
清廷和盛宣怀等中央大员们不该忽略的另一点,是1911年的中国已不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时代了。清末新政,特别是1905年开始的立宪运动,已使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的中高层官吏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政的各项措施中,影响最深远的是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和预备立宪,后两者对当时官绅士子在思想观念上影响尤深。

盛宣怀像
1905年,始于隋朝的科举制被废除。一项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制度一旦终结,其影响绝非决策者可以完全预料。就在这一年,赴日留学生人数有6000人之多,为此前此后历年之最。新式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不能像传统士人那样在政权内立德立功立言,他们开辟并占领了报刊这一近代舆论工具,臧否时事,评论国政,宣扬民族主义,鼓吹立宪,逐渐地掌握了舆论主导权。一批思想开明、头脑清醒的封疆大吏的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逐步倾向于立宪。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迫使载沣同意预备立宪缩短至1913年,足见立宪派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央决定产生影响。同时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如果在哪项政策上自食其言,必将面临激烈的反对。
1909、1910年,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相继成立。按咨议局章程,凡“本省应兴应革事件”、“本省权利之存废事件”、“本省担任义务之增加事件”等,均应经咨议局议决;按资政院章程,凡“国家岁入岁出预算事件”、“国家岁入岁出决算事件”等,均应由资政院议决。签订借款修路合同,向外国举借巨款,交资政院审议是必经程序,铁路国有政策所涉各省的咨议局也有权质询。盛宣怀当然知道这个规定,但由于交资政院审议各案,“资政院认为可行者,方能照办;一经否决,势须取消”,所以他知道借款合同在资政院肯定通不过,“如果交议,资政院认为不应借贷,彼时国家有此权力销毁四国合同乎?”索性硬着头皮,不交院议。而令盛宣怀估计不足的是,招致的反对是如此激烈。1911年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专门提议“内忧外患,恳请本标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从会议记录看,可谓群情激昂。随即上奏弹劾盛宣怀,导致盛的下台。
不考虑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按资政院、咨议局章程办事,逆历史潮流而动,从这点说,“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出台是不合时宜的。
借款合同之不交院议,盛宣怀的另一辩解是此笔借款他并非始作俑者,最初的策划者是两湖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
粤汉铁路之兴建,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即与清政府订立《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取得了粤汉铁路的修建权及沿路矿山开采权及其他特权。1905年,在收回权利运动中,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主持,中国以675万美元赎回。由于资金缺乏,自建步伐蹒跚不前,1907年,只好又寻求借外债筹款。几经周折,1909年5月,张之洞与英国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代表贾思纳、德国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订立草合同25款,名为“中国国家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借款总额550万镑,作为建设官办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干线和鄂境川汉铁路干支两线之用(川汉铁路干线指京汉线上之广水经荆门至宜昌段,支线指荆门至汉阳段,干线长约1000里,支线长约600里)。草合同签订后,俄、美、日亦闻风而至,最终美国插入进来,三国银行团遂成四国银行团。
从1908年张之洞着手谈判时起,两湖人民就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拒洋款斗争,加上1909年10月张之洞去世,两湖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事宜由邮传部接管,两个因素阻碍了清政府正式签字的步伐,同时迫使清政府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先后准许湘境粤汉铁路和鄂境粤汉、川汉铁路商办。
四国银行团为尽快正式签订借款合同,于1910年4月向清政府重申反对中国粤汉、川汉铁路商办。5月,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并于8月照会清政府要求速订立正式借款合同。9月、10月、11月又接连照会清政府。迫于压力,邮传部从1910年底开始和四国重开谈判,最后于1911年5月20日和四国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
铁道干线的筹划,有明显的随意性。铁路国有还是商办,本非原则问题。但清政府在借外款的同时匆匆抛出铁路国有政策,不免令人生疑。通盘筹划全国铁路,并作出干路、支路的划分,始于1906年,是当时掌管铁路的商部为进行全国线路的规划而提出的,但未提出具体方案。1907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主张以北京为中心的四大干路计划:京汉、粤汉至广州为南干线,京张、库张至恰克图为北干线,北京出关到瑷珲为东干线,京陕、陕新抵伊犁为西干线。进而又划分了各干线的支线。邮传部尚书陈璧基本同意这一主张,并指出这是从政治地理角度的划分。1909年,邮传部又提出,把已建好的汴洛路向两边延伸,“东达徐海,西展至陕甘、新疆,成东西一大纬线”。1910年,邮传部再次上奏,主张“以自开商埠之海州为尾闾,西连汴洛,以达甘新,为中原东西一大纬线”,但并未说明此“纬线”是否就是“干线”。同年锡良上奏中始称川藏铁路为干线,次年郑孝胥的“四大干路说帖”中也把川藏铁路列入干路之列。但两人的主张未见邮传部的反应,此时旧事重提,显然不是深思熟虑之举。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七日(1911年8月11日),云贵总督李经羲还致电内阁,询问滇路到底为干为支。李经羲是主张铁路国有的,他的意图是想把西南边陲的滇桂线列入干路之列。到保路运动已不可阻挡的9月30日,邮传部又生花样,提出既有川路商办,另筑一路由陕入川归国有。轻率随意至此,若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真的实施,不知又会造成何等混乱。
出台国家政策去适应一个对外借款合同,有“劫路误国”之嫌。借款合同中引人注目的一款,是用宜夔段替换了荆汉段。从地理位置上说,宜昌至夔州在鄂境,但由于湖北财力不厚,而这段又关系川路的出口问题,经两省协商,由四川省修筑。借款草合同亦只言宜昌到广水一段,为什么在正式合同中作变动呢?盛宣怀的解释是:“原合同借款用法,于湖南、湖北干路之外,今干路既定国有,枝[支]路自应听鄂人自办,以符奏案。而洋人以成约在先,汉荆枝[支]路里数不能让减,持之甚坚。本部调停办法,特以宜昌至夔州之干路六百里,以换汉荆枝[支]路六百里。”之所以以宜夔段换,是因为这一段“为世界第二险工”,“非用专门洋工程司不能建妥”。
西方列强对川汉铁路觊觎已久未果,这次铁路借款又给列强提供了机会。1909年8月10日,费莱齐致美国国务卿电中谈及:“中国反对提及延长入四川。”可见,四国银行团早就想把川汉全线纳入借款合同,但遭到了张之洞的拒绝。1909年10月5日,张之洞去世的次日,费莱齐又致电美国国务卿,称:“不论在中国派定另一官员接替张之洞代表中国后,目下这样的合同能否立即签订,抑或此案须全盘重新商讨,而我国对川汉铁路的既定立场是不能动摇的。”这里的“重要立场”,主要的一点显然即是把借款合同中鄂境川汉铁路延入四川境内。1910年5月23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达成妥协,其中对川汉全路如何瓜分已有详细约定。在1910年重新开始的借款合同谈判必然会涉及这个问题,只是慑于两湖人民反借款的压力,邮传部始终未敢公开这一点。1911年5月2日,四国公使照会外务部,称关于借款合同,“现在他项各节,皆已妥协议定”。“他项各节”应该包括将宜夔段纳入借款合同。盛宣怀自己也说得明白:“查四国借款合同不能消灭,所以提议铁路国有。如铁路不为国有,则借款合同万不能签字。是铁路国有之举,其原动力实在于借款之关系。”以此看,铁路国有即是为了一项不合理的对外借款合同而出台的并非必要的国内政策。
进一步分析,借款合同共借600万英镑,除去用于赎回美国合兴公司金圆小票的50万镑,剩下550万镑,约合银4000多万两,根本不敷粤汉、川汉两线所需,以后必然要续加借款。这必将扼住出川咽喉,带来无穷之弊。
而且,“铁路国有”仅指干线,声明支路仍允民自造,难道就不怕再重复“路工缓慢”、“侵蚀”、“虚糜”的问题吗?又说保留民力,“以造枝[支]路,其工易成,其赀易集,其利易收,使其土货得以畅行,亦如河南之芝麻、黄豆,岁入数千万之多,民间渐资饶富。此枝[支]路之可归民办又一也”。既可“岁入数千万”,就不能修干路吗?粤路、夔州至成都之川汉路,民又可附股,能说是国有吗?前后如此自相矛盾,进一步暴露了铁路国有政策出台的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