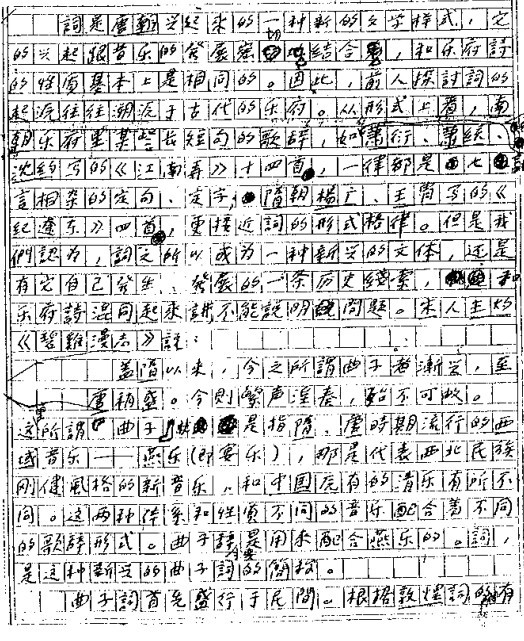第三节 胡云翼对现代词学理论的贡献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审视过去的文学;然而这样的认识与评价总是有其时代局限的。当我们回顾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词学研究的历程,也是如此。胡云翼是受现代新文学思潮影响的词学家,在其四十年的词学研究中正反映了从新文化运动到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学术思潮主流。在他逝世三十余年之后再来评价其词学成就时,是不应脱离其历史文化条件的,尤应看到它在现代词学研究进程中的意义。

胡云翼像
胡云翼,原名耀华,生于1906年,湖南桂东县人。1927年毕业于湖北武昌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湖南长沙岳云中学、南华女中、湖南省立一中、江苏无锡中学、镇江师范、暨南大学等处任教。后又在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江浙一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曾担任过地方行政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继而到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于1965年在上海去世。他在学生时代参加文学活动的同时,即开始研究词学。1925年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书时,与同学组织艺林社,创办 《艺林旬刊》,受到郁达夫的指导和重视。这年在 《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了 《文学欣赏引论》《词人辛弃疾》和 《李清照评传》等论文,出版了 《中国文学概论》(上海启智书局)。早期的文学作品有小说 《西泠桥畔》《爱与愁》,散文 《麓山的红叶》 《爱晚亭的风光》 (艺林出版社)。1926年出版了 《宋词研究》(上海中华书局)。此后陆续出版的词学论著有 《词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词史大纲》(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中国词史略》(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词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主编了 《词学小丛书》(上海文化服务社1937年),编选的词集有 《词选》(上海中华服务社1936年)、《唐宋词一百首》(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61年)、《宋词选》(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62年)。此外还著有 《唐诗研究》 《宋诗研究》和 《中国文学史》等。胡云翼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词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词学家。
在现代词学研究里是胡适开辟了新的道路,以新的社会审美观念描述了宋词发展的轮廓。胡适的词学观点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其研究方法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其表述方式采取了新的白话文体。胡云翼正是在新文学观念的鼓舞下和胡适词学思想的影响下进入词学研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熏陶习染,使其词学观点在新的条件下又得到发展。胡云翼的词学观点很有时代理论特色,他初步建构了词史的规模并充分肯定了豪放词的历史地位:这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有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胡云翼同当时许多新文学的倡导者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态度。他研究词学的目的与保存国粹的守旧派有根本的区别。在谈到 《词学ABC》写作的主旨时,他说:
第一,我写这本 《词学ABC》,并没有提倡中国旧文学,这是最要辨明的。我们为甚么要研究词?乃是认定词体是中国文学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许许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让我们去鉴赏享受,我们当然不愿抛弃这种值得鉴赏享受的权利。可以说,我们的和词发生关系,完全是建立在读词的目标上面。因为要读词,便得对词作一点粗浅的研究,懂得一点词的智识。我写这本小册子的主旨,便只是想告诉读者一些词的常识,做读词和研究词的帮助。目的仅仅如此而已。我绝不像那些遗老们,抱着 “恢复中国固有文学之宏愿”,来 “发挥词学”的。
第二,我这本书是 “词学”,而不是 “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填词。如果读者抱了一种热心学习填词的目标,来读这本书,即便糟了!因为我不但不会告诉他一些填词的方法,而且极端反对现代的我们,还去填词。为甚么我们不应该去填词?读者不要疑心我是看不起词体才说这种话。我们对于曾经有过伟大的光荣的词体,是异常尊重的。可是这种光荣已经过去很久了,词体在五百年前便死了。[1]
这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将词体文学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学遗产对待,而不是要去恢复这种古旧的文体。但仅仅为了个人鉴赏享受才去了解词学,而且极端反对现代人去填词,这样的看法有其片面性。我们研究词学应有更为深一层的意义,而某些现代人偶尔填词也并非坏事,虽然不宜提倡。尽管如此,我们如果将胡云翼的态度与国粹派相比较,显然前者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关于宋词的特点,胡云翼认为它是 “时代的文学”和“音乐的文学”。他说:
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宋以前只能算是词的导引;宋以后只能算是词的余响……这种词是富于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活动,以音乐为依归的那种文体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一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歌词之法传自晚唐而盛于宋。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声,制词与乐协应。又有自度腔者,并作新词,任随词家的意旨,驱使文学在音乐里面活动。这种音乐文学的价值很大。[2]
这是在词学史上第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宋词的基本特点,尤其是第一次提出了 “音乐的文学”的观念,此后遂为词学界所接受。基于这样的认识,胡云翼高度评价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强调宋以后的词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生命已经完结,而成了文学史上的陈物,因而根本否定宋以后词的价值并反对现代人再去填词。虽然词体在发展过程中有与音乐结合的一面,也存在脱离音乐束缚的倾向;因此,它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可以脱离音乐而获得新的生命。关于对宋词的评价,胡云翼虽然以时代文学和音乐文学的观念给予了很高评价,承认其“特殊价值”,但对其 “弊点”的揭示则是近于苛酷的。他说:“宋词的弊点,我们至少可以从宋词的颓废发现出来。据我的观察,宋词有两个本体上的病根,有两个现象上的弊点。”其所谓两个本体上的病根即 “音数上的限制”和 “声韵上的限制”;两个现象上的弊点即 “描写对象的狭隘”和 “古诗辞意模袭”。“宋词既然有了这种种的缺陷,加上晚宋讲究词派,讲究词法,作品之陈腐,千篇一律,无非为前人作书记,其下者书记还不如呢!这正如晚唐、西昆诗文发展一样,国家要亡了,而他们这些文人仍沉醉于象牙之塔,高唱他们的艳歌,不知时代是何物。这不是宋词的厄运最后临到了吗?”[3]似乎北宋和南宋的灭亡,宋词都是责无旁贷的了。这未免过高地估计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如果我们联系新文学运动以来,人们急切要求文学直面现实人生以期唤醒民众、复兴中华的时代文化心理,自然可以谅解当时对宋词脱离社会现实倾向的严厉责备了。
《宋词研究》初版于1926年,至1928年已出了第三版,它在我国现代词学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著者在 “自序”里说:
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的特殊地位,自有她的特殊价值,而作文学史的分工工作,对于宋词加以条理的研究和系统的叙述的专著,据我知道,现在似乎还没有。以前虽有词话、丛话一流书籍,偶有一得之见,而零乱掇拾,杂凑无章。我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组织化、系统化的一种著作。
著者并未夸大其辞,它的确是词学史上最早的系统研究宋词及其历史的专著,尤其可贵的是它以新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宋词。近世词学家刘毓盘的 《词史》出版于1930年,王易的 《词曲史》和吴梅的 《词学通论》都出版于1932年。它们基本上采用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而且都比 《宋词研究》问世迟了数年。因此,《宋词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忽视的。我们应庆幸我国现代词学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宋词研究》的上篇为宋词通论,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词的起源,特点和发展规律;下篇为宋词人评传,评介了两宋的主要词人,基本上是宋代的词史。著者期望它能使读者明了词的内涵外延,知道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审识宋词作家作品,从而对词的欣赏和研究发生更大的兴趣。《宋词研究》是胡云翼全面研究词学和词史的基础。以后,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词学专著 《词学ABC》和 《词学概论》,形成了词史专著 《中国词史大纲》和 《中国词史略》。胡云翼关于词学知识的介绍,不同于梁启勋等人主要讲解词的体制、声韵及作法,而是注重理论的探究。在 《词学ABC·例言》里,他将词学的范围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什么叫词?已是颇不易回答的问题,本书从诗词的分野上,从词的特质上,而下一定义。
二、本书依历史的考察,最先说明从诗到词嬗变的理由及其路径,以期阐明词在文学史上所留的痕迹。
三、词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一一加以批评,并从词与乐的关系上作一答案。
四、词的发展历史,及为研究词学最切实重要之部分,本书详加叙述,并指示著名作品,以助欣赏。
这为词学的宏观研究开创了途径。胡云翼关于词史的面貌作了较细的描述,如在 《中国词史略》里追溯了词的起源,关于晚唐五代词分别介绍了晚唐词、西蜀词和南唐词,关于北宋词则分为四个发展期来评述,关于南宋词则分为南渡词坛、南宋的白话词、南宋的乐府词、晚宋词来评述,对金词、元词和明词也分别作了简要介绍,关于清词则分别评述了清初词、浙派词、常州派词和清末词。其中评介的词家有百余人,阐明词史的流变,剖析了词派兴替的原因。从上所述,可以认为胡云翼为词学和词史的研究建构了初步的系统与规模。
胡云翼研究宋词特别突出了豪放词的历史地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早在1925年,他在论文 《词人辛弃疾》里便表露了对豪放词的态度。他认为:
北宋为了受金兵不堪的压迫,把一个都城不得已的由汴京移到临安来,政治上显示了许多的纷动,社会上感受无穷的疮伤。经过这样巨大的牺牲以后,而有所成就的,不过助长几个英雄志士的成名,几个诗人词客作品的成功而已。弃疾便是成名的英雄里面的一个,同时又是成功的词人里面的一个。伟大的词人辛弃疾,近人王国维氏评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相颉颃者,惟一幼安耳。”其实,我们即老实说辛弃疾是南宋第一大词人,也不算夸张吧。[4]
胡云翼发展了王国维推崇北宋词的观点和胡适关于白话词的理论。他在 《宋词研究》里论述宋词发展过程时,对宋词的发展线索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如说:
词体经过五代至北宋长期的发达,无论在小令方面、长调方面,婉约的词或是豪放的词都有专门的作家,极好的作品。本来体格谨严的词体,描写的对象又是很狭的,经过这么长期的开展,差不多开展已尽,无路可走了。而且北宋词既有很好的成绩,很好的作品,作为范本,南宋词人不由的,便走上古典主义的路上去了。讲词派,讲词体,讲求字面,讲求雕琢,尽在作法上转来转去,虽有警字警句,而支离破碎,何足名篇名家?况所谓作法之讲求,也不过以北宋名家词为摹本。是则虽有成就,无非北宋人之皂隶,更何能超北宋而上之呢?故在量的方面讲,南宋词或成熟发达到极地无以复加了;若论到词的本质,则南宋词确乎是词的末运了。[5]
继而胡云翼在 《词学ABC》里更鲜明地肯定豪放词的历史地位,认为:
词体之得着解放,自苏轼始,柳永虽然倡导了慢词,还是因袭晚唐五代词的曼艳风气,还没有打破 “词为艳科”的约束。到苏轼便把词体的束缚完全解放了。他一方面超越了 “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变婉约的作风为豪放的作风,一方面又摆脱了词律的拘束,自由地去描写……
我们则认定这种 “别派”,是词体的新生命。这种新词体离开了百余年来都是这样温柔绮靡的旧墟,而走上一条雄壮奔放的新路。这条路可以使我们鼓舞,可以使我们兴奋,而不是叫我们昏醉在红灯绿酒底下的 “靡靡之音”。[6]
从胡适、胡云翼以来对豪放词的赞赏与对婉约词的贬抑的词史观点,是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动乱不安和反传统的思潮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这种词史观点带有两极意识的特色,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盛行的社会学方法有某些相近或相通之处,于是它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宋词选》里,胡云翼发展了其前期的词史观点,认为豪放派是宋词的主流。他说:
词至南宋发展到了高峰。向来人们都认为宋朝是词的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如果把这话说确切一点,这光荣称号应归之于南宋前期。这时期爱国主义词作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复杂的民族矛盾,放射出无限的光芒……
辛弃疾、陆游两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以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词人陈亮、刘过等进一步发展了南宋词。辛弃疾一生精力都贯注在词的方面,成就更为杰出。他继承着苏轼的革新精神,突出地发扬了豪放的风格。在总结前人词思想艺术方面的创获的基础上,进而扩大词体的内涵,使其丰富多采,把词推向更高的阶段。他们的词作汇成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著称的豪放派。
由于我国现代文化精神中存在着一种两极意识,强调事物对立面的绝对斗争,于是认识方法趋于极端:肯定一方便绝对地否定一方,有主流则必然有与之相对抗的逆流。在这种两极意识的支配下,胡云翼认为:
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词里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这是一方面……与此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坛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这又是一面。
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是依附于统治阶级以清客身份出现的词人。他们承袭周邦彦的词风,刻意追求形式,讲究词法,雕琢字面,推敲声韵,在南宋后期形成一个以格律为主的宗派。[7]
在 《宋词选》里从选录、注释与作家作品评介,都贯彻了关于宋词主流与逆流的观点。选注者说:“我们根据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来评选宋词,便不能不定出新的标准。这个选本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这个 “新的标准”非常符合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但是,这种豪放派主流论与宋词实际不完全一致,而且对柳永、晏殊、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婉约词人的评价是极不恰当的;反映出对他们的作品未能深入理解,片面地强调思想性,并未在选评中达到 “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社会美学思潮也 “通常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①进入80年代以后,词学界在探索新的研究途径时,对社会学批评模式予以检讨,较为注重作品的艺术性,认真研究婉约词——特别是南宋的婉约词,并对它作了重新的评价。这无疑是词学研究的可喜进展。当我们回顾自清代初年词学复兴以来的词学史时,又不能不承认:胡云翼关于豪放词在词史上地位的高度评价是有其反传统的合理性,其社会批评方法对宋词思想性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很深刻的。因此,我们在评价胡云翼词史观点时应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能重蹈两极意识的覆辙。学术的发展总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合理的因素是会保留下去的。但愿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寻求到一种较为理想的批评模式,可以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批评中真正地统一起来。
胡云翼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是我国现代词学史上以新文化思想来研究词学并取得很大成就的专家。词是音乐文学、词为艳科、宋词无流派,这三个论断关系着对词体文学本质的认识,是胡云翼对现代词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词与音乐的关系曾为宋人认真探讨过,而自清代凌廷堪的燕乐研究和谢元淮探寻词乐以来已引起了近世学者的关注。从现代的学术视角对此现象加以概括的任务是由胡云翼完成的。他第一次在中国学术史上提出了 “音乐的文学”的观念:
中国文学的发达、变迁,并不是文学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关系,而与音乐有密切的关连……中国文学的活动,以音乐为归依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跃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末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也自然停止活动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8]
这样,“音乐的文学”或称 “音乐文学”即是与音乐配合或结合的文学。中国古代音乐曾经发生过数次变革,旧的音乐为新的音乐所代替,宫廷音乐受到民间音乐的冲击,传统音乐受到外来音乐的影响;这些都可造成与之配合的文学的变化,它们的艺术生命是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关于音乐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胡云翼补充说:“本来单独的文学效力在社会里面,远不及音乐的效能来得大。因为音乐的关系,因此宋词也跟着音乐而得着较大的普遍性。”[9]音乐文学可以随着音乐的流行而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故能起到更大的社会效应;这是它远胜于纯文学作品之处。从音乐文学的角度以认识词体性质,便可进而认识它的时代文学意义和特有的文学价值,可使词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即具现代社会科学的特点,从而避免了纯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弊端。胡云翼因持音乐文学的观点,在探讨词体起源时作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词的起源,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 (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最初只是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辞。这种歌辞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10]
时过七十余年,我们现在看来,此论断是能经受学术检验的。胡云翼首创的音乐文学观念在20世纪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边缘性学科。1935年朱谦之的专著 《中国音乐文学史》由商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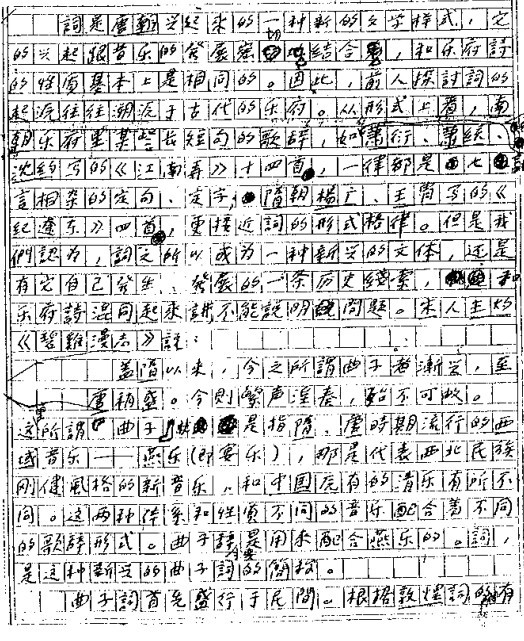
胡云翼手稿
印书馆出版,它系统地探讨了自 《诗经》以来的历史上各阶段的音乐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从音乐文学来考察词体,不难发现它是音乐文学最典型的形态。1946年词学家刘尧民论述词与音乐的关系时认为真正的音乐文学应是:“不但要求诗歌的系统和音乐的系统相结合,而形式也要求 ‘融合’无间,才够得上称为 ‘音乐的文学’。”[11]中国各种音乐文学中在形式上完全与音乐融合的只有词体,因为它是倚声制词而以音乐为准度,使文学服从音乐的艺术导向的。自此以后,中国学术界接受了“音乐文学”的观念。词学家施议对系统地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后说:“词为 ‘声学’,即 ‘音乐文学’;音乐性是词的突出的艺术特性之一。研究词的特性,研究词体演变过程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都不可忽视词与音乐的关系问题。”[12]这些皆可见 “音乐文学”观念对现代词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有着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很强调文学体性规范的。关于词体的基本内容特点,在 《花间集序》里已表明它是以华丽的词语、秾艳的风格,表现永恒的爱情主题。此种倾向亦为宋人继承和发扬而成为词的体性传统。宋代词人将描写爱情的作品称为“艳体”或 “侧艳体”。南宋初年词人程大昌谈到 《六州歌头》说:
《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如 “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者是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之事实之。闻其歌使人怅慨,良不与艳辞同科,诚可喜也。
—— 《演繁露》卷一六
文中所举的 《六州歌头》词例即北宋初年李冠的作品。此曲音调悲壮,声情激越,雄姿壮彩,不同于倚红偎翠的柔婉作品;所以程氏以为它不与艳词同类。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属于艳科,即涉及艳情的。自北宋中期苏轼改革词体以来,词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其艳科的特性并未因之丧失。[13]中国现代词学怎样从理论上来概括词的体性?胡云翼从分析宋词的时代文化背景而探讨词体文学繁荣的原因时,他以为 “一种文学发达,也必有它的时代背景”。北宋前期曾经有一个升平富庶的时代,“既是国家平靖,人民自竞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他继续分析说:
到了南宋,经过国破家亡,才有那些英雄志士,创为英雄气魄的词,抒写伟大的襟怀,描写壮美的情绪,把词为艳科的观念一下打破。但到了南宋偏安已定,渐渐又恢复了北宋的酣眠状态。国力既微,人心已死,金元天天要南侵。既无力抵抗,又不自努力,只好苟延残喘,多活一天,便算一天;得快活时,且尽量快活一番。由这种畸形的时代心理作背景,艳词作品之多而靡,比北宋更要活动。[14]
胡云翼又在总结宋词之弊时,认为 “宋词所描写的对象不过是‘别愁’、‘闺情’、‘恋爱’的几方面而已”。他最后得出结论:
这更可证明词只是艳科。虽有苏轼、辛弃疾辈打破词为艳科之目,起而为豪放的词;但当时的舆论均说是别派,非是正宗。[15]
这是在词学史上第一次提出 “词为艳科”的观念。稍后胡云翼概述北宋词的发展情形说:
柳永虽然倡导了慢词,还是因袭晚唐五代词的曼艳风气,还没有打破 “词为艳科”的约束。[16]
这从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社会享乐意识和宋词描写的内容的分析,结合宋代词学家关于词体性质的论述,作出了“词为艳科”的结论。此论是有历史事实、文学现象和传统词学理论为依据的;虽然论述尚不够深入,但却为认识宋词的文学性质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词为艳科,这是词体文学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它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是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当然,以 “艳科”来概括整个宋词的题材内容是不够全面的,但它确能解释词体的基本体性和作品中爱情主题的普遍现象。这一观念所包含的理论价值是不能与传统词论中的 “小道”和“诗余”概念相提并论的,因为后者表现了守旧文人对词体的轻蔑和误解,在现代词学中是应予以摈弃的。我们回顾现代词学的发展时,不能不承认 “词为艳科”观念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因为由此可将传统词论中的政治教化说、尊体说、寄托说等否定,发现它们与词体的相悖,于是能更为真切地认识词的历史真实。
宋代词学文献中有关于 “体”、“雅词”、“豪气词”、“自成一家”的概念,以及关于词人个体风格和群体风格的分析,然而却无 “流派”的概念。这是由于词的体性决定的。词人写作歌词是用于花间尊前遣兴娱宾以抒绮怀的,不将它视为正统文学,以致有的作者不收入自己的文集。词人在即兴挥毫抒写相思离别之情时,不像作诗文那样严肃并刻意于艺术追求,仅是表达个人的自然之情,无意于树立宗派以在文学界造成声势。所以这是与宋诗的自觉的流派意识相反的。词学史上的流派概念可溯源于明代的张,经王士祯的推行而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分;近世更有关于宋词诸种流派的划分。由于文学流派概念引入词学,因其不符合宋词的实际情况,若据以阐释词史,必将严重影响现代词学研究的科学性。胡云翼认为婉约与豪放并非词派,只是宋词发展中的两种趋势,或者可说是两种艺术趋势。因此,他断定:“根本上宋词家便没有一个纯粹属于哪一派的可能。”他进而在分析了苏轼与辛弃疾词后说:“我们既然不能说某一个词家属于某派,则这种分派便没有意义了;何况分词体为豪放与婉约,即含有褒贬的意义呢?”[17]在20世纪20年代词学界不仅将宋词划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还分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白话派与古典派等。胡云翼最后作出结论:
总之,宋词人作词是很随意的,有时高兴做白话词,有时高兴做古典词;有的时候很豪放,有的时候很婉约;没有一定的主义,没有一定的派别,我们决不能拿一种有规范的派别来限制他们。[18]
在此观点指导下,胡云翼于1933年出版的 《中国词史略》和《中国词史大纲》两部著作里都坚持了宋词无流派的学术见解,对宋词作出了较合理的分期,对词人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建立了中国词史的理论框架。[19]
词是音乐文学,词为艳科,宋词无流派,这三个论断构成胡云翼词学理论的基础,是他关于词学、宋词和词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它们都是在1925年胡云翼青年时代确立的。我们纵观这位词学家的整个著述,其词学专著和选集极多,而论文甚少,尤其是对其早年形成的词学观点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仅具草创性质。他的著述在词学普及工作中有重大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然而在词学界某些学者看来,它们不够深刻,而且具有偏离传统词学的倾向,以致每有极不公正的批评。胡云翼的词学理论又因其普及性而对词学界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发展时,理应全面研究这位词学家的词学理论并从中吸取合理的因素。
中国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之间和从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之间的历史是断裂的,标志着规范形态的转换。学术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想象从古代到现代是直线的进程,后者的出现即意味着对前者的否定。当现代社会重建规范形态时,必须以新的价值观念进行文化选择,亦必须从传统中接受于现代有意义的因素。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词学,怎样在批判传统词学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理论,它既是现代的而又有传统的根基,尤其是应以现代的叙述方式适合现代的语境:这是非常困难的。胡云翼以新文化思想为指导,完成了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重建了现代词学理论基础。这是他对现代词学的重大贡献。
[1] 胡云翼:《词学ABC》第1~2页,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
[2]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4~6页,中华书局1926年版;又见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第4~5页。
[3]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71~73页,中华书局1926年版。
[4] 胡云翼:《词人辛弃疾》,《晨报副刊》1925年8月24日。
[5]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47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6] 胡云翼:《词学ABC》第44~45页,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
[7] 胡云翼:《宋词选》卷首第1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5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9]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28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10]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12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11] 刘尧民:《词与音乐》第2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
[12]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3] 谢桃坊:《词为艳科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14]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29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15]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66~67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16] 胡云翼:《词学ABC》第4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
[17]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59~60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18] 胡云翼:《宋词研究》第62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本。
[19] 谢桃坊:《宋词流派及风格问题商兑》,《词学辨》第49~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