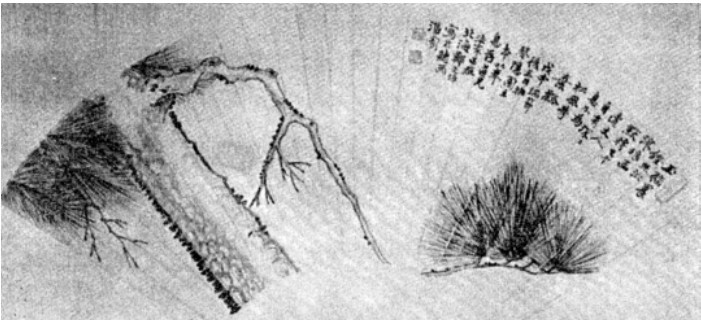-
1.1引论
-
1.2第一章 词学的创始
-
1.2.1第一节 唐代新体音乐文学——曲子词及最早的词学文献
-
1.2.2第二节 宋人词体观念形成的文化条件
-
1.2.3第三节 宋人词体起源说
-
1.2.4第四节 宋人的词话
-
1.2.5第五节 李清照的词 “别是一家”说
-
1.2.6第六节 王灼的词学思想
-
1.2.7第七节 朱敦儒试拟的词韵
-
1.3第二章 词学的建立
-
1.3.1第一节 宋元之际词体的衰微与词的理论总结
-
1.3.2第二节 沈义父论词的创作
-
1.3.3第三节 张炎的词学理论
-
1.3.4第四节 陆辅之论词的创作
-
1.4第三章 词学的中衰
-
1.4.1第一节 明人的词体观念与词体的继续衰微
-
1.4.2第二节 明代的词话与词籍的整理
-
1.4.3第三节 杨慎的词学
-
1.4.4第四节 张綖的 《诗余图谱》与词的婉约、豪放之分
-
1.4.5第五节 顾从敬关于词调分类
-
1.4.6第六节 沈际飞与词的评点
-
1.4.7第七节 沈谦的 《词韵略》
-
1.5第四章 词学的复兴
-
1.5.1第一节 清代词学复兴的文化背景
-
1.5.2第二节 词学资料的编辑
-
1.5.3第三节 刘体仁、王士祯和邹祇谟的词话
-
1.5.4第四节 金人瑞、先著与许昂霄的词评
-
1.5.5第五节 朱彝尊与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
-
1.5.6第六节 万树与词体格律的总结
-
1.5.7第七节 凌廷堪的燕乐研究
-
1.5.8第八节 戈载与词韵的总结
-
1.6第五章 词学的极盛
-
1.6.1第一节 近代词学与中国近代学术思潮
-
1.6.2第二节 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
-
1.6.3第三节 周济与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
-
1.6.4第四节 谢元淮关于词乐的探寻
-
1.6.5第五节 刘熙载的词品说
-
1.6.6第六节 谭献与冯煦的词评
-
1.6.7第七节 陈廷焯的沉郁说
-
1.6.8第八节 郑文焯的词学研究
-
1.6.9第九节 朱祖谋校辑词籍的成就
-
1.6.10第十节 况周颐论词的创作
-
1.6.11第十一节 王国维建立词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及其意义
-
1.6.12第十二节 梁启超与近代词学研究的进展
-
1.7第六章 现代的词学研究
-
1.7.1第一节 中国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以来的词学研究概况
-
1.7.2第二节 胡适与新文学建设时代的词学研究
-
1.7.3第三节 胡云翼对现代词学理论的贡献
-
1.7.4第四节 龙榆生的词学成就
-
1.7.5第五节 夏承焘的词学成就
-
1.7.6第六节 唐圭璋的词学成就
-
1.8余论 新时期词学研究述评
-
1.9附录 词学研究著作索引(1978~2000)
-
1.10后记
1
中国词学史 (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