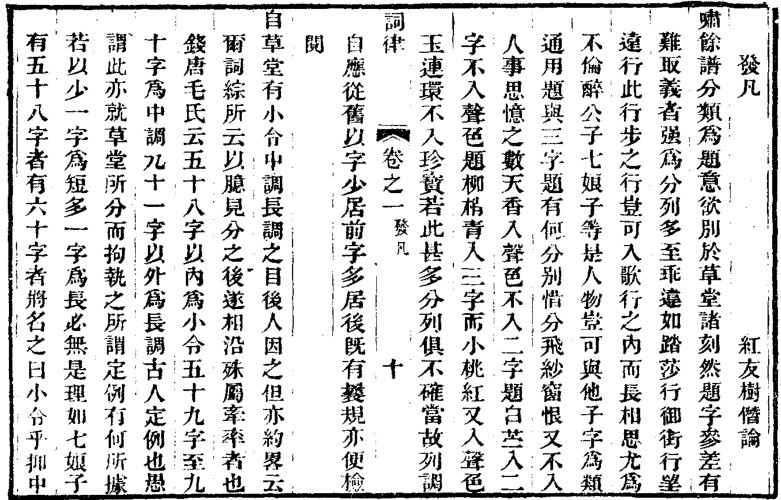第六节 万树与词体格律的总结
康熙二十六年 (1687)《词律》刊行,这是词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了自明代以来,词学家们研究词体格律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是词体脱离音乐以来,人们关于词体格律认识的总结。在 《词律》之后,出现了王奕清等的 《词谱》、郭巩的《诗余谱纂》、许宝善的 《自怡轩词谱》、舒梦兰的 《白香词谱》、叶申薌的 《天籁轩词谱》、谢元淮的 《碎金词谱》,以及现代学者编的种种词谱,但均未超过万树的 《词律》所达到的学术水平。词体格律的总结,对清词的创作实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助于词学复兴。
万树,字花农,一字红友,号山翁。江苏宜兴人。其主要生活时期在康熙朝。吴兴祚为两广总督时,万树以监生入其幕而以才称。所作曲二十余种,今可考者有杂剧八种:《珊瑚珠《舞霓裳》《藐姑仙》《青钱赚》《焚书闹》《骂东风》《三茅庵》《玉山宴》;传奇八种:《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锦尘帆》《十串珠》《万金瓮》《金神凤》《资齐鉴》。所制杂剧或传奇脱稿,吴兴祚即令家伶排演。此外还著有 《堆絮园集》和《香胆词》。万树对词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康熙七年 (1668)在京都时,他便将初步意见与著名词人陈维崧讨论过,得到支持。后于康熙十六年 (1677)开始撰著,又十年方成书于岭南。由于图书条件的限制,万树仅据 《花间集》 《草堂诗余》《尊前集》《花庵词选》《宋六十名家词》《啸余谱》《词统》《词汇》《词综》等词籍,汇列词调,考订字句,辨别平仄。这必然存在某些讹错与疏漏之处,但如近世词学家陈锐所说:“征以久佚复出之各词集,万说十九有验。”他又说:
万氏之书,虽不能谓绝无疏舛,然据所见之宋元以前词,参互考订,且未见 《乐府指迷》,而辨别四声,暗合沈义父之说。凡所不认为必不如是,或必如何始合者,不独较其他词谱为详,且多确不可易之论,莫敢訾以专辄。识见之卓,无与伦比。后人不得不奉为圭臬矣。
—— 《声执》卷上
清咸丰间,杜文澜对 《词律》详加考订,著有 《词律校勘记》二册。同治间徐本立撰成 《词律拾遗》八卷。光绪初年,恩锡久与杜文澜重校增补 《词律》,将 《词律校勘记》分散于各调之后,附 《词律拾遗》,又附杜氏 《词律补遗》一卷,合刊以行。[1]这样终使万树的词体格律的总结趋于完善了。
《词律》共收词调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体。以调字数由少到多为序排列,每调内之各体也依字数为序排列。每调下注明调之异名和字数;若有数体者,每体下亦注明字数。每调与每体均选一典范之作为例,旁注韵、句、豆,于词字可平可仄者旁注明,未注明者则依原词字之平仄。每调或每体后间有详尽的说明与考校。万树避免了图谱方式的先图后词不相连接的缺陷,也避免了圈法易于讹误的通病。这样,填词者便可根据某调格律进行创作了。作词者若按词律规定的句式、韵数、分片、词字平仄试填,这可以认为是填词的宽式;若进一步参考调后的说明,分辨四声,严别上去,注意拗句,这可以认为是填词的严式。后来的 《词谱》虽然有其平仄明显、体调完备的许多优点,但仅属宽式,因而不能取代 《词律》,也未达到 《词律》的学术高度。所以万树之著一直为词学界所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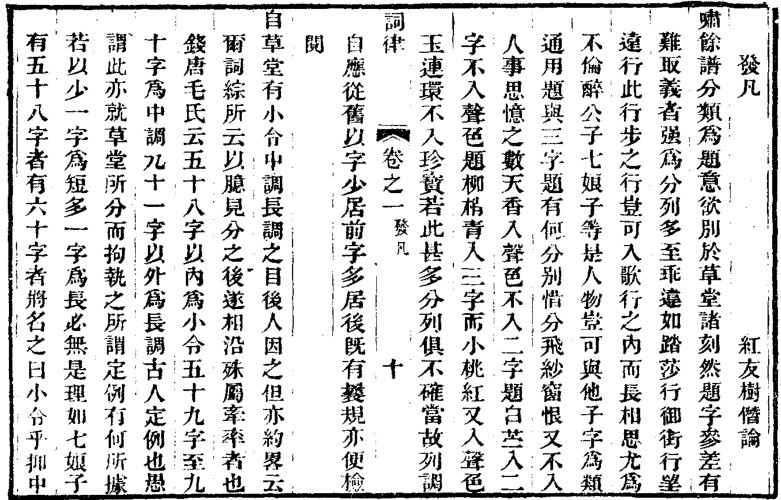
清刊本 《词律》书影
万树在 《词律发凡》和许多词调后的考证里,深入地探讨了词体的声律问题,有非常精辟而独创的见解。兹试评述如下:
(一)词的四声体。宋代周邦彦的词是很讲究格律的。南宋时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都曾遍和周词,依其词字四声,不敢逾越。据近世词学家杨易霖 《周词订律》的分析,三家和清真词之作,全首词之四声仅数字不合者共十余首;方千里和《瑞龙吟》于四声无一字不合。[2]这种少数格律极严的词调被称为四声体,但是宋人并未总结出四声体的格律。万树发现:
美成造腔,其拗处乃其顺处,所用平仄岂慢然为之耶?倘是慢然为之者,何其第二首亦复如前,岂亦皆慢然为之至再、至三耶?方千里系美成同时,所和四声,无一字异者,岂方亦慢然为之耶?后复有吴梦窗所作,亦无一字异者,岂吴亦慢然为之耶?更历观诸名家,莫不绳尺森然者。
—— 《词律发凡》
他通过对一些词调的考证,确认宋词中存在四声体,如说:“词至千里而绳尺森然,纤毫无假借矣。四声确定,欲旁注而不可得矣……千里之和清真,无一字声韵不合。”(《侧犯》方千里词后注,《词律》卷一一)他又说:“余每赞叹方氏和清真一帙,为千古词音证据,观其字字摹合,如此不惟调字句考,且足见古人细心处,不惟有功于周氏,而凡词皆可以此理推之,岂非词家所当蒸尝者耶?故字旁不敢复注平仄。”(《四园竹》周邦彦词后注,《词律》卷一一)据此,万树批评旧谱只分平仄,于仄声不辨上、去、入的现象。他说: “若照 (旧)谱注,则词调千余,不管何体,遇五字七字则照诗句,遇四字非平平仄仄,即仄仄平平,遇六字非平平仄仄平平,即仄仄平平仄仄,一概施行,于仄字又不辨上去入而乱填之,则作词有何难事,而古人制腔俱可不必缕肝刿肺,亦为太愚,所称高手名篇,亦不足贵矣。”(《绛都春》吴文英词后注,《词律》卷一六)方千里等人和清真词的例子,从文学创作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失败的,不足为法。所以万树之论遭到不少词学家的指摘,如潘飞声说:“万红友苦心孤诣,撰为 《词律》,自诩严定字句之功臣,却于古人名曰一调与字句不同者,判之为又一体,盖已附会牵强,依谱填之,几无一自然之句矣。近复有人变本加厉,谓必须吻合四声,始称能事。不知古人必无自制一词,而令人复依其四声者。”[3]如果我们将四声体仅限于极少孤僻的词调,则它确是存在的。王琴希认为:“四声体为少数词调之特别体,非不可不依者……至孤僻调则平仄无法考校,不可不悉依原平仄……宋人作僻调时,平仄相差多甚少,自难任意更动。”[4]虽然如此,但后世作词者实无必要如方千里等人和清真词四声一字不易,而对某些声律较严的僻调应当谨严对待而已,或者选用其他常用词调。
(二)词中的拗句。词的声律是在近体诗基础上形成的,但却已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词中拗句即是词体与近体诗在声律方面的重要区别之一。许多词调在起句、过变、结句或某最美听之处,其声律都很特别,不再按平仄对称协调的规律,而是以不协调的拗句方式出现。万树的这一发现是认识到了词体声律的特殊性。如果说四声体在创作实践中不甚适用,而拗句则如元曲中的务头一样是词家所必须遵从的。万树说:
读词非仅采其菁华,须观其格律之严整和协处。人见其严整,便以为拗句,不知其拗句,正其和协处。但多吟咏数遍,自觉其妙,而不见其拗矣。字之平仄,人知辨之,不知仄处上去入,亦须严订。如千里之和清真,平上去入无一字相异者,此其所以为佳,所以为难。
—— 《词律》卷一九:《丹凤吟》
万树又说:“词中此等拗句,及故为抑扬之声,入于歌喉,自合音律。由今读之,似为拗而实不拗也;若改之作顺,而实拗矣。”(《蕃女怨》温庭筠词后注,《词律》卷二)这类拗句,万树在 《词律》中多有考订,非常确切地把握了词调声律的特点。
(三)词中的上去声字。与四声体和拗句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是词中的上去声字。宋末沈义父在 《乐府指迷》里已注意到去声字在词调声律中的特殊作用。他说:“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两三支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万树著《词律》时未见到 《乐府指迷》,而关于去声字作用的论述却与沈氏的见解相合。由此可见,词调的字声运用确是存在某种规律的。万树以周邦彦 《夜游宫》为例云:“‘照’字、‘射’字、‘再’字,俱用去声,妙甚。如千里、放翁、东堂、梦窗、芦川,皆词家矩矱,于此数字,莫不用去声。可见读词与填词,须要熟玩深味,方得其肯綮,不可谓遇仄填仄,便以为无憾也。”(《词律》卷八)他又以周邦彦 《一寸金》为例云:“自首至尾”,所用 ‘下’、‘是’、‘望’、‘面’、‘退’、‘夜’、‘正’、‘外’、‘渡’、‘正’、‘事’、‘信’、‘念’、‘梦’、‘处’、‘利’、‘易’、‘谢’、‘便’、‘钓’等去声字,妙绝。此皆跌宕处,要紧,必如此,然后起调。周郎之树帜词坛,有以哉!梦窗之心,如镂尘剔发者,故亦用 ‘看’、‘瘦’、‘正’、‘地’、‘透’、‘尚’、‘暗’、‘记’、‘绣’、‘挂’、‘事’、‘爱’、‘叹’、‘思’、‘重’、‘袖’、‘下’、‘醉’、‘露’等字,又一首亦同。”(《词律》卷一九)万树解释说:“夫词曲中四声,以一平对上去入之三仄固已,然三仄可通用,亦有不可通用之处。盖四声之中,独去声为另一种沈著远重之音,所以入声可以代平,次则上声亦有可代,而去声则万万不可。人但于口中调之,其理自明。南北曲之肯綮全在此处。人或谓今日之曲付于歌喉,尚且不必拘泥,词又不入歌,何妨混填。此大谬之说。何也,词即曲之先声,当时本以按拍,岂可以謷牙捩嗓者号为乐府乎!”(《宴清都》词后注,《词律》卷一七)词中关于去声运用的规定,可以理解为某些四声体或某些词调的独特要求,一般词调是不可能严守的。
(四)词的入派三声。我国的音韵在元代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主要是原来的入声消失了,分别转为平、上、去三类声调之中,这即是 “入派三声”。周德清在 《中原音韵》的韵目中 “以入声配隶三声”,标志了我国近代音系的形成。万树对戏曲的声韵格律很熟悉,创作了二十余种杂剧与传奇,因而探讨词律时,借用了元曲 “入派三声”说。他认为:“入之入派三声,为曲言之也,然词曲一理。今词中之作平者比比而是,比上作平者更多,难以条举。”(《词律发凡》)他又说:“盖入声作平,北音皆然,故予谓不通于曲理,不可言词也。至于入既作平,亦仍可作仄,但于口中调之,其音自见,其理自明。”(《江城子》黄庭坚词后注,《词律》卷二)万树在 《南歌子》石孝友词后,对这个问题作了较详的阐述:
愚谓入声可作平,人多不信曰:入声入派三声,始于元人论曲,君何乃移其说于词?余曰:声音之道,古今递传,诗变词,词变曲,同是一理。自曲兴盛,故词不入歌,然北曲 《忆王孙》《青杏儿》等,即与词同。南曲之引子与词同者将六十调,是词曲同源也。况词之变曲,正宋元相连接处,岂曲入歌当以入派三声,而词则不然乎?故知入之作平,当先词而后曲矣。盖当时周、柳公制调,皆用中州正韵。今观词中,如 “不”音 “逋”, “一”音“伊”之类多至万千,正与北曲同,而又何疑于入作平之说耶?且用韵句亦可以入为叶,如惜香 《醉蓬莱》以“吉”字叶 “髻”、“戏”,坦庵以 “极”字叶 “气”、“瑞”等甚多。若云入不可叶,则此等词落一韵矣。至通篇入叶之调,有可兼用上、去,如 《贺新郎》 《念奴娇》之类,有本是本韵而以入代叶者,如金谷此篇之类。虽全用入声,而实以入作平,必不可谓是仄声,而用上去为韵脚也。
—— 《词律》卷一
万树的词 “入派三声”说之要点可概括为:词曲一理,入派三声先词而后曲;词中入声字与阴声字相押;词调有以入代平;句中字亦有以入代平。第一点是万氏立论的基础,其余三点都是宋词中的个别现象。由于万树对汉语音韵学史上的入声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他为某些现象迷惑而陷于错误。
关于入派三声先词后曲,稍后 《词谱》的编者即指出这是万氏的谬误。如 《词谱》卷一七 《千年调》辛弃疾词后注云:“《词律》……至论 ‘合’字平声。按 《中原雅音》合音呵,《中原音韵》歌戈部入声作平声有 ‘合’字。此亦金元曲谱所用。北方之音,不可以律宋词。”又 《词谱》卷二四 《黄莺儿》晁补之词后注云: “不知中州韵始自元时,全为作北曲而发。若填词自依古韵,岂有宋词在前,反遵后世曲韵之理。此论(万氏之说)纰缪不可从。”但是也有现代语言学家和词学家以万氏之说加以补充,认为入声的特点是收声不能延长,而歌唱时字音要延长才可以叶乐;这样,入声在词中就不能保存它原有的性质,而作为韵脚的入声,唱时延长尤其厉害,因此,入派三声起源于词。[5]这涉及音韵学理论和宋词歌唱的实际问题。“入派三声”是中古汉语语音变化的结果。决定和推动这个变化的原因,只能从汉语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中去寻找。词或曲只能看作入声变化的外部条件之一,而不是主要原因。宋人沈义父曾说平声 “得用入声字替” (《乐府指迷》);张炎曾说“平声字可为上、入声”(《词源》卷下)。这是宋末元初词的歌唱时,歌者为叶律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如果说词的歌唱时入声必得延长而丧失其收声,这仅是一种猜测而已。入声在宋词之中之所以被视为独立的一类,因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与音律的巧妙配合能起到特殊的表情作用。我们从柳永、周邦彦、姜夔、张炎四家词中入声韵的严格分部,即可说明词的歌唱并不会改变入声的性质。它用于某些词中可以表达激越峭拔的情感,有自己的特色。关于入声字与阴声字相押,万树举了赵长卿以 “吉”叶 “髻”、 “戏”,赵师侠以 “极”叶 “气”、“瑞”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并非 “甚多”,与整个入声韵的使用比较起来便微不足道了。如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的 “近一千六百次的用韵中,可以肯定是入声字与阴声字相押的有六例”[6],仅占千分之四。其余对宋人入声韵使用情况所作的统计,入声字与阴声字相押的比例也都是千分之几。这都证明少数的例子尚未构成一种普遍的规律。关于词调的以入代平,因各词调用韵有自己的规定,绝不能因某词调要求押平声韵或入声韵便以为此调平、入不辨,也绝不能因某词调要求用仄韵便以为上、去、入无别。宋词中入声韵非常严格,不与其他三声混用。若以某调可押平声又可押入声就叫 “以入作平”,这只是一种误解,因为它们并未相混。关于句中字的入作平,万树在 《三台》《女冠子》《阮郎归》等调后列举了不少例子,如果我们细加订正,便可发现:这些以入作平之处,原是可平可仄的。宋人作词,关于词字的平仄,并非如万树所想象的那样严格。
入声的有无,这是汉语中古音与近代音相区别的标志。词的入声既非 《广韵》系统的三十四部那样严,也非如 《中原音韵》系统的 “入派三声”那样消失了;而是处于一个由中古音向近代音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仍属中古音的范围,还存在着入声,但韵部已有所合并,个别入声字在运用中已有所变化了。尽管如此,入声在宋词里仍是独立的一类,“词韵于入声更严”的说法是较为真实的。
万树对词体声律的探讨,除关于词 “入派三声”之说而外,其余的发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认识词体格律的特点。清代词学家吴衡照说:
万红友当轇輵榛楛之时,为词宗护法,可谓功臣。旧谱编类排体,以及调同名异、调异名同,乖舛蒙混,无庸论矣。其于段落、句读、韵脚平仄间,尤多模糊。红友《词律》一一订正,辩驳极当。所论上、去、入声,上、入可替平;去则独异,而其声激厉劲远,名家转折跌荡,全在乎此,本之伯时 (沈义父)。煞尾字必用何音方为入格,本之挺斋 (周德清)。均造微之论。
—— 《莲子居词话》卷一
这段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词律》应是清初词学复兴的重要成果之一。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出版的 《词律》即是据杜氏光绪二年之合刊本。
[2] 参见夏承焘:《唐宋词论丛》第7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3] 潘飞声:《刘廉生词集序》,《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33年8月。
[4] 王琴希:《宋词上去声字与剧曲关系及四声体考证》, 《文史》第2辑, 1963年4月。
[5] 参见唐钺:《入声演化和词曲发达的关系》,《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26年1月;夏承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之说》,《唐宋词论丛》第8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6] 参见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