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央是谁?美人梅奇河又是哪里?这个人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坐着一辆颠簸的小马车打猎归来,被云翳的夏日的闷热所困绕(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日子,有时往往比晴朗的日子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没有风的时候),打着瞌睡,摇晃着身子,闷闷不乐地忍耐着,任凭燥裂而震响的轮子底下辗坏道路上不断扬起来的细白灰尘侵袭我的全身,忽然,我的马车夫异常不安的情绪和惊慌的动作唤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这刹那以前是比我更沉酣地打着瞌睡的。他连扯了几次缰绳,在驾车台上手忙脚乱起来,又开始不住地喊马,时时向一旁眺望。我向周围一看,我们的马车正走在一片宽广的、耕种过的平原上。有些不是很高的、耕种过的小丘,形成非常缓和的斜坡,一起一伏地奔向这平原。一望可以看到大约五俄里的荒凉的旷野。在远处,只有小小的白桦林的圆锯齿状的树梢,打破了差不多成直线的地平线。狭窄的小路蜿蜒在原野上,隐没在洼地里,环绕着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们的大路相交叉,我看见这条小路上有一队行列。我的马车夫所眺望的就是这个。
名师指导
写出了马车夫的惫懒。
名师指导
遇到出殡的队伍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是出殡。在前面,一个教士坐在一辆套着一匹马的马车里,慢慢地前进。一个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驾马,马车后面有四个农人,不戴帽子,扛着盖白布的棺材,两个女人走在棺材后面。其中一人的尖细而悲戚的声音突然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倾听一下,她正在数一数二地号哭着。这抑扬的、单调的、悲哀绝望的音调,凄凉地散布在空旷的原野中。马车夫催促着马,他想超过这行列。在路上碰见死人,是不祥之兆。他果然在死人还没有走上大路之前超过了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一百步,忽然我们的马车剧烈地震动一下,倾侧了,几乎翻倒。马车夫勒住了正在快跑的马,挥一挥手,啐了一口。
“怎么了?”我问。
我的马车夫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爬下车去。
“到底怎么了?”
“车轴断了……磨坏了,”他阴郁地回答,突然愤怒地整理一下副马的皮马套,使得那匹马完全偏斜到一旁,然而它站稳了,打了一个响鼻,抖擞一下,泰然地用牙齿搔起它的前足的小腿来。
我走下车来,在路上站了一会儿,茫然地陷入了不快的困惑状态中。右面的轮子差不多完全压倒在车子底下了,仿佛带着沉默的绝望把自己的毂伸向上面。
“现在怎么办呢?”最后我问。
“就是那个不好!”我的马车夫说着,用鞭子指着已经转人大路而正在向我们走近来的行列,“我以前一直留心着这个,”他继续说,“这预兆真灵,碰到死人……真是。”
他又去打扰那匹副马。这副马看出他心绪不佳,态度严厉,决心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偶尔谦逊地摇摇尾巴。我向前后徘徊一下,又站定在轮子前面了。
这时候死人已经赶上我们。路被我们阻塞了,这悲哀的行列就慢慢地从大路上转人草地里,经过我们的马车旁边。我和马车夫脱下帽子,向教士点头行礼,和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下。他们费力地跨着步子,他们的宽阔的胸脯高高地起伏着。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年纪很老,面色苍白,她那呆滞的、 由于悲哀而剧烈地变了相的颜貌,保持着严肃而庄重的表情。她默默地走路,有时举起一只瘦削的手来按住薄薄的凹进的嘴唇。另一个女人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少妇,眼睛润湿而发红,整个面孔哭得发肿了。她经过我们旁边的时候,停止了号哭,用衣袖遮住了脸……但是当死人绕过我们的旁边,再走上大路的时候,她的悲戚的、动人心弦的曲调又响起来了。我的马车夫默默地目送那规则地摇摆着的棺材过去了,向我转过头来。
“这是木匠马尔登出丧,”他说,“就是略波伏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那两个女人才知道的。年纪老的一个是他的母亲,年纪轻的一个是他的老婆。”
“他是生病死的吗?”
名师指导
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女人的眼泪之多,与上文说女人的眼泪不值钱相呼应。
“是的……生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医生,可是医生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稍微喝点酒,但却是一个好木匠。你瞧他的女人多么悲伤……不过,当然喽,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像水一样……真是。”
他弯下身子去,爬过副马的缰绳底下,双手握住了马轭。
“可是,”我说,“我们怎么办呢?”
我的马车夫先把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把轭摇了两下,整理好了辕鞍,然后又从副马的缰绳底下爬出来,顺手把马的脸推一把,走到了车轮旁边。他到了那里,一面注视着车轮,一面慢吞吞地从上衣的衣裾底下拿出一只扁扁的桦树皮鼻烟匣来,慢吞吞地拉住皮带,揭开盖子,慢吞吞地把他的两根肥胖的手指伸进匣子里去(两根手指也还是勉强塞进去的),揉一揉鼻烟,先把鼻子歪向一边,便从容不迫地嗅起鼻烟来,每嗅一次,总发出一阵拖长的呼哧呼哧声,然后痛苦地把充满泪水的眼睛眯起来或者眨动着,深深地陷入沉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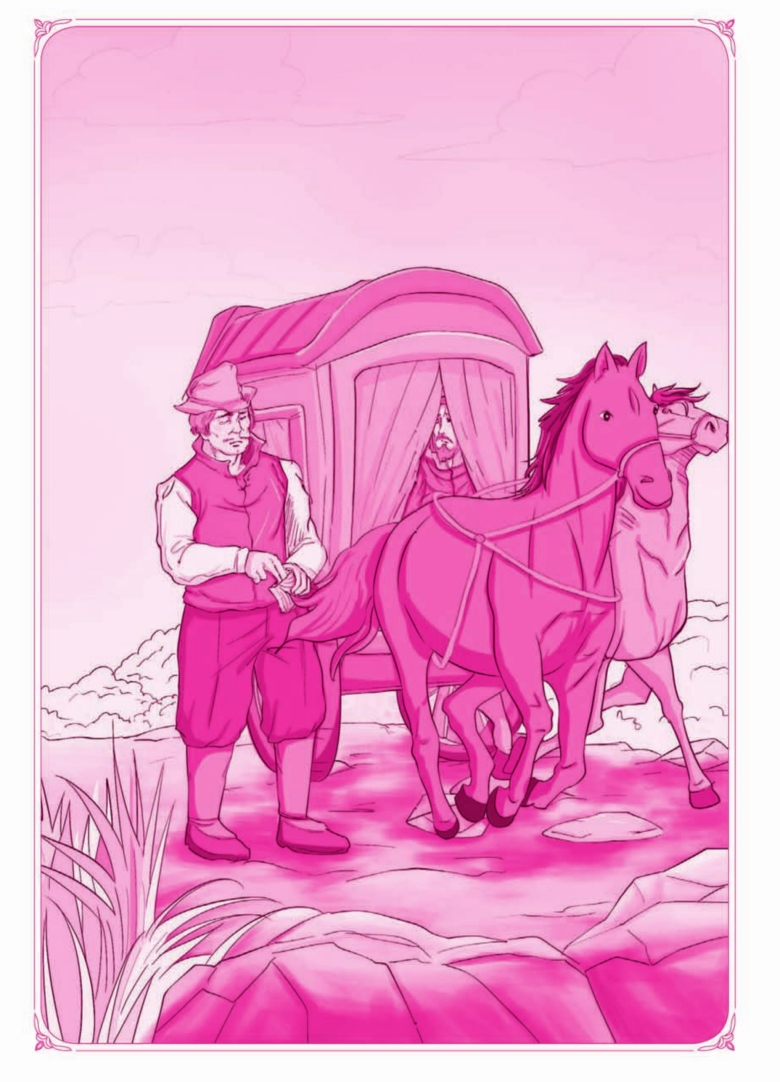
名师指导
写出了马车夫检查车子想办法的神态。
“喂,怎么样?”最后我问。
我的马车夫把鼻烟匣子小心地藏进衣袋里,不用手的帮助而只用头的动作来把帽子抖落在眉毛上了,然后一股心思地爬上驾车台去。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我不免惊奇地问他。
“您请坐吧。”他坦然地回答,拿起了缰绳。
“可是我们怎么能走呢?”
“能走的。”
“可是车轴……”
“您请坐吧。”
“可是车轴断了……”
“断是断了,可是我们可以勉强走到移民村……当然慢慢地开。在那儿,树林后面,右边有一个移民村,叫作尤季内。”
“你认为我们到得了吗?”
我的马车夫并没有赏赐我一个答复。
“我还是步行的好。”我说。
“随您的便吧……”
于是他挥一下鞭子。马出动了。
我们果然到了移民村,虽然右边前面的轮子勉强支撑而且转动得特别奇怪。在一个小丘上,这轮子几乎脱落,但是我的马车夫用愤怒的声音吼叫一声,我们才平安地走下了小丘。
名师指导
一片穷苦荒凉的景象。
尤季内移民村由六所低矮的农舍组成,这些农舍已经歪斜了,虽然建造的时间大概并不长久,农舍的院子还没有全部围好篱笆。我们的车子开进这移民村里,没有遇见一个人。路上鸡都不见一只,只有一只黑色的短尾狗在我们面前匆忙地从一个完全干了的洗衣槽里跳出来(它大概是被口渴所驱使而走进这槽里去的),一声也不叫,慌慌张张地从大门底下奔进去。我走进第一所农舍里,开了前室的门,叫唤主人,没有人回答我。我又叫唤一次,一只猫的饥饿的叫声从另一扇门里传出来。我用脚把门踢开,一只很瘦的猫在黑暗中闪耀了一下碧绿的眼睛,从我身旁溜过。我把头伸进房间里去一看,黑洞洞的,烟气弥漫,空无一人。我走到院子里去,那里也没有一个人……栅栏里有一头小牛在那里哞哞地叫,一只跛脚的灰色鹅一瘸一瘸地略微拐向旁边。我又走进第二所农舍里,第二所农舍里也没有人。我就走到院子里……
在阳光普照的院子的正中央,在所谓最向阳的地方,有一个人脸向着地,用上衣盖着头,躺在那里。据我看来,这像是一个男孩子。离开他若干步地方的草檐下,一辆蹩脚的小马车旁边,站着一匹套着破烂的马具的瘦小的马。太阳光穿过了破旧的屋檐上的狭小的洞眼流注下来,在它的蓬松的、枣红色的毛上映出一小块一小块明亮的斑点。在近旁的一只高高的椋鸟笼里,椋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从它们的高空住宅里带着安闲的好奇心向下面眺望。我走到睡着的人旁边,开始唤他醒来……
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立刻跳将起来……“嗯?你要干什么?有什么事?”他半睡不醒地嘟哝起来。
名师指导
这是一个侏儒,而且看起来并不可亲。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他的外貌把我吓坏了。请想象一个年约五十岁的矮人,瘦小而黝黑的脸上全是皱纹,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不大看得出,鬈曲而浓密的黑发像香菌的伞帽一般铺展在他的小头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而瘦削,他的目光的特殊和怪异,无论如何不可能用言语描写出来。
“你有什么事?”他又问我。
我就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他听我讲,一双眼睛慢慢地眨着,一直盯着我看。
“你能不能替我们买到一个新的车轴?”最后我说,“我愿意付钱。”
“可是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猎人?”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这样问。
“是猎人。”
名师指导
写出了卡西央不赞成杀生。
“你们一定是打天上的鸟?……树林里的野兽?……你们杀上帝的鸟,流无辜的血,不是罪过吗?”
这奇怪的小老头说起话来语调拖长。他的声音也使我吃惊。在这声音里不但听不出一点衰老,而且有可惊的甘美、青春和差不多女性一样的柔和。
“我没有车轴,”他略微静默一下之后又说,“这是不合用的(他指着他那辆小马车),你们的马车大概是大的吧?”
“那么在村子里可以找到吗?”
“这里怎么算得上村子!这里没有一个人有车轴……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家,都干活去了,走开吧。”他忽然这样说,又躺在地上了。
这样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喂,老人家,”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劳驾,帮个忙。”
“快走开吧!我累了,到城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说,就把上衣拉到头上。
“劳驾啦,”我继续说,“我……我会付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
“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爬起来,盘起他的两条瘦腿坐着。
“或许我可以领你到开垦地[15]去。那阵儿有商人买了一片树林,——真作孽,砍掉了树林,盖了一个事务所,真作孽。你可以在那儿叫他们定做一个车轴,或者买一个现成的。”
“那好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好极了!……我们去吧。”
“橡树木的车轴,很好的。”他继续说,并不站起身来。
“到那开垦地远不远?”
“三俄里。”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坐你的小马车去。”
“不行啊……”
“走吧,老人家!马车夫在街上等我们呢。”
老头儿不乐意地站起来,跟我走到了街上。我的马车夫正在怒气冲冲,因为他想给马喝水,但是井里水少得很,味道又不好,而照马车夫们说来,这是第一件要事……然而他一看见那老头儿,就露出牙齿来一笑,点点头,喊道:
“啊,卡西央!你好!”
“你好,叶罗菲,你这正直的人!”卡西央用消沉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把他的提议告诉了马车夫,叶罗菲表示赞同,就把马车开进院子去。当他用熟练的手法忙着拆除马具的时候,那老头儿靠着大门站着,一副不太高兴的模样,有时向他望望,有时向我望望。他仿佛在那里惶惑不安。据我所能看到的,他不太喜欢我们这种不速之客。
“你也给迁移过来了吗?”叶罗菲在卸去马轭的时候突然问他。
“我也给迁移过来了。”
名师指导
马车夫明显为人不怎么样,冷嘲热讽地对待卡西央。
“咳!”我的马车夫从牙缝中含糊地说,“你知道吗,木匠马尔登……你不是认识略波伏的马尔登的吗?”
“认识的。”
“嘿,他死啦。我们刚才碰见他的棺材。”
卡西央哆嗦了一下。
“死了?”他说着,低下了头。
“可不是死了。你为什么不医好他呢,暖?人家都说你会治病的,你是医生。”
我的马车夫显然是在拿这老头儿来开玩笑,在挖苦他。
“怎么,这是你的马车吗?”他又接着说,用肩膀来指着它。
“是我的。”
“唉,马车……马车!”他反复说着,拿起它的车杆,几乎把它翻了个身……“马车!用什么载您到开垦地去呢?……在这车杆上我们的马是套不上的:我们的马都很大,可是这算是什么呀?”
“我可不知道,”卡西央回答,“该用什么载你们去,要么就用这个牲口吧。”他叹一口气,这样补充道。
“用这个牲口?”叶罗菲接着说,就走近卡西央那匹弩马,轻蔑地用右手的中指戳戳它的颈子。“瞧,”他带着责备的态度说,“睡着了,这笨家伙!”
我要求叶罗菲赶快把它装备好。我想自己跟卡西央到开垦地去,因为那里常有松鸡。后来那辆小马车完全装备好了,我就带了我的狗,胡乱地坐在那树皮做成的凹凸不平的车身里,卡西央缩成一团,脸上带着那副忧郁的表情,也坐在前面的车栏上了,——这时候叶罗菲走到我跟前来,带着神秘的样子轻声地说:
“老爷,您跟他一同去,那很好。您可知道他这人很怪,他是个疯子呀,他的绰号叫作跳蚤。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了解他的……”
我想告诉叶罗菲,卡西央直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明白道理的人,但是我的马车夫立刻用同样的声音继续说:
“您只要留神,看他是不是带您到那地方去。车轴请您自己选,要一根结实些的车轴……喂,跳蚤,”他高声地接着说,“你们这里可以弄点儿面包吃吗?”
“你去找吧,也许会找到的。”卡西央回答,扯一扯缰绳,我们就出发了。
名师指导
比喻句,形象地写出了两个青年牙齿洁白。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马跑得很快。一路上他都保持沉默,断断续续地、不情不愿地回答我的问话。我们不久就到达了开垦地,又在那里找到了事务所——一所高高的木屋子,孤零零地建立在用堤坝草草地拦住而变成了池塘的小溪谷上。我在这事务所里遇见两个青年伙计,他们的牙齿像雪一样洁白,眼睛甜蜜蜜的,说起话来机敏又伶俐,笑容调皮而又狡猾。我向他们买了一根车轴,就出发到开垦地去。我以为卡西央将留在马的地方等我,但是他突然走近我来。
“怎么,你去打鸟吗?”他说,“啊?”
“是的,如果找得到的话。”
“我跟你一块儿去……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们就去了。伐去树木的地方一共约有一俄里。老实说,我对卡西央看,比对我的狗看得更多。他真不愧绰号叫作跳蚤。他那乌黑的、毫无遮盖的小头(然而他的头发可以代替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忽隐忽现。他走起路来特别灵巧,仿佛一直是跳着走的,常常俯下身子去,摘些草,揣在怀里, 自言自语地嘟哝几句,又老是向我和我的狗注视, 目光里显出一种努力探求的异常神色。在低低的灌木丛中和开垦地上,常常有一些灰色的小鸟,这些小鸟不断地从这棵树换到那棵树,啾啾地叫着,忽高忽低地飞行。卡西央模仿着它们,同它们相呼应。一只小鹤鹑吱吱地叫着从他的脚边飞起,卡西央也跟着它吱吱地叫起来。云雀鼓着翅膀,响亮地歌唱着,从他上面飞下来——卡西央接上了它的歌。他和我一直不说话……
名师指导
卡西央不愿与人交流,却很喜欢和各种鸟呼应。

天气很好,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暑热仍未减退。在明澄的天空中,微微地飘浮着高高的稀疏的云朵,像春天的最后的雪那样发乳白色,像卸下的风帆那么扁平而细长。它们那像棉花一般蓬松而轻柔的花边,慢慢地,但又显著地在每一瞬间发生变化。这些云正在融化,它们没有落下阴影来。我和卡西央在开垦地上走了很久。还没有见过一俄尺[16]高的嫩枝,用它们的纤细而光滑的茎来围绕着黑簇簇的低矮的树桩,有灰色边缘的圆形的海绵状木瘤,就是那可以煮成火绒的木瘤,贴附在这些树桩上,草莓在这上面抽放出粉红色的卷须,蘑菇也在这里繁密地聚族而居。两只脚常常绊住那些饱受烈日的长长的草,树上到处有微微发红的嫩叶射出金属般的强烈的闪光,使人眼花缭乱,到处有一串串浅蓝色的野豌豆、金黄色花萼的毛茛、半紫半黄的蝴蝶花,斑斓悦目。在红色的小草带状地标示出车轮痕迹的荒径旁边,有几处地方矗立着由于风吹雨打而发黑了的,以一立方俄丈[17]为单位的许多木柴堆;从这些木柴堆上投下斜方形的淡淡的阴影来,此外没有一个地方有别的阴影。微风有时吹动了,有时又静息了。忽然一直扑上脸来,仿佛要剧烈起来了,——四周一切都愉快地呼啸、摇摆、动荡起来,羊齿植物的柔软的尖端袅娜地摇动,——你正想享受这风……但是它忽然又停息下来,一切又都静止了。只有蚱蜢齐声吱吱叫着,仿佛激怒了似的,——这种不停不息的、萎靡而干巴巴的叫声使人感到困疲。这叫声和正午的顽强的炎热很相配。它仿佛是这炎热所产生的,是这炎热从晒焦的大地里唤出来的。
我们一只鸟都没有碰到,最终来到了一处新的开垦地。在那里,新近砍倒的白杨树悲哀地横卧在地上,把青草和小灌木都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其中有几棵白杨树上的叶子还是绿色的,但是已经死了,憔悴地挂在一动不动的树枝上。别的白杨树上的叶子则都已经干枯而且卷曲了。新鲜的、淡金色的木片,堆积在润湿的树桩旁边,发出一种特殊的、非常好闻的苦味来。在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斧头钝重地响着,有的时候,一棵葱茏的树木好像鞠躬一般伸展着手臂,庄严地、徐徐地倒下来……
我一直没有找到任何野禽。最后,从一片广大的满生着苦艾的橡树丛中飞出一只秧鸡来。我打了一枪,它在空中翻了个身,便掉下来。卡西央听见枪声,连忙用手遮住眼睛,一动也不动,直到我装好枪、拾起秧鸡为止。我走开了之后,他走到被打死的鸟落下来的地方,俯身在洒着几滴血的草地上,摇摇头,恐怖地向我看一眼……后来我听见他轻声地说:“罪过!……唉,这真是罪过!”
名师指导
写出了“我”完全沉浸在对美丽景色的欣赏中,思绪飘远了。
炎热终于逼得我们走进树林里去。我投身在一丛高高的榛树下面,在这树丛上面,有一棵新生的、整齐的槭树翩翩然扩展着它的轻盈的树枝。卡西央在一棵砍倒的白桦树的粗的一端上坐了下来。我看着他。树叶在高处微微地摇晃,它们的淡绿色的阴影,在他那胡乱地用深色上衣包裹着的羸弱的身体上和他那瘦小的脸上徐徐地移来移去。他低头不语,我厌倦于他的沉默,便仰卧了,开始欣赏那些交互错综的树叶在明亮的高空中的和平的游戏。仰卧在树林里向上眺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上面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树上的叶子有时像绿宝石一般透彻。有时浓重起来,变成金黄色的墨绿。在某处很远很远的地方,细枝的末端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显现在一块透明的淡蓝色的天空上,它旁边另一片叶子在摇晃着,好像鱼潭里的鱼儿在跳动,这动作仿佛是自发的,不是由于风吹的。一团团的白云像被施了魔法的水底岛屿一般静静地飘浮过来,静静地推移过去。忽然这片海、这新鲜的空气、这些浴着日光的树枝和树叶,全部都动荡起来,闪光一般震撼起来,接着就发出一种清新而颤抖的簌簌声,好似那突然推过来的微波的无穷尽的细碎的潺湲声。你一动也不动,你眺望着,心中的欢喜、宁静和甘美,是言词所不能形容的。你眺望着,这深沉而纯洁的蔚蓝色天空在你的嘴唇上引起同它一样纯洁的微笑来,一连串幸福的回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像云在天空移行一样,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一样,你只觉得你的眼光愈去愈远,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安静的、光明的深渊中,而不可能脱离这高处、这深处……
“老爷,喂,老爷!”突然卡西央用他那嘹亮的声音说起话来。
我惊异地抬起身子,他在这以前不大肯回答我的问话,忽然自己说起话来了。
“什么事?”我问。
“喂,你为什么要打死这只鸟?”他直望着我的脸,开始说。
“什么为什么?……秧鸡——这是野味,可以吃的啊。”
“你不是为了这个打死它的,老爷,你才不会去吃它呢!你是为了取乐才打死它的。”
“你自己不是也吃鹅或者鸡之类的东西吗?”
“那些东西是上帝规定给人吃的,可是秧鸡是树林里的野鸟。不单是秧鸡,还有许多:所有树林里的生物、田野里和河里的生物、沼地里和草地上的、高处和低处的——杀它们都是罪过,应该让它们活在世界上直到它们寿终……人吃的东西另外有规定。人另外有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面包——上帝的惠赐——和天降下来的水,还有祖先传下来的家畜。”
我惊奇地望着卡西央。他的话流畅地迸出来,没有踌躇,说话时显出一种沉静的兴奋和温和的严肃,时而闭上眼睛。
“那么,照你看来杀鱼也是罪过吗?”我问。
“鱼的血是冷的,”他深信不疑地回答,“鱼是哑的生物。它没有恐怖,没有快乐。鱼是不会说话的生物。鱼没有感觉,它身体里的血也不是活的……血,”他略停一会儿,继续说,“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见太阳,血要躲避避光明……把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极大的罪恶,是极大的罪恶和恐怖……唉,真作孽!”
名师指导
写出了卡西央的话让我非常惊奇,这些话是那么不同寻常。
他叹一口气,低下了头。我向这奇怪的老头儿看看,觉得十分惊异。他的话不像是农人说的,普通人不会说这样的话,饶舌的人也不会说这样的话。这种语言是谨慎、庄重而奇特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
“卡西央,请告诉我,”我开始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微微发红的脸,“你是干什么行业的?”
他不立刻回答我的问话。他的眼光不安地转动了一会儿。
“我依照上帝的命令生活着,”最后他说,“至于行业——不,我不干什么行业。我这人很不懂事,从小就是这样。能干活的时候就干活,我干活干得很不好……我哪里行!我身体不好,一双手又很笨。在春天的时候,我捉夜莺。”
“捉夜莺?你不是说过,所有树林里和田野里和其他地方的生物都是碰不得的吗?”
“杀它们的确是不可以的,死是自然来到的。就拿木匠马尔登来说吧:木匠马尔登曾经活着,可是没有活得长久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在悲伤丈夫,又悲伤年纪很小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物能混得过死。死并不来缠住你,可是你也逃不掉它,但是帮助死是不应该的……我并不杀夜莺,决不!我捉它们来并不叫它们受苦,并不害它们的命,而是让人高兴高兴,得到慰藉和愉快。”
“你到库尔斯克(库尔斯克地方产一种莺,鸣声甚美,被视为珍品)去捉夜莺吗?”
“我到库尔斯克去,有时候也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沼地里和森林里过夜,独自在野外和荒僻的地方过夜,那里有鹬鸟啾啾地啼着,那里有兔子吱吱地叫着,那里有鸭子嘎嘎地叫着……我晚上留神看着,早上仔细听着,天亮了的时候就在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莺唱歌唱得那么可怜,却很美妙……”
“你拿它们来卖钱吗?”
“卖给心地善良的人。”
“你还做些什么事呢?”
“做些什么事?”
“你干什么活儿?”
老头儿静默了一下。
“我什么活儿也不干……我干活干得很不好。可是我会识字。”
“你识字的?”
“我会识字。上帝和心地善良的人帮助我。”
“你有家眷吗?”
“没有,没有家眷。”
“怎么呢?都死了,是吗?”
“不,是这样的,我的命运不好。这全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大家都在上帝的意旨下生活,可是做人必须正直——这才对啦!也就是说,要合上帝的心意。”
“你有亲戚吗?”
“有的……嗯……是的……”
老头儿讷讷地说不出口了。
“请告诉我,”我开始说,“我刚才听见我的马车夫问你为什么不医好马尔登,难道你会治病吗?”
“你的马车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卡西央沉思地回答我,“可也不是没有罪过。说我是医生……我怎么好算医生呢!谁能够治病呢?这是全靠上帝的。有些……草呀,花呀,的确有效验。就像鬼针草吧,是对人有益的草,车前草也是这样。说起这种草,也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都是圣洁的草——是上帝的草。别的草可就不同了,它们虽然也有效,却是罪恶的,说起它们也是罪恶的。除非做祈祷……唔,当然也有些咒语……可是必须相信的人才能得救。”他降低了声音,这样补说一句。
名师指导
卡西央的确是懂得治病的,但是他也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写出了他因为现实生活艰难转而在精神上求得寄托。
“你什么药也没有给马尔登吗?”我问。
“我知道得太迟了,”老头儿回答,“可是有什么关系呢!人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的。木匠马尔登是活不长的,他在世界上是活不长的,一定是这样。不,凡是在世界上活不长的人,太阳就不像对别人一样地给他温暖,吃了面包也没有用处,——仿佛在召他回去了……嗯,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吧!”
“你们移居到我们这边来已经很久了吗?”略微静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
卡西央颤抖了一下。
“不,不是很久,大概有四年。老主人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向住在原来的地方,可是现在监护人把我们移过来了。我们的老主人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脾气很好,祝他升人天堂!可是监护人呢,下的决策当然是正确的,看来总是非这样不可。”
“你们以前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美人梅奇河[18]的人。”
“那地方离这儿远吗?”
“大概二百俄里。”
“哦,那)儿比这儿好吗?”
“比这儿好……比这儿好。那儿是自由自在的地方,有河流,是我们的老家。可是这儿地方很窄,又少河水……在我们那儿,在美人梅奇河上,你爬上小山冈去,爬上去一看,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啊?嗳?又有河流,又有草地,又有树林。那边是一个礼拜堂,那边过去又是草地。可以望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得可真远……你望着,望着,啊呀,实在太好了!这里呢,土壤的确好些,是砂质黏土,庄稼汉都说是很好的砂质黏土。我的谷物到处都长得很好。”
“喂,老人家,你老实说,你大概想到故乡去一趟吧?”
“是的,想去看看。不过,到处都好。我是一个没有家眷的人,喜欢走动。实在嘛!坐在家里有什么好处呢?出门走走,走走,”他提高声音接着说,“精神的确爽快些。太阳照着你,上帝也更加清楚地看得见你,唱起歌来也和谐些。这时候,你看见长着一种草。你看清楚了,就采一些。这里还有水流着,譬如说泉水,是圣水。你看见了水,就喝个饱。天上的鸟儿歌唱着……库尔斯克的那边还有草原,出色的草原,叫人看了又惊奇,又欢喜,真是辽阔自在,真是上帝的惠赐!据人家说,这些草原一直通到暖海,那儿有一只声音很好听的鸟叫作‘格马云’ [19],树上的叶子无论冬天、秋天都不掉下来,银树枝上长着金苹果,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我就想到那边去……我走的地方实在不少了!我到过罗姆内,也到过美好的新比尔斯克城,也到过有金色教堂圆顶的莫斯科。我到过‘乳母奥卡河’,也到过‘鸽子茨那河’,也到过‘母亲伏尔加河’,我看见过许多人,许多善良的基督教徒,我游历过体面的城市……所以我真想到那边去……而且……真想……还不单是我这个有罪孽的人……别的许多教徒都穿了草鞋,一路乞讨着,去寻求真理……是啊!坐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啊?人间是没有正义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最后的几句话,卡西央说得很快,几乎听不出来。以后他又说了些话,我简直听不清楚,他脸上显出那么奇怪的表情,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疯子”这名称。后来他低下头,咳嗽一下,仿佛清醒过来了。
“多么好的太阳!”他轻声地说,“多么好的惠赐,上帝啊!树林里多么温暖!”
他耸一耸肩膀,沉默了一会儿,漫不经心地望望,低声地唱起歌来。我不能听出他那悠扬的歌曲的全部词句,我只听到下面两句:
我的名字叫作卡西央,
我的绰号叫作跳蚤……
“啊!”我想,“是他自己编的……”突然他哆嗦一下,停止了歌唱,眼睛凝视着树林深处,我回转头去,看见一个年约八岁的农家小姑娘,穿着一件蓝色的无袖长衣,头上包着一条格子纹头巾,太阳晒黑的、赤裸裸的手臂上挽着一只篮子。她大概没有料到会遇见我们,她正是“撞着”了我们,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青葱的榛树丛中阴暗的草地上了,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慌张地对我看。我才看清楚她,她立刻躲到树背后去了。
“安奴喜卡!安奴喜卡!到这儿来,别害怕。”老头儿亲切地叫唤。
“我怕。”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
“别怕,别怕,到我这儿来。”
安奴喜卡默默地离开了她的隐避所,悄悄地绕了一个圈子,她那双小小的脚踏在浓密的草地上不大有声音,——从靠近老头儿的丛林里走了出来。这并不是像我起初依照矮小身材而推测的八岁的小姑娘,却是已经十三四岁了。她身材瘦小,但是体态匀称,模样儿很伶俐,漂亮的小脸蛋酷似卡西央的脸,虽然卡西央不是一个美男子。同样尖削的颜貌,同样奇妙的目光,调皮而信任,沉思而锐敏,举止也相同……卡西央对她打量了一下,她站在他旁边了。
“怎么,你采蘑菇吗?”他问。
“是的,采蘑菇。”她羞怯地微笑着回答。
“采得多吗?”
“多的。”她很快地对他看一眼,又微笑一下。
“有白的吗?”
“白的也有。”
“让我看,让我看……(她把篮子从手臂上拿下来,把一张遮盖蘑菇的阔大的牛蒡叶子揭开一半。)啊!”卡西央俯身在篮子上,说,“好极了!安奴喜卡真不错!”
“卡西央,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安奴喜卡的脸微微地泛起红晕。“不是,唔,是亲戚。”卡西央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好,安奴喜卡,你去吧,”他立刻接着说,“你回去吧。当心点……”
“为什么让她步行回去!”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可以载她回去……”安奴喜卡的脸像罂粟花一般红了,她两手抓住篮子上的绳,惊慌地看着老头儿。
“不,她会走回去的,”他用同样淡然的、懒洋洋的声音回答,“她有什么关系……会走回去的……去吧。”
安奴喜卡迅速地走进树林里去了。卡西央在后面目送她,后来低下了头,微笑一下。在这悠长的微笑中,在他对安奴喜卡所说的不多的几句话中,在他和她谈话时的声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热烈的慈爱和温柔。他又向她走去的方向望望,又微笑一下,摸摸自己的脸,点了几次头。
“你为什么这样快就打发她走了?”我问他,“我要向她买蘑菇呢……”
“您如果要买,到我家里还是可以买的。”他回答我,第一次用“您”字。
“你这小姑娘很可爱。”
“不……哪里……嗯……”他不情愿似的回答,就从这瞬间起,他又陷入了和以前一样的沉默。
我已然看出要使他再讲话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就出发到开垦地去。这时候炎热已经减退了些。然而我打猎的失败,或者像我们那里所谓“晦气”,还是照旧,我就带了一只秧鸡和一个新车轴回到移民村去。马车开近院子的时候,卡西央突然向我转过身来。
“老爷,啊,老爷,”他说,“我真对不起你了,是我念个咒把你的野禽全都赶走了。”
“这是怎么的?”
“我懂得这方法。你的狗又聪明又好,可是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想,人啊,人真是了不得,啊?就像这畜生,人把它训练成了什么?”
我想说服卡西央,使他相信“念咒”驱除野禽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徒然的,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况且这时候我们的车子立刻就转进大门里去了。
安奴喜卡不在屋里,她早已回来过,把一篮蘑菇留在那里了。叶罗菲装配新车轴,一开始就给它苛刻而不公正的评价。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就出发了。临走时我拿些钱给卡西央,他起初不肯收,可是后来想了一想,在手里拿了一会儿,揣在怀里了。在这一个钟头里,他基本上一句话也没说,他照旧靠着大门站着,不回答我的马车夫的非难,极冷淡地和我告别。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就注意到我的叶罗菲又在那里闷闷不乐了……的确,他在这村子里没有找到一点食物,马的饮水场又不好。后来我们出发了。他带着连后脑上也表示出来的不满意,坐在驾车台上,一心想同我谈话,但是他要等我先发问,而在这等待的期间,他只是低声地发出些怨言,对马说些有教训意义的、有些刻毒的话。“村子!”他喃喃地说,“还算是村子!要点克瓦斯,连克瓦斯都没有……嘿,天晓得!水呢,简直糟透了!(他大声地啐一口。)黄瓜也好,克瓦斯也好,什么都没有。哼,你呀,”他向着右面的副马,大声地继续说,“我认得你,你这滑头!你大概想贪安闲……(他抽了它一鞭。)这匹马完全变得狡猾了,以前这畜生是那么听话的……哼,哼,你敢回头瞧!……”

“叶罗菲,我问你,”我开始说,“这卡西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叶罗菲不立刻回答我,他一向是一个有思虑而从容不迫的人,但是我立刻猜测到,我的问题使得他快慰了。
“跳蚤吗?”终于他扯一下僵绳,说起话来,“是一个怪人,简直是一个疯子,这样奇怪的人,还不容易找到第二个呢。他就跟,喏,就跟我们这匹黑鬓黄马一模一样,也是不听话的……就是说,不肯干活的。唔,当然,他干活干得很不好,——他身体很虚弱,不过总归……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起初他跟他的伯叔们当运送人——他们是驾三套车的。可是后来大概厌烦了,不干了。他就住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也住不长久,他是那么不定心的人,——活像一个跳蚤。幸亏他的主人是个好心肠的人,并不勉强他。从这时候起他就一直荡来荡去,像一只没有管束的羊。这个人那么稀奇古怪,天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像树桩一样不作声,有时候又突然说起话来,——说些什么呢,那只有天晓得。这像样吗?这不像样。他真是一个不合情理的人。唱歌倒唱得很好。的确唱得好——不坏,不坏。”
“他会治病,真的吗?”
“治什么病!啊,他哪里会治病!他这样的人。不过我的瘰疬腺病倒是他治好的……”他静默一下之后,又说,“他哪里会治病!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你早就认识他吗?”
“早就认识的。在美人梅奇河的时候,我和他们同住在塞乔甫卡做邻居的。”
“那么她是谁,我们在树林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安奴喜卡,她是他的亲属吗?”
叶罗菲回头向我一看,露出满口的牙齿笑着。
“嘿!……是的,算是亲属。她是一个孤儿,没有母亲的,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她的母亲。呃,应说是亲属吧,因为相貌很像他……她就住在他那里。是一个伶俐的姑娘,没有话说;是一个好姑娘,老头儿宠爱她。而且他,您不会相信的,他也许还想教安奴喜卡识字呢。他真的干得出来,他真是一个特别的人。他这人那么反复无常,简直不成体统……嗳——嗳——嗳!”我的马车夫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话,勒住了马,把身子弯向一边,在空气中嗅起来。
“不是有焦味儿吗?一点也不错!新车轴真讨厌……我好像涂过很多油了啊……要去拿点水来,这儿正好有一个池塘。”
于是叶罗菲慢吞吞地从驾车台上爬下去,解下水桶,到池塘里去打了水回来,当他听到车轴的轴衬遇到水而发出吱吱声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在不过十俄里的路程上,他在灼热的轮轴上浇了六次水。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阅读鉴赏
小说语言朴实自然,但也有展现作家高超才能的精彩片段。卡西央是该主人公的名,小说没有提到他的姓。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侏儒……他的整个身体异常虚弱和瘦小,而他的眼神奇特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后来“我”问车夫关于他的为人,车夫说他是个怪人,简直是个疯子、傻子,不会干活儿……他是这样一个不安心的人,真像是一只跳蚤。不过他歌唱得好。车夫虽然说他不会治病,但又说治好了他的瘰疬症……就是这样一个有才能的“怪人”,带着一个小姑娘住在这个贫穷的移民村。他的家一贫如洗, 四壁空空,只有小姑娘刚从树林里拾来的一筐蘑菇。
知识拓展
-跳 蚤-
跳蚤属于昆虫,触角粗短, 口器锐利,用于吸吮。身上有许多倒长着的硬毛,可帮助它在寄主动物的毛内行动。跳蚤的外壳,最具对生命的保护能力,可以承受比体重大九十倍左右的重量。有一种说法,人的身体,如果有了如同跳蚤身体一样的外壳,而不是如今的皮肉,那么,人可以从1000米的高空,摔跌到硬地而安然无恙,也可以承受1000千克的重物,自1000米高坠下的重压。